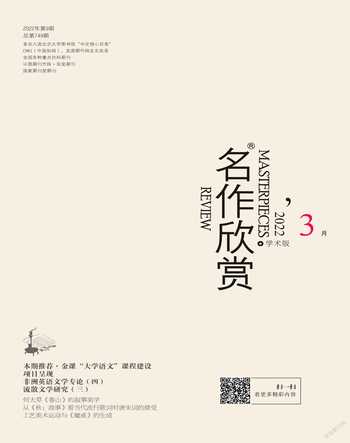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标题中的物象
2022-04-05陈倚
摘要:小说标题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张爱玲小说的标题非常独特,常以具有丰富含义的物象直接作为小说标题,如《沉香屑》《茉莉香片》《琉璃瓦》《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张爱玲对小说标题的选择独具匠心,这些标题中的物象蕴含丰富的意义。张爱玲通过隐喻、象征、反讽等艺术手法,使小说标题与文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即本质与表象、生命与非生命、变与不变、现代与历史、现实与理想五种深层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标题物象
一
小说标题是小说真正的开头,既是小说的眉目,又是小说的点睛之笔,小说标题有时候比小说内容显得更重要。张爱玲的小说不仅主题特别,标题也是非比寻常。小说中意象的运用可以体现一个作家的功力,如沈从文从大自然中取象,用诗性物象营造和谐自然的意境;茅盾用二元对立的物象来再现现实和表现人物;在穆时英的小说中,物取代人而成为主角。 a夏志清对张爱玲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b。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各种各样有意味的意象,“意象和故事共同虚构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世界,并与某种意义形成相似性关系”c。张爱玲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意象,她小说标题中的物象充分反映了张爱玲独特的创作心理。
物象是实体性意象,物象作为小说标题,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张爱玲的小说共三十余篇,以物象为标题主体的小说主要收入小说集《传奇》中,有《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琉璃瓦》《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张爱玲凭借其在经营意象上的造诣,能够从抽象的人事物关系中抽丝剥茧出具象的本质,使她的小说具有通俗的特征,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比如,《琉璃瓦》中的女儿被比作琉璃瓦,读者很容易联想到琉璃瓦华丽且易碎的特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关于米饭和蚊子血的譬喻能让读者认识到爱情和婚姻易变质的特征。
同时,张爱玲也擅长选取熟悉的物象,拉近读者与小说的审美距离。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生活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而张爱玲将生活比作看得见、摸得着的华丽袍子,将生活的阴暗、腐败比作袍子上的虱子。张爱玲通过精辟形象的譬喻,轻松勾勒出读者的想象空间,读者对于这个空间的构成物是不陌生的,由此,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物象是具体而不陌生的,而张爱玲选择的物象又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即物象构成的小说标题无法直接指涉小说内容,使标题与小说之间生成一个意义的想象空间。张爱玲以其敏锐细腻的感受力和“从说书体小说中汲取说与听的审美思想及叙述精华,并从诗歌中汲取‘诗言志’‘诗缘情’及注重喻说的诗性传统,将两者水乳交融地合成为隐喻性小说”d。
二
張爱玲小说标题中的物象通常是带色彩或气味的,如金色的锁、清香的沉香、气味略苦的茉莉香片、流光溢彩的琉璃瓦。物象的色彩和气味显示出故事的繁华和排场,在这表象的背后是颓败的调子,物象背后的实际意义渲染出的却是苍凉的落幕。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香港处处显着繁华,却处处都是惨败的气息。沉香木是一种可以产生浓郁香气的木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却处处透出腐败的气息。葛薇龙姑妈的白房子表面繁华,却是“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绿玻璃窗里灯光晃动,“像薄荷酒里的冰块”。白雾和冰块都是会消散的事物,就如同眼前的繁华和此刻的享受,都会消散殆尽。“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烟卷儿窝在花瓣子里,一霎时就烧黄了一块”,留下的是烧焦的痕迹,不复曾经的美好。金色象征着富贵和平安,然而《金锁记》中的金锁却是劈杀曹七巧人性的凶器,“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更衬托出“黄金的枷”对曹七巧命运的残忍禁锢,最终葬送了她和子女的一生。琉璃瓦使人联想到五光十色的华丽,“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就像是“琉璃瓦”,然而《琉璃瓦》中最后的结局是冷色调的绝情,留得一个“活不长了”的悲哀无望。茉莉香片让人联想到茉莉清香淡雅的芬芳,然而《茉莉香片》开篇就说:“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华美与悲哀如同双生,小说里尽是主人公聂传庆的痛苦绝望。
张爱玲小说标题中的物象以一种非生命的角度来审视其中的人和事,反衬出生命的卑微和人生的苍凉。如同张爱玲常用的月亮意象,也许是一轮“三十年前的月亮”,也许是“一团蓝阴阴的火”,月亮就像是局外人,它冷眼看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看这苍凉人生的残酷。无生命的物象似乎在故事中无处不在,将有生命的人联系起来,却不动声色,犹如隔岸观火。《金锁记》中的“黄金的枷”是无生命的,而“金锁记”讲述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茉莉香片”是无生命的,而《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人性是被残忍压抑的。在“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街道上只有寥寥几家店铺,玻璃橱窗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黄肥皂,“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琉璃瓦》),然而这童话既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晶亮的玻璃窗易碎,金砖砌成的堡垒也许下一秒就土崩瓦解。无生命的物象使得生命的面目变得可憎起来,一切都可能在刹那间消失殆尽。
物象是时空中的固定存在,张爱玲的小说标题往往是通过不变的物象来隐喻一种变动的关系,以小及大,以不变及变,物象的不变与文本中表现的变形成一种落差。《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最后成了“蚊子血”,白玫瑰成了“白饭粒”。《琉璃瓦》中原本承载美好寓意的“琉璃”最后变成了“瓦”,活脱脱是对现实的讽刺。《茉莉香片》氤氲出的不是芬芳香气,而是聂传庆焦灼煎熬的内心之苦。“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张爱玲小说标题的不变与故事内容的变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意义上的张力。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处于无尽的变动之中,人物的命运悲剧也永远不会结束,即使“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张爱玲小说标题选取的多是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物象,而故事的背景多是现代的大都市——香港和上海。上海的现代“来自于它尚待成形的、不稳定的、探索性的地位”e,是与成形的、稳定的、循规蹈矩的传统截然相反的。张爱玲在现代都市的故事中置入古典元素,使历史与现代相交织。在《琉璃瓦》中,张爱玲“把身处上海十里洋场所感受到的女子做人方式的变化,投影到‘琉璃瓦’意象中,对传统的女性观作了某些置疑”f。张爱玲喜欢看评剧,认为“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京剧里的悲哀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流言·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的小说标题具有古典意蕴,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故事框架中,又预示了故事的戏剧性。张爱玲小说常见的说书人口吻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久远的老故事,与标题正相配合。“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小说中的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都无法明哲保身,历史的车轮碾过现代都市,在张爱玲笔下,奏响的是一曲生命的挽歌。这种挽歌情调和张爱玲的怅惘体验使得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天然的感伤性和抒情性。 g
张爱玲小说标题中的物象还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爱情仿佛处于理想和现实的两极,故事中的人一旦获得了理想的爱情,这爱情就会堕入现实的尘埃中,不复曾经的美好。在张爱玲笔下,每一个男子的一生都有过热情似火和温柔如水的两个女人。若是娶了女人味十足的“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玫瑰”就会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若娶了“白玫瑰”,日子久了就成了衣服上的一颗饭粒子,红的却变成了心上的一颗朱砂痣,让人念念不忘。红玫瑰和白玫瑰都象征理想的爱情,而蚊子血和白饭粒是理想坠入残酷现实的结局。金锁象征富贵和平安,而《金锁记》用金锁表达了一种残忍的人生抉择与宿命。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除去被她折磨死的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茉莉香片》中理想的家庭关系和实际畸形的家庭关系形成对比,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而故事也是“一样的苦”。沉香屑是用“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的沉香的残余物,《沉香屑·第一炉香》整个故事充斥着烧焦的灰烬和死寂感,葛薇龙看到“那板板的绿草地,那怕人的寂静的脸,嘴角那花生衣子……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等天色暗下来了,沉香屑“仿佛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有点残酷”,而这残酷恰恰是理想与现实之不可调和的冲突所造成的。
三
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出于张爱玲自身对物的关注,另一方面是物本身可蕴含的精神性。关于张爱玲小说中的“恋物”有不少研究,如“恋物起始于创伤,衣服成了目光在创伤压力下随意而又宿命的选择,成为记忆的胶着点”h。张爱玲童年時家庭破碎,加之其自幼便显露出的才华,使她对物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依赖和情感表达方式。
张爱玲善写物,也爱写物,她笔下的物象折射出对人、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照。对物象的关注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个体生命经验对物象重新进行了意义组织,建构出一个物象占有重要地位的意象世界。物象是靠得住的,又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安稳”的一面,而靠不住的是“飞扬”的一面。“飞扬”若不以“安稳”为底子,最终只会落得一个苍凉的结局。
张爱玲的笔下始终有一种“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小说标题中物象的对立意义往往显出一种苍凉,本质与表象、生命与非生命、变与不变、现代与历史、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永恒存在。对她而言,“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文章》),这种苍凉仿佛是人生无法逃避的宿命。张爱玲小说标题中的物象正是如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张爱玲偶然在书中的一句喟叹,“人生往往是如此——不彻底”(《沉香屑·第二炉香》),道出人生的苍凉本色。
a 柯贵文:《1930年代中国小说物象论——以沈从文、茅盾、穆时英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第 103—107页。
b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34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d 刘俐俐:《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 113—121页。
e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90—102页。
f 王文参:《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选择及视角创新》,《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第179—183页。
g 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20页。
h 萧纪薇:《欲望之衣: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恋物、电影感与现代性》,《文艺研究》2009年第4期,第72—82页。
参考文献:
[1] 柯贵文.1930年代中国小说物象论——以沈从文、茅盾、穆时英为例[J].文艺争鸣,2009(3).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3] 刘俐俐.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4]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J].文学评论,2002(5).
[5] 王文参.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选择及视角创新[J].中州学刊,2005(1).
[6] 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1999(1).
[7] 萧纪薇.欲望之衣: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恋物、电影感与现代性[J].文艺研究,2009(4).
作 者:陈倚,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