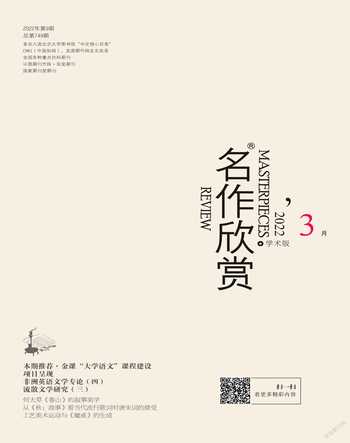女性自主意识探究
2022-04-05王嘉怡曹玮炜
王嘉怡 曹玮炜
摘要:本文试图对《一间自己的房间》和《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中体现的女性自主意识进行探究。女性自主意识体现在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批评中,即指对一切有关妇女的文学作品的评估和研究。本文通过文本和观点分析,点明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内涵,即拒绝依附、拒绝定式,自主选择、自我认同,并且从男权文化本身和男性优越感两方面指出在男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对女性自主意识的阻碍;本文还对脱离男权文化价值取向之后的选择提出思考,即女性面临的是出走或是回归传统生存状态的双重压力。此外,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其未来走向也值得关注:女性自主意识会日趋完善,并最终走向带有双性文化特征的道路。
关键词:《一间自己的房间》《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女性自主意识
一、女性的自主意识:我是谁?
(一)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
女性文学概念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是偏向于指向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过去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普遍将作家性别定为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认为只有女作家的创作才可以算是女性文学,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男权文化下对于女性存在的异化的关注。无论中西,最早的女性文学都有着迎合男权观念的色彩,并且囿于女性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身份认同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从社会学意义转向文化和文学意义,而所谓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也更为模糊。
不过在这两本书中,都有关于女性文学相似的界定与判断,可以作为时代视角下的新构建。《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以下简称为《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试图建构的新的女性文学批评主要依据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更倾向于女权主义批判。女性主义批判与作家性别无关,而与文学作品的内涵有关,这是对传统男权文化和文学观念的批判和重新审视。《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所谓女性与小说,可能意味着或者按你們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所写的小说;也许,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a在作者看来,女性与小说是复杂性、整体性、交织性的。伍尔夫在她的另一部著作《妇女与小说》中明确地提到作品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b 因此,我们不妨将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批评视为对一切有关妇女的文学作品的评估和研究。
(二)女性的自主意识
在对女性文学批评较为清晰的界定之下,我们便可以从女性文学中看到女性的自主意识——拒绝依附、拒绝定式,自主选择、自我认同。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提到了中外文学中存在的三种故事程式:才子佳人程式、诱奸故事程式、社会解放程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自主意识存在与消亡的痕迹。才子佳人程式在中国古已有之,反映的是男权文化下男女性别角色的期望和定式——男人必须强大伟岸,女人必须娇弱柔顺。这种程式在西方也并非不可察。歌德、席勒就对中国才子佳人小说赞赏不已c,鲁迅则提到才子佳人小说“在国外却很有名”,“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d。才子佳人程式在西方的广泛传播,正可以体现中西方男权社会背景下对于性别角色的定式思考—— 男性趋于外向性质,才华或者说强大是男性必备的品质;而女性则需要扶持男性,趋于内向性,美貌贤淑是女性所必须具有的。在这种特定程式下,女性的自我意识消亡,而转向依附男性,充当男性身后的角色。在诱奸故事程式中,女性自主意识的迷失则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柔弱美丽、贫穷无依,在社会等级几乎和其完全对立的男性的引诱下失身,并最终面临被抛弃的结局,走向悲剧的命运。相较于才子佳人程式,这种模式展现的完全是女性角色的被动性,其自主意识也就更为淡薄。正是由于其自主意识的消逝,她们在面对自己献身的对象和悲剧命运时,只能被动地身处其中、无法脱逃。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不乏这样的形象——如四凤(《雷雨》)、侍萍(《雷雨》)、苔丝(《德伯家的苔丝》)等。而这种文学程式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将外部因素作为女主人公走向不幸的最终根源。但实际上,女性角色的悲剧来自自身的不反抗,来自自主意识的淡薄,才促使她们成为男性角色的附庸,会因诱奸一方的抛弃而陷入苦难的结局。因此,将女性的悲剧归因为社会的局限其实是男权文化下的思维定式,女性自身无法意识到人生和理想的价值才是悲剧产生的根源。在看到四凤、侍萍、苔丝等人的悲剧时,反观简·爱(《简·爱》)、妮娜(《海鸥》)的结局,则可以看到,虽然她们未必有着被诱奸的生活经历,但由于自身信念的存在、对人生和生命价值的认同、自我的独立意识而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换句话说,女性自主意识的存在与否才是决定女性命运的关键。社会解放程式体现的则是对女性自我的回避和否定。 e 当然,这种程式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的革命和改造时期,但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出女性自主意识的虚无。从表面上看,政治制度的更新和社会变革的发展使女性获得了解放;然而,这种女性解放只是女性形象被革命同化、为革命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空洞地接受新的命运的安排,而非自主意识的体现和选择。
顾名思义,《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正是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五百英镑的年金。这正体现了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缺失。在物质上,女性所拥有、所享受的都远少于男性。甚至在大学城中,对女性的束缚和制约都不曾减少:面对女性,学术关起了大门。甚至在餐食上,男性所拥有的都比女性好许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远少于男性,因此她们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与男性随行。在全文的开篇,作者便描写了女性在大学中所受的种种制约,甚至连吃食都与男性迥然不同。女性的生存境遇也极其窘迫:丈夫可以随意打骂妻子,男性可以随意嘲笑女性。女性没有单独的房间,一切女性的创作都在共用的起居室中完成。她们必须藏藏掖掖,避免被外人发现。这种空间的不自由感无疑会对女性的创作产生影响——当我们读到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时,便会注意到书中的突兀和激愤——她的创作天赋永远有着扭曲的一面,而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是在与社会作对、与命运抗争。物质的缺失必然导致精神的缺失,而其鲜明的表征就是女性自主意识的缺失。在纯粹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写作的固有价值观给女性创作的自由度带来了阻挠和批评。并且,男性话语的形成使女性创作的文学形式囿于原有句式的囹圄之中。一间自己的房间和金钱的背后,其实是女性对文学形式、文学内容的再创造。一间自己的房间和金钱能带给女性的不只是空间上的自由,也是安全感、独立感和成就感,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孕育之地。
通过对《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女性自主意识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前者主要集中在其在文学形象上的体现,而后者则集中在女性作者创作自主意识的体现,二者相得益彰。我们通过对二者的把握,便可以从作品内部和作品外部(也即作者)两方面明白什么是女性自主意识,它又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深埋于什么样的土壤,可以真正明白“我们究竟是谁”。
二、觉醒:男权传统的阻碍
(一)男性对女性的蔑视和阻碍
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男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的阻碍。这一点在两本书中都有明确的展现。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一书中,贯穿全文的一个背景是女性长久以来陷于社会固有的道德评判和价值标准中,即依附于男人、服务于家庭。女性是男性的一件物品,而物品自然是没有自我选择、自我价值的。虽然新女性开始出现,试图反抗这种物化女性的价值标准,但新女性是相当脆弱的,并且极可能被传统男权所侵吞或最终自行凋零。女性生存中的种种匮乏使其自主意识难以维系。这种男性凝视是根深蒂固的,无疑对女性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带来了持久的伤害。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这种对于男权文化对女性自主的蔑视和阻碍的论述则更为明显。在第三章中,伍尔夫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个天资聪颖的妹妹,她的命运会是如何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很有天分,然而父母剥夺了她上学的机会;她写的每一张文字都只能偷偷收藏或者烧毁;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迫要嫁为人妇;她拒绝嫁人,不成后私自出逃,来到剧院想要演戏,却被丑陋的剧院经理嘲讽;最后的结局是被演员经理收留,却怀上了他的孩子,她的诗人之梦就此破碎,而她也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自杀了——把她的灵魂和生命一起埋葬。这个设想中包含了一位自主意识觉醒的女性可能拥有的人生经历。她想要跟随自己的内心,摆脱命运的定式,奔向一个热烈的梦想,然而她面对的是来自父母与成年男子的蔑视,是社会强加的责任和义务的阻碍。这些阻碍何其沉重,足以压倒她,足以让她用永恒的死亡来祭奠自己无处施展的才华。从她的结局构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传统的文学程式:诱奸故事程式——贫穷美丽的女性被男性收留,结局便是性关系和生子,这似乎是女性避免不了的命運。然而对于莎士比亚的妹妹来说,她的自主意识正在身体里萌发——她想要反叛、想要创作、想要拥有自己的人生,因此,她的命运只能是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悲剧、共同陨落。
(二)男权文化视角下的男性优越感
在男权文化社会中,男性自然会认为自身的各个方面都比女性更为优越。这种优越感会造成对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和发展的阻碍,但也会成为女性反叛的着力点。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女性作品的难以找寻和男性面对来自女性的挑战和责难时的愤怒都是男性自我优越性的体现。由于社会对女性所谓贞洁的苛刻要求,女性创作的作品是不会署名的,她们会如此来保护自己。甚至晚到19世纪,贞洁观的遗风仍然迫使女人隐姓埋名。“科勒·贝尔、乔治·爱略特、乔治·桑,无一不是她们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从她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出来,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如此一来,她们就迎合了男性所树立的女性不能抛头露面的常规。由此,我们不由得发出疑问:男性对女性创作的阻碍究竟是因为对女性贞洁的要求,还是因为害怕和畏惧女性超越自己?换句话说,男性是否在潜意识中认为一切作品与成果都只能由男性创造?当作者收集男性立下的有关“妇女与贫困”的一系列论题时,她找到了一篇冯·X教授的著作——《论女性脑力、品行和体力的低贱》,并描绘了丑陋、愤怒的冯·X教授的样貌,猜测了他被女性挑战和责难过的境遇。冯·X教授对女性低劣的评价,来自强调自身的优越。一向温和谦逊的Z先生看到丽贝卡·韦斯特对于男性正确但不算中听的评价后,竟会愤怒地宣称:“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她说男人都是市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男性获得自信和优越感的来源正是对女性的贬低,而男性的愤怒则来自女性对其优越感造成的冲击。当然,反观这种优越感在男性愤怒情绪上的激发,不正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吗?正是女性对男性的挑战和对男权文化的反叛激发了这种男性优越感的外在表露,男性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危及、被挑战,因而对来自女性的一切不符合男性期望的刺激都格外敏感,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对自身强烈的优越感和对女性的复杂的愤怒情绪。
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作者提到了对男性的传统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坚实伟岸的“男子汉”形象。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从许多女性文学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不管是男性的高大威猛,还是女人对“男子汉”的企盼,都是这种传统价值的直接展现。除此之外,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存在女性试图求“男子汉”而不得的失望、苦闷和悲哀。比如在张洁等人的作品中透露出一种遗憾——似乎没有伟岸强胜的“男子汉”便是全体女性的不幸。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所传达出的正是男性自身优越感的体现:他们认为由于自身的强大,女性理所应当地依附于他们。然而,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对于这种优越感的否定也不断出现。她们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女性渴望作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打破男权文化下的传统价值观念,从而反叛男性自身的优越感,诋毁和否定“男子汉”的意义价值。当然,“男子汉”形象所代表的男性更为优越的传统价值取向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对于“男子汉”的否定和诋毁其实反映出女性面对陡然转变的价值取向时的孤寂和迷茫,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即使否定“男子汉”的道路中难以摆脱男权文化的传统观念,女性对另一性别没有依据的天然优越感的排斥只会更加强烈,女性自主意识的光芒仍旧难以掩盖。
三、发展:出走还是回归?
在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抉择就是脱离男权文化价值取向之后的选择:出走或是回归传统生存状态的双重压力。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作者对女性创作历程进行了梳理。从16世纪到18世纪,女性创作常常受到男权社会的限制,她们的才能被局限于客厅里。因此,作者提出,女性应当拥有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走出客厅,走出限制,拿起笔来,看到现实。这是对传统生存状态的出走和反叛,是对女性自主意识的期望和愿景。然而,在《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作者则提出了一种生存困境——出走还是回归?由于男权主义价值观对女性的苛求,女性被要求在外在与内在的双重标准上符合男性的期望,但女性又有获得独立人格的愿望。然而这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两难处境,不可能兼得。“五四”以后大量的女性文学作品中试图寻求解放的女性往往面临的只有两条道路:回来,或者堕落。实际上,这两种道路都是对传统生存状态的回归——前者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屈服;后者则是无法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当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拥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新时代的女性是脆弱的、惶惑的。她们在夹缝中生存,面对的困境是要么舍弃追求事业的自己要么舍弃投身家庭的自己。有些女性看似获得了事业的成功,但这未免令人觉得依然是对男权传统秩序的认同——女人必须像男人一样去生活才是标准意义上的成功。随着女性生存环境的逐步改善,女性的斗争仍在持续。一些作家为女性生存困境的选择问题提出了回归的答案:“与其使广大妇女长久跋涉于传统与现实的缠绕和泥泞之中,还不如让她们回到一种更为自然和单纯的传统生存状态中去。”这种回归实际是一种对于母性的呼吁和照应。但是这种回归真的可行吗?我们绝不能否认女性母性的光辉和女性的权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女性由于对男性的依附感而产生的屈服,是“在长期的自我迷失的状态下养成的一种无助的牺牲精神”f。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回归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出藩篱,才能找到自己。在男女关系中永恒存在的就是性别的不对称:“女人寻求关系,男人追求占有。”g女人投身于母性与爱;而男性在普遍意义上则是被依附、被投身的对象,而非依附者。所以当女性或被迫或自愿选择回归时,所面临的形势必然是其自主意识被传统价值观念所侵蚀。但是,我们仍要看到,选择回归的背后是女性在所处的两难境地之中的无奈选择,是女性自主意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失败的分支——虽然其自主意识被侵蚀而陨落,但这个分支本身是有意义的:它让我们产生对女性现状的反思和自省,考虑女性所面对的处境;让我们看到女性自主意识发展道路的漫长和艰难。
我们要走出男权传统的价值观念,既不被其要求,也不被其束缚。换句话说,就是贤妻良母与像男人一样的女性都是对男权传统的回归而非反叛。真正的出走是女性不被定义、不被局限,从而创造无限可能。
四、未来展望:在路上
(一)充满希望的道路
女性的抗争不会停歇,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道路也艰难漫长,但这条道路绝不是通向虚无,而是通向必定会达成的充满希望的未来:两性之间被固定的尊卑和荣辱终会消解,两性都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末尾,作者再次提起关于莎士比亚的妹妹的隐喻。她象征着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因为性别而被困于男权文化打造的囹圄之中的女人。她是一个本具有文豪之才,却因为没有五百镑的年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而隐没于人海、埋葬于路边的人。当她的才华死去时,她的灵魂和生命便一同死去。但她是不灭的魂灵——当女性终于得到平权,而不畏惧写下自己的想法时;当她们敢于面对现实,并且有着观察现实世界关系的眼光,而并不被男性压制、不依靠男性关系时;当她们终于能够做出自主选择、产生自我认同时,她就会在每个女性的身上复活——连同着她的梦想、她的期盼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待到她复活之日,便是女性梦成之日。
(二)双性文化
两部作品都提到了一种双性文化的观念:《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提到的是带有双性文化特征的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设想,《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则提出了双性同体的伟大构想。这种两性的融合便是当女性自主意识走向完善发展之后的结果。
伍尔夫从女性创作的角度举出了许多伟大作家的例子来表明睿智的头脑是半雄半雌的。由于女性特有的生活经验,女性的创作中常常有更敏锐的观察、感受和思考,这是已经形成的固有的男性话语所缺失的。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应该尝试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即破除男性创作与女性创作的壁垒,感受另一性别的思维。只有消除了性别的偏见和界限,让两种性别意识相交融,才能使创作得到升华和永恒。
如果脱离创作这个小语境,而放眼两个性别的差异本身,我们也会看到在差异之中的趋同和融合——这也是两部著作中相似的观点。女性的解放需要解构传统、解构性别之间的对立,从而建立了新的文化精神和意义,达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融合。女性可以涉足男性的思想领地,反之亦然。使两性在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以平和健康的心态面对另一性,走入与自己不同的性别思想中,才可以达到两性人格的独立、人性的完善。刘慧英在全书的末尾则将这种双性文化特征上升到人类意义的层面:这种双性间的融合是两性间传统偏见的消逝,也是人类更为理性和自由的表现。传统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内容渐渐被更改或者取消,人也便成为了更自由、更独立的个体。
五、结语
《一间自己的房间》和《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有关女性自主意识的问题。前者更偏向于根据西方女性文学的时间脉络,主要通过叙述 16世纪至19世纪西方女性作家的创作,阐明自己的女性主张;后者则偏向对20世纪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的探究,兼以对西方文学作品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与研讨,聚焦于女性文学作家的创作发展以及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虽然二者分别着眼于西方和中国,聚焦于不同时间阶段,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是类似的。男权价值标准和男权历史意识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早已筑成了难以跨越的高墙,而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道阻且长。女性要想得到解放,要想解构传统、更新处境,要想达到社会风气乃至文化意义上的扭转,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当然,女性自主意识发展的尽头绝不是取代男性,而是使两性都能够正视自己的性别,正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而最终达到两性偏见的消解和两性在文化意义上的交融。
a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贾辉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c 〔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d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08页。 e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f 邓益:《女性世界低矮的天空——萧红〈生死场〉底层农村妇女的生存困境与婚姻悲剧》,《小说评论》2011年 S1期,第111—114页。
g 〔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 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7]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 邓益.女性世界低矮的天空——萧红《生死场》底层农村妇女的生存困境与婚姻悲剧[J].小说评论,2011(S1):111-114.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
作 者: 王嘉怡,華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学生;曹玮炜,现在南昌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就读。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