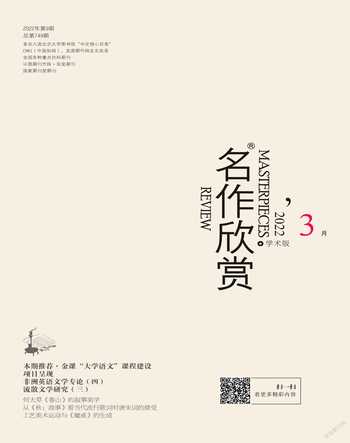论晚明中西商教活动与文学的“变容”
2022-04-05刘朋鑫
摘要:文学是创作主体精神世界和其所在的物质世界交融发展的产物,晚明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大变局阶段,以隆庆开海为契机,与西方的交往渐趋密切,同时,经由晚明心学的催动和商业的变动,晚明的社会思潮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动直接影响了晚明文学的相关活动,引发了晚明文学的变动。本文主要从中西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引起的晚明文学的变动入手,从诗歌、话本小说以及传教士著作及其回应三个方面出发,对晚明文学经由中西交流洗礼而达成的变动做一个简要分析。可以窥见,晚明中西方的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对晚明文学相关活动的变迁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晚明商业活动宗教活动文学变动
隆庆开海后,西方商人逐渐进入中国,使得中国融入“大航海”的时代浪潮之中,沿海地区商业逐渐发达,经济结构逐渐改变,同时影响了社会思想体系,为晚明文学的变革营造了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而同时,晚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因以“合儒”“补儒”为策略,以古儒的外衣作为进入中国文人群体的“通行证”,使其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很大意义上的成功,耶稣会士以“耶儒”的姿态在中国通行,与中国士人平等交往,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观念和科技,这些内容或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融入思想底层,与中国西方文士相交融,成为中国士人的底层思维逻辑或观念,最终反映在文学和日常文字作品中,引起文学的新变动。
一、晚明诗文中的新质料
诗歌作為古代最为流行的文学体式,篇幅短小,语言凝练,乐感强烈,适合日常随笔写作和文会交流所用。晚明耶稣会士与文士间的交往,首先渗入了这种文体之中,从总体上看,这些诗文作品主要以酬唱诗的形式出现,同时,也有少量以新事物的方式呈现在某些诗人的日常随笔和诗歌著作中,出现的方式亦有科技事物、宗教事务、地理观念、哲理论题等多种形式,为明末诗文带来了一抹新鲜色彩。
较早记录与西方教士交往和遇见西方商人感受的是晚明文士汤显祖,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意料之中被贬岭南,不仅在此寻觅到了《牡丹亭》的诸多灵感 a,也在此处收获了异域视野,其目之所及,写就了《香岙遇胡贾》。所谓香岙,便是“香山岙”,也即澳门,而“胡贾”便是异域商人,他们“不住田园不树桑”,而是通过海上商贸以求营生,所携货物珍奇,有“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之势。在广东肇庆,据传他还与利玛窦有过一面之缘,其“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的随记诗中的“二子”也定是耶稣教士,不然也不会有“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b 的描述了,早期如汤显祖的文人并没有深入了解基督教观点,也没有对其披着佛教外衣的番僧身份产生极大兴趣,因而表述仍多停留在见闻式的现象描写方面。
而随着基督教活动的日益频繁,教士与文士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学交流越来越频繁,因而产生了较为密切的酬唱现象,最为突出的应以《熙朝崇正集》为代表,作为福建文士与艾儒略的酬唱赠集,文士群体和艾儒略之间表现出较为特殊的关系色彩。同时,《崇正集》中的诗作也不仅仅局限于现象性的事物描写,而是产生了观念性的变动。集中的诗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集中于教内事物和教内思想的,如徐渤“教传天主来中夏,恩沐先朝见盛明”、柯宪世“大千宁净土,三一信分身”等,均以“天主”观念和“三位一体”观念,与世俗的明朝政权和佛教的“大千世界”“净土”观念交织,体现了基督观念与晚明本土宗教、世俗政权观念的交织;第二,耶稣会士还带来了先进的地理观念,“万历时……利玛窦……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崇正集》诸作之中,如徐渤“五大部州占广狭,两轮日月验亏盈”,何乔远“艾公九万里,渡海行所学”,林叔学“五州形胜披图狭,八万舟车计路劳”,林珣“舆地图旋溟海才”,黄鸣晋“五大部州归一统,欧罗巴国应昌期”等,其中“五州”“五大部州”的观念均有鉴于利玛窦或艾儒略的先进地理知识,这是地理观念在《崇正集》中的集中表述;第三,亦有结合当时社会状况与耶稣会士带来的“罪恶”“救赎”观念的,如董邦廪“情知世乐非常享,故向中华涤众邪”等,但这样的诗句在其中仍显得稀薄,说明基督教对明末底层伦理的渗入还处于浅层阶段。
当然,当时“天学”盛行,有许多沉迷于科学的文士,以科技为底色,做了许多科技探讨诗,如“测量变西儒,已知无昔人”“句股测体量,隐杂恃方程”等;亦有新奇见闻所录的杂感诗中出现西方科技事物的,如“窥船千里镜,定路一盘针”等。这类诗篇存世较少,科学和记录价值高于文学价值,但仍是文学的产物,在此并不详论。
综合来看,晚明教士与文士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带来了新的科技事物、新的观念等,为晚明诗文抹上了一笔异域色彩。
二、晚明小说戏剧的写作转向及其新质素
(一)俗文学的道德讽谏化转向
晚明文人虽受到商业的浸染,思想上产生了开放的思潮,但由于自幼接受的儒学伦理思潮固有之“先见”的影响和自身社会责任感,形成了匡救世道人心、挽救乱象的固有观念,这表现在思潮上是内泛性的人文思想的萌发,而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世情小说创作的兴盛。作为最接近大众的通俗读物,话本小说和戏剧的虚构性与传奇性为作者戏剧化身边所见不平之事提供了基础,小说家们往往借助话本“寄意于时俗”c,通过夸张的描写让世人引以为戒,以“导愚”为警策,而以“忠孝、节俭、耳和目章、口顺心贞”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进行规约,以“悖逆、淫荡、即聋从昧,与顽用嚣”这些反封建性的伦理为“醉”者之标准。 d 这些小说、戏剧中虽然有些许西方思想的渗透,但总体上仍以匡救理想的封建伦理体系为主要目标。许多名著如《金瓶梅》《三言二拍》《花神三妙传》《十二楼》等世情或拟话本小说在此时以为世人之诫的目的或夸张或写实进行创作,写作内容中常渗入“善恶有报”和“轮回观”等对封建伦理秩序进行回护的内容,从正反两面或激烈或温和地劝勉世人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这种写作观的转变,无疑是中西商业融合以及先进技术流入中国后,中国商业发展进入新一阶段而极大冲击传统伦理秩序产生的资本异化现象导致的中国文人的反击,故其根基应在中西商教活动之中。
(二)晚明话本戏剧的西方新质素
话本小说和戏剧作为有商业因素催动的消费文学,在晚明极为盛行,话本小说和戏剧通常取材真实经历,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度的改编,因而,话本小说与戏剧中通常包含一些日常所经历的新鲜景色,晚明由于中西商贸活动而引入许多新鲜的西方科技和事物,这些事物与传教士所引入的“寓言”一起,成为晚明戏剧和话本小说中的新质素。
西方事物较早出现在戏剧中,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代表,《谒遇》中“原是番鬼们建造”的寺庙,便是“光光乍”(老和尚)所居的“多生多宝多菩萨”庙 e,这样的空间架构,赋予《牡丹亭》一抹异域的奇妙色彩,将观众剥离舒适区域,以吸引观者眼球,
这便是较早期的中西商教活动在戏剧话本文学中留下的痕迹。同时,随着西方科技的普及,航海器具亦逐渐深入日常生活,成为普遍出现的科技产物,虽然“千里镜”并非西方独有,但其在晚明的普及应与西方传教士有密切的关系。汤若望的《远镜说》中便有对这种航海工具的科普性描述,因而,明末清初小说作者们,便将其融入了小说之中,如吕熊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洋人“拿着千里镜,朝岸上打了一回”,至明末李玉《夏宜楼》中詹公“终日对着千里镜长吁短叹,再三哀求”f,千里镜的作用便发生了变化,成为闺阁密探之物,但其延伸视力的作用并未改变。
西士在利用交游、学术交流传教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利用通俗故事传教,圣教故事、寓言故事便是教士们所利用的最常见的两种手段,而寓言故事更容易为世俗听众所接受,同时也更容易为俗文学作者所吸收,因而逐渐迭演,成为中国的一种俗文学叙述方式。早期的寓言故事出现在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中,是利氏引西人“阨索伯”(伊索)的故事来证道,明人张萱便在其著作《西园见闻录》中对“阨索伯”(伊索)进行了复述。而影响较大的便是借鉴金尼阁所译的《况义》中的寓言故事本源于《物感》,在书中,李世熊借“青蛙”“雕”“佛猫”等“寓庄于谐”,讽刺时事。中国从庄子起便有寓言的传统,但相对而言与西方寓言仍有较大的差异,李世熊的寓言故事处于寓言学习的初期,其故事仍有较大的中国特色,在体式和语言描写上均以庄子传统寓言为例。不同的是李世熊在其书中应用了许多西方观念,化用“西士曰”的口吻,以表微言大义,如《蛙怖》一章中所总结的“西士曰:有生者,夫各有所制矣”g 等。
总体来看,晚明的中西商教活动不仅为戏剧和话本小说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契机和素材,同时,也以其寓言故事形式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对晚明中国俗文学的变容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晚明传教士著作及其反响
在晚明文士对西方事物、观念进行吸收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进行了较多的翻译、传教创作,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这些传教著作不仅在晚明文士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被文士们吸收,融入自身的文学品评中,同时,文士们为这些作品所作的序言,也是重要的文学资料。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首先进行翻译的便是以《几何原本》和《泰西水法》为代表的西方科技著作,这些作品的翻译促进了中国科学思潮的勃兴,也促进了天学的发展。同时,以科技为媒介,传教士们开始进行西方伦理思想和教义渗透,或直接翻译西方文典,或改编西方作品,适应儒学环境,如利玛窦的《交友论》《畸人十篇》和《二十五言》、庞迪我的《七克》以及金尼阁的《况义》等。这些翻译著作并非由教士自己独立完成,大多得到了中国信教儒士的帮助,以促进中国文士的理解。这些著作促进了西方科技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宗教观念的传播,在中国文士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首先,中国文士通过翻译、阅读这些作品,获得了较多的感悟,这些感悟直观地以序言体现出来,如冯应京“其悟道也深”“其论而益信”,瞿汝蘷“师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藉有录之”,徐光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等,同时这些序跋文字也体现出写作者对书籍内容的信服。
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也为当时的文学批评家所吸收,运用到文学评论中,如朱日浚利用《交友论》“墨卧皮”“折大石榴”的故事笺注《伐木》,吴震生、程琼《才子牡丹亭》评点《惊梦》“我常一生儿爱‘好’是自然”运用了《暗狱喻》中“地狱”“大烛小烛”等暗示后文“巫山云雨”的发生等,这些文学评点文字多多少少受到西方教士著作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观点。
传教士在华亦经常进行与中国文人的讲学和交游活动,在这些交游活动中,虽然文人们经常保持自己的“先见”,并不完全吸收耶稣会士们的思想,但对于耶稣会士们所带来的新鲜思想仍然是有所吸收的,在其随笔、诗文中均有所表现。如叶向高诗句“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冯应京“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的发阐、邹元彪《答西国利玛窦》的记录、陈继儒“人之精神,屈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非朋友不能弥缝。不意西海人利先生乃此见”的感慨等,这些交游的经历在东林文士们的日常生活中画上了浓重一笔,也在他们的日常笔记中留下了蛛丝马迹,为他们的作品添上了一抹异域色彩。
最后,西方传教士在受到一些文士的青睐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徒和反耶人士的反叛。西士曾与晚明保守儒士和佛教高僧们进行过较为激烈的或纸面化或讲论化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想交锋被以随笔、专论等形式记录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绝妙的内容。如云栖祩宏和尚的《天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文字,针对对方思想缺陷,引用例证、故事等进行反驳,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再如明末徐昌冶辑录的《圣朝破邪集》也是极为重要的作品,其以西士之说“如火之燃,如川之沸,如狼魅之暴者也”的西学为夷狄之邪说,以为信教乃寄托魂灵于外世,是自暴自弃之行为,其中收录有沈榷、黄贞、杨光先、许大受等人的作品,均富有煽动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强、例证性高,作为学术交流的文论集,有着较高的文学意义,这属于文士对于教士学说的一种反叛性的反响。但总体上,无论是在思想还是文字记录上,这些保守人士对西学的记录均保持在较为浅显的阶段,并没有如晚清某些文人那样深入了解西学的学术思想,也没有在深层与西士进行学术交流,更多的仍是道德保守性的回护论述。由此可见,中西思想层面的交流亦多停留在初级阶段。
总体来说,西学翻译和教士著作对文士的思想影响较大,而其思想也随着阅读者的写作行为进入中国文学作品之中,对中国文学的品评、随笔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与哲学、伦理思想有着较强的关联性,西学的传入不仅在思想层面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质素,亦对中国文学作品写作技巧、论证力度的提高有所促进,因而,西士的著作可谓给中国文学思想史吹来了一阵新风。
四、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传教士带给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贯穿性的、多元的,而同时传教士的活动并没能与商业活动完全剥离,这一点可以从传教士活跃的地点与当地商业的活跃度的结合程度对比而得出,福建、江南、北京周边,作为商业最为繁盛的几个地区,对于基督教的接受程度也是最为开放的,这或许与商业文明下的人文视野有关。人们可以指出传教活动的不单纯性,而在这个复杂的传教动因的基础上,更会发现其对信仰的坚定度的反作用,正是伴随着世俗性质的传教欲望,更加坚定了晚明初期传教士们的传教决心。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晚明中西商教活动与晚明文学变容之间的交融互动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基督教士对中国晚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以中西商业活动为基础的,商业活动所提出的需求以及其提供的开放环境均影响着文士们对天主思想的接受需求和接受程度,因此也影响着文士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对西方思想的突入式回响。
其次,在晚明政治形势和商业冲击的双重影响下,天主思想对晚明文士的影响是由浅入深的,从表层的西方科技层面,逐渐深入到中国士大夫所普遍关注的人文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最后深入到底层伦理的碰撞之中。这或许可以归结到西士传入思想和宗教的方法上,正如加达默尔所说:“先见是人不可拒绝的历史存在,它是任何新的理解之先决条件。”西士携带着西方视角先入为主地突入中国文人士大夫之中,其所持之观点,难免带有对中国的误解和西方文化化生下的“己见”。而从中国方面来讲也是一样的,中国文人在理解西方的内容时,当然也会不自觉地带有这样的先入为主,因而,中西方的思想变动其实是交互进行的。而这种交互必然從晚明形势下文人阶级最为需要的地方开始,逐渐深入到文人们最为关注的地方,逐渐形成由器物到思想再到伦理,由表层渐入深层的思想交互阶段。随着中西思想的交互,文学主要创作主体的文人们的思想逐渐受到冲击,随之反映在文人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因而,晚明文学的变容受到中西商教活动的影响也同样呈现出此种阶段性特征。
同时,单纯考察文学变容这个层面,可以发现西方质料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和初级性。由汤显祖初期的局限于所见的西方场景到后期闽中众人与艾氏相互唱和中所携带的宗教思想和其领悟,再到明末清初文学家们批评、文论中所带有的西士所作、所译文段的引用摘注,由目之所及到心之所发再到文之所用,这样由浅入深的变动性正呼应着中西思想交互的阶段性。而同时,总体上看,文士们始终没有完全将西方思想内化,字句、语词、场景等的摘注引用均体现一种初见的浅显性和初用的生疏性,故而体现出一种文学接受的初级性。
总之,晚明中西商教活动从社会层面、思想层面逐渐波及晚明文人的创作,催动了许多古已有之的开放因子的复萌,也促动了晚明思想与部分西方思想的初次交汇,给晚明文坛带来了一抹神秘的异域色彩。
a 周松芳:《汤显祖的岭南行及其如何影响了〈牡丹亭〉》,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be 徐晓鸿:《汤显祖诗歌与基督教》,《天风》2010年第1期。
c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线装书局2013年版,第2页。
d 傅承洲:《明代话本小说的勃兴及其原因》,《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
f 蒋文浩:《晚明文学新质素——传教士的汉文写作及其影响》,山东大学文学院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页。
g 孙琪:《明末遗民李世熊及西学之关联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42页。
参考文献:
[1] 利玛窦,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 李奭学. 明清西学六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3] 徐世昌著,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张西平,罗莹.东亚与欧洲文化的早期相遇——东西文化交流史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陈伯海.中国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6]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 者:刘朋鑫,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 :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