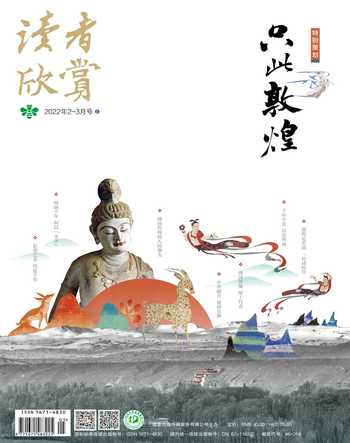佛国世界的人间烟火
2022-04-04张立峰
张立峰

莫高窟第148窟 婚宴图 盛唐
那些由洞窟壁画、文书写卷和鲜活生命共同绘就的画面,向世人讲述着政权更迭的刀光剑影和社会升平的繁荣景象,也讲述了佛国世界的成住坏空和市井小民的生老病死。1000余年间,几十代的善男信女用虔诚的信仰,描摹出一方辉煌灿烂的佛国景象,也保存了他们曾经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让这佛国世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莫高窟隋代第62窟壁画中的供养人—成天赐一家,大约是敦煌当地一个有余财礼佛的普通家庭,壁画反映了当时平民的衣着服饰。女子自首到脚有包头帕、圆领窄袖衫、翻领窄袖披袄子、素色或间色条纹裙,裙前加飘带;男子身穿交领短衫,内衬圆领中单,腰系绦带,下裳宽肥,足服高头履。
从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第159窟《挤奶图》和榆林窟第25窟《耕稼图》看,唐代平民女子的服饰更加多样,既有沿袭而来的窄袖衫、长裙,也有胡服、男装。她们的衣裙更加艳丽多彩,窄袖衫的领式从小圆领发展到交领、敞领,折射出唐代女性服饰由保守到开放的风气之变。
身份的不同会带来装扮的差异。雇工多着长袖、汗衫、褐袴等“工作服”;军士有袄子、长袖、半臂、单袴、复袴等“制式军衣”;僧尼更有其独特的打扮—袈裟、覆膊、头巾。敦煌百姓喜胡帽,劳作时却多戴笠子。唐代皮靴风行,但普通百姓仅在重要场合才穿,夏日劳作还是以麻鞋、草鞋、木屐为主,冬季则穿牛、羊毛纺编的毡鞋。

莫高窟第62窟 家族供养像 隋

莫高窟第23窟 雨中耕作图 盛唐


榆林窟第25窟 婚宴图 中唐

榆林窟第25窟 耕稼图 中唐
置办一身衣服可价格不菲。在富足的唐代天宝年间,即便是用最便宜的小水布制作服饰,一套上衫和单下裤,再加上幞头和麻鞋,大约也要1000文钱。因此,在王梵志的诗里,贫穷的田舍汉常是一副“衫破肚皮开”的模样。
民以食为天。敦煌壁画中有很多饮食画面,如“婚礼宴饮图”“酒肆宴饮图”“斋僧图”等,蔚为大观。藏经洞出土文书中,记载了敦煌得天独厚的饮食文化,可谓无所不包。仅食物名称就有60多种,如胡饼、炉饼、馎饦、馄饨、冷淘、粽子、须面等,大部分都是面食。敦煌人爱吃面,唐末时就开始用天然碱来发酵面粉。
今天的揪面片,敦煌人曾这样描述:“馎饦,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敦煌文书中有种特殊的面食叫“浆水面”,唐代人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浆水配上面条或稀饭,酸酸爽爽非常可口。“烧尾宴”食单中还有“长生粥”“神仙粥”,虽不明其用料,却寄托着敦煌人“寿长千年”的梦想。

莫高窟第85窟 《楞伽經变·断食肉品》情节之一 晚唐

高窟第61窟 亭中宴饮图 五代

莫高窟第98窟 亭中宴饮图 五代

莫高窟第146窟 亭中宴饮图 五代

榆林窟第3窟 从左至右依次为:酿酒图、舂米图、锻铁图、犁耕图 西夏
曾有数十个酒家载录于敦煌文书,其中很多是胡商开的,还有不少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如马三娘、灰子妻、石婆等,可以想见当时胡姬当垆卖酒的风情。在敦煌文书《高兴歌》中,有10多种驰名一时的名酒,如渌酒、鹅儿黄、鸭头绿、桑落酒、葡萄酒、清酒、竹叶、九酝、黄花酒、拨醅酒等。
敦煌人需要饮酒的场合有很多,如禳灾祈福祀酒、祆寺求雨祀酒、浴佛节饮酒、丧葬饮酒、招待寺家磨面师傅饮酒、招待淘麦僧人饮酒等。仅以结婚而论,就有求婚纳聘时的“纳采饮酒”,置办婚事的“荣亲饮酒”,新郎到女家迎亲的“闹房饮酒”,以及新婚夫妇求吉共饮的“合卺饮酒”。莫高窟第61窟有《酒店图》,人们饮酒之时,一位婀娜舞伎在酒客面前舞蹈助兴。敦煌文书里,还有当时人对于醉酒行为的文雅道歉。
在敦煌,寺院酿酒、沽酒、用酒,僧人开酒店营利,以及僧人饮酒都是寻常事,并得到僧、俗两界的认可。西夏榆林窟第3窟的《酿酒图》绘有炉灶,灶台上叠压四层大小不同的方形或梯形器物,顶上还有烟囱。据考证,该器物就是酿造高度烧酒的蒸馏器。

莫高窟第61窟 牛车及绘有精美花纹图案的遮阳篷 五代
敦煌地属丝路重镇,商贸繁盛,街衢中店铺林立、人流如织、货无停滞。当时交通出行的重要工具如车、轿等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多有出现,其中有马车、骆驼车、独轮车等实用车,也有力士、龙凤、麒麟驾驭的神仙车,另有四抬轿、八抬大轿等各种轿舆。
隋唐以来,随着《法华经变》故事画的大量绘制,表现“火宅喻”的牛车、羊车、鹿车形象在壁画中大量出现,用以劝诱“愚痴者”出“火宅”。敦煌壁画中还有极为少见的四轮车和多轮车,但主要形象还是双辕双轮车,其中既有装饰华美的载人安车或轺车,也有高栏大轮的载货车。

莫高窟第85窟 《法华经变》中的院落、马厩 晚唐
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中,护卫队后面有一辆马车,车顶人字形高棚向前后伸出长檐,车前画榜题“司空夫人宋氏行李车马”。司空夫人的坐车装饰极为豪华,双层顶篷的上层更为宽大,且可拆卸,能够很好地遮蔽烈日,避免阳光直射下层棚顶,从而确保车内凉爽舒适。稍后还有四辆马车,表现的是侍女跟随主人游乐的场景。整幅作品展示了唐代贵族春游踏青的烜赫气派,堪称敦煌版的《虢国夫人游春图》。
在敦煌壁画中,历代画师为后人留下了平民百姓的日常居住印记,将当时的茅庵、草棚、邸店、厩舍、监牢、坟墓等建筑形象,如戏剧舞台的布景道具一般,穿插在佛经故事或经变绘画之中。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法华经变》中,有一座以廊庑围合、前后两院的宅邸,外侧还建有马厩。宅邸前院横长,后院方阔,中有两层楼阁,前廊与中廊的正中分设大门和中门,这与现代北京四合院将门设置在中轴线偏东略有不同。纵观全画,建筑规整有序,人物悠然自得,富有生活气息。

莫高窟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局部) 晚唐 段文杰临摹


莫高窟285窟 斗鸡图 西魏

莫高窟第85窟 帷屋闲话图 晚唐
敦煌写卷P.3644记载了更多普通百姓的居住细节。当时的房舍有正堂,一扇或两扇的户门,内有椅子、交床等家具。厨舍内的物品相当丰富,包括釜灶、三脚铛、镬子等炊具,栲栳、簸箕等盛具,烧炭、灰火等引火物,钵盂、杯盏等饮食具,以及橘皮、高良姜、槟榔、椒、蒜、干枣、饴糖等用于调味、提色和增香的调料。庭院棚屋绘有牛羊等牲畜,以及车驾、农具、扫帚等用具。
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僧尼还存在“居家现象”。特别是随着佛事日盛、僧团渐多,导致寺无寮房、僧乏口粮,僧人“居家过活”更为普遍。莫高窟晚唐第468窟前室南壁題记写有“亡祖父乾元寺老宿法号慈善初创建内龛记”,说明窟主的祖父为僧人慈善。有意思的是,此窟对应的祖母供养像为女尼。由此可知,慈善夫妇均为僧人,至该洞窟营建之时,已是家室兴旺。
敦煌文书《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崇恩和尚蓄有大量的田地、房舍、奴婢、车辆等,俨然一个世俗富人。“僧文信经数年间,与崇恩内外知家事”,僧人文信可能就居于崇恩家内,为其管家,也为自己免去衣食居所之忧。更多僧人还是选择回归自己的家庭,享受家居的温情,年老也能得到子孙的照顾。僧人亡故后,家属可继承其部分财物,订立遗书时亲属须在场。
事实上,当时的敦煌僧人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他们从事农耕,拥有私产,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晚唐《归义军军籍》残卷里,如僧法义、僧明振等名列军籍的僧人比比皆是,几乎占军籍名录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当时归义军队伍中有很多僧人,他们同普通战士一样,也会冲锋陷阵、浴血疆场。
这些都是敦煌僧尼脱离清修戒律,受尘缘牵绊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表现,是古代敦煌社会生活的独特风景。

《报父母恩重经变》之浴儿 绢画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相传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于王城四门分别见到分娩、老人、病人、送葬的情景,顿感人生之苦。生老病死,佛教认为这是人生所必须经历的四种痛苦,“苦谛”正是佛教基本教义“四谛”之一。
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古代妇女生子是极危险的事情。在敦煌,妇女分娩被称为“难月”,产妇犹如走一遭鬼门关。为此,她的家人常祈求神佛保佑母子平安,甚至会亲赴寺院,施舍财物,延请僧人诵经助产。在敦煌文书《难月文》中,产妇家人拜佛祷告:“惟愿日临月满,果生奇异之神童;母子平安,定无忧嗟之苦厄。”
妇女产后也一样要坐月子。敦煌文书P.2661记载:“妇产不满百日,不得为夫裁衣、洗衣。”妇女生产后不满百日不能从事家务劳动,不沾水,不裁衣,与今天别无二致,这有利于妇女产后护理,防止疾病,恢复身体。
成住坏空,人与时老。身体衰颓,无人可免。老之将至,眼花耳聋,力不从心,觉悟无常,使人倍感痛苦,谓之“老苦”。为保证老有所养,中国儒家十分注重尊老的传统美德。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儒家爱老、护老的思想,也倡导尊老、敬老。
敦煌写本《庆寿文》中,记载了孝子贤孙们尊老敬长的场景。从“拖张绮席,陈列画图”之语可见,老人的寿诞之庆办得很隆重。“陈列画图”是指将老人的画像陈列于庭堂绮席上,供子孙叩拜。他们还延请僧众做法会,祈求在佛力加持下,老人能“更添益算之寿”,“永等鹤龄之固”。

莫高窟第156窟 《父母恩重经变》之栏车 晚唐

莫高窟第302窟 汤水浴 隋

莫高窟第159窟 《彌勒经变》之净齿图 中唐

敦煌写卷S.6300则记载敦煌乾元寺白僧院大法师与乡司判官李福绍结为弟兄,两人还签订了“兄弟契”。发愿文中写有“其弟兄所有病患之日,便须看来”这样的内容,从中或可读出这僧、俗二人希望在自己老迈之后,能够相互慰藉,以减轻“病苦”的折磨。
从敦煌写卷《新菩萨经》和《劝善经》可知,佛教始终关怀人间病痛。敦煌有个重要风俗就是“择吉日治病”,《雍熙三年历书》就有其概况和“治病时间表”。其中,每月择吉规定四到五天是治病的时间,平均每星期找医生看一次病,这对环境艰苦的边地百姓而言,是有益无害的。
敦煌曾出土古代手抄本医方一千余剂,治疗范围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甚至还有美容方剂。文书写卷中反映,晚唐时敦煌已有治疗类似白内障、肠外科的手术。《食疗本草》残卷更是我国唐代最著名的饮食疗法专著,总结和发展了药食同源、药食同用的宝贵经验,许多药理至今仍旧适用。
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展现了很多运动练功、养生保健、诊疗疾病等珍贵的古代医学活动,绘有洗浴、洗发、理发、刮脸、刷牙以及清扫等画面。莫高窟唐代第186窟《刷牙图》,描绘上身赤裸的刷牙者蹲在地上,左手握净瓶,右手持齿木横于嘴上,正在刷牙。这是我国最早的口腔卫生保健绘画。
病人就医后,病情好转,家庭会举办庆贺斋会;如不见好转,家中要举行建福斋会,敦煌斋文中众多的《患文》《僧患文》《俗患文》就是例证。这是敦煌人在医药无效的情况下,寻求的心理安慰。莫高窟盛唐第103窟《念经治病图》中,有位病人在家人的搀扶下坐于地毡上,双手合十,正在虔诚祈愿。

莫高窟107窟 喜和母女供养像 晚唐

榆林窟第25窟 老人入墓图 中唐
当神佛也回天乏术时,病人只能等待死亡降临。敦煌壁画《老人入墓图》就描绘了这样的无奈。
死者临终前,家人会提前准备后事。老人要写下遗书,交代财产归属,作为日后子孙分家的依据。家属要请人为其画像题赞,以供日后祭奠、瞻仰之用。在老人病危或临终前,要将其从卧室转移到堂屋,为其更换新衣,为官者要换上朝服,在肃穆的气氛中让老人安静地逝去。
吊丧、入殓以后,就是出殡。出殡要选择一个吉日,在行过“辞灵礼”之后将棺材抬上灵车,由挽郎牵引,孝子手持纸幡前行,晚辈和亲友随后,唱挽歌直至墓所。富贵之家在出殡过程中,还要设置“路祭”,祭祀沿途的山川诸神,使死者的亡魂得以顺利通过。
对于亡者,不论僧俗,寺院往往都要通过烧香设供、诵经祈愿、安魂助葬,施予最后的关怀,为丧亲家属提供精神慰藉。借此,佛教的“四苦”观也由圣入凡,慢慢褪去神秘的外衣,深深地融入俗世人间。
当人们见到了生命的无常、感叹“苦海波涛”,仰望着巍峨壮观的北大像,期望“天堂户开”时,都会虔诚发愿,愿为逝去的亡人、健在的亲人和来世的自己,开窟造像、写经供养,积攒功德,祈求佛祖的保佑。因此,他们在莫高窟留下了8000多身供养人的画像,崖壁上密布的小洞窟也多是普通百姓出资修建的,哪怕是家贫者,也想竭尽所能地供奉几幅精美的绢画、麻布画或刺绣画。

供养人像 绢画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莫高窟晚唐第107窟是个仅有几平方米的小洞窟,营造它的这个唐代普通家庭除了正式家庭成员外,连身份卑微的奴婢喜和母女也参与了洞窟凿建。在供养人壁画中,喜和母女二人衣着简单朴素,榜题中说,她们出资绘制了6身释迦牟尼像,并“愿舍贱从良”。
以个人身份参与洞窟重修营建的,在在有之。很多时候,他们在别人开凿好的洞窟内,出资占得方寸之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绘上佛画和个人供养像。在莫高窟第98窟中,绘有超过1000身的供养像,从残存的题记看,这些供养人来自广阔的河西地区。
除了参与营造莫高窟,敦煌的庶民百姓也十分热爱它,将其视作精神上的寄托。敦煌文书S.3553记载,一位小牧主利用日常劳作之余为莫高窟提供颜料,并托一位牧人带给窟上的僧人,让僧人替自己找一位好画师画壁窟;自己因故不能亲自到窟上,如果还需要颜料,他会继续寻找。不论人在何地,他们都是心系莫高窟的,并时刻倾注着心血和热诚。
佛经说,极乐佛国,天乐常鸣,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宝装饰楼阁;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为此,世世代代的敦煌人和无数的工匠、画师,用勤劳的双手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描,借用人間最美好的景象,构筑出这个美妙奇异的天国,也铸就了莫高窟的灿烂辉煌。
如是,佛国当自人世间创生。

莫高窟第98窟 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夫人曹氏像 五代

莫高窟第61窟 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像 五代

九层楼 102.3×61.5cm 常书鸿 1952年 敦煌研究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