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的2亿“合伙人”
2022-04-04秦朔
秦朔
又到了“金三银四”招聘季,企业迎来了新一轮用工荒。在大洋彼岸,美国“大辞职潮”愈演愈烈,科技巨头纷纷适应员工混合办公的需求,更多高端人才选择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总体占比稳定保持在36%。
而在中国,自由职业有着另外一个统称——灵活用工。
中国政府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回首过去10年,我们应该致敬数字时代的服务业发展,让中国就业结构“从制造到服务”的历史性大转型悄悄完成了,基本没有什么动荡。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灵活就业是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伴生现象。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大量和数字经济平台联系在一起的灵活就业者,他们更加自由,更加自主,也获得了更多收入,是继中国制造之后的新就业力量。
中国离不开灵活就业,中国需要更好的灵活就业。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数字时代的2亿“合伙人”——灵活就业者。
这是一篇关于就业的文章,关于数字时代中国2亿人的灵活就业。
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讲一段从美国到中国的创业与就业故事。
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是我最近又在重读的一本书。书中有这样的内容:乔布斯在上高中时,对数学、科学和电子学很感兴趣。他加入了惠普探索者俱乐部,每周二晚上到惠普的公司餐厅,和十几个学生听一位工程师讲正在研究的东西。他也在这里做了一台频率计数器。为了做计数器,需要一些惠普制造的零件,他就通过电话本找到了当时惠普的CEO休利特,在电话里聊了20分钟。
休利特给了他零件,也给了他一份在制造频率计数器的工厂的差事,高中第一年暑假,乔布斯就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安装基本元件。
乔布斯喜欢工作。他曾经送过报纸——下雨的时候父亲会开车送他,高二的周末和暑假他在一家巨大的电子器材商店Haltek做仓库管理员,对电子零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会去电子产品的跳蚤市场,为了一块带有值钱芯片的电路板跟人讨价还价,然后把芯片卖给Haltek商店的经理。
苹果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在同一个高中,比乔布斯大5岁。他很小就对无线电和新式计算机感兴趣,8年级时基于二进制理论造出了一台计算器,12年级时做了一个电子节拍器,可以在音乐教室里打拍子,这一年他还在喜万年(sylvania)得到了一份兼职,人生第一次有机会在计算机前工作。他自学了FORTRAN语言,研究最新的微芯片的规格,开始用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设计计算机。
1970年秋天,在朋友介绍下,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在一个车库相识。这次见面被认为是硅谷历史上第二次最重要的车库见面。上一次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见面,两人共同创立了惠普。5年多后,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创立了苹果——今天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

接着把故事切到中国。
2012年5月16日,中国台湾《商业周刊》为到台访问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举办欢迎晚宴。鸿海精密(下属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郭台铭出席,首次与何享健碰面。
郭台铭说:“搞工厂是件苦差事。有订单发愁,没订单也发愁。”但当何享健问起“中国制造业优势能维持多久”时,他立刻眉飞色舞,说中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是世界第一。“我在中国大陆有整条产业链,所有的塑胶粒、电阻、电容、半导体,所有东西都在这儿。”
“前年,奥巴马逼乔布斯问我,能把iPhone、iPad搬回美国吗,我说搬回来,加钱事小,一台多个十几美元,还能赚回来。问题是你供应链没有啊!所有东西都要送過去再装,员工又懒,连材料全都Kitting(成套搬运)过去,那我省什么?惠普主管告诉我,美国圣地亚哥一律师事务所有500个律师,每个人就是针对美国500强,一个人管一家,每天的任务就是告状。打官司要花钱,只好和解。如果你是消费型产品,有品牌的,一定要买产品保险,否则哪一天就有律师说,有个小孩怎么了,狗死掉了,是因为你的空调温度不够。所以美国不适合搞制造业。”
何享健问郭台铭国际化的经验。他回答:“选地点很重要,我在印度投资不小,也做了很多年,但是不成功,印度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却是多民族的联邦制,巴西也是一样,政府有心,民间无力。”
郭台铭还对中国大陆制造业做了预见,如工资会持续上涨,年轻人不喜欢进工厂,所以必须走自动化,机械手臂代替人工,企业从制造走向技术、商贸、服务。
上面的故事,对我有四点启发。
首先,任何创造都需要开放、灵活、自由的大环境。
乔布斯、沃兹尼亚克从中学起就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并通过灵活工作等方式了解电子行业和商业社会。如果学校、企业有很多条条框框,这个不许那个不行,这个要怎么规范那个要怎么监管,他们很可能就被束缚住了,缺乏创造力。
其次,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自生长的结果。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最深刻动力,是让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成长。很多发明创造,都是一些年轻人凭兴趣摸出来、试出来的。今天的小苗可能是明天的参天大树,今天的微光可能是明天的熊熊大火,谁知道呢?因此对年轻人的选择和市场的自发有效力量,要特别包容。
再次,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要考虑与企业竞争力的平衡。
美国今天不适合搞制造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用工成本、合规成本、诉讼成本太高。提高工人收入,保障其权益,是正确方向,但如果成本增速超出效率增速,影响到市场竞争力,最终受害的是工人本身。美国的“铁锈地带”就是证明。
最后,产业升级是渐进的,但一定会发生。
乔布斯一代站在惠普一代的肩膀上,又赶上计算机和互联网浪潮,为全球科技产业开拓了新边疆。中国是后发经济体,科技底子弱,只能从代工起步,发挥勤劳、低成本、有组织、守纪律的劳动力红利。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制造已走遍天下。之后,中国经济必然也必须转型升级,发展高技术,发展服务业。
讲到这里,我们切入中国的就业、创业话题。
人的一生,说到底,就是生存与发展。要生存就要有饭碗,但饭碗远不只是为了解决一日三餐,更是赚钱养家、学习成长、通过劳动成果的交换获得社会认同的地方,最终是为了人尽其才,实现全面发展。
就业为民生之本,全世界都一样。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对于在1978年时超过70%的人口都是农民的中国来说,就业更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程。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就是不断造饭碗、造出更多更新更好的饭碗的过程。
到2020年年底,中国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为23.6%、28.7%、47.7%。正是工业化、城镇化和服务经济的新饭碗,让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价值,这就是中国GDP增长的源泉。
中国造饭碗,主要靠什么?靠市场。2020年年底中国就业人员有7.5亿多,城镇就业有4.6亿多,其中2亿左右为灵活就业,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

習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中国的灵活就业者,“不找市长找市场”,自助者天助,可敬可佩!
郭台铭和何享健见面是2012年,当时他已感受到大陆制造业的用工压力,年轻人不愿像上一代那样当工人,而国家有保证的铁饭碗又不多,制造企业自己可以选择自动化,机器换人,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哪里能容纳每年上千万的新增就业需求?
服务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潮兴起后的数字时代的服务业。
2017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文指出,2012年至2016年中国就业格局呈现出的第一大特点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 2012年至2016年三产就业人数占比从36.1%升至43.5%,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第二大特点是,民营经济成为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主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就业创造效应持续显现。
中国政府把“稳就业”放在“六稳”之首。回首过去10年,我们应该致敬数字时代的服务业发展,让中国就业结构“从制造到服务”的历史性大转型悄悄完成了,基本没有什么动荡。当然,政府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长期投入和对“双创”以及灵活就业新形式的大力支持,是发生这一切的基础和根本原因。
2015年10月,我从一个有事业编制的总编辑,转变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服务业创业者。6年多来,我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在公众号写文章。我和腾讯没有雇用关系,是个体和平台的合作关系,没有公众号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工作,所以我对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有着深深的感激。
作为观察者,我采访过不少基于数字经济平台的店主、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主播。数字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仅此一点就值得充分肯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是中国经济向着创新驱动和美好生活方向演进的重要路径。
经济的本质是供求,经济发展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和新供给被不断激发出来。我小的时候,只用一块“矛盾牌”肥皂就完成了洗手、洗脸、洗头、洗澡,现在我女儿光面部化妆品就多得让我眼花。早不止三百六十行,而是几千几万行。
无数个体为生存与发展所做的各种尝试,造就了无比复杂、多元、变化的经济生态,而生态的演化又创造出更多需求、供给和分工。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对人民生活更加多元和更加个性化的满足就是这样实现的。
你我身边,一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真方便”“太方便了”“越来越方便了”。这就是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的结果。而方便的背后,是数字科技的突飞猛进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
我采访过拼多多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店主,他们在青海、甘肃、四川大凉山,我也去过浙江农村的淘宝村,采访过网商。我看到很多有特色、但过去人们不知晓的产品和手工艺品,现在有了市场。他们在做天下人的生意,有了一点成绩,就多一分自信和微笑,家庭的气氛也更好了。
我在安徽临泉县专门调研过当地的外卖骑手和商家,仅美团的骑手就有200多人,连接的商家有1300多家,加上管理、推广人员,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在美团这样的平台出现前,中国也有外卖,但是是分散的、规模很小的。而饿了么、美团通过多年努力,帮助广大商户实现了数字化迁移,在线提供服务,同时创造了专业化骑手这一岗位,目前在全国有数百万人。在我看来,能帮助解决数百万人的就业,能帮助一个巨大的行业实现服务在线化,能帮助几亿消费者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也是星辰大海。
我自己身边,有很多数字内容的创业者,从博主到UP主(上传者),从视频主播到带货达人,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美术人员、服务人员,他们创造了许多有价值有趣味的内容,有一技之长,就有生存之道。很多人笑话自媒体肤浅,只追流量,但我很清楚,大量创作者绝不会随波逐流。

我也听到和看到许多奇妙新职业的出现,比如大众点评和小红书上,有密室剧本设计师、PPT美化师、宠物摄影运营师和宠物殡葬师、侍酒师、电竞教练和室内冲浪教练、古风造型师、全屋收纳规划师、剥虾师、砍椰师、餐厅育儿师、球鞋鉴定师、撸猫师、STEM创客指导师、酒店收益管理师、无人车安全员、线上餐厅装修师等。
我最近一次去互联网公司是上周到Soul APP(社交APP),其定位是“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个新职业是捏脸师,就是帮助用户美化自己的虚拟头像。2021年6月底Soul推出“个性商城”,短短几个月已有80名捏脸师入驻,上架了1.3万多个原创头像作品。虚拟头像有三档价格,最低价位是180 Soul币(对应30元),西安有一个宠物美容师,也是Soul上的捏脸师,有个月靠出售虚拟头像获得4万多元收入。我并不太懂这些新职业,但看到有才能的普通人能在一个平台上实现过去想不到的价值,很开心。
有人说,年轻人沉湎于数字服务,会影响制造业就业。年轻人走出传统流水线确实是大势所趋,除非工厂更自动化、智慧化,是“办公室化”的新工厂。同时我也看到,灵活用工的服务业就像蓄水池,在制造业用工旺季,付出平时的两三倍工资的时候,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又灵活地回流过来。前不久我在潍坊的歌尔股份就听到,虽然为客户赶工的高峰期(如客户赶美国“黑色星期五”大促),要给灵活就业者很高的工资,他们有时干两三个月顶平时差不多一年,但对企业来说也有好处,就是淡季也没多少闲人。总体上,服务业的灵活就业者和制造业用工之间,有一种互补和熨平劳动力峰谷的作用。
正因为实实在在看到了数字时代服务业的作用,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支持多渠道靈活就业的意见》,指出坚持市场引领和政府引导并重、放开搞活和规范有序并举,顺势而为、补齐短板,清理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强化政策服务供给。此后从国家人社部到各个地方,出台了大量“拓渠道”“优环境”“强保障”措施,同时提出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这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赋予了灵活就业和传统雇用就业一样重要的地位。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比2020年增加5.46%。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指出,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到2035年,也许中国一半的就业者(接近4亿)都会是灵活就业者,U盘式就业、分时就业、斜杠职业、合作型就业普遍存在,人们从关注工作岗位转为关注工作任务,“社会工作任务与精准的人力资本匹配”变成常态,组织型、集中型、单一型的就业模式向着自主型、分布型、多元型的就业模式迁移。与此同时,学习变成终身学习,一个人的一生,工作与学习融为一体。
前不久我和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交流,他说最近在思考混合办公(Hybrid working),这是《柯林斯词典》2021年度热词。
2021年5月,谷歌CEO桑德尔·皮查伊给全体员工发邮件,表示谷歌将进行混合办公,即办公室工作和远程办公并行。工作不是非得在公司工位、用特定终端才能进行,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使得随时随地、多终端的灵活办公成为可能。
灵活就业和混合办公,在思想上有相似性,就是越来越“去中心化”。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人固定在机械化生产线上,信息革命时代人和PC工位捆在一起,那么在元宇宙时代,人将越来越摆脱固定的物理空间的束缚。
和梁建章交流后,我查了不少报告,发现灵活就业已经是全球性的趋势。
美国凯利服务公司发布的《零工经济报告》(Gig Economy Report)指出,随着员工和工作本身要求更大的灵活性来推动创新和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的概念变得越来越不固定,企业可以采用“工作匹配”(workfit)的方式来管理员工,人才供应链不仅包含全职员工,还包括各种零工——临时员工(如派遣者、待命者)、独立承包人、顾问和自由职业者(独立合同者)。以工作时间和场所划分,可以分为非全日制工作、临时性工作、季节性工作、合同制工作、自雇就业和远程工作等。
德勤《2018年全球人力资本趋势调研》指出,多元劳动力生态系统正在兴起,企业主导的传统用工模式正向员工主导的开放模式迁移。劳动力生态系统被定义为“一个专注于为组织创造价值的结构,具有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这个结构包括来自组织内外的,追求个人和集体目标的实践者”。
2020年秋季,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和德勤对来自世界138个国家、29个行业的5118名经理和领导者进行了调查,约87%的受访者认为,员工和外部员工(承包商、服务提供商、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众包贡献者、零工)都是劳动力的一部分,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外部员工。
研究举出的案例包括:
总部在英国的传播集团WPP拥有超过10万名员工,同时依赖几十万名自由职业者。
企业软件公司Workday的高管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劳动力连续体,从非雇员(如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的工作,到包括小时工和工资工在内的员工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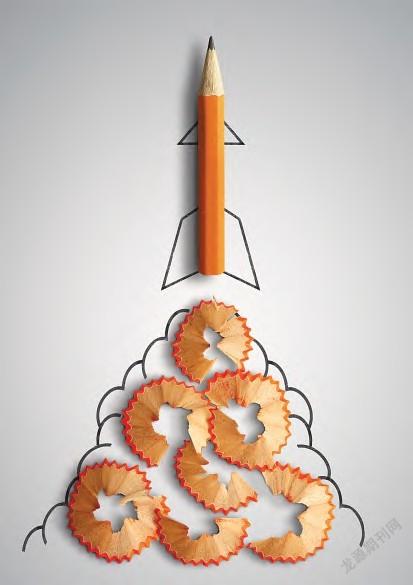
美国NASA这样的传统模式组织也认为,未来的劳动力既包括“有人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将在当前岗位停留30年,也包括以项目为基础的临时工,他们在美国宇航局工作一个季度,可能同时还在其他多个工作岗位上工作”。
软件测试公司Applause将员工队伍视为一个社区,它自己的400名员工中没有一个软件测试人员,但其众包社区——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70万名人员完成了软件的测试工作。公司CEO说:“这比专门雇用某人做这项工作要好得多,在这里,你能知晓有关于外部员工的数据——他们参与了哪些项目,提交了哪些bug(程序漏洞),通过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带来的价值。”
伴随工作方式的变化,在全球很多地方,工作观也在深刻变化。过去的工作观注重KPI(关键绩效指标)、机械化、流程驱动,新的工作观注重速度、创新、协作关系。过去的工作观注重“人岗匹配”,一劳永逸;新的工作观注重“人工匹配”,精准完成工作任务。
就业者自己的偏好也在变化,一位接受调研的CEO说:“对于千禧一代来说,任期时间长短以及忠诚度都是过去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喜欢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就会离开。”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忠诚员工”,新一代希望拥有自主权、目标和动力,希望有更多的项目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像早期的几代人,更喜欢连续性、稳定性和向上走。
中国的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灵活就业,是中国经济和中国就业的一部分,而且符合全球性的趋势。各级政府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在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时,也应高度重视劳动者权益,但一定要看到,灵活就业和传统雇用就业存在不少区别,简单移植传统的劳动关系,初衷良好,可能并不适用,反而约束了很多新行业、新职业的存在与发展。
我经常听到一些对灵活用工的批评,主要是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够。这方面确实需要不断改进,但保障性高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央国企、金融机构、高级白领和金领,这样的岗位在整个就业大军中的占比毕竟有限。很多零工和互联网平台用工,确实只有日结等劳务关系而没有完整的劳动关系,确实只缴纳了工伤保险,当终止劳务关系时也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我亲自调研过一些骑手,他们原来是在企业工作的,缴纳“四金”比较齐全,但他们宁愿选择骑手的“灵活就业+简单保险”,原因一是拿的现钱多一点,可以还房贷、供孩子上学;二是行动自由;三是职业人际环境相对简单,不像在企业或商店里有些是是非非。
更重要的,正是在这种相对的灵活中,很多企业才能生存,才能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工作项目和工作岗位,这也就意味着让更多人获得了发展机会。也许第一步很平凡,但有第一步,未来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新生事物长起来是不容易的,但让它下去,太容易了。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说,“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引导”和“协商”两个词非常精当和重要。
企业用工形态主要包括雇用型、合作型、自由型三种。雇用型可以理解为传统劳动关系,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合作型主要是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业务外包。如美团的专送骑手就属于合作型。自由型是包含多方主体的动态稳定的人力资本配置形态,甲方(企业)在工作节点对劳动者承担支付报酬的责任,基于完成工作结果实行结算。如美团的众包骑手就属于自由型。
从《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等调研来看,中国的用工形态正从雇用型为主导,转向雇用型、合作型、自由型并存发展,灵活用工所占比例正持续提升。
在这一进程中,传统工厂时代的固定雇用模式(一个萝卜一个坑,像螺丝钉一样拧得紧紧的)正逐步减弱,灵活就业的非传统用工(如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务派遣、传统零工等)大量涌现。政府需要加强监测、调研,需要加强对劳动条件、最低工资标准、社保等基本劳动权利的维护,但也要注意到,新就业形态不等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它本身是共创共建的,雇用、合作、自由等因素兼有,劳动治理必须加强,但不等于回到传统模式。
我最后的结论是:
1.无论是从解决社会就业的角度,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传统雇用制度自身演化的趋势看,灵活就业都是一种必然,充满活力。
2.灵活就业是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转型发展的伴生现象。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大量和数字经济平台联系在一起的灵活就业者,他们更加自由,更加自主,也获得了更多收入,是继中国制造之后的新就业力量。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他们正是这样的奋斗者,不当让政府发愁的包袱,而做服务社会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全社会的人力资源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配置和利用。
3.在我们面对2亿灵活就业者必然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固定思维,而要顺势而为,补齐短板。政府倡導民众灵活就业,也要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灵活用工,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中国离不开灵活就业,中国需要更好的灵活就业。让我们共同关心、善待和帮助中国数字时代的2亿“合伙人”——灵活就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