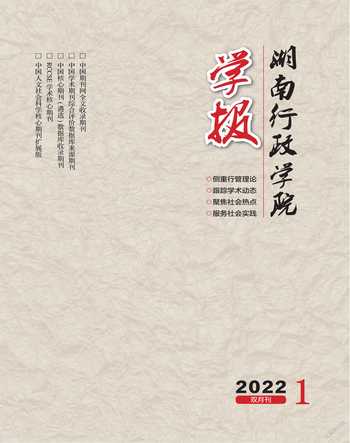权力转换与价值认同:政治仪式视域下的 宪法宣誓研究
2022-03-25姜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2018年正式入宪,自此宪法宣誓作为宪法载明的宪制仪式,通过制度设计和仪式举行为公权力的转移完成最后的确认。宪法宣誓仪式本身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仪式,具有可重复性和规范化的仪式特点,通过仪式符号发挥作用。在我国的宪法宣誓仪式中,国徽、国旗、国歌、誓词、宪法等,作为权力符号助推宪法宣誓仪式的完成,并产生“政治借喻”的效果,在仪式的进程中将世俗的权力变得神圣化,同时使得仪式参与者建立起多样化的价值认同情感。
关键词:政治仪式;宪法宣誓;符号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2)01-0127-08
宪法宣誓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法学界多从宪法宣誓制度的内涵、意义、效力、价值实现等方面进行诠释,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界则多从仪式的角度对宪法宣誓进行深入的剖析。从制度层面看,宪法宣誓制度完善了选举或是任命这样的权力授予程序,为权力转换结果的合法性做出了最后的确认。从具体的实施看,宪法宣誓本身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仪式,具有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所说的可重复性和规范化的仪式特点,其蕴含着丰富的政治隐喻和政治象征,不仅可以强化对宪法的信仰与价值认同,还能授予权威、完善新的权力秩序。“权威的公开授予是一个需要借助仪式得以实现的象征过程”[1]61。宪法宣誓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国旗、国徽、宣誓台、宪法等象征之物的存在,这些象征之物作为国家的代表,在举行仪式时发挥了重要的渲染作用,宪法宣誓仪式中权威授予的神圣性由此得以显现。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宪法载明的宪制仪式,以顺应国家法治化进程而生,通过制度设计和仪式举行为公权力的转移画上了神圣的句号。以权力为核心的宪法宣誓则引发一系列的议题:宪法宣誓中的权力从何而来?权力转移的合法性如何能得到确认?从制度规定到仪式的具体实施,其中的“象征之物”又在权力的转换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制度规定和仪式实施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概言之,本研究将打破对制度或仪式的单一探讨,从制度规定和仪式举行的双重角度出发,探析宪法宣誓中的权力转换过程与宪法宣誓产生的仪式效果。
一、政治仪式下的宪法宣誓
尽管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献对仪式进行了研究,但是仪式这一词却没有统一的概念。大卫·科泽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中通过分析仪式如何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仪式如何用于建构政治合法性,仪式如何在缺乏政治共识的情形中创造出政治一致性,以及仪式如何形塑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来解释仪式的重要性。[1]19并且提出仪式是“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1]11。但是,他并未对政治仪式提出规范的理论界定,这也使得其书中的政治仪式探究有着不明确的理论倾向。政治仪式作为仪式研究的分支,具有更加明显的象征意义,也更加触及权威授予、权力分配的问题。国家政权最初的形成与宗教、神话是密不可分的,此時的政治仪式也不可避免的和宗教、神话联系在一起。张光直认为,“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2]。早期政权依靠祭祀等盛典来成为人民与神祗联系的中介,由此获得人民的认可,达到权力获取的目的。当政治系统进一步的发展后,政治仪式则开始与宗教、神话分离,走向世俗,仪式的重点也开始由神本位转向君本位。马敏先生在解读中国帝制时代的儒家礼制观念时指出,“根基于儒家礼治学说的仪式化政治就成为帝制中国时代政治生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政治仪式承担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生成、再造、反复确认、强化的基本性任务,从而达成维持现存权力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3]。资产阶级革命后,现代民主意识逐渐觉醒,“主权在民”取代了“君权神授”,此时的政治仪式也不再局限于王权,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的总统誓词中就有着“以忠于国,为众服务…”的表达,此时,民本位成为了政治仪式的核心。时至今日,仪式仍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独有之物,只要以权力关系为内核的政治社会形态存在,政治仪式就不会消亡。王海洲在其著作《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中,借由2008年的“全国哀悼日”活动,对政治仪式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种政治仪式成为运作和维持国家权力系统,或者说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而塑造和维护了权力系统的政治合法性”[4]3。关于政治仪式的探讨始终离不开权力之眼,而从这一角度来说,政治仪式是利用象征性表达对仪式参与者的政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产生规范性影响,以此来维持权力秩序、整合社会并获取合法性资源的温和性手段。
宪法宣誓是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仪式,宪法宣誓仪式的完成不仅意味着就职者进行了角色的转换,还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新的权力身份。在西方,古希腊以城邦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要求每个官员在任职前都要进行宣誓,以保证他们执政的公正性。西方的宪法宣誓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作为英国最具有奠基意义的宪法性文件,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保障了一些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自由大宪章》第63条规定表明,英王约翰以宣誓的方式遵守《自由大宪章》,这被认为是宪法宣誓的首次实践。而宪法宣誓真正被作为一项制度写入宪法,则是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美国总统在就职前要公开对宪法进行宣誓,第6条则规定了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行政和司法官员的宣誓程序。在中国,君王登基时要祭祀天地,昭告天下,进行一套“应天顺人”的典礼,表明君王“顺应天命”的合法权力来源。而中国成文的宪法宣誓制度可以追溯至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誓仪式,1912年1月1日,许绍桢担任司仪,现场鸣礼炮21响,孙中山先生庄严而正式的宣读了总统誓词①,并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该宣誓仪式由此开辟了中国近代宪法宣誓的先河。1913年10月5日,《大总统选举法》颁布,这是民国最早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正式法律文件,在192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其中也做了总统就职时需宣誓拥护宪法的规定。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应有之义。从政治仪式的发展之路得以窥见,社会政治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从迷信走向理智,从神权走向民权。罗素在《权力论》中就指出,“人们对神的服从源于恐惧,服从神的意志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这种感觉会使许多不服从任何尘世之人的君主对宗教表示谦卑”[5]。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众不在受制于自然,宗教和神话逐渐得以祛魅,人不再服从于神,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崛起,对神的宣誓也逐渐演变为对法律的宣誓。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授予并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规范,宪法宣誓的兴起是我国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体现,也是国家民主法制进步的集中表现,宪法宣誓不仅表达了对宪法的信仰,更表达了对人权的尊重。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和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进步,国家机关也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的宣誓活动,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2014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6]。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对我国宪法宣誓的主体、誓词、组织者、程序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7]这不仅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8]。至此,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正式入宪,受宪法保障,宪法宣誓活动也在各地有序开展。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依托于宪法的法治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其中,宪法宣誓的权力来源也离不开这两个原则。宪法既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又是一种限制性规范,是授权规范和限权规范的统一体。[9]对于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而言,宪法的重要功能就是授予国家政府机构必要的权力,限制私权力,保障公权力。国家机构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作为公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则有必要在就职时宣誓忠诚于宪法和法律,以保证公职人员可以更加公正、合理的行使权力。人民主权原则又被称为主权在民原则,它所要解决的是权力来源与国家合法性问题。我国的1982年《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0]。正因如此,我國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公职人员对宪法进行宣誓的本质则是对人民宣誓,向人民负责。“政治仪式中流淌着对政治生活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权力,离开了权力,政治仪式将失去其生命力”[4]27。现代国家通过一套严格的权力授予和制约程序来使得权力合法有效的运行,宪法宣誓制度是权力授予程序的最后一环,该制度的作用是以神圣的宣誓对选举或是任命产生的权力转移结果做出最后的合法性确认。而宪法宣誓仪式作为公开性的权力转移的程序,是法治精神和仪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仪式本身则发挥出对参与者的影响作用,此时权力的合法性则来自公众的认可和宣誓者的认同,只有公众产生对权力的转移产生认可和拥护,权威才能得到确立,权力转换的合法性也才能得到最终的确认。
三、仪式展演:宪法宣誓的权力象征
(一)宪法宣誓仪式的符号象征
“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缺乏这种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1]12。象征的存在为仪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正因为有象征,仪式才能凝聚更深刻的意义。在部落社会的仪式中,图腾象征着神的旨意,这一象征将世俗的权力变得神圣化;封建中国的充满政治色彩的仪式中,宗庙为皇帝的权力带来了被视为“天命”的合法性;当代社会中的合法权力,也一样通过象征表现出来。权力表达的象征性能够显现的前提是符号作为仪式与权力的纽带,发挥出象征意义,符号可以成为权力的容器,通过仪式的展演过程,将权力象征显现出来。在传播学的领域中,就涉及到了符号权力的概念,“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11]。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系统将象征之林中的可象征之物一一赋予一定的意义,这些可象征之物在政治仪式中则成为了拥有权力色彩的政治符号,政治符号在入场时经过一系列的操演被编码,当符号到达了受众脑中,才会被受众脑中的政治解码器解码,在这一系列编码解码的阐释过程中,符号权力在被象征的过程中逐渐被接受。宪法宣誓中的象征符号颇多,从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来看,其中的象征符号有国旗、国徽、宣誓台、宪法这一类物质符号,还有誓词、国歌这一类语言符号,以及右手握拳、左手抚按宪法的行为符号。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庄严、肃穆的政治仪式,其中的象征符号具有强大的隐喻和暗指的能力,虽然这些象征符号有着具体抽象或是简单复杂之别,但它们都能够作为权力的容器,将其象征意义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二)宪法宣誓仪式的符号运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直接规定了宣誓场所要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国旗和国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象征,代表了国家权力,直接彰显了国家在场的政治意义,表明了宪法宣誓是在国家这一神圣形象的监督下进行的,宣誓人不仅是对宪法和人民宣誓,更是对国家进行宣誓。并且,国旗和国徽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出现于宣誓场所,是对宪法宣誓场景的神圣化渲染,使得宣誓人可以第一时间进入“角色”,浸染在神圣且不可玷污的仪式场景之中。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宣誓人需到宣誓台进行宣誓,宣誓台则是这一神圣场景中的另一重要符号,宣誓台起源于我国古代祭祀时期的“供台”,是我国古代祭祀仪式不可缺少的器具,宣誓台的使用则意味着更多的“展示”内涵,宣誓人走向宣誓台就如同表演者踏上舞台一般,首先迎来的就是如同聚光灯般的关注目光,在目光的集中注视下,仪式变得更加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带有万众瞩目的期待。宪法宣誓仪式中,宣誓台上端放着一本《宪法》,宣誓人需要左手抚按《宪法》进行宣誓,就如同美国总统就职宣誓需要手按《圣经》一样,《宪法》代表了宣誓人的信仰,此刻的这一本《宪法》,是我国宪法权威的象征符号,表明了宣誓人的权力由宪法授予,不仅表明了宪法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更彰显了我国的法治进步。
誓词是宪法宣誓这一政治仪式中最为重要的语言符号,誓词不仅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价值表达,可以直接展示出宪法宣誓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意义。《决定》同时也对宣誓的誓词做了详细的规定:“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在宪法宣誓的誓词中,“我宣誓”一词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将自我这一宣誓主体直接呈现出来。其中“忠于宪法”的誓词则体现了我国的宪法权威,表明宣誓人的权力由宪法授予。“忠于祖国”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表述,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忠于人民”更是表达了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决心。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举行政治仪式的必要之举,国歌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首先具有声乐的动情机理,在仪式中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象征,其次我国的国歌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能让奏唱者心中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让仪式变得更加庄严、神圣。音乐在仪式中常常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乐记》有载:“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一些音乐作品在诞生之时,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蕴,例如被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马赛曲》,作为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广为流传,1795年被确立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被暂定为国歌,2004年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国歌在宪法宣誓仪式的进程中,能起到振奋政治情感,进行政治动员、塑造政治文化的功能,从而为宪法宣誓这一权力转移程序塑造更加完善的仪式场景。
仪式通常具有表演性质,表演中除了场景和语言,行为动作也是表达仪式情感的重要部分。右手握拳和左手抚按宪法是宪法宣誓仪式中的行为符号,右手握拳进行宣誓的动作在我国一般的宣誓仪式中常有出现,学生加入少先队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成为共青团员也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需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可见右手握拳进行宣誓是我国一个一般化宣誓手势,并且常常带有政治色彩。左手抚按宪法这一动作则充分体现了宪法的权威,美国总统进行宣誓时右手抚按圣经的动作代表了美国民众的信仰,而我国宪法宣誓仪式的左手抚按宪法,代表的是对宪法的信仰,更是将宪法化作更加神圣的符号,代表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原则。
随着宣读宣誓词的结束,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也迎来了尾声,仪式中的物质符号、行为符号、语言符号共同建立起符号的编码作用,将其中所蕴含的符号象征整合到整体的仪式场景中,在仪式的规范进行中产生出“政治借喻”的效果,助力宣誓人完成其权力的合法性获取,宣誓人和观看仪式者通过脑中的解码器再对这一系列符号进行解码,从而起到唤醒政治情感,完成政治动员的最终效果。
四、仪式效果:宪法宣誓的价值认同
(一)唤醒集体记忆,加深民族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加深民族认同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2]。美国学者康纳顿在1989年出版的专著《社会如何记忆》中认为,“集体记忆的载体主要是口傳故事、物件、仪式与身体等”[13]。宪法宣誓仪式通过隆重而神圣的仪式表征,将参与者带入了仪式所构建的情感化场景中,具有国家形象象征的场景、奏唱国歌的行为,可以唤醒仪式参与者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集体记忆。记忆是“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14]。记忆既是个人记忆,也包括社会记忆,个人记忆是人脑对于过去生活的经验保存,社会记忆是一个社会群体对该群体过往的识记,中华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拥有民族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从教学、生活中塑造与刻写,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仪式被唤醒与固化。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宪法宣誓仪式,以现场直播的方式给亿万国民观看,庄严肃穆的会议被实时展现在国民眼前,在宣誓仪式的进行中,国歌作为能引起参与者情感波动的声音符号,唤起了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民族共同记忆,结合国旗国徽的祖国象征,可以刻写更加深刻的民族记忆,进一步加深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民族认同感,深化对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
(二)建立共同信仰,加深政治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建立共同信仰,提高政治认同的作用。宪法宣誓仪式的核心就是宪法,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对宪法进行宣誓,则是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信仰。宣誓这一行为本身就带了一定的神话色彩,充满了宣誓者的决心,更是一种对所宣誓对象的信任表征,古人有“对天起誓”的习惯,天对于古人来说就是高度可信的神圣之物,这建立起来的是对“神”的信仰。宪法宣誓的起誓对象是宪法,其建立起来的是对宪法的信任,是将宪法放到了神圣高度上,在此基础上,宪法宣誓建立起来的是人们对于宪法的共同信仰。随着宪法宣誓仪式的进行,宣誓者宪法信仰建立的同时,观看者对于宪法的信仰也会随着与宣誓者的共情而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共同信仰由此产生。 政治仪式中的人物、声音、器物、数字等符号从被选中纳入仪式展演实践中起,就成为了搭建信仰框架、推进政治认同的基石。宪法宣誓仪式通过一整套符号体系的展演,政治权力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政治意图悄无声息地附着在符号内蕴的意涵之中,借助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协调配适,有效调动起民众的政治情感,民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在这样一个意义互动的场域中得以强化或扭转,宪法宣誓仪式则用宪法作为共同信仰,加深了民众的政治认同。
(三)完成角色转换,建立身份认同
宪法宣誓仪式具有完成角色转换,建立身份认同的作用。宪法宣誓仪式究其根本是一个权力的转移程序,宣誓人在宣誓完成时即意味着完成了角色的转换,获得了新的权力身份。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接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必然会成为各党派和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权力的转移越是具有合法性就越能减少矛盾和冲突,越能降低权力转移过程中整个社会所承担的各种成本。权力的转移不仅需要程序上的合法,更是需要人民心中的合法,宪法宣誓这一政治仪式,拥有强大的国家象征符号,以及以宪法作为保证者及权力的授予者。在人类学家看来,象征能够产生一种抽象的想象力,让人们从内心认可这种权力的转移。宪法宣誓仪式中的象征符号,在此时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让人认可此时的权力转移程序,这种认可不仅是人民的认可,更是宣誓者自身对自我的认可,宣誓者在这一程序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并通过仪式的力量不断加深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此带来对自身权力的认同,只有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权力,宣誓者才能更有效的发挥权力的最大功效,真正做到对来源于人民的权力负责。
五、结语
我国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由宪法代为授予,国家公职人员需要对权力的授予者进行宣誓,保证对公权力的合法行使,宪法宣誓的本质是国家公职人员对人民通过誓言做的保证。而宪法宣誓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宪法宣誓制度中所规定的象征之物,这些象征之物组成了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权力符号,使得宪法宣誓仪式中的权力转移合法性可以得到国家在场的背书,誓词宣读是宪法宣誓仪式的核心环节和最后环节,誓词宣读的结束也就意味仪式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权力转换的合法性得到了最终的确认。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宪法宣誓制度和宪法宣誓仪式在价值认同方面共同发挥了作用,可以加深参与者对于国家、民族、宪法以及自我价值的认同,这也是宪法宣誓的价值所在。但是,宪法宣誓在制度规定和仪式实施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宪法宣誓是否是空有形式,是否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商榷。从制度的角度说,宪法宣誓的有关规定比较宽泛,只对宣誓主体、机构、誓词做了相关规定,具体流程细则并没有具体涉及,并且关于地方部门的宪法宣誓,也没有做具体的规定。从仪式举行的角度看,宪法宣誓仪式的受众范围较狭窄,能参与到其中的受众人数较少,难以起到普及宪法、增强宪法权威的效果,宪法宣誓所应发挥出的社会整合效果也难以实现。概言之,宪法宣誓在我国的施行时间较短,具体的实践也尚未成熟,但宪法宣誓作为比较典型的政治仪式,具有仪式的规范化、重复性的特点,并突出了仪式的政治效果,在仪式日复一日的演练过程中,宪法宣誓也将逐渐完善、成熟,公众也将在重复化的仪式展演中被其收编,达到国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所期待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13:142.
[3] 马敏.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J].社会科学论坛,2003(4):18-22.
[4]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5] 罗素.权力论[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10.
[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8-04-28)[2021-09-21]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28/content_2771714.htm.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EB/OL].(2018-02-24)[2021-09-21]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4/content_5268528.htm.
[8] 宪法宣誓入宪进一步彰显宪法权威[EB/OL].(2018-03-14)[2021-09-20]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1/ 2018/0314/c40531-29866393. html.
[9]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6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2018-03-22[2021-09-20])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803/e87e5cd7c1ce46ef866f4ec8e2d709ea.shtml.
[11] 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J].湖北社会科学,2008(2):171-174.
[1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
[13]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2.
[14] 恺撒·弗洛雷.記忆[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22.
责任编辑:叶民英
收稿日期:2021-10-13
作者简介:姜晨,女,云南楚雄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法治、传播伦理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