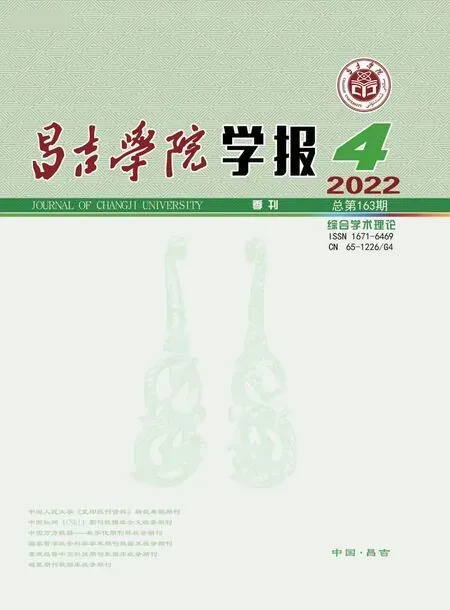悲剧愉悦:跨学科讨论语境中的多元视角
2022-03-24果玉
果 玉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引言
数据时代与生物技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认知模式与感知方式,在围绕审美机制与审美活动的探讨中,辩证的立场包括了对既有美学研究方向的批判和呼吁科学与人文的共融。刘旭光在《审美人文主义及其敌人》中以审美价值、思维方式与意义来阐释审美人文主义立场对校正美学研究方向的必要性。他认为神经美学研究将“审美”裁减为形式美感,将“美学”简化为愉悦的快感,将审美看作是神经性反应或是身体反应,不仅无视审美的人文性,还违背了审美活动的精神性,并将这种研究称为“本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对人文活动的入侵”。[1]胡俊在回应的文章中呼吁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贯通,在她看来审美活动是一般脑区与核心脑区共同加工的复杂的联动过程,而美感是集感性、理性与情感的智性愉悦,这种智性愉悦是结合自下而上的感觉体验与自上而下的意义调节所形成的综合机制。[2]斯诺提出弥补人文与科学“交流鸿沟”的解决之道已偏离其最初设想,实现二者之间有效对话的期许尚未实现。乔纳·莱勒结合当下语境认为,双方描述世界的语言仍旧是不对等或不通用的,莱勒尝试结合现象学与生物学建立“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会“自由地移植科学与人文,会专注于将科学简化的事实与我们真实的经历连接起来。”[3]234认知和阐释人类身心是人文探索与科学研究的共同分母,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架起了二者沟通的桥梁,那我们不禁要思考结合人文与科学的神经美学领域能否实现两种文化之间有效的对话。
构建范畴是人类本性使然,可以被视同主体做出判断和剖析意义的根基。在哲学与神经科学的视域下,始于审美活动的悲剧是在脑部各区域高效互动中认识人类与世界的逻辑思维及表达方式。悲剧愉悦不再仅仅依赖人文学科的视角来描绘自己的轮廓,科学性的发现也充盈着悲剧研究的理论景观,在“悲剧”这一审美范畴的照耀下,深描悲剧愉悦可以为我们探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提供范例。因此,更好的研究思路应是在人文与科学的交相辉映中,探索并诠释悲剧愉悦研究新路径的可能及其价值。
一、悲剧愉悦问题的哲学源考
悲剧展示并追问了人的此在与现实存在的哲学意涵。以雅思贝尔斯的话来说,即研究个人体验的“临界境况”达人之存在的“基本境况”。“悲剧愉悦”作为悲剧范畴的核心议题,照亮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之间一个重要的哲学链接点——“我们是如何从人类再现痛苦中获得愉悦?”围绕其所形成的思辨方式、基本设问与解决路径在不同学者的阐释中逐渐形成。
古典悲剧诞生于宗教与理性的冲突之中,“命运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秘索斯(mythos)和逻各斯(logos)之间强大的张力。”[4]6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5]63净化说使人作为一个亲历者投入悲剧之中去接受客观实在,但是卡塔西斯的原意,何谓净化历来是莫衷一是。卡塔西斯作为悲剧悖论的关键节点,对前者的把握可谓是理解后者的必要条件,穆尔从不同方面(宗教、医学、道德寓意、心理治疗等)阐释卡塔西斯的内涵,结合穆尔对卡塔西斯的分析及厄尔·沃瑟曼对悲剧悖论的梳理,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把握悲剧悖论的归属问题,从微观层面提炼悲剧愉悦的情感转换机理。
第一,从起源来看,源于宗教的悲剧与酒神崇拜联系在一起,与神契合欣喜若狂,在此意义上的卡塔西斯是指醉酒后的一种能够缓解恐惧与悲伤的迷狂状态。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卡塔西斯还可以被译为“净化”,指的是对含有罪恶之事的救赎。不同文化中都包含着本体论差异(如人/神,男/女)与规范性差异(如善/恶,真/假),当其中的界限含混不清时则被视为污染,以宗教中的仪式或献祭来“清除”污染,恢复宇宙秩序。
第二,治疗学意义上的卡塔西斯被译为“清洁卫生”,如类病类治的医学治疗原则,“强烈的感情可以通过用一种情感的调节性的管理而获得净化,之后就唤起一种愉悦的慰藉。”[4]138
第三,受柏拉图影响的基督教传统倾向于卡塔西斯的道德寓意——同情。在同情学说的拥护者们看来,即使在悲剧中传达出的情感是令人悲痛的,但也会因同情的运作及其社会效用,使人自然而然地感到愉悦。[6]417如奥古斯丁认为愉悦来自对悲剧英雄受难的怜悯,与别人分享英雄磨难以此获得愉悦体验。叔本华将怜悯与同情理解为一种积极的能力,同情唤起人类恻隐之心,“能够对他人的磨难展开移情与调试”。[7]艾德蒙·伯克认为真实的悲剧相比模仿的悲剧更为有趣,原因在于作为人类社会本能之同情才是真实目的,他建议剧作家的任务是接近现实,进而强化同情和愉悦。[7]道德哲学将悲剧愉悦放置在道德价值的运作之中,主体的道德满足感才是悲剧愉悦的根本原因,“将所有的激情都指向自我满足的欲望来决定这种情感是愉悦的还是痛苦的”。[7]最后,在心理学论域中的卡塔西斯经由笛卡尔的激情学说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雅各布·伯奈斯那里被视为“精神磨难的净化”,悲剧引起的强烈情感经由观众“宣泄”终获镇静与愉悦。在悲剧悖论的哲学解释中,从悲伤之情到愉悦之感必定是经历了某种推动和转换,这一推手则是卡塔西斯的“调节性管理”。卡塔西斯犹如意义集合体,肉体与精神的净化、清洁、救赎、解放、同情、利己、疏泄、模仿、实践等都被涵盖其中,正是在卡塔西斯的调节运转中,主体的悲剧体验实现了从悲伤到愉悦的转换。总体来看,上述学者们分别从客观认知和主观情感各有侧重的建构了自己的学说,悲剧愉悦问题使我们看到了这一议题立足点的多样和基本问题的开放未决。
“最丰富的审美体验来自与使人感到痛苦的艺术的接触,因为一个人很少像在艺术面前经历痛苦的情感反应那样,在智力、知觉和情感上完全投入。”[8]人们在悲剧艺术作品中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在此过程中人的智力、知觉和情感高度投入,愉悦则是这种高度投入的产物。对于悲剧审美体验中的愉悦,我们需要联合认知与情感使得此项研究更具系统性与深度性。对于悲剧愉悦议题,经典的哲学思辨与现代的美学论证为其在人文学科的更新带来了动力,也为神经科学理论框架提供了立论依据。朱光潜对哲学家们研究悲剧的方式颇有微词,他认为哲学家是将悲剧作为例证来证明先验演绎,缺少对作品归纳析解后的经验阐释,“哲学家有特权抽象地处理事物,但是把纯分析方法应用于精神活动往往有歪曲精神活动本质的危险。”[9]6随着历史进程的变迁,传统哲学对悲剧愉悦的析解已然不够充分,因此探寻一种更加贴合现实感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充盈美学研究空间,还能够对聚焦文学艺术、理解审美体验、塑造大脑认知提供思路。如今神经科学研究的认知积累已辐射至人文社会科学,由此诞生的神经美学一方面深化人类对自我生物基础的理解,另一方面将更多具有启发式的美学理论和洞察式的经验现象融入到自身理论的建构与验证之中。[10]6
二、悲剧愉悦问题的科学省思
正如加布里埃尔·斯塔尔所言,“审美体验之效果既可以是科学的精准详细,也可以是诗学的漫无边际。”[11]124神经美学是传统艺术哲学与美学之间的纽带,它为阐释文艺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搭建背景,对哲学描绘下的审美体验提供了补充。[12]探索悲剧审美体验的神经基础,既有助于阐明悲剧愉悦的机理,又可以发掘哲学与美学中重要概念对神经科学研究的中介作用,“哲学美学的概念中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一研究领域比前面所述的更加复杂:一个给定的美学对象往往为不同技能、不同背景、不同时间的不同人服务于多种目的。”[13]科学为美学理论补充客观性,认知科学为把握审美价值提供实验数据,在神经美学研究意义上得以拓展的悲剧愉悦开启了神经科学与美学关联路径的多样性,使对悲剧愉悦的探讨获得了综合的,跨学科的维度。
基于国外神经美学研究成果,胡俊对悲剧愉悦的阐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她主要以如下三条路径展开。首先,神经美学家瓦塔尼安的审美快乐理论认为,基本的核心感情作为审美中认识与情感的理论连接点,上承主体与客体利害关系的认知,与此同时激活了其后的情感体验机制。胡俊由此基础上思考悲剧愉悦的审美过程,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先是产生并确定了悲伤这一核心感情,经由审美主体情感的流溢,主体经历、记忆、想象、意义的再加工,结合后天有关世界、社会与文化的情感而形成的综合审美判断,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具高峰体验的审美愉悦。但是,胡俊对瓦塔尼安的理论构架有所保留,是因为他是依据已有的理论成果,还需接受神经美学实证检验。其次,神经美学家通过观测神经递质的方法来研究审美体验,在欣赏文艺作品时,人脑在激活奖赏机制的同时也会分泌多种神经递质,如内啡肽、多巴胺、五羟色胺等,进而产生愉悦感。胡俊借此理解悲剧愉悦,在她看来当我们在欣赏悲剧时,悲伤、痛苦、难过等消极情感体验会激活自我情绪免疫能力,释放人脑中如内啡肽等快乐神经递质,GABA抑制多巴胺,内啡肽的产生可以抑制GABA进而增加多巴胺引起兴奋,随后释放血清素归于安宁的愉悦。[14]最后,胡俊根据泽基教授的实验来阐释悲剧愉悦的发生机制,根据实验发现,悲伤在激活内侧眶额叶皮层时也激活了背外侧前额叶。我们知道内侧眶额叶皮层即美感体验区,而背外侧前额叶则是有关推理反思和意义判断的高级认知区域。“虽然最初从悲剧中感受到痛苦、恐惧、悲伤的不快感,但随着我们从悲剧中进一步体会到崇高的意义,我们通过消极共情也可激发审美愉悦体验。”[15]
综上所述,我们在审美体验中生发出的混合情感并非是大脑对某一刺激的历时性加工,而是源于大脑的智性运转,促使运转成功的则是数量庞大的神经结构与不同脑区的互动协作。悲剧愉悦是感觉知觉、情绪情感、动作想象、记忆加工、审美判断和奖赏机制等脑部各区域协调,动态交互的产物。在审美语境中,被称为是消极情绪的悲伤常常和积极情绪的愉悦联系在一起,目前神经美学主要以音乐和视觉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亟需关注。美学中的一些概念于不同时期经由西方正典的解构与重构已然发生改变,而与之相伴的对于审美体验与审美愉悦的诠释也在历史演化与文化演变中移宫换羽,神经美学需要结合当下语境提炼抽象的美学原理,更需要丰富的文学作品样本与详实的实验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美学和文艺理论批评提供更好的实证支撑。
三、认知与情感:悲剧愉悦的双向运作机制
加布里埃尔·斯塔尔以绘画、文学与音乐中的形象化为切入点搭建审美体验的神经科学模型,即结合神经科学的框架与文学艺术的批评理论,探索审美愉悦的体验过程与运作机制,重塑美学认知。愉悦作为悲剧审美体验的终端,本文试图结合斯塔尔建构的神经美学模型与西方的移情学说,从审美愉悦的发生机制入手来梳理并完善悲剧愉悦的认知与情感双向运作机制。
第一,多项研究表明相较于日常情感,审美情感更受认知的控制。在情感反应实验中,视觉艺术的情感反应与其他行为的情感反应有所区别。在审美体验中,被称为积极情绪的愉悦和消极情绪的不愉悦都表现出了大脑左半球的单侧性活跃。斯塔尔认为这项研究也许印证了“审美反应之情感只是名义上的‘消极’(例如,我们一般将悲伤冠之为消极)这一说法,那些被我们称之为‘消极’的情感在一种积极的审美反应语境中其神经评估或许会发生改变。”[11]38人类审美体验与审美反应是大脑运作机制与人类主观活动动态交互的产物,“深度审美体验使我们回到了静察的状态,守候核心意识特征的出现,我们还会在对某个对象的观照中产生一种愉悦的觉知,并对它的价值进行思忖与评估,或许深度审美体验综合了我们总是在期待的以及我们无法预料的东西。”[11]57深度审美体验能够产生新的神经评估与价值评价,其中包含着大量神经元的默认神经网络涉及到自我意识与经验、社会环境、他人心理等更为全面的认知与评估。我们在欣赏悲剧时多项通道参与其中,比如不愉悦的感觉、悲伤的情绪、对以往经历的联想、对悲剧情境的回忆和对人物的想象等,它们均参与了大脑的奖赏加工机制形成审美认知。参与深度审美体验的默认模式网络在悲伤情绪中,在不同脑区的动态交互下,结合高级的认知神经评估机制与积极的审美情感反应,将内在与外在、自我与社会、感知与评价整合为愉悦感,在悲伤的体验中发现悲剧本质、悲剧精神、世界秩序、人类存在等更为宏伟的意义。第二,形象化是通达审美愉悦的关键枢纽,我们是以感性的形象化理解不同的艺术形式与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既是视觉的又是具体化的动作,动作想象以具身模拟的方式体验他人行为。语言艺术中动作想象是核心,作者以文字实现形象化使审美主体获得生动的形象体验,我们能够紧跟悲剧主人公感官景象在形象化的感知中体验悲伤之情,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动态跨感官想象让审美主体产生联觉、移情、共鸣等体验,“动作的发生不仅是作为一种暗示或描述,而是一种感受,是我们的思维或肢体或声带中所伴随的一种合法的节奏韵律。这种联结所产生的愉悦感被编码进了动作想象之中,并分布于一系列形象之中,最终,我们是通过多种方式或感知模式将它们再次形象化、生发愉悦感。”[11]83作为人类有意识知觉体验,它是以具体的形象和象征来被读者理解,这个过程也是有“时间序列和意外的瞬间”,时间性是阐释悲剧精神意蕴的关键因素,我们能够紧跟悲剧主人公感官景象在形象化的感知中体验悲伤之情,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动态跨感官想象让审美主体产生联觉、移情、共鸣等体验,也正是形象化将悲剧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信息,情感体验与语义认识联合在一起生发愉悦之感。
雅思贝尔斯认为一部作品被称为真正悲剧的条件是主人公与观众都投入悲剧知识(悲剧性)当中,当二者双方融为一体,个人体验进入了主人公的“临界状况”,产生“自我置身于其中的存在的意义上的同情。”[16]49今道友信则将悲剧中的感动视作是同情,这种感动或同情使观众在悲剧中获得解脱与超越。[17]178正如前文所述,同情常常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而移情则掌握了道德与情感双重维度,迪萨纳亚克认为以移情阐释审美经验的身体现象是合理的,重要的是这种阐释要建立在以自然审美倾向为基点的心理生物学之上,“艺术作品在感知者的身上书写自身:即电化地写在由大脑皮层图谱构成的活动的信号模式中,它们也具有伴生的生理效果和动觉效果。”[18]259康德奠定了共通感的先天机制,如今我们能够依托大脑神经科学推进康德所谓的共通感,将悲伤与愉悦的共通感归因于人类的移情能力,分布在额下回布洛卡区、杏仁核及颖上回等结构中的神经镜像元使我们能够推断和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首先,移情关系到我们掌握他人思想内容的能力,以及预测和解释他们想法、感受和行为的能力。其次,移情与我们在道德上对他人做出反应的能力有关——使我们不仅能了解他人的痛苦,而且能以适当的道德方式作以回应。”[19]IX移情是一个复杂的模拟过程,在品读悲剧作品的过程中,审美主体可以模拟字里行间关于主人公的描述,将他人情境移入自我,体会人物生活与情感,可以模仿作者的创作过程与其产生共鸣。在自我与他者的分离,悲伤与愉悦的交织中倾听、理解、回应他人苦痛,沉思自我概念与社会价值,深思人类命运,这恰恰是悲剧艺术重要性之所在。
从神经美学角度来研究美学内部历来存在的经典性议题,不仅展现美学理论的延续性,也可以使我们梳理出这一经典议题在时间变迁中是如何被论证的。神经美学是备具现实价值的实证智慧,但其对文化性、个体性,多层意义的解读上略显不足。安简·查特吉认为感觉,情绪与意义作为审美体验的三大要素,只有前两者可以为神经美学所研究,要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蕴含作品文化意义的概念艺术进行研究是困难的。[20]143文学作品、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以不同的方式触动我们,通达文学艺术中的意义层面是需要审美主体去体验、欣赏、感受、理解和品鉴,在其背后牵涉到更为广阔的个人知识背景与社会文化价值。再其次,索尔索在分析艺术与语言的结构性质时提出的“第三水平的艺术”即汇聚艺术智慧的悟(感觉认知的“道”),这也被视为是一个人对艺术的更为高级的自我回应,从这个层面来说很难用神经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最后,神经美学的研究对象应更加多元。在迪萨纳亚克看来“神经美学领域的更好的目标是发展出一种综合的、高级的审美反应理论,该理论适用于所有被评价的对象,而不仅是艺术品(就这点来说,可以是风景或同伴)。”[21]44在神经美学视域中探讨悲剧愉悦充分展示了人文与科学的相互支撑与互相论证,但如莱勒所言,分割简化法与实验只能够对局部的问题做出阐释,人文学科对现实感知与现象阐释此种“最深层积淀”为科学的雄辩力提供了媒介,人文学科在阐述关于人类意识的独特性,主观体验的差异性与自我感受的私人性时则更为全面。
结语
人类深度审美体验发生于多感官的临界之处,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美学应该吸纳不同学科领域的成果,“范围扩大到涵盖‘感知’所有领域的超越美学的美学,不仅对于完全把握审美来说是势在必然,而且对于充分理解艺术也有着特殊的意义。”[22]137我们应该关注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演变发展,联结神经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多重论点,关注差异与区分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交界之域,结合理论与实践来理解悲剧精神及其价值,以跨学科的视野研究美学中的悲剧议题,为人类审美认知提供广阔图景。悲剧向我们传达出悲痛之感,在人类认知与情感双重作用下主体终获审美愉悦,结束对悲剧核心问题的探讨我们不禁要追问悲剧的意义,李泽厚将悲剧的实质引向创造崇高和激发人们伦理精神的高扬。区别于表象的美感,悲剧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引导式与启发性的审美,这归因于它用人类独具一格的感知力与想象力将人性囊括于形象之中,弥散于动作想象之中。宇宙秩序与人类本质在悲剧中得到了呈现与表达,宏大历史叙事总是在冲击着我们的记忆,诺拉认为能保留下来的只有所谓的“记忆之场”,能否将悲剧看作是悬置的“时间的岛屿”,视作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消逝的记忆场域,它以独特的意象系统表达宣泄与净化,以文本系统书写文化记忆与社会价值,这种书写融合认知与情感,表达伦理与道德,抒发记忆与创伤,其背后一切关于人类对生的向往和对美的憧憬被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