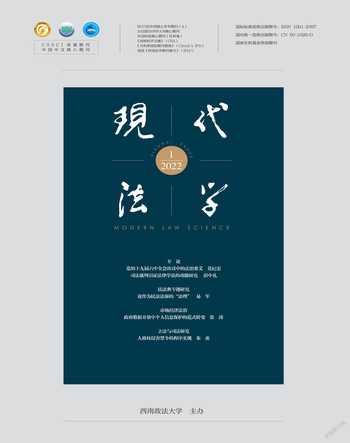“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2022-03-24王海军
摘 要:“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
关键词: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2.01.02
“法律监督机关”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新中国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监督职能的理解和认知,并在理论层面成功转化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法定化,1982年宪法则将其宪法化,最终成为中国宪法上的特有概念并沿用至今。“法律监督机关”自法定化以来,其概念内涵在各历史时期体现出中国检察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轨迹,但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宪法定位未变,机关职能所蕴含的“法律监督”属性也一以贯之,并在职能维度予以扩展,始终是国家权力监督机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机关”的概念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变化和衍生出的新内涵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今后人民检察院的职能范围和改革方向,因此,对“法律监督机关”概念的初始立法内涵、演进逻辑与内在机理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监督机关”概念的初始立法内涵
“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前,在理论层面上作为法学概念进行表述,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予以明确后方成为法律概念,其中所蕴含的立法内涵則体现出了“法律监督机关”概念演进的时代特性。
(一)“法律监督机关”的最初理解和运用
从人民检察史角度看,“法律监督机关”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检察院性质的表述。1950年6月,李六如在《检察制度纲要》中提到苏联检察“主要是政府的监督机关”,“实行法律上的监督”,[李六如:《检察制度纲要》,载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页。]而在《各国检察制度纲要》中则直接指出检察机关“主要是政府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制度》,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印行1950年版,第2页。]如此定位是基于苏联检察院拥有包括一般监督和司法监督在内的检察监督职能,将其理解为遵守法律执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监督机关,称之为“法律监督机关”。
此后,这个术语开始在党的文件和报告中使用。1950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九四指示”)中指出:“苏联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保障各项法律、法令、政策、决议等贯彻实行,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关于建立检察机构问题的指示》(9月4日),转引自闵钐、薛伟宏:《共和国检察历史片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可以说,中央对“法律监督机关”性质的认可释放出一种信号,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也应如此,而且开始将这一认定转移到对中国检察机关性质的确认之上,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如此。王桂五在相关论述中就提到,“1953年11月,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法党组在向党中央的建议中认为:‘检察署是法律监督机关,它检察所有国民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王桂五:《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在1954年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召开后,《人民日报》就此刊发的社论《加强检察工作保障国家建设》中直接指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工作。”[《加强检察工作保障国家建设》,载《人民日报》1954年5月21日,第1版。]可以说,在这两个层面的肯定,已经说明了“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在当时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监督机关”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中央的认同,但并未直接进入立法。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检察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其中第4条对人民检察院的职能予以列举,即“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以及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监督的司法监督职能。这部法律体现出了人民检察院职能的法律监督属性,但并未基于这种属性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予以明确。此后,在195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试行程序〉的说明》中明确提到“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关于〈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试行程序〉的说明》,载闵钐、谢如程、薛伟宏编著:《中国检察制度法令规范解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这部法律文件在性质上属于检察院内部的规章,是检察院根据当时情况对自我性质的认知,与立法上的认同具有质的差别,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法律监督机关”定位人民检察院性质已成为可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律监督机关”并未因中央文件的认可而直接反映在立法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学理论上的概念,因为此时检察立法重点是能够有效开展检察工作的检察职能,而非是检察机关的性质。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在立法中出现具有监督性质的话语已经为此后“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做好了准备。
(二)“法律监督机关”使用的争论与法定化
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对人民检察院性质的讨论后,新中国检察制度处于发展停滞期,“法律监督机关”的问题也失去了讨论空间。1978年宪法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但是由于这部宪法的过渡性质,对人民检察院性质并没有讨论,真正起到作用的是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也是基于这部法律再次进入讨论视野。
1978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有关事项的通知》,此后各级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恢复重建中开始工作。1978年12月,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召开了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七检会”),会上提出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但相关工作在之前已经启动。经过讨论和整理,1979年2月16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案〉的说明(修改稿)》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中明确说明了关于争议的最后意见,即“大家一致认为,在事关检察机关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拨乱反正,重新肯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性质”,因此在坚持原来各项检察职权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这个规定在6月12日送交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中依然坚持。这可以证明,“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人民检察院性质问题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已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统一,并认为可以成为立法条文。此后,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再次重申了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1979年7月1日,第1版。]这最终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中予以明确,完成了法定化的任务。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讨论,“法律监督机关”这个高度概括、凝练的法律概念正式获得立法层面的认可,体现了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的自我发展,“奠定了法律监督机关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机关这一基调,并且也奠定了法律监督机关要实行法律监督这一方向”[田夫:《什么是法律监督机关》,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第52页。]。
(三)“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后的初始内涵
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人民检察署性质的理解,检察体制恢复重建时期“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前的讨论,以及最终法定化的结果,可以证明“法律监督机关”已经成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并凸显出其重要的立法内涵。
第一,“法律监督机关”凸显了重视法律监督、重建法制权威的意涵。从前文所提及最高人民检学院对草案进行说明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是对此前否定法制的“拨乱反正”,并以此树立力全党全社会对法制的正确认识,是重建法制权威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打击叛国和反革命活动,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决非此前被指责和污蔑的“右倾”“矛头对内”和“官僚机构”。因此,人民检察院法定化为“法律监督机关”是重建法制权威的重要表现,并用以阐释人民检察院因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所具有的国家机关属性,明确了“法律监督机关”的时代内涵。
第二,“法律监督机关”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虽然源自列宁的检察监督理论,但是其最终定位为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结果。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经过立法草案的多次讨论,最终将法律监督界定在刑事犯罪领域,取消了“一般监督”。[删除了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和第4条规定,代之以“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统一实施的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因此可以认为,虽然“法律监督机关”在文字表述上与此前保持了一致,“但是在检察体制和检察职权上恰恰是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实现了重大意义的‘中国化’。”[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立法中取消“一般监督”和“垂直领导”,是否存在“一般监督”和“垂直领导”实质上并不影响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也不会影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这一终极任务和目标,因此,也不会影响到对人民检察院为“法律监督机關”的认定。可以说,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开始在制度架构上逐渐呈现出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的优势,最终形成了在职权和体制上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第三,“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为刑事法律监督机关。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镇压一切叛国的、分裂国家的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可见,1979年制定检察院组织法时,人民检察院的主要任务都是通过打击刑事犯罪来完成的,突出检察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角色。
从职能角度看,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五大职能:“(一)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二)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三)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于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四)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五)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可以说,“法律监督机关”是刑事办案机关,或者是刑事诉讼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倾向于刑事法律监督的情况在立法讨论时就已经认定。1979年6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对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督,只管严重违反政策、法律、法令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正草案〉的说明》,载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 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也再次提到,“检察院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1979年7月1日,第1版。]可以说,最后落实到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维度应为“监督违反刑法情况的机关”,其中主要的监督重点在于刑事侦查、刑事诉讼监督、刑事判决执行方面,缩小了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197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执行刑事诉讼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进一步规定了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更加明确了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的监督对象和范围。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在历史转型时期一种意义重要的立法表达,在自我发展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进行了中国化。从具体职能来看,“法律监督”职能回归人民检察院再次与“法律监督机关”互嵌,并在取消了一般监督后,开始朝诉讼监督方向发展,呈现出全面铺开成为一个整体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发展趋势。
二、“法律监督机关”内涵的演进逻辑
“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后,其概念内涵也在动态发展中不断演进。在“不变”中求“变”,坚持“法律监督”为核心话语,以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法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求为导向,不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凸显人民检察院的权力监督属性,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宪制基础,并将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具体化为履行广泛的诉讼监督职权的专门机关。同时,在整体权力监督体系下与监察委相互配合成为从事监督法律实施的专门机关,而这个过程也是“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变的逻辑进路。
(一)“法律监督机关”须为宪法规范的机关
经过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法定化,“‘八二宪法’‘接纳了’1979 检察院组织法在‘检察院性质’这一问题上的‘规范决定’”,[黄明涛:《法律监督机关——宪法上人民检察院性质条款的规范意义》,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4期,第19页。]首次在宪法中将人民检察院规定为“法律监督机关”,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及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宪法地位。鉴于法律监督职能是对公权力予以制约的职能,因此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属性必须由宪法予以规定,在以根本法方式强化监督职能的同时体现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也是人民检察院真正成为“法律监督机关”的逻辑起点。
第一,“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在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从立法措辞上来看,“法律监督机关”在1982年宪法中的表述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一致,“但并不是文字上的简单重复,从宪法角度讲,这意味着法律监督机关或法律监督成为了一个狭义的宪法概念,进而获得了允许宪法解释的空间。”[田夫:《监督与公诉的关系——以苏中比较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第47页。]一方面,延续此前对否定法制问题拨乱反正的任务,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和功能依然被重视,其中也蕴含着拨乱反正目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而且在宪法层面对“法律监督机关”进行表达和解释更加符合中国当时的政治法律要求;另一方面,与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法律监督机关”不同,作为宪法概念的“法律监督机关”已经成为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而非将其再以一个扩大化的概念予以无限扩展,其内涵需要结合宪法制度,尤其是人大制度进行考察和解释。
第二,“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履行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化提升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即确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宪法基础上的机关属性,在法律遵守和执行层面实施法律监督职能也具有了宪法高度。具体而言,“法律监督机关”是在人大监督下,具体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从监督职权维度看,人大监督是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被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职权和措施,是最高层次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与之相比较“存在位阶和性质上的差异,检察院法律监督权不得超越自身位阶,即法律监督对象不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的活动。”[秦前红:《两种“法律监督”的概念分野与行政监察监督之归位》,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73页。]在宪法中将人大监督与法律监督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体现出法律监督职能是宪法职能,人民检察院不僅是一个承担诉讼职能的机关,更是一个承担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机关;另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成为通过实施法律监督而具体落实人大监督职能的机关。因此,“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具有宪法地位的、专司监督除人大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和遵守法律情况的机关。
第三,“法律监督机关”是一种宪法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机关。在制定1982年宪法过程中,曾就人民检察院是否需要成为独立机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种说法认为,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纳入司法部;一种说法则认为,人民检察院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予以保留。当时,是否将人民检察院作为独立机关的宪法地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胡乔木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而修改宪法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汉斌则认为,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部门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张友渔和彭真对此也都同意。对于这个问题争论的最终结果,邓小平基于加强法制的需要,决定保留人民检察院,不与司法部合并。[参见刘松山:《八二宪法的精神、作用与局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4-75页;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这最终也决定了1982年宪法中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实体独立性。应当注意的是,1982年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行使法律监督权”,这可以表明人民检察院是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法律话语中特有的概念,因此了解这个需要从中国语境出发。对此国内学者就指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一种全称判断概念。”[韩大元:《关于检察机关性质的宪法文本解读》,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第13页。]在宪法之中定位“法律监督机关”,实质上是将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赋予了人民检察院。
“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化提升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其法律监督职能也成为人大监督的一种延伸,成为宪法职能并逐渐朝具体化方向发展,“法律监督机关”也不仅是一个承担诉讼职能的机关,更是一个承担宪法职能的机关,成为了具有宪法地位、人大制度下的专司法律监督的机关。
(二)“法律监督机关”基于宪法职能侧重诉讼监督
1982年宪法为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奠定了宪法基础,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也是基于“法律监督”职能为主要面向的表述。如前文所述,“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后的监督职能主要集中在刑事领域,但基于整个诉讼活动对司法公正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功能,法律监督职能必须与整个诉讼制度相互依托,由此“法律监督机关”的概念内涵也随着诉讼制度改革而更加细化,并由在宪法框架下履职而具体为监督整个诉讼活动的机关。
第一,“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有广泛监督范围的机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最早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也是诉讼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由于当时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如何参与民事诉讼的看法不尽相同,检察机关内部的认识也不统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序等内容。”[王玄玮:《中国检察权转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这也导致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民事诉讼领域呈现出一种概括性的内涵。
1991年,在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基础上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新规定,这无疑充实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内涵。同时,其中并未限定抗诉的范围,但是据研究表明,1995-2003年之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九个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不予受理检察机关部分抗诉。[参见王玄玮:《中国检察权转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人民检察院通过法律监督进行抗诉一定程度上是受限的。2007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将抗诉情形由四项细化到十六项,夯实了“法律监督机关”在抗诉领域发展的基础。
2012年,《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将法律监督对象从“民事审判活动”修改为“民事诉讼活动”,这样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监督从审判监督拓展到民事执行监督和民事调解监督,并相应增加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条款,抗诉的对象也在判决和裁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调解书的抗诉,同时增加“检察建议”这种监督形式。按照当时的规定,“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2009年11月17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1条。]《民事诉讼法》经过几次修订后,逐渐充实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外延,扩展到了抗诉、二审、审前、审后、执行和调解监督,从很大程度上使得“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在民事诉讼领域拥有广泛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
第二,“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在行政诉讼领域加强对公权力监督的机关。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领域的法律監督职能的正式确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其中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具体包括对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的抗诉。这奠定了“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诉讼领域具体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基础,并通过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强了对行政权的监督,拓展了对公权力的监督范畴。2011年,两高会签下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对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职权做出了协商性补充,即“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申诉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有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人民法院公正审理的行为,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并将相关情况告知人民法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1条。]该意见使得法律监督职能再次得到延伸,“法律监督机关”的全面性也逐渐显现。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中提出了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之后的《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对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执行的监督适用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参见2014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这使得法律监督在行政诉讼领域得到了一个质的发展,并使人民检察院成为一种对行政机关及其权力行使进行外部监督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三,“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将法律监督职权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机关。相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的法定化迟一些。在196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中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法院审理公诉案件的当庭监督、以抗议形式规定二审监督和再审监督,以及对刑事判决执行的监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第132条、第156条、第183条、第199条。载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41-449页。 ]但这部法律当时并未提交审议,因此也没有成为最后的正式立法。
1979年,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同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二审抗诉、再审抗诉和当庭监督的内容,这才使得刑事诉讼领域的法律监督被被正式确立下来,但是并未使用“法律监督”的术语,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没能在这个层面上体现出其概念中的内涵。首次将“法律监督”作为法律条文写入刑诉法是在1996年,即“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相关条款的规定,包括了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同时废除了当庭监督。这个时候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职能维度发生了变化,即审前、审后监督。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并在这个目标指引下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的一系列法律监督强制性措施。具体内容包括:对申诉或者控告的审查,对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简易程序案件和再审案件派检察员出庭,增加了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完善了对执行活动的监督,呈现出了一种法律监督贯穿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的态势。这充分表明立法者对刑事诉讼监督的高度重视,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责任,在从法律监督职权维度强化了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
此外,检察机关也将法律监督的视野拓展到公益诉讼领域。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全面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据此决定,《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7年6月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中央高层配置给检察机关独有的诉前行政违法监督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法律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增加第25条第4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上述修改内容来看,公益诉讼扩大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功能,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的属性更为凸显,从之前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涉及的法律进行监督开始将其内涵在诉讼领域得到进一步充实。
在诉讼制度持续改革下,“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职能维度不断扩充,已然成为了在诉讼、执行方面实施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推动了对“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发展。
(三)监察体制改革下“法律监督机关”的自我更新
监察体制改革体现了对腐败的打击和公权力的强力监督的法治意愿,为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在整体上的重大调整。《监察法》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被划转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相应得到了修改,人民检察院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动。同时,在坚持法律监督宪法职能和性质宪法定位的基础上进行了职能整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专门监督意义的国家机关。
第一,夯实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2018年,在宪法修订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了自1979年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修改,但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和宪法定位并未改变,其目的依然是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完整和统一的实施,在全社会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同时,检察院的职能需要调整定位,但实质上此时的人民检察院的使命和职能比单纯的反腐败要广泛得多,意义也更重大。这样,“法律监督机关”的内涵也再次明确了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完整而统一的实施”的机关,夯实了“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
第二,推进了“法律监督机关”向着专门化机关的方向发展。职务犯罪侦查权此前归属人民检察院行使时,在中国语境下起到一种独特的震慑效应,被认为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能够产生应有效果的重要保障。但同时,“职务犯罪侦查的存续却形成了反噬效应,严重削弱了法律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李奋飞:《检察再造论——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为基点》,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33页。]职务犯罪侦查权转归监察委后,人民检察院一定程度上将其职能集中于专项的法律监督领域,突出了“法律监督機关”职能的专属性,更加明确了其监督属性的内在意义:一是除对刑事侦查、审判、执行的监督权予以进一步确认外,对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予以授权,针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对法律监督的范围进行了适当和必要的扩展;二是法律监督方式和操作性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确认了检察调查核实权、相关案件侦查权、补充侦查权以及“抗诉”,“提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逐渐成为主要的监督方式;三是法律监督刚性得到加强,有关单位应当及时将采纳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的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应当说,人民检察院在弱化侦查层面职能的同时,提升了在诉讼领域的监督话语权,法律监督职能在进入司法程序后更为突出。可以说,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了各自的重要性和针对性,能够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这样,剥离了职务犯罪侦查权后的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司法属性更加明显。同时,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在人大监督之下,成为整个监督体系中的一个元素,只不过其特殊定位更加凸显其监督职能中的法律色彩,使得其能够成为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三,成为与监察机关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法律监督机关”。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在监督职能方面均具有权力监督属性,监察委取代检察院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进一步厘清和划分了检察院和监察委的职能,并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监察委具有的监督职能,此举符合“法律监督机关”本身监督职能所具有的理念性目的,因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权力监督改革,这一改革的制度逻辑实际是将权力监督的分散格局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机构内部。”[段瑞群:《监察体制改革下的检察机关“主业主责”》,载《时代法学》2020年第3期,第82页。]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规定的“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内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会介入监察监督行为,并引导和配合监察委的调查取证工作,二者的工作关系也体现出了法律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内在互补性。一方面,监察委需要将涉嫌职务犯罪的对象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也可通过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对监察机关移送来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必要时的自行补充侦查和决定是否起诉,[参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66-67页。]实现了法律监督对监察监督的适当补充;另一方面,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过程中也会将违纪贪腐的线索移交给监察委,监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和职能划分基础上通过行使监察监督职能完成法律监督所不能实现的监督行为,形成了监察监督对法律监督的“接力”。这样,二者在行使各自监督职能过程中形成了配合机制,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互相制约的运行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的解释,两个机关在协调合作中进一步形成监督合力和配合机制,更加符合“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内涵。
在监察体制改革下,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并未改变,对侦查权、行政权和诉讼活动依然有监督的权力,在职能方面发生的变化逐渐将其主责主业明确和集中,“法律监督机关”的内涵得到了深化。
应当说,“法律监督机关”在其演进过程中,职能维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为基础,逐渐成为承担广泛诉讼监督职能的机关,并成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实施法律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但并非是一种单项演进,而是具有叠加性的,与各个时代的政治、法制发展互动,在完成自身内涵发展的同时也反作用与相应阶段的政治与法制,形成了两相契合状态。同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以及行使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基本功能始终未变,在国家权力监督机关体系中的作用也未变,基于特有的监督范围和监督手段成为了无法替代的专门机关,实现了维护法制统一和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对公权力的制约。可以说,以上所阐释的“变”与“不变”体现了“法律监督机关”内涵的演进逻辑。
三、“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演进过程是围绕着“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和“法律监督”宪法职能展开的,外在表现为立法条文的体系化和监督职能的具体化,而背后则蕴含着演变的内在机理,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化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之于人民检察院行使包括法律监督在内的检察权的制度必然,诉讼监督职能的强化和细化则是落实宪法规定“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在监察体制改革下检察职能的变化则是“法律监督机关”参与宪制层面上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一)人大体制下的权力分工模式的制度必然
1982年宪法是一部致力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法,“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机关的框架”,[刘松山:《八二宪法的精神、作用与局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0页。]提高了人大的地位和权力,并在宪法中通过构建各种宪法制度予以支撑,结合人大制度在宪法层面予以解释和言说,而“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实现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的必然选择。
第一,“法律监督机关”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支撑人大制度良性运行。1982年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为“法律监督机关”,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宪法意义的国家机关,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人民检察院性质予以确认,但绝非单纯是以一个静态宪法条文对检察机关性质予以定位,而是国家民主政治层面的一种宪制设计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国家机关方面支撑人大制度的完善。当时中国的改革发展也使得1982年宪法在基本权利、国家机构、宪法实施制度等方面都体现出新要求,而其中国家机构相关条文是很重要的部分。人民检察院作为人大制度之下“一府两院”设置中的重要国家机关,其所行使的法律监督职能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其性质依然停留在组织法层面就无法在宪法层面上与人大制度形成统一,在理论上专司“法律监督”的国家机关应当被容纳于被改进和发展之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参见王桂五:《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205页。]因此,将“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宪法化,使得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之下的主要国家机关之一的专属指称,并开始在作为宪法概念、宪法层面上的国家机关予以解释就成为必要,其所具有的宪法意义也就相对清晰了。
第二,人大最高监督职能具体化的要求。根据1982年宪法的规定,人大具有“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权,这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对一切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监督权,这符合中国政治制度中权力一元论的价值取向。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角度看,虽然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已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为“法律监督机关”,但在没有获得宪法确认之前,其所行使的法律监督职能也仅为其自身内部属性的,即便在人大制度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也无法通过宪法进行对接。人大作为权力本源层面上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全面法律监督与局部监督之间存在间隙,在覆盖全领域范围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对具体对象的监督,而“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化使得法律监督职能与人大制度在宪法层面上得到了结合,人民检察院在人大监督为最高监督的理论基础上,成为被授权的具体履行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机关,以法律监督作为人大监督的分支监督具体实行。
第三,通过国家权力分工保障人大制度的良性运行。1982年宪法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通过权力分工来加强和发展人大制度。在1982年宪法草案讨论阶段,彭真就加强和发展人大制度方面指出了包括人民检察院在内的国家机关“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各有分工,各司其职,都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这样,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行使,将使我们的国家比过去更能经得起风险,更能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王桂五也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是专门职司法律监督的国家机关,这是由我国所实行的人民大会制度的整体所决定的,也是检察机关于其他国家机关在职能属性上的区别。”[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因此,人民检察院的具体职能行使应基于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根据国家权力分工承担的工作任务围绕法律监督职能展开。可以说,基于人大制度的发展,在进行权力合理分工的要求下,人民检察院被定位为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所蕴含的人民民主专制体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理论与国家权力理论,人大监督权力产生了檢察机关的监督权力,二者形成抽象与具体、授权与职责、监督与负责的关系。[参见姜伟:《中国检察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在这个框架下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了维护国家政权的重任,维护实现人民权利的使命,为人大法律监督提供条件和依据,并且通过自身的监督活动使具有最高监督性质的人大监督落在实处。[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二)强化诉讼监督是落实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重要选择
在“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化后,与之相配套的诉讼制度并未同步改革,因此并不能完全按照宪法规定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随着诉讼法将法律监督职能融入其诉讼环节之后,“法律监督机关”在诉讼监督领域的角色愈发重要,尤其在取消了一般监督后,法律监督的主要部分就是诉讼监督,依据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定位和法律监督宪法职能的肯定,在诉讼领域发挥法律监督,强化诉讼监督也就成为必然。
1996年《刑事诉讼法》废除当庭监督后,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审判活动顺利进行,最大程度消除监督对审判活动干预的弊端,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运行。这不仅是与宪法中对人民检察院为“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的呼应和落实,也是为了与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保持一致。在2004-2008年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第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强化了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了民事抗诉制度,诉讼制度改革也加强诉讼监督的要求。2008年以后,“各地检察机关加强了诉讼监督工作力度,积极向本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诉讼监督工作,全国掀起了一波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热潮。”[王玄玮:《中国检察权转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在2008-2011年之间,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诉讼监督的决定或决议。这体现出了诉讼领域对法律监督的需求,也体现出检察院要将法律监督进一步拓展的发展需要。具体而言,“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监督领域更加有利于保护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合法权利,追诉犯罪分子。加强了抗诉权层面法律监督职能,同时也扩充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维度,使“法律监督机关”内涵在职能范畴内得到加强。
2012年,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抗诉职能进一步扩大,此种变化的理由在草案讨论中也已经提及,即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的说明》指出:“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对民事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活动能否实行检察监督。针对执行活动中一些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建议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同时,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出抗诉。”[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的要求。这不仅再次强调了检察院在诉讼领域的监督,尤其是加强了行政诉讼的监督方式。
公益诉讼制度也是丰富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内涵的一个重要表现。尤其是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决定》中提出:“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此种提法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双方很难达到平等,行政相对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并不利于司法公正,也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对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施十分不利。因此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人民检察院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法律监督,将“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扩展到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方面。
基于对诉讼领域加强监督的目的,人民检察院在诉讼领域法律监督职能逐渐扩张和完善,使得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更加明确,也使得其内涵在诉讼领域具体化,朝着法律监督方向发展和靠拢,更加符合“法律监督机关”的宪制内涵和价值。
(三)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为保障作为国家宪制层面的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确定对于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负责调查的职能,对人民检察院的侦查职权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必然之举。权力监督并不能依靠单一的监督机关实现,因此,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督体系的以此重整,并以此形成主体多元化的监督体系,彼此之间相互配合最终完成权力监督的目标和任务。在监察体制改革之下,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没未发生变化,但在监察委具有一定监督权的基础上,“法律监督机关”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开始被讨论,其内涵也随着相关立法的修改发生变化,其内在机理就是人民检察院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为配合监察体制改革,以及使监检衔接和配合得更加默契,2018年10月28日,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继续肯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20条再次明确了检察院的职权:“(一)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二)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三)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持公诉;(四)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五)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六)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七)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八)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上述职权再次说明了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该维度的价值并未改变。
根据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其报告工作,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下,与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人民檢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并没有改变,监察委员会取得职务犯罪侦查权后,再加上对公职人员违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权,取得了远比此前检察院更大的监督,这一个刚性权力的转移给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带来了改变,但是同时也是以其他方式改变了监督方式,因为它对监察委的活动依然存在制约关系,这也是其法律监督的一种方式,因此监察委并没有取代检察机关成为了“法律监督机关”。
监察委和检察院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规定符合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也意味着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需要受到检察院的制约。因此检察院在监察体制改革之下,进一步也形成了对监察委工作进行监督的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制约具有外部监督的性质”[朱福惠:《论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的制约》,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14页。]。“法律监督机关”的内涵显然远远超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范围,而且“从我国的法治监督体系观察,监察机关的全覆盖监督与检察机关等监督的适度交叉,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尹吉、王梦瑶:《新时代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制度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37页。]。
“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的演进是随着每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政治法制改革要求为导向进行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范围不断具体和明确,并逐步加入了新的元素,在现有立法基础上,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在“法律监督”的核心职能基础上遵从其演变的内在机理继续发展。
结 语
在“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演变的几个阶段,实质上都是通过加强法律监督职能,在“法律监督”这个场域完成自己的组织性质和概念内涵的阐释,最终形成了一种宪法意义上的,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施、在人大监督之下,并与监察委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行使审前监督、侦查监督、诉讼监督、执行监督的专门机关,这是人民检察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创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检察机关主动进行适应性改革,在“四大检察”格局下设置“十项业务”,法律监督职能融入了新理念、监督精细化、全面协调发展,并在各个监督领域相互延伸,体现出了“法律监督机关”时代特色的新内涵,如果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观察,这其实表现出了党领导的百年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凸显出党的运用法治方式治理和领导国家能力不断增强。[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3页。]当然,“法律监督机关”是一个扩展性很强的概念,其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政治改革、司法改革的需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义检察理论的范畴之内继续发展,如果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定位不变,那么它就会朝着加强监督职能的方向发展,在更为宏观的权力监督体系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特位置,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础上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The Legislative Content, Evolution Logic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WANG Hai-ju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Legal supervision organ” is the nature orientation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 China’s Constitution. The enactment of Organic Law of the People’ s Procuratorate in 1979 for the first time confirmed the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statutorily, the legislative connotation is to focus on rebuil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legal system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law. It is an organ form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rocuratorial theory, focusing on the task of criminal litigation supervision and cracking down on crimes. The 1982 Constitution made the "legal supervision organs" a state organ on constitutional norms,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functions an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litigation supervision, under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t has conducted self-renewal and become an organ that cooperates with the supervision commission to exercise the legal supervision functio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organs"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division of power mode under the system of NPC, the important choice of carrying out the legal supervision function stipul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is malleable, and will derive new conno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long with the legislative revis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onstantly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st procuratori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eople’ s procuratorate; legal Supervision;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the Organiz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本文责任编辑:龙大轩
青年学术编辑:梁 健
收稿日期:2021-12-01
基金项目:2021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重点课题“90年人民检察发展历程与启示”阶段性成果之一(GJ2021A01)
作者简介:王海军(1983),男,黑龙江绥化人,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