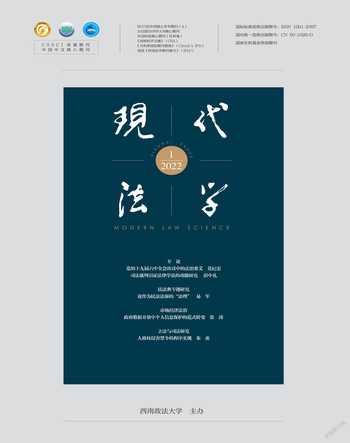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三论
2022-03-24屈茂辉
摘 要:基層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在《民法典》中被定位为特别法人,但性质上应属公法人,一是其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二是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 “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三是财产来源的公共性。其章程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而实际法律化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即为法律性章程,主要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同时,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而且,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受其“职能”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与监护人能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也不宜被赋予破产能力,除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外,不能为他人提供担保。
关键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公法人;法律性章程;民事能力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2.01.11
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我国1982年《宪法》首次确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包括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①虽然自1982年以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直在我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是否应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立法上一直不明确。现行法律中涉及居民委员会的约有45部,涉及村民委员会的约60部,都没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规定。就实践来说,截至2019年10月15日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显示,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作为当事人的民商事法律文书分别有430-130份,其中涉及村民委员会的约有38万份,且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也许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回应,作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第一步的《民法总则》首次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两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明文规定为特别法人之一[ 王晨指出:编纂民法典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第6版)《民法典》第10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法人和村民委员会法人这两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人资格,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可是,《民法典》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规定仅有一条(两款),规定还是过于简约,如何在《民法典》实施中准确把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性质、章程、民事能力等问题,以促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值得深入研讨。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属性
《民法典》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定为“特别法人”之一,即表明其既不是营利法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法人。[ 从逻辑学而言,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即能涵摄法人的全部类型,《民法总则》在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之外另行规定一类“特别法人”,即表明《民法总则》所言的“非营利法人”仅指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法人,而将本也为“非营利法人”的四种特别法人独立成类。]而从民法学界关于法人最基本的类型区分来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究竟是公法人还是私法人,似乎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公法人属性应当十分明显。[ 关于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划分标准,学者间见仁见智,不过“设立行为、目的和法人以何种身份出现”乃较为有力的观点。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30页。]
首先,成立依据的公法性。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民法典》之前的法律文本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不是民法上的概念,也不是当然的民事法律主体。虽然《民法典》第101条确认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法人,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立的主要依据是《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经由基层人民政府主导成立的,其作为民事主体客观上早就先于《民法典》而存在。也就是说,尽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法人是经《民法典》才得以确认的,但其成立所依据的并不是《民法典》,而是《宪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典型的公法,依据公法成立的法人当属于公法人。此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产生与撤销受到较多的法律规制与行政约束,如“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中指出:“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调整国家政治关系,主要包括……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从实际情况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具体组织法,是《民法典》这一条两款之外的法律依据所在。因此,按照公法人划分的法律调整依据说,村民委员会法人、居民委员会法人属于典型的公法人。[ 据笔者了解,其实,在比利时公法人和私法人在涉足市场时所遵守的法律法规并无差别,除非公法人有特别规定即依其特别规定。一般公法人、公务法人(Public corporate)在国家控制下行事,但只要他们进行经济活动,仍受制于公司规则。参见Gérad Marcon,Les Mutations Du Droit de L’administration en Europe, Paris: Editons L’Harmattan,2000,p.313.]
其次,目的上的公益性。“公法人具有行政组织属性,享有固定之任务、职掌、管辖与权限”。[ 秦奥蕾:《〈德国基本法〉上的公法人基本权利主体地位》,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8页。]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然不是行政组织,但其目的乃是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宪法》(2018)第111条。],以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2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2条。],即通过履行一系列管理职能以实现公法人“服务于公益”这一职能目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活动范围限定为只能“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可以理解为其民事活动是以辅佐履行职能为限度的,开展民事活动不是其原本的目的(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我国直到2017年才确认其法人地位的缘由)。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目的上具有公益性。
最后,财产来源的公共性。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财产来源比较复杂,既有“筹集”又有“上级拨付”,且“上级拨付”的现象相当普遍。所谓“筹集”财产是指村(居)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社区)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向本地村(居)民自愿筹集。[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16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37条。]“上级拨付”的经费即国家财政支出,具备公共性,这是公法人的特点之一。笔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财产几乎就是上级拨付的经费,筹集的财产占比极小。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属于经常性的财产来源。村民委员会开展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工作时,一般由该委托部门承担经费,在经费确有困难时,可由地方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属于非经常性的财产来源。[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17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37条。]对于村民委员会而言,其在设立时并没有“独立的经费”,尽管可以管理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8条第2款。],但集体土地毕竟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财产而不是村民委员会法人的财产。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法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在我国农村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发布的《深化農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指出:“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交织,构成了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撑。”并且强调“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在《民法典》颁布之前,虽然二者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法律上都不明确,但依据基本法理,村民委员会属于公法主体,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源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具有民事主体的身份,但由于1982年以后随着乡镇人民政府的恢复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许多地方没有得到相应恢复,法律上允许村民委员会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而管理财产。[ 《民法典》第262条第1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8条第2款。《民法典》第101条第2款规定:“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现在看来,依据《民法典》第99条和第101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法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是两个均属于特别法人但却彼此独立的法人,都属于民事主体。从性质上而言,村民委员会法人则属公法人,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属私法人,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本质区别。[ 戴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制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第85页。]
特别需要澄清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民法典》确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地位以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唯一身份就是民事主体。如前所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原本仅为宪法关系主体,只是基于中国实践而作出的重要制度创新——将原本不为法人的组织明确为法人,以回应社会之需。这个源于法人制度功能路径的制度创新[ 关于我国法人立法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歧,参见张新宝:《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 基于功能主义的法人分类》,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4期,第16-34页。],为世界法人制度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但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人化并未否认其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固有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它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身份,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 这种现象对于机关法人而言也是同样存在的。]作为公法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具体主体,它既不是国家机关的下级组织,又不从属于居民(村民)居住地范围内的其他任何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基层群众组织。作为私法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其成立之日起即具有特别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章程法律化
按照法学界的一般理解,法人通常是需要章程的。[ 诚然,我国机关法人等诸多公法人都没有章程,但这不能作为否认法人当有章程的理由,恰恰是我国未来法治建设应当加强的一个领域。]“章程者,法人之组织也。”[ 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社团之章程为社团之宪章,系社团组织实现其目的之准则。”[ 刘清波:《民法概论》,台北开明书店1979年版,第58页。]团体作为主体的存在,其章程的地位是基础性的。没有章程,由众多人组成的社员只能是一盘散沙,无从形成统一的意志,由此也不能形成独立的法律人格。故而有学者把它称为社团的“行为要件”。[ 郑玉波:《公司法》,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而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虽然章程并非法人的法定要件[ 按照《民法总则》第58条的规定,成立任何类型的法人均须具备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这四个要件,法律、行政法规如果有特殊规定则依其规定,如公司法人、基金会法人的成立除了上述四个要件外,还须具备章程。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02页。],亦即有的法人可以不需要章程,但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而言,其章程体现为法律形式,而无须另行制定章程。[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像机关法人没有章程,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对各类机关都制定了“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该类规定性质上属于“软法”。此外,还颁布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已经涵盖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所需内容,实质上成了村(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章程。一般来讲,法人的章程应包含法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费和组织机构。具体来看,村民委员会法人的组织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二章“村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第三章“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第四章“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中均作出了规定。居民委员会法人的组织机构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7条至第14条中有所体现。村(居)民委员会的经费问题也分别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37条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17条予以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名称和住所均根据其所在地的村(社区)名称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而定,无须额外规定。法定代表人即村(居)民委员会主任。可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应当具备的法人章程内容,均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得到了体现。
其次,除去两部组织法,还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予以规制。国务院的相关部门规章中都有专门调整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某一方面行为活动的准则,如《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印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规范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等。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也普遍存在这类规范,如辽宁省的《本溪市村民委员会建设若干规定》、上海市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等等。
最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章程法律化是其必然选择。[ 我们可以将这种方式存在的章程称之为法律性章程。]其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层性是其治理复杂性的原因之一。自古以来,王权止于县政,直到民国时期,行政权力才从县级下沉到乡镇级,诸多规定会因为相对复杂的乡村自治而得不到执行力上的保障。法律性章程比一般私法人章程多了“强制力”这一执行力保障,能确保基層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的实现。传统的私法人章程具有较强的意思自治性,以“权利”为基础来构建法人的机关及其权利义务,而且经过董事会提议还可以通过股东(大)会修改章程。公法人则更需要突出公共性,若不以法律性章程为准,则可能会因内部成员的私利或其他缘由而导致章程无法履行,从而影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目的实现。其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成人员(居民委员会由5至9人组成,村民委员会由3至7人组成)本身并非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发起人,而是依法定程序由村民或居民选举来的,是在该法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的本区域的自然人,具有一定意义上公职因素。与因内部股东人数众多而需要拟定章程的大多数私法人(如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其股东会成员均为法人的设立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一般是股东或者股东的代表[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存在独立董事或者外部董事制度,他们不是股东。],只有经理层才是聘任的。可以说,只有法律性章程才能解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自治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三,法律性章程能够克服自治性章程的固有弊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组成人员是经过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虽然具有较为出众的人缘关系和领导能力,但是其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在目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治理能力较弱的现实状况下,如果实行自治性章程制度,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村规民约中得到印证。村规民约是被诸多村民奉为“小宪法”般的存在[ 陈忠实所著的《白鹿原》中就有约束原上族民的“乡约”,由原上的年长之人和饱读诗书之人共同拟定,询问老家在偏僻山区的友人,也证实了现如今仍存在此类乡约。],大多数村(社区)都有自己的村规民约[ 如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新河乡十三刀村村委会、鲤鱼鳃村村委会等均有“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村规民约,就婚嫁、丧事等人情酒席做了限制规定。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玉潭街道花明社区居民委员会除居民公约外,还有单独的“红白理事章程”。],但是,绝大多数村规民约,并不涉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的成立、职权、监督等内容。这些村规民约的条款主要涉及建房、土地征用、环境保护和婚丧喜事人情活动的限制规定。如湖南省华容县十三刀村等村委会的“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村规民约,总共17条规定中有10条是处罚性规定。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居)民委员会的一般规定、村(居)民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村(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村(居)民会议和村(居)民代表会议、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作了较为详细规范的框架下,即使个别地方的村规民约对村(居)民委员会有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也只能是在法律框架下的细化规定或者补充性规定,无论是基本精神还是具体内容,显然都不能与法律相违背。换句话讲,只有法律化的章程才能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诸多重大事项规划好,才能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范围
尽管《民法典》第59条规定了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与法人资格同时产生、同时消灭的规则[ 民法学界一般将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有的学者还将民事责任能力从中分离出来)等统称为民事能力。参见李昊:《对〈民法通则〉中民事能力制度的反思》,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第92-94页。],但其范围如何,则无一般规定。由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有范围上的一致性[ 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其范围限于与其性质、法律规定、目的事业相适应范围之内。[ 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根据《民法典》第101条规定,完全可以认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民事能力范围是只能“为履行职能所需要”;换言之,只有在“为履行职能所需要”范围内,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方可从事民事活动。如此一来,如何正确厘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职能则是关键所在。
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7条、第8条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3条、第4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主要为四个方面,即:(1)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2)支持和组织村(居)民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建设;(3)青少年教育等其他公益事业;(4)管理村(社区)的财产。由于中国农村地区很多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没有实体化,“所以《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规定,由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土地和其他财产,包括发包集体土地和以土地等集体资产出资、租赁、联营合伙等投资或经营活动。”[ 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30页。]由此可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履行上述职能时,其民事能力大体包括四个方面: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侵权责任能力、劳动合同能力以及监护人能力。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财产支配和交换能力
从法律规定来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成立时并没有财产的要求。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村民委员会一般情況下没有自己的财产,因此也不享有财产所有权。但近些年来,上级人民政府会拨付一定的经费给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对这部分经费当然享有所有权。此外,由于村民委员会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组织,所以对于没有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即以民事主体身份代为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动产和不动产进行管理。[
《民法典》第101条第2款。]村民委员会法人对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管理,通常表现为下列四种方式:(1)代村集体与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合同;(2)代村集体接受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3)作为一方当事人签订农田、山林等流转及其对外的承包合同;(4)代村集体支配其他财产。笔者在调研时发现,湖南省华容县北景港镇村民委员会代为出租村的门面和鱼塘,湖南省慈利县象市镇各村的村民委员会代为出售集体种植合作社的药材,山西省晋中市西北街村民委员会和湖南省长沙市天马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城中村的村民委员会,代其村签订了大量的房屋租赁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值得指出的是,“代行”是“代表行使”还是“代理行使”,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原《物权法》第60条规定的是“代表”行使,但既然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已然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在二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当可以通过《民法典》规定的代理制度进行委托代理;而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存在的情况下,则此处的“代行”还应当解释为“代表”较为妥当。换言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时应当具备,并且只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和章程等具体问题可以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28-40页。]
居民委员会虽然在成立时也没有自己的财产,且城市并没有像农村那样的集体经济组织,但几十年来的历史积淀,使得城镇中的居民委员会不同程度地管理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有的是上级拨付的建设资金积累的财产,还有的是集体企业向居民委员会缴纳的财产。在法律属性上,这些财产应当归居民委员会法人所有。湖南省宁乡市花明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社区财产的管理主要是出租社区房屋及该社区的土地使用权,并对社区的建设项目进行发包管理。此外,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地加快,城中村在全国各地城市普遍存在,城中村有着诸多门面房,涉及社区集体经营性大型物业的门面出租、水电管理、城中村改造、城建工作,这样由村民委员会转化而来的居民委员会,支配的财产便多了起来。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履行其职能时还会产生诸多合同之债。如采购便民产品、消防用具及防灾用品、开展远程教育和法制宣传活动均会产生买卖合同关系,又如修建公益设施设备、拆除维护违章建筑物则会产生建设工程合同关系,还有日常办公的水电消耗与供给所产生的合同关系。诸如此类的债权债务关系均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以自己名义支配及使用财政拨款所产生,属于财产的直接支配。
(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侵权责任能力
依据《民法典》第265条第2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8)第36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法人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应承担法律责任。《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第57条规定,若村委会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村(居)民委员会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在管理村(社区)财产时具有妥善管理的义务,因管理不善导致财产受损或其他损害集体或他人利益的情况时,村(居)民委员会也可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实践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作为侵权赔偿责任主体的案件仍时有发生。以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为例,平均每年受理村(居)民委员会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件5件以上。不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作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义务主体时,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财产,无法切实履行人民法院依法确定的财产责任。[ 黄细苟:《村民委员会承担侵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相关问题之思考》,载“大律师网”http://www.maxlaw.cn/l/20151104/832985626854.sht,2019年10月10日访问。]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行的对策之一是购买责任保险。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劳动(劳务)合同能力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履行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和其他公益职能时还具有劳动合同能力,它们需要雇佣正式编制之外的员工而与被聘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从而成为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主体。例如,为退休人员雇佣保姆、雇人为居民维修故障水管、雇请医生为居(村)民提供疫苗接种及为孕产妇和老年人体检、雇人进行沟渠梳理、河流整治和垃圾管理、雇请安保人员、为文艺社会团体(如腰鼓队、广场舞队)聘请指导老师等。
(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监护人能力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还具有监护人能力,在特定的情形下担任监护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担任监护人,不仅可以补充传统的亲属监护力量,而且能有效缓解国家民政机关面临的监护压力,最终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民法典》第24条、第27条、第28条、第31条、第32条、第34条和第36条,分别确立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申请人民法院认定成年人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选任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为监护人的权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对监护人存在争议时指定监护人的权利,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争议未解决和发生突发事件时担任临时监护人的义务,以及对监护资格进行撤销的权利。
根据《民法典》第34条的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监护职责主要包括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法律行为和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两项。具体而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担任监护人时,应当照顾被监护人生活,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管理和保護被监护人财产,合理管束被监护人和教育被监护人。同时,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也承担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的监护人责任,以及因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虽然在特定情形下担任监护人,但其职能定位并非专业的福利机构,而在人、财、物等相关资源缺乏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其监护职能往往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尹志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监护人范围及监护类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28页。]据不完全了解,在现实生活中,已很少有人民法院会指定“两委会”来承担具体监护职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在监护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已主要转向监护人指定和监护监督工作。[ 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民事能力的限制,下述二个问题尤其值得研讨。
其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是否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题。
基于行政法治原则,德国学界一致认为公法人的活动范围应当受到限制,既不能超出其活动范围,也专注于法律预定的任务。[ 周友军:《德国民法上的公法人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7年第4期,第142页。] 由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不为营利法人,当然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除依法代行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营利性民事活动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不能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为交易行为等营利性活动。并且,基于其法律性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也不应当被赋予破产能力。这是因为,第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性质上不属于企业法人(营利法人),依理则不适用我国的《企业破产法》。[ 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于2019年10月在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办结。许多人称之为“个人破产”案件,但法律上还不能称为个人破产,而应是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其与真正的破产尚有许多根本差异。]第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目的是基层群众自治,赋予其以破产能力,在我国目前的破产制度框架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立法上均不具有可接受性。[ 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2期,第28-40页。]
其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的担保能力限制问题。
根据《民法典》第683条第2款的规定,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为保证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是带有鲜明公益性的公法人,基本没有财产,即使有一定的财产,一则数量相当有限,二则来源于本地区居民或村民的集体以及国家拨付的经费,以这些财产为他人商业行为提供保证担保是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精神的,毫无疑问应当被禁止。同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设立担保物权的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5条对此予以明确的认可,即原则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不过,基于现阶段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特别是村民委员会法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殊关系,其担保能力需要区别对待。
在实践中,因村民委员会为他人提供担保而涉诉的案件很多,有的司法案例认定村民委员会具有担保人资格,而有的学者予以完全否认。[ 杜潇洒对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市坡胡镇营张村委会担保案进行了讨论,对两级人民法院认定村民委员会具备担保人资格持相反观点。参见杜潇洒:《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民事保证人资格问题探讨》,载《中国外资》2011年第19期,第83-84页;编辑部:《村委会该不该承担保证责任》,载《村委主任》2011年第14期,第46页。]在笔者看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二者交织在一起,在《民法典》颁布以前,学理上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而村民委员会仅是自治组织而不是民事主体,但《物权法》等法律允许村民委员会代表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物权法》(从2021年1月1日起,随着《民法典》的生效而废止)第60条、《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第12条。],如果村民委员会作为担保人,而其实质则是以村集体财产承担责任的,则宜认可其担保行为。《民法典》颁布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村民委员会法人是两个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只有在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村民委员会才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此时如果作为担保人,其承担的担保责任实际上是以村集体财产承担的,其法律本质乃代理人的民事能力而不是自己的担保能力。
诚然,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而对外提供担保时,应当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讨论决定程序。[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5条但书。]如此一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超出民事能力范围所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区分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分别对待。[ 囿于本文主旨,该问题将另文专门探讨。]
四、结语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事主体制度,在成立、章程、财产、责任承担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传统法人的特点,关乎这方面理论的深入系统研究也就至为重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加快更新法治实施观念。我国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者开展此项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素材,比如社会实践已经将“居民委员会”更名为“社区居民委员会”。随着城镇化进程地加快,村民委员会转化为居民委员会的情况越来越多,广大农村的合乡并村也给村民委员会法人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观之,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主要法律规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其修正的迫切性也就愈加突出了。尤其是《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过于简单,仅有23条,必须针对居民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予以完善,其规定应当尽量具体明确。另外,农村村民委员会法人和城镇居民委员会法人虽然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但其具体职能、财产状况等方面都各有特殊性,特别是在地域广袤的中国,各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情况也有各自的特点,昭示着实证研究在当下法学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惟在采取科学抽样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展开对《民法典》第101条这种仅有两款的法律条文深入细致的规范研究,以促进该制度的有效适用。
The Three Main Issues of Legal Person System of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QU Mao-hui
(Law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legal person of the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is conceptualized as a special legal person in the Civil Code, it is essentially a legal person of public law. Firstly, i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the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the Organic Law of the Resident Committee. Secondly, by performing a series of management functions, it is realizing the functional purpose of "serving for the public welfare". Thirdly, its property comes from public source. The regul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for-profit legal persons and non-profit legal persons, and the actual laws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Organization Law of Villagers Committees and Organization Law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the Organization of Village Committees and Law on the Organization of Residents Committees have already covered the contents required by the legal person charter of the village (resident) committee, which has essentially become the charter of the legal person of the village (resident) committee. At the same time, the legal charter has more "compulsory power" than the general private legal person charter, which can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moreover, only the legal charter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autonomous process of the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legal person, and then overcome the inherent disadvantages of autonomous regulations. The civil capacity of the legal person of the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must be restricted by its "function",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bility of property control and exchange, the capacity of tort liability, the capacity of the labor contract, and the capacity of guardian’s capacity. They cannot conduct transactions in their name, nor should they be granted bankruptcy capacity. They cannot provide guarantees to others except for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that acts as a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llowing the law.
Key Words: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s legal persons; public legal persons; regulations; civil capacity
本文責任编辑:林士平
青年学术编辑:孙 莹
收稿日期:2021-12-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法在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研究”(21ZDA050)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研究过程中,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熊婧对资料的收集、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屈茂辉(1962),男,湖南新宁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我国颁布了280多部法律,对一些法律还进行了多次修正,比如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对《宪法》进行了五次修正。为行文准确,对于经过多次修正的法律条文的引用,本文加注法律的颁布或修正的年份。关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参见《宪法》(1982)第11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