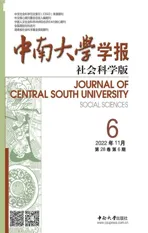明清易代士人“诗史”书写中的自我建构
——以钱谦益为中心的探讨
2022-03-23张娜娜
张娜娜
(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江苏无锡,214122)
明清易代之际,“诗史”理念重炽,“志风雅者当纪亡”的观念风靡一时。士大夫群体的“诗史”论说,及其以诗证史、补史的实践,向来为学界所关注①。在这个生存意义亟待论证的时代,易代士人如何熔铸“史笔”与“诗心”,将公共空间的史事记录与私人向度的自我书写相结合,进行一种“自传性”②作业,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议题。
对易代士人而言,“诗史”不仅是保存国故、对抗新朝的方式,更是他们安顿生命、确立自我身份的途径。诉诸公共空间的文学场域关乎立场、声名、权力和荣誉,具有一定的剧场性,不同的诗人以历史进行自我言说的方式又有所不同。这当中,钱谦益对传统“诗史”理念的阐释与批评实践影响尤为深远,其诗歌中的史事亦有学者论及③。然而,钱谦益本人先身罹党祸,后侧身虏庭并阴谋复明,其“诗史”作品中难免有偏颇之论或想望虚美之言。那么,他如何在诗歌这一抒情体式中编排材料,记录历史?这其中又呈现了怎样的自我建构意识?本文拟以钱氏为中心,探讨这些“史诗”书写中自我言说的不同方式与特征。
一、其事其心即史:“诗史”理念中诗人主体的突显
自孟棨在《本事诗》中以“诗史”说称誉杜甫诗作,“诗史”逐渐演变为中国诗学的重要概念[1](127-162)。“诗史”这一概念,既指对时事的记录和反映,也包含诗人主体的自我言说。如关于杜甫及其“诗史”,孟棨提到杜甫把个人行迹“毕陈于诗”;黄庭坚称杜诗“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2](310);苏轼言其“一饭未尝忘君”[3](318);惠洪《冷斋夜话》认为老杜“诗史”之“大过人在诚实耳”[4](2436)。故而,诗人一旦被冠以“诗史”称号,就会与以上论者所言的忠君爱国意识、忧国忧民的儒者情怀、正心诚意的高尚品格产生关联。而且,他们的行迹得以“毕陈于诗”,形貌亦“剥换于竹帛之间”,与读者言笑相接。总之,“诗史”作品和诗人的主体呈现密不可分,这一点在世变之际尤为突出。钱谦益在《胡致果诗序》中论述他的“诗史”观:
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
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5](800-801)
以上论述进一步开拓了诗人自我书写的空间,并将“诗史”纳入遗民诗的传统之中④。首先,这里指出曹植、阮籍等人的诗歌反映的是“千古之兴亡升降”,诗人的“感叹悲愤”发于诗中,能由一人之精神见时代之精神。其次,指出宋“遗民”诗“风高气慄,悲噫怒号”,表示易代诗人的“诗史”蕴藏着悲恸的亡国经验。最后,点明“空坑”“厓山”的故事不为新史所录,然考诸诗歌,其人、其事犹存。所以,他们的诗歌不仅可以“补史之阙”,还可以将自身行迹载录其中,“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让后人了解并传颂。这一点源于文人立言不朽的初衷,但对于易代士人而言,尤其对于以“忠臣孝子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自述的钱谦益来说,更有着非凡的意义。
当时,突显“诗史”中诗人主体的言论并不罕见。比如,毛晋论亡国人物与易代历史的关系,称韩偓在唐亡之际,“借自述入直、扈从、贬斥、复除,互叙朝廷播迁、奸雄篡弑始末,历然如镜,可补史传之缺”[6](580);黄宗羲指出,“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7](49)。另外,“心史”[8](297-332)说和“年谱”说也在这一时期再次引起学者关注。前者和郑思肖《心史》在晚明被重现有关。吴伟业称徐映薇诗:“可以史矣!可以谓之史外传心之史矣!”[9](1206)屈大均也认为:“君子处乱世,所患者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10](320)年谱既是生平,也是历史的记录。钱澄之就在《生还集自序》中写道:“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11](704)“诗史”中诗人自我书写的意味愈加明显。他们对传统“诗史”说的超越在于,从史家和受政治影响的传统诗学观的立场回到文学的主“人”立场。
二、模糊的公私领域:历史叙事中的个人影像
在“诗史”传统中,诗人进行历史叙事的方式、内容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性情、人格等密不可分。他们以看似端正客观的姿态在“公领域”的文学场域中记录历史,同时“建立自身的现实性、自身的身份以及周围世界的现实性”[12](38-43)。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说,所谓公私领域的界限本就是模糊的。而在易代之际,以诗为史是士人论证个人生存意义的重要途径,他们不仅记载历史风云,更希望呈现“自身的身份”。晚明时期,钱谦益被目为“清流魁首”“山中宰相”,却因党争旋用旋废,数陷囹圄。他记录朝野大事,同时也彰显了个人乃至众多朝臣的处境,如“缘钩党遭涂炭”的“清流魁首”,意欲“犁庭扫穴”的儒生,有拜相之才却屡遭倾轧的“孤臣”“逐臣”,忠义史家等多重角色⑤。钱谦益后因降清而为士人不齿,为扭转声名,他书写了痛悔不迭、以期世人谅解的“心史”,并极力建构其抗清志士和遗民身份。他对自身的复杂性亦有清晰的认知,故在自题小像诗中写道:“揽镜端详聊自喜,莫应此老会分身。”[13](381)约略而言,其所呈现的“分身”有如下几种角色。
(一) 钩党清流与明政知兵的“爱官人”
钱谦益曾写道:“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14](298)顾苓也在《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中说:“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钱谦益)与东林为终始。”[15](961)钱谦益的“党魁”身份也使他在朝局纷争中首当其冲。他在《吴门送福清公还闽八首》中记录了东林党于神宗晚年的政治斗争。钱曾⑥在其指导下,于注释中梳理了明末党争兴起的过程,其中涉及“庚戌科场案”,即钱谦益本为殿试第一,却为浙党汤宾尹置换为韩敬之事。实际上,韩敬本就是颇有制义才华的名家胜流,夺得状元亦名副其实。根据时人评说,所谓汤、韩二人辇四万金通内之事疑点甚多,这一点学界已有考证[16](202-204)。钱谦益选择性忽略这些事实,在诗注中直称汤、韩二人为结党营私、交通盘牙的奸邪小人,并一再宣扬自己作为东林清流的受害者身份。直至去世之前,他依旧愤意难平,在自注中提及这一“庚戌胪传之谶”[5](645)。此案是引发晚明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纷争的导火索,亦是钱氏一人之事兼一朝之史的重要关节。此后,从天启元年(1621)的“浙闱科场案”到崇祯元年(1628)的“枚卜”大典,钱谦益随东林党的盛衰消长而沉浮起落,这既是其“阅尽艰危五十春”的“个人之史”,也是晚明政治斗争的缩影。
崇祯元年(1628)的“阁讼”是党争的延续,钱谦益是此案的主角。他本人自诩有名士之风与宰相之才,尝直言“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14](325)。当时崇祯即位,起复废籍诸臣,钱氏距相位一步之遥,却因周延儒、温体仁的阻挠和崇祯的偏听偏信而遭贬斥。他在《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中将案件始末以及相关人物言行一一记录下来,堪称“枚卜”大典的实录。其中详细记录了周、温一方与钱谦益一方辩难激烈、众人上书为钱氏陈情的场面。当时,“群臣交章攻温,上概置不省。……公(钱谦益)削籍南还,竟一斥不复,皆党之一字害之耳”⑦。《明史》《明实录》省略了诸多“阁讼”细节,尤其是温体仁攻讦之言中的漏洞。因此,诗注详载群臣奏疏,为使后人“见人心之倾附于公(钱谦益)”。诗中有句曰:“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14](277)这里表现的是钱氏的个人痛史,更是党派林立、政荒治弛的朝局。钱氏将个人经历融入公共历史,期望使“盈庭公议,不逐穷尘劫灰,相沦没于终古”[14](278)。
钱谦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谈兵事者”常聚其家中,“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17](1018)。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兴兵反明。当此之际,钱氏在《夜泊浒墅关却寄董太仆崇相四首(戊午)》中讨论征兵、练兵之事。他指责女真违背盟约屡屡犯边,并推举董崇相、吕纯如驱逐异族,建立功业。实际上,钱氏正预备还朝⑧,谈兵、练兵是其心系边事的表现,也是在为复出做准备,对董、吕的称颂是其扩展人际关系的策略之一。当时,董应举在《答钱受之》中写道:“知今春出山,欲自效于一障一堠,为国报仇,义不旋踵之意,弃卿相而乐死亡,真男子也。”[18](549)崇祯九年(1636),钱氏在狱中依然关注边事,“莫倚居庸三路险,请封函谷一丸泥(逆虏吞并高丽,夺我属国,中朝置之不问)”[14](628),提议在函谷关设军抵御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他还在诗歌自注中提到,“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19](1157),表示他曾在朝势倾颓之际被委以重任。钱谦益始终在史事的记录中标榜自己的明政知兵之才。
(二) 微言“国本”的史家角色
在钱氏的“诗史”理念中,《诗》和《春秋》一脉相承。他在诗歌创作中,也将《诗》“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讽喻精神与《春秋》“微言褒贬”的手法相结合。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指出,一些议论将“春秋笔法”和“忠义”精神视作“诗史”的本质,是想在“诗史”中突出诗人的存在[20](319-320)。此说适用于包括钱谦益在内的诸多易代诗人。当时,“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明朝历史中“国本之争”的表现。钱氏据此创作了多篇“诗史”作品,并采用了“春秋笔法”和“志婉微讽”的写作方式,塑造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身份,揭示了当时的军国大故、朝廷大议、人才摧折和忠邪消长。
神宗宠爱郑贵妃是“国本之争”的源头之一。光宗朱常洛之母王恭妃薨后,朝中秘不发丧,钱氏为神宗所作挽词中有“杨柳深宫月,梧桐别院深”句,钱曾笺曰:
寂寞悲凉,两言尽之,不数《长门》一赋矣。夫公(钱谦益)身为臣子,何忍明斥椒风?故婉约其词,使读者回环吟咀,深思自得,黯然魂消,几有鸟乌枯菀之虑,若以为泛指宫闱之景,不已颠乎?[14](4)
这条注释开示了读者阅读钱谦益诗史作品的方式,“夫公身为臣子,何忍明斥椒风”,即“婉约成章”,屈曲其辞,有所避讳;不可泛指“宫闱之景”,表示诗旨的“微而显”,有文见于此而义在彼的意味。对于情词婉约、事典密集的钱诗来说,需要读者反复吟咀、深思。
钱氏以史家“微言大义”的笔法评判宫闱秘闻。“忧危宗社并,呵护鬼神知”[14](7)句涉及“梃击案”。当时一男子持木棍撞入太子居所,打伤守门内监,一时间聚讼纷纭。神宗为了“安贵妃”“安东宫”,命人将庞保、刘成等主要涉案人员处死,案件无从查起。正如钱曾注中所言,“张差何人?青宫何地?而遂能阑入慈宁乎?……邀呵护于鬼神,此公之微词,亦公之直笔也”[14](9)。为避免大狱兴于骨肉之间,神宗“庇于其间”。这是君王身不由己之处,也是钱谦益“微言”的缘由。“禁近终难问,弥留竟可疑”[14](10)句指涉“红丸案”。光宗即位不到一年病逝,“或传女谒使然”。钱曾在注释中没有怪罪进献红丸的李可灼,而是用大量笔墨历数方从哲之过,称其“漫无主持,凭依翕合”,是“移宫之衅”的开始[14](10)。钱曾视方从哲为“移宫案”的导火索,于注中大肆批判,亦是站在钱谦益东林党人的立场所展露的“史家之心”。
有感于“征东之役”的记载“功罪失实”,钱谦益以“微而显”“一字褒贬”的笔触将之寓于诗中。“天为摧丑虏,(关白平秀吉自毙)地不爱金银”[14](3),指出征东结束的原因并非明末将领的忠勇与谋略,而是“天”,即平秀吉之死,这是钱谦益“春秋笔法”的体现。征东之事历时七年,主要原因在于将领争功诿过、策略失当。“平壤城边战骨丛,更闻丽妇哭征东”[14](74)中的“哭”字可见“春秋大义”,是钱氏对群臣罔顾大局的谴责。另外,袁崇焕自诩五年复辽,是思宗初期抗清主力。钱谦益《奉酬山海督师袁公兼喜关内道梁君而(廷栋)将赴关门二首》中有句“白山好勒《磨厓颂》,衰晚何因借后车?”自注曰:“袁自诡五年灭奴,颇以讲款为秘计,故有讬讽之言。”诗歌暗讽袁崇焕大言罔上,既“委曲隐讽,望其有成”,又“料其必无所成,早危之矣”[14](345)。
(三)“史外传心”的复明志士
钱谦益视“诗史”为《春秋》义理和诗人“情志”的融通。黄宗羲也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说,“逮夫流极之运”,史随国亡,其间“痛哭”之情,“危苦之词”,“非史之所能尽矣”[7](49),点明诗人“悲噫怒号”之辞在补史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一人之史与一代之史的关联。明亡后,“诗史”是钱谦益面对大众审视的个人“证言”,他撰写“史外传心之史”,塑造了一个奔走于复明运动,意图挽救危亡的策划者、参谋者形象。
钱氏在弘光朝再次走到政治舞台的前沿,《鸡人》一首“自述弘光元年乙酉时事,颇有史料价值”[21](1173)。诗曰: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胡骑已扬舲。(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对,讲官奏胡马畏热,必不渡江。余面叱之而退。)刺闺痛惜飞章罢,(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绕新亭。[13](388)
颔联“方”“已”二字表现了清军进逼的紧迫和弘光朝臣的散漫无知。“刺闺”句写钱谦益请求出京援扬却未被采纳之事,“空烦侧坐听”足见其危迫身坐却无用武之地的无奈。钱曾注曰:“公之疏请援扬,自愿督兵者,意在求出国门,借此远祸害,亦无聊不得已之谋也。……侧目切齿之徒,咸思剚刃于公。”[22](2259)钱氏上疏“援扬”或为避祸,可见钱谦益在弘光朝应当扮演相对关键的角色,故为诸多势力所嫉恨。他在朝中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老谋硕画”,“年年流恨”是家国之恨,更是身世之恨。
《投笔集》既是郑成功北伐之役前后的时代画卷,又是“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21](1193)。该集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⑨,这里主要谈论钱谦益在其中隐含的身份建构。他在组诗中一再显扬自我,记录了从风流文士到降清“贰臣”,再转变为复明遗老的心路历程。
钱谦益屡次以反清复明之筹谋者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郑成功兵败金陵城下,钱谦益作诗:“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警候,骤骄彼是灭亡时。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23](5-6)他劝诫郑成功勿因小挫灰心,而要审时度势,慎重思考。“金陵要奠南朝鼎,铁瓮须争北顾关。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23](6)他主张要攻下金陵首先要控扼镇江,切断清军在长江下游的通路。
他还对自己的复明历程进行“自传”式的追记和总结。如第十一叠诗其四曰:
廿载光阴四度棋,流传断句和人悲。
冰凋木介侵分候,霜戛风筝决战时。
觚竹悬车多次舍,皋兰轻骑尚逶迟。
灯前历历残棋在,全局悠然正可思。[23](60)
他在诗中回忆了自己二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四度棋”分别指:弘光元年(1645)企图登莱开府,力挽残局;顺治三四年(1646—1647)间为复明义军筹集资金,东窗事发而下金陵狱;顺治六年(1649)通过瞿式耜给永历上“楸枰三局”之疏,接受永历任命,秘密联络东南;顺治十六年(1659)接应郑成功、张煌言水军进南都。以上基本上贯穿了钱氏的复明事业,其本人也逐步向抗清志士这一新身份靠拢。“十年戎马暗青山,自窜江村水岛间”[23](29),表示自己穿行于江村小岛,秘密传书递简;“兵残蜗角频搔首,乐阕龙宫一破颜”[23](29)句用“柳毅传书”的典故,有学者推测钱氏传书递简的使命有关南华北胡之治事[24](421-422)。
此外,钱氏还以“孤臣”“衰翁”“老翁”“遗民”“开元鹤发翁”“野老”等多重形象出现在对战况的描绘中。在《后秋兴之三》其七中,钱谦益写道:“此行期奏济何功,架海梯山抵掌中。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23](14)他俨然已将自己视作挽回残局的鲁阳公、班超以及姜太公,呈现的是立志“效铅刀之一割”的顽强老者形象。
总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称,公领域和荣誉、声名、权力相关,人们努力表现优异的言行,犹如在一个剧场中,把最卓越的言行表达给在场的人[12](43)。钱谦益在历史这一公共场域中,模糊了客观史实与私人情感的界限。他在晚明时期将诡谲多变的时局和一腔孤愤诉诸笔端。入清后,他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评判者,更是一个“备残棋之一着”、意图挽救危亡的策划者。诗史既是钱谦益挽救现实的良药,也是他扭转声名和安顿生命的重要途径。
三、以“他人”系史:自我诠释的另一路径
钱谦益在“诗史”作品中记录当朝历史人物,并表示以相对客观的“叙述者”立场,“以诗存人”“以人存史”。他不仅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构建自己“明之遗民,清之功臣”的身份⑩,也在诗歌中剪辑和提炼当朝人物的言行事迹,以之勾连历史事件,彰显个人情志。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不以他人为参照,很难确立自我;个人作为主体,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钱谦益对当朝人物的书写,涉及建立名声的社会网络和群体文化。他对文韬武略的阁臣、饱受非议的武将、杀身成仁的抗清志士以及伉俪情深的人生伴侣的记录和点评,不仅是士人反思明之存亡的体现,更是诠释自我生存境遇、建构自我的方式之一。
(一) 推售恩主:理想人格的表达
钱谦益曾被孙丕扬“以古名宰相相期许”[25](210),却因党争而屡遭屏废,他在笔下人物身上寄托了这种入阁拜相、昌隆诗道、鼓吹盛世的理想。比如,备受钱氏推崇的李东阳,其诗文被誉为“洋洋乎盛世之音”[26](994)。钱谦益也将其政治目标与人生理想倾注在孙承宗、王图等阁臣身上。作为史家,钱谦益为他们撰写人物叙传诗,宣扬其品德与事迹,存之史册;作为追陪的学生和同道知交,对师生交往的追忆给了他回顾本人经历、表达自己理想的空间。
孙承宗既是鼓吹休明的东阁大学士,又是功勋卓著的边将,这正是钱谦益追求的人生志业。《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谒少师高阳公于里第,感旧述怀,即席赋诗八章》记录了孙承宗督师蓟辽以及罢官归乡的经过:“帘栊即可当储胥,铃索长疑畏简书”,言孙氏谈笑间解决军务;“厅事只堪容旋马,讲堂犹自见衔鱼”,称其廉洁;“能文裴度差相似,健饭张良正不如”,道其文武兼备[26](806-807)。他将孙承宗比作姜太公、赵充国、裴度、张良、司马光等前贤,映照了其本人的理想人格,即如孙承宗一般奋策儒素,建功阃外。孙承宗曾对钱谦益寄予厚望,嘱咐他:“公归自爱,天下多事,还须几个老秀才撑拄。”[5](826-827)“卅载师门何所效?谨传衣钵事归耕”[26](816),可见这一光明俊伟的人物对钱氏的指引。
因为相似的仕宦经历和社会声望,钱谦益从王图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王图官至礼部尚书,位高声隆,为天下仰慕。钱谦益当时也为一“山林领袖”,门下执弟子礼者数千人。“座主龙门峻,诸生雁塔联”,钱谦益将王图比作独持风裁、声名自高的李膺,他本人亦尝以李膺自喻⑪。钱谦益的《送座主王文肃公之子、故户部郎中淑抃归关中,叙旧述怀一百韵》,以王图在明万历、天启朝,和自己在崇祯朝的宦海沉浮为叙述对象,勾勒了万历后期党争发生的前因后果,串联起自己的人生经历。诗中“衣钵援垂手,宫墙企及肩”之语,对于其早年追随王图之事颇为自得。他还借王图于明末党争的境遇宣泄内心愤懑,“文肃领袖清流,党人披猖,避位去国”写的是王图,更是其个人的遭遇。又,自注中“此后并言文肃长翰典试及余登第及门之事”,“崇祯元年,予自废籍召入京,旋构阁讼,再遭谤铄”[14](501-503),回顾了自己于京中追陪王图的岁月和归田屏居之事。
此外,钱谦益称福清公叶向高“先忧系于民誉,爰立简于帝心”“以精诚之一寸,格神圣于久阍”[27](1695)。叶向高尝主持内阁长达七年,为平息党争殚精竭虑。钱谦益在《吴门送福清公还闽八首》中道其生平事迹,指出叶向高对争储、福王之国等事的妥善处置,所全于国体者良多。钱谦益对之钦佩不已,并借钱曾之注使其事迹见知外廷。他一直以叶向高的奖掖自励,称:“岂云报德,足当衣钵之私。”[27](1696)钱谦益渴望承其衣钵,“廉平以牧身,诚敬以格主”,实现“结主知,镇国论”的人生志向。
(二) 同慰死生:哀悼者的隐衷
哀悼为生者提供了一个将逝者生平加以盖棺定论的机会,具有沟通生者与逝者的表演性特征。生者个人化的哀悼之情居于史实性的纪念之上,获得了自我表达的空间。钱谦益将逝者生平脉络化或业绩典型化,将之铭记在历史这一“公领域”之中,并在人际关系话语中重申其本人所隶属的政治群体。故而,褒扬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的师友门生,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学或史学行为,而是钱谦益追记个人事迹、重塑自我的媒介。
杨涟、梅之焕和王洽三人皆为朝中重臣,与晚明时局密切相关,并与钱氏过从甚密,由他们的交往可见士大夫之间相互确证和建构的情谊。如杨涟与钱谦益二人,“倾盖投知,精神胶结”。梅之焕称钱谦益“虞山如龙”,在温体仁攻讦钱氏之时,“移书中朝”,极力庇护;钱谦益也曾言“用梅长公办寇,天下可安枕矣”[27](1627)。又如王洽得知钱氏下狱,“恨不能为其排九阍,叫阊阖,执谗慝之口而白其诬也”[27](1769)。钱氏在《二髯篇戏简甘肃梅中丞,兼呈兵部王尚书、左坊文中允》一诗中曾摹写三人影像:“先朝昔煽乱,妇寺据肘腋。四海一应山,奋髯相抵格”[14](368)写“东林六君子”之一杨涟在魏忠贤、客氏干政之时,首发其奸,揭露魏阉二十四条罪状;“尺书来酒泉,忠愤壮羽檄”[14](368)写梅之焕巡抚甘肃时大破套寇的卓越功勋;“堂堂髯司马”“所以妇寺流,颐颔如脯腊。何用拔须眉?天为芟与柞”[14](368)写王洽于浙江赈灾而为魏忠贤陷害之事。据《明史》记载,清兵进犯,周延儒进言王洽兵备疏忽之过,致其下狱瘐死。钱谦益亦曾作《干将行》伤王洽之死。钱氏借对这些人物的书写讨伐阉党,鞭挞周延儒、温体仁之类的佞臣。
钱氏忧国心切,恨不能立征沙场,力挽倾颓,其决心由书写及门弟子的《三良诗》可见一斑。当时清军势若破竹,诸多将士接踵而死,“哀哉殉国心,耿耿殁犹视”表现了他对逝者的痛惜与敬重。反观自己“槁项黄馘,视息牖下”[19](1195)的处境,他坚定了复出的信念。“段生湖海士,矫志营儒术。道心既渟泓,侠气亦迸逸”[19](1195)句表彰段增辉既精通儒术,又有侠肝义胆。“孤身策马箠”“首已离鱼剑,胸犹集蝟矢”[19](1198),再现了汪乔年决战沙场的情景以及誓死无畏的精神。“三良”中的高名衡事迹又见于《和高中丞平仲乘城记事诗八首》,称其乘城死守之举“可以办贼,可以办天下事矣”[19](1094)。钱谦益在诗中用以人系事的方式描述了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罗汝成攻破襄阳的过程。这一年他写下《请调用闽师议》《向言》,大谈用兵之法、救世之略,崇祯也称其“博通今古,学贯天人”[19](1182),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三位门生的事迹更激发了他再次复出、经营四方、名勒狼胥的志向。
这里不得不提及弘光朝一位富有争议的关键人物——左良玉。钱谦益在《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记录了顺治二年(1645),左良玉从武昌挥师南下,声讨马阮直至身死舟中之事。“万斛青蝇掩墙翣”[13](275)写左氏死后,世人对其评价多为不知内情的谗言。诗歌最后寄语柳敬亭:
柳生柳生吾语尔,欲报恩门仗牙齿。
凭将玉帐三年事,编作《金陀》一家史。
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
从来百战青燐血,不博三条红烛词。
千载沈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
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13](275)
他忧心左氏“沉埋国史”,似乎想到了百年后同样要面对历史检讨的自己。这时的钱谦益已投入到复明运动中,他深知此行为很可能不为世人知晓,就如左良玉,身经百战,呕心沥血,却抵不过文字评说。他希望柳敬亭重为左氏“开生面”,重定功过是非。
(三) 镜像人物中的自我审视
降清后,钱谦益一时间为舆论所不容。他曾感慨曹能始以“全人”之身离去,而自己“楚囚越吟,连蹇不即死”,“临流揽镜,往往自憎自叹,辄欲引而去之”[15](844)。不单单是他个人无休止的揽镜自伤,故友旧交都是他反观自我的镜像。于钱谦益而言,他践行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儒家传统,亦借助笔下的“贰臣”或“遗民”乃至女性,反思与重塑自我。他在共有的亡国之痛中,与他人建立跨越立场的情感联结,迈向一种个人与群体相互激荡、感知合一的境界,从而将自己纳入遗民诗的话语系统中。
对遗民志士的书写是钱氏心系故国、表露复明动向、扭转声名的表现。瞿式耜在十六岁时即从学钱谦益,师徒二人在晚明出入患难数十年。国变后,钱氏成为大节有亏的“贰臣”,而瞿式耜赴广西莅梧州任,成为九死如饴的孤忠之士。钱氏在听闻瞿式耜去世后作《哭稼轩留守一百韵》[13](138-156),堪称稼轩的个人“小传”。诗中“庚寅降生”“少壮授经”“登朝贬谪”等自注,层次分明地梳理了稼轩的生平。因钱、瞿二人在晚明同遭贬谪,性命相连,钱氏在叙写中自然地串联起个人行迹、心迹,包括于南明王朝的事功。他用大量笔墨写永历政权建立的过程和桂林的情势,可见他对南明小朝廷的密切关注,印证了稼轩在《报中兴机会疏》中所说的“(牧斋)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28](106)。稼轩被执时赋诗,自期完节不负门墙,已然将钱氏视为“忠躯义感”的引路人。《梅村家藏稿》写道:“盖其师弟气谊,出入患难数十余年,虽末路顿殊,而初心不异。”[29]钱氏也称稼轩为国士,表示二人“虽末路顿殊”,然始终同气连枝、同声相应。
钱谦益通过对清廷江南大吏陈名夏的记载自讼、自省,寻找当世乃至后世“知我者”的情感认同,体现了“贰臣”之间“对话”的微妙意味。陈名夏承认了宁完我攻击他的复明制度一项,“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殊可哀也”[21](1187)。钱氏写百史道:“披发何人夜叫天?亡羊臧谷更堪怜。长髯衔口填黄土,肯施维摩结净缘。”[13](421)以《左传》中无辜的浑良夫比百史,因为他数次论死,暂得宽逭,最后却以“留发复衣冠”的言论处绞[21](1187)。他哀挽百史并思诸身后百年,惧怕自己的复明之心不为人知。被清廷目为南党党魁的百史都存有复明之志,更何况自己呢?针对钱氏以文墨自饰之论,章太炎认为:“以人情思宗国言,降臣陈名夏至大学士,犹拊顶言不当去发,以此知谦益不尽诡伪矣。”[30](902-903)所以,钱谦益追悼百史,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身在清廷之“贰臣”的真实心境。
此外,在明清政治失序的状态下存在性别声音的混杂,钱谦益之类的文人多在与女性的投赠往来中隐含着自我揭示与剖白。明亡后,柳如是成为“情”与“忠”的化身,是钱谦益“赖以自壮”、完成从降清“贰臣”到爱国“遗民”身份转变的关键助力,也是他复明事业中的精神支撑。《后秋兴之三》其三:“破除服珥装罗汉,减损齑盐饷佽飞。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钱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始成一军。”[23](11)柳如是资助姚志卓指挥的五百人军队,可见其侠肝义胆,以及钱氏本人对复明事业的支持。郑成功海师溯江而上,逼近南京,钱氏作诗记录当时的情状。一方面,“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23](12)句中“子声迟”“兵势老”隐喻郑成功进军的拖延。另一方面,“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23](12)视柳如是为击鼓助战的梁红玉,暗示自己像韩世忠阻击金兵一样反清复明。钱氏将柳如是视为爱情与政治的联结点。《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中“埋没英雄芳草地”“共简庄周《说剑》篇”句[19](1092),俨然模糊了二人之间的性别界限,他以英雄自期,更将柳如是视为同道中人。巴赫汀的对话理论把主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人的主体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交流中建立起来的,或者说“自我”是由对“他者”的理解创造而来的[31](20)。钱氏与书写对象之间就是一种精神的“对话”,其自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他者的认识以及与他者的价值交换而建立起来。他在诗史作品中剪裁、熔炼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表达了对理想人格的期许,对“贰臣”之举的悔愧。钱谦益曾在诗序中写道:“听者将同病相怜,抑或以为同床各梦,而辗尔一笑也?”[13](116)深知读者的诠释未必如其所愿,他预先为自己作了宽解,同时也尽力在社交网络中倾诉衷曲,期望以之影响舆论、公论和史论。
四、殊途同归:明清“诗史”自我言说的其他形式
钱谦益在“诗史”中的“自传性”作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其本人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即“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一见于诗”[32](2243)的作品,这里的“诗史”建立在诗人主体呈现的基础之上。二是以史官自居,以诗之“比兴”与《春秋》之“微言”褒贬人事的作品,彰显其作为士大夫的责任担当与忠义精神,也反映出他的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和好贤恶恶。三是在其身处的社会网络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裁剪他们的言行事迹,在对“他者”的描绘中回顾其本人的经历,发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这几个方面不失为解读其他易代诗人“自传性”创作的一种策略。同时,我们又应当关注到,在明清易代这个特殊时期,诗人以诗史呈现自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下文将围绕几位被冠以“诗史”称号[33](333-337)的诗人展开论述。
一些诗史作品塑造了一批人物群像,借“儿女情踪”将“易代之感,与夫身世之悲,盖有不能质言、不敢昌言者”[34](565)寄寓其中,吴梅村是其中的代表。不同于钱谦益的是,他选择的人物并非其社交网络中的士人群体,而是诸多与之身份迥异的“野夫游女”。正如他在《且朴斋诗稿序》中写徐懋曙“一遁而入于野夫游女之群,相与一唱三叹,人之视之与其自视,皆不复知为士大夫也”[35](1206)。其本人创作的有关“野夫游女”的作品消解了其“士大夫”的身份,故可以在掩盖其本来面目的前提下拥有更多的“面孔”,或者说身份、角色。孙康宜谈论梅村诗,认为“透过女性角色——其身份无论性别或社会地位皆迥异于诗人自己——寄托情志,梅村成功地赋予诗歌一种外物假借,一种主体凭借的‘面具’”[36](182)。他的《永和宫词》《临淮老妓行》《玉郎曲》《琵琶行》等对人物群像的描摹,映照出内廷、官僚和民间对于史事的不同记忆。他本人如同笔下的陈圆圆,在陆沉巨变中的颠沛流离、遇与不遇都非其本心,却无可推卸地背上了亡国的罪愆和耻辱。他唯恐不为后世人理解,故曰:“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用心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35](1409)他在感喟江山易代的同时,又时时进行着自我观照。
以女色、冶游的感官刺激再现晚明盛世,表达故国之思,是一部分遗民以诗存史、标记自我身份与寻求情感认同的重要载体。比如杜浚的《初闻镫船鼓吹歌》,从“记我来时卯与辰,其时海内久风尘”到“此生流落江南久,曾听当时煞尾声,又听今朝第一声”,将晚明灯船盛世、文人名士和秦淮名妓的交往结合起来。“太平久远知者稀,万历年间闻而知”[37](121-123)之语糅合了个人的生命经验,在对社会风尚的描摹中感慨兴亡。张清标云:“茶村扫去依傍,一灯船琐事,而衡其盛,则推原江陵之当国;考其衰,则归咎马、阮之秉政。一篇中于理乱兴亡,三致意焉。”读此诗者无不“痛痒无端,久之欷歔太息而不自禁”[38](357)。这是因为杜浚再现了金陵秦淮灯船的历史语境,激发了易代士人的创伤经验和故国记忆。
以诗集为年谱,以年谱为诗史,也是诗人记录历史、呈现自我的方式之一。钱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中说:“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11](704)他的《悲愤诗》将妻女殉道、投身起义的个人经历融入弘光朝覆灭的史事之中。《行路难》六十四首写逃避党祸、由闽入粤一路的所见所闻,呈现了阛阓烧残、垝垣遍地、溃卒蔽江、猺贼复起的战争场面。邝露《峤雅》集有诸多亡国之作,他在自注中系年系事,犹如年谱,并融入身份言说。如《后归兴诗》题下注“乙酉六月”,“南北神州竟陆沉,六龙潜幸楚江阴”记录中原陷落,弘光覆亡;“蹈海肯容高士节?望乡终轸越人吟”[39](324)以鲁仲连自比,表达愿蹈海而死的不屈;《浮海》题下注:“时南都已失”,“孤槎与客曾通汉,长剑怀人更倚天”[39](324),借张骞乘槎寻河源事的典故表复明决心。
五、结语
总之,易代士人的诗史多预设了文本、作者与广阔世界之间的对话,个人记忆与公众记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贰臣需要以此表达对故国的哀思和降清的悔愧,重塑自我,打入“遗民诗学”的文学场域。遗民志士更需要用历史诠释不死或者后死的价值和意义。他们预想着后代看待自己的方式,尝试形塑这个观感,也试图为自己承担的关乎苍生生存权的文化使命赋予意义。他们将未能缓解的心理负荷与历史的、教化的、美学的能量交织互映,开辟了一种诗歌美学实践和诠释体系,丰富了明清之际的抒情传统。这些将自我建构寄寓于历史书写的方式,对我们探求世变之际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于身份、心态转变的境遇下,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考察钱谦益等人作为“明清痛史”的典型,在近现代“新痛史”中如何被重新解读,由此揭示中国传统诗性文化与新文化、新思想的交融与新变。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有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文艺研究》2003 年第5 期),魏中林、贺国强《诗史思维与梅村体史诗》(《文学遗产》2003 年第3 期),陶俊《“诗史”意识于明清文学之特质》(《求索》2010年第1 期),姜克滨《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河北学刊》2011 年第3 期),郑伟《清初诗史观念与身份认同》(《江西社会科学》2013 年第10 期),叶晔《“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文史哲》2019 年第1 期),邹福清《明清“诗史”说与诗纪事著述的价值建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2 期)等。
② 这种“自传性”源于钱谦益诗史的写作以个人行迹、心迹为观照对象,“以自身内在的变化为轴而追忆往昔”,且在重要的节点书写回顾性的作品,甚至在晚年有《病榻消寒杂咏》这类总结一生的大型组诗。诗史的写作贯穿钱谦益一生,是其自我言说的方式之一。
③ 特别是钱谦益对杜诗的笺注和《列朝诗集》的编撰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具体参阅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 年版)、刘福田《钱曾〈牧斋诗注〉之史事考察》(台湾东海大学2000 年博士论文)、綦维《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试析〈钱注杜诗〉中钱氏隐衷之抒发》(《杜甫研究学刊》2001 年第4 期)、丁功谊《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变化》(《江汉论坛》2009 年第2 期)、李欣锡《论“东涧诗法”传承、演变及其诗学意义:以“诗史互证”为观察视角》(《中国文学学报》2017 年第8 期)、李宗娟《钱谦益“诗史”观念再探》(山西大学2020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④ 台湾学者严志雄先生的《钱谦益的“诗史”理论与实践》(中华书局2019 年版)一书认为,钱谦益主张在“诗史”的写作模式中,个人、私人的情感不妨与政治、历史的情况相互交融发生,其“诗史的概念被巧妙地移接到遗民诗的传统中”,这一点对本文启发良多。严先生也指出,钱谦益在《投笔集》中以诗歌介入历史,将自己描绘成复明运动的一员。本文重点关注的是,除了降清以后的《投笔集》,钱谦益又如何在晚明史事的记录中建构自我,通过塑造当代人物剪影即“他者”,来寄托个人隐衷。
⑤ “角色”本身是来源于戏剧的一个概念,人们通过面具来扮演某个角色,其中人物与角色之间是分离的。诗歌中的角色显然不能脱离诗人主体,他由诗人组织而来。无论是钱谦益试图扮演这些“角色”,还是“角色”扮演他的一部分,这些人物都在为“他是谁”提供一种解释,都是其内在性格和渴望的表现。显然这些经由抒情人传达的“角色”是相当矛盾和不稳定的,也正是这些表面“角色”下的复杂性使钱谦益具有了独特的魅力。
⑥ 钱曾自二十岁左右即伴随钱谦益左右,亲炙其学,在注《初学集》《有学集》的过程中得到钱谦益耳提面命的教诲。清人竹樵在钞本《初学集诗注》序后题记中说:“此直是东涧自注者,而托名为遵王。”钱曾注释中有诸多例证,如“刊章一老余头白,抗疏千秋托汗青”后注解了发生在崇祯十年(1637)的张汉儒案。当时钱曾只有八岁,其中路振飞刺温体仁之言论亦不见于史料,注释材料当为钱谦益提供。又《神宗显皇帝挽词四首》其三“摧丑虏”条注释:“公(钱谦益)尝以丁应泰《东事始末》手稿示余。”又《次吴德舆韵六首》其一中钱曾对“金马”的注解:“公曾梦生前为金马道人。”注中有钱谦益梦中事。因此,钱谦益本人参与诗注,钱曾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他的“代言人”。具体钱曾如何为之发声,参见拙文《论钱曾注〈病榻消寒杂咏〉对钱谦益形象的书写》(《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4 期)。
⑦ 《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卷1《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上册,第278 页。按:钱曾在注释中多使用称谓词“谦益”,诗注极有可能是钱谦益自为。
⑧ 钱谦益的友人沈守正也在《署中怀人十绝》中写道:“编修钱受之谦益,虞山人,迹潜誉远,是将出矣。”
⑨ 《投笔集》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有裴世俊《〈投笔集〉初议》(《苏州大学学报》1998 年第1期)、孙之梅《〈投笔集〉的结构艺术》(《山东大学学报》1989 年第4 期)、龚艳《〈投笔集〉研究》(暨南大学2006 年硕士论文)、李欣锡《钱谦益明亡以后诗歌研究》第五章“记录时事,感慨兴亡——确立诗史的地位”(台湾师范大学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第四章“一生诗歌集大成之作——《投笔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严志雄《钱谦益的“诗史”理论与实践》下编“投笔从戎:钱谦益《投笔集》诗史之作论析”(中华书局2019年版)等。本文特别关注的是钱谦益反清复明的心路历程及其中隐含的自我形象塑造。
⑩ 参见:谢正光《清初士大夫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78—80 页;叶晔《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南京师大学报》2016年第3 期。
⑪ 钱谦益诗曰:“上为刘伯升,下为李元礼。”(《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卷8《后饮酒七首》)钱曾亦以李膺称之,如“江左龙门惭奉袂,诗坛轩翥许谁同”(《钱遵王诗集笺校》)。清代汤修业称牧斋:“初年楷模李元礼,晚岁官阶褚彦回。”(《赖古斋文集》卷3《书某公诗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