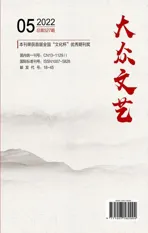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梅州香花佛事舞蹈研究*
2022-03-22彭媛
彭 媛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广东广州 510500)
“香花”二字,笔者翻阅了相关书籍,查到了如下的解释:“香花(华),普遍出现在佛教典籍中,具有功德供养的含义,在佛教经典中,手执香花、长跪合掌,往往是佛徒善信礼敬请法的开始;……香花的原初含义应主要指有香味的花……”;“在佛教《大疏演奥钞卷一》中,这两个字并不组成一个名词,而是单独解释:‘香’为精进之义;‘花’为万善之行。‘香花’由此可解释为:精进万善之行。”由上述文字可知,“香花”与佛教中的“供养之法”“善举之行”有关。
梅州客家普遍信奉佛教。据《梅县志》载:“佛教传入梅县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为了宣传教义,寓化于人,产生了“变文”“宝卷”等佛教文学。但由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有不同的流派,地域不同、方言不同,因此由“变文”“宝卷”而产生了不同的名称。而客家地区,“变文”“宝卷”发展成了“香花”。
那么香花佛事,应是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一个族群、一个民系的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兼容佛教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的文化新实体”。
在香花佛事中,涉及舞蹈的仪式主要有四个,分别是:“打席狮”“鲫鱼穿花”“打铙钹花”“打莲池”。“打席狮”在似狮与非狮之间充满了审美意趣;鲫鱼穿花与打铙钹花的技艺形式之美让人流连忘返;而打莲池则因其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而显得意蕴深长。四个舞蹈各有特色,它们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带着民俗民间舞蹈特有的质朴与灵动,在当代审美的视角下应赋予崭新的意义。以符号学的理论为基石,探索香花佛事舞蹈的艺术文化价值,取其形、传其意,在传统与现实的交融中让民俗艺术瑰宝得以传承与发展,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不同于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符号学理论,20世纪另一位研究符号学的大师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以逻辑学为基础,强调“三分式”的理论。他将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像似符”是第一性、“指示符”是第二性、“规约符”是第三性。当然除此之外,皮尔斯的“三分式”还有其他的分法,比如“质符”“单符”“型符”;“呈符”“述符”“议符”。这让我们想到了中国哲学中道家的至理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皮尔斯对于符号运动的无限衍义的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的“终而复始”“循环往复”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了上述的相通之处,相信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来研究中国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不至于会“水土不服”。
一、“打席狮”像似性的审美意趣
符号化的第一步,实际上是比拟模仿。这里的像似性似乎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的形式,但这个形式是纯粹的形式,它不应该带有意义。当然,形式与内容是相互依存的,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皮尔斯在其著作中也说过符号的三个性质在一起,才是完美的符号;而在这一篇章中,我们就仅仅论纯粹的形式。
上文中提到的比拟模仿,正是“打席狮”的审美形式特征。“打席狮”中的狮子是通过一张草席摆弄而成,具体做法是将草席用五指卷成“狮头”状,模仿狮子的行走跳跃进行表演。而这里的狮子是非常“直观”的形象,可以说是一种“纯像似符号”;它不依赖于任何意图,只是单纯表达狮子的形象。这似乎就是视觉艺术对比逻辑语言的一个优势,在像似符与其对象“退化了”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审美距离感,而这种距离感因其无法“直接言说”而让符号最终的解释项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
第二个距离是空间距离,符号表意需跨过一定的空间,这样意义和符号就不会同时在场;“意义充分在场,就不需要符号”。
第三个距离是表意距离,符号不能等同于对象;若是两者之间的等号成立,那么这两者就是同一物,而不需要所谓的“替代”或是“再现”,符号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二、“毫光指”和“禹步”的指示性特征
在皮尔斯的三分符号系统中,像似符因自身的品质而存在,就算对象不存在该符号也不受影响。而指示符恰恰相反,若失去了对象,那么代替该对象的符号也不存在,这也是指示符不同于像似符与下文中的规约符的特征。皮尔斯对于指示符是这样定义的:“一个符号可能存在这样一种事实:它能够代表其对象的那种实在关系,而这种事实应当作为它的表意特性。那么,对于任何解释项来说,它就可以充当那个对象的符号,通过直接地反映对象来再现这个(对象)。这种就是指示符……”。因此,指示符受到对象的影响,又可以代替对象。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红绿灯、公共场所的指示牌、专业名词“黄河”等,都是指示符号。红绿灯代替了交通秩序,假如当交通呈现出一种永远不拥堵、人车和谐的理想状态时,那也就不需要红绿灯了;但就目前来说这种状态不存在,因此需要红绿灯来维持交通秩序。
在香花仪式中,一些固有、独特的手诀和步伐,因其指示性特征而为整个仪式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如“毫光指”和“禹步”。“毫光指,即将中指、无名指弯曲,用拇指相抵,食指、小指伸直,单手为‘单豪光指’,双手为‘双豪光指’……在‘打莲池’的仪式段落中,毫光指被运用结‘打’‘破’‘地’‘狱’四种手印,用右手无名指在珠杯上画‘吽’字(黑蓝色之大圆镜智光,净除地狱中之瞋恨,断除热寒苦),表演中香花僧(斋嫲)会用右手无名者在珠杯上画‘吽’,表示金刚部心,是祈愿成就的意思……”。“打莲池”主要叙述的是目连用佛所赐的九环禅杖打开地狱之门营救母亲,豪光指结印出的“打”“破”“地”“狱”共同指代了这一故事情节的主要事物和行为,加上舞蹈肢体的运用,让人产生联想,联系起整个“目连救母”的故事。这四个指示符号共同完成了对象与观赏者之间的“交流”,它们“一方面,与个别的对象存在一种动力学(包括空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这个对象所影响的符号——“毫光指”,是佛教手诀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系统符号所反映的对象是“用手势动作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与祈福求安”,人们在观赏“打莲池”这个仪式时,若受到后面一个对象的影响,将产生一种更大的情感世界观,这个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的连接,也就是下文中所提到的符号运动。
在香花佛事中,另一个舞蹈节目“鲫鱼穿花”,则是运用了禹步,形成了变化无穷的队形美,以体现西天快乐无忧之景。相传禹步为夏禹所创,“因其步伐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而禹步除了营造一种形式之美外,其步伐更是带有独特的意指性。禹步斗罡,共有九步,各有其象征意义。《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说:“一步象太极,两步象两仪,三步象三才,四步象四时,五步象五行,六步象六律,七步象七星,八步象八卦,九步象九灵,万罡之祖也”。
“象数”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符号,它是数字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自然宇宙与人文审美的结合,它带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比如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里面多次强调了“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由“一”到“十”的每个数字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一”为万物之始,是无穷、是太极、是“道”、是“天一”;“二”可为两仪、可谓阴阳;“四”化为东、南、西、北四方,春、夏、秋、冬四时……每一个数字后面都隐藏着“象”,它们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天文、礼仪、艺术、医学等多个领域。中国古代先贤们通过“象数”拨开了茫茫宇宙的神秘之光,让生活变得有序而多彩。
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于《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极数概》中引其老师王宣的话说:“物皆数也,数皆理也,圣人不违物理,故天不能违圣人,极数知来,如屈其指。然圣人至此罕言,因数付数,犹因物付物”。圣人言不尽意,故托至于“象”,而“数”为“象”的抽象,让一切事物变得竟然有序。这不正如皮尔斯所说:“指示性使对象集合井然有序”。
指示符所指称的对象往往是符号所代表事物的一部分,但接收者却可以通过感觉与记忆,在接收到符号时于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象。舞蹈作品中合理地运用指示符,可如“管中窥豹”“庖丁解牛、未见全牛”,由局部看到整体;在保持舞蹈作品“欲言又止”的意境时,又充分地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在多人舞《壮士》中的一面大红旗指示着浴火的战场;舞剧《花木兰》中的《铜镜舞》,在特定语境之下的镜子,指示女红妆;舞剧《薪传》里面的跺脚动作,指示“开垦”;舞剧《倩女幽魂》里面的拂尘指示道士……舞蹈艺术作品运用逻辑的思维以及经验的联想,在对象与观赏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完成了作品中符号的指示功能。
皮尔斯指出,一个完整的指示符,它可以包含着像似符。按照皮尔斯的理解,这样子形成的符号可以是“像似——指示符”,在“打莲池”中,用拇指、食指、中指直立成“鼎指”,用手势代替施食。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个公告牌上画着一根燃烧的烟头和在烟头上的×字,我们立马会想到这个公告牌是“禁止吸烟”的意思,在这里画着的烟头就是像似符,而整个牌子的图画构成了指示符。再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用快步与伞代替下雨;蒙古族舞中用揉臂的动作代替大雁;在舞蹈作品《小溪、江河、大海》中,用白纱及碎步代替“小溪”“江河”“大海”。
三、香花佛事舞蹈中的传统文化规约性内涵
符号——对象——解释项,与像似符和指示符不同的是,规约符受到解释项的影响,若没有了解释项,那这个符号就不成立。而且这个解释项为众人所理解,是一种社会法则。因为规约符不是指称个别的事物,它是一般类型;规约性让符号表意准确有序。例如“龙”指称华夏民族的图腾;“男”“女”“man”“women”指称性别之分;这些是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在社会中早已约定俗成的事实。但倘若我们无法理解“男”“女”的概念,那么这两个符号就不成立,因为它们无法被解释。
一个规约符的范围小至一个群族,大至全人类。因为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尽管符号的规约性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一样,比如上文说的“男”“女”与“man”“woman”,就是符号同样意义的不同社会规约性体现;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实现规约符的彼此认同,实现“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共同诉求。
梅州客家的香花仪式,历经千年传承,已经形成了追悼亡者、传递孝义的规约符号。香花仪式中的“打莲池”,其内容来源于佛教故事《目连救母》,客家人通过仪式再现《目连救母》的故事,整个过程寄托了客家人对逝者的追思以及对勤劳质朴的客家女人的颂扬之情。舞蹈“鲫鱼穿花”是模拟西天快乐场面的歌舞,由香花僧(斋嫲)扮演仙人,通过舞蹈来传递孝者希望亡者能在西天得享安宁的真切心愿。“打铙钹花”是属于闹坛的一种形式,属于香花仪式的准备阶段,主要是请来各路神仙、仙人、亡灵参与仪式当中。“打席狮”的目的一是调节仪式中的气氛,二是承担着敬神驱鬼的功能。这四个舞蹈,以其鲜活的艺术形象,不仅使人们在烦琐冗长仪式中的疲惫得以舒缓;而且其“寓教于乐”,更能使人们产生“移情”作用,达到“追思悼念、祈求平安”的仪式效果。
房学嘉在《围不住的围龙屋》一书中对香花民俗的表述说:“香花完成了一个亡者在形体消逝后进入后代记忆行列的进程,同时也成为人们开始正常生活的微妙表达,它已经不是纯粹的‘阴事’,而真正成了旧人仙逝之后一代新人与屋外的世界进行关系调整,人际交往的开始”。举行香花仪式是客家人孝道之举的体现,人们希望通过仪式来纪念亲人,为逝者颂德祈福。香花仪式正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与佛教形式相结合,把不可言说之情转化为可见、可感的艺术形式,实现了在生者的精神诉求。通过仪式,跨越了生死的界限;通过艺术手段,使文化符号得以传递。
“孝义之道”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粹,传承千年、历久不衰。这种精神已深入骨髓,在梅州地区,客家人愿为已故长者做一场香花仪式,已延续生前的“孝道”。这是客家群族的记忆,通过代代相传,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个符号可以说是“先验”的,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记忆。
集体无意识,是由荣格所提出来的,是指一种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远古祖先的种族记忆。荣格认为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是原型:“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这些形象给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以形式”。而这种先验的、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其解释项是群族缔造的结果,不以个人为转移。比如说非梅州客家人看一段席狮舞,觉得非常有趣,是一种集合了高难度技艺的纯表演性舞蹈。而当地人却告诉他席狮舞本来是在丧仪中穿插的表演,为的是缓解仪式上的悲痛之情,并驱凶避邪,在寄托哀思之情的同时祝在世之人吉祥安康。不管他接受这个解释与否,席狮舞的内涵不会变,因为在客家人的心目中它就是约定俗成的所在。就如同皮尔斯所说的:“你可以写出‘星’这个字,但这不能使你成为这个字的创造者,即便你擦掉它,也不会消灭这个字。这个字存在与使用它的那些人的心中,就算是这些人都睡着了,它也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
小结
从“打席狮”的具象感知,到“打莲池”手诀与“鲫鱼穿花”步伐的经验理解,最后到香花仪式舞蹈内涵的抽象概括,这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三种符号的各自意指,也有三种理据性的完美汇合。而这个过程是不断前行且趋于无限的,因为人不可能停止探索的脚步,正如《序卦传》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随着未来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香花佛事舞蹈必将跟随时代的步伐,“变则通、通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