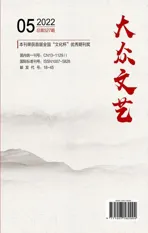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经验”与“形式”视域下的快乐情感与审美起源*
2022-03-22马正应
马正应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艺术、审美与快乐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不管其中夹杂着多少复杂情感,审美体验最终都指向审美愉悦,都以快乐为目的。快乐是古今中外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人类的永恒追求,钱穆更是强调“乐”对于人生、艺术的地位和意义:“乐则人生本体,当为人生最高境界、最高艺术。”然而,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与审美情感的关系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而言人人殊。
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原始人在狩猎时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在他们狩猎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野蛮人在自己的舞蹈中往往再现各种动物的动作……只能解释为想再度体验一种快乐的冲动,而这种快乐是曾经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而体验过的。……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舞。”实际上,原始人在狩猎时,由于武器及其他工具的简陋,所遭遇的猎物可能比较凶猛,他们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必须随时提防猎物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狩猎活动中不可能产生快乐感情;即便是面对没有多少威胁的狩猎对象,也须全神贯注于捕捉活动。更何况,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随时面对着神秘而变化莫测的大自然,在这些充满斗争和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伴随着鲜血和死亡的残酷的劳动中所产生的,只能是紧张、压抑甚至恐惧、刺痛等情感而不是别的。
“审美的敌人既不是实践,也不是理智。它们是单调;目的不明而导致的懈怠;屈从于实践和理智行为中的惯例。一方面是严格的禁欲、强迫服从、严守纪律,另一方面是放荡、无条理、漫无目的地放纵自己,都是在方向上正好背离了一个经验的整体。”按杜威的这一观点,狩猎活动是一个实践的事实,也是理智的行为,故而不能排除审美和愉悦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狩猎者至少必须“屈从于实践和理智行为中的惯例”的,是“强迫服从、严守纪律”的。因而,普氏所谓“这种快乐是曾经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而体验过的”即认为狩猎时是快乐的,似乎无从谈起。
也因此,狩猎舞是对动物动作的模仿,普氏这一判断虽然没有完全颠倒因果关系,却在情感上将其产生的原因看作是对狩猎期间所产生的快乐的再度体验。马克思断言:“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活动来享受。”从原始狩猎和过程上说,快乐情感的产生只能是在劳动之后,经过艰苦的狩猎,成功获得劳动成果,身心放松下来,只有在这个时候,快乐才会油然而生。据医学研究,劳作、动作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和吸收,而多巴胺能使人产生兴奋、开心等快乐情绪,当然,这是指身心放松而非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如此说来,原始人的确是在“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的情况下进行狩猎活动的模仿从而创造了狩猎舞,但需注意的是,这种快乐是在狩猎之后产生的而非狩猎之中产生的,只有在脱离了狩猎的时间和空间,处于安全、舒适而休闲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时候,才可能是快乐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狩猎舞。
当我们“走完历程而达到完满”,诸如完成一件作品、解决一个问题、吃完一餐饭、下完一盘棋等活动,就拥有了“一个经验”:“这一个经验是一个整体,其中带着它自身的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原始人完成某次狩猎活动后获得了“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所产生的情绪可能是紧张的、压抑的甚至是恐惧的、刺痛的而不一定是快乐的,但在这个经验之后产生的情感必然是快乐的——普列汉诺夫所谓“再度体验”的对象或许并非“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而是狩猎之后产生的快乐。这一后续性快乐可以看作是狩猎活动这一经验在情感上的最终结果,换言之,当我们把作为结果的快乐情感纳入狩猎活动这一经验时,这一经验才具备了一定的审美因素从而真正形成一个完满的、绵延的“整体”经验,并由此达成整个经验的“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
原始人在完成这一经验后,为了快乐情感的体验而创造出狩猎舞,这可以看作另一个经验。这一经验与前一经验完全不同,不再有斗争和冲突,所处的是安全、舒适而休闲的环境,故而不再有前一经验的负面情绪。它是对前一经验的再度体验:可以想象,原始人要么在回忆中升起欣赏之情而产生快乐情感,要么在狩猎舞的形式中直接产生快乐情感。但无论如何,它不同于前一经验的所谓后续性的快乐,它是直接的、全身心的快乐。快乐情感与这一经验是合而为一的,而且这种快乐情感在本质上已经是审美的愉悦了。
故而,以上两个经验又可以合并为“一个经验”,一个整体的可欣赏的经验。前一个经验充满斗争和冲突而且是痛苦的,但它是后一个经验的铺垫、积累和背景,有了前者才会有后者;后一个经验以前一个经验为内容,这时,前一个经验的斗争和冲突已经成为过去,痛苦不再,故而可以成为被欣赏的内容,有了后者才会有前者的情感意味。如果说前一个经验是内容,那么后一个经验则是形式;如果说前一经验侧重于劳动,后一个经验则偏重于艺术。二者共同形成一个完满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经验中,每个相继的部分都自由地流动到后续的部分,其间没有缝隙,没有未填的空白。与此同时,又不以牺牲各部分的自我确认为代价。”艺术,或者说艺术形式,从来不是无中生有;审美愉悦同样如此,它产生于史前的实用性快乐的积淀并始于其形式上的消融。
再看另一种劳动:“今夫举大木者,皆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淮南子·道应训》)鲁迅应之以“杭育杭育派”。喊着“邪许”或“杭育杭育”的号子,一方面是为了大家的身体运动的一致协调,另一方面也是为着自己身心的协调。先民们扛起木头喊着号子,自然地形成了一种音乐、文学或舞蹈的形式。喊号子是为劳动之需,其“举重劝力之歌”是无意形成的;只有用“记号留存了下来”,才会成为音乐、文学、舞蹈等艺术。就前者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搬运很重的木头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实际上就是与神秘而变化莫测的大自然作斗争,是无所谓快乐的——当然并不排除在号子的作用下因身心协调从而获得快乐的情况。就后者而言:当他们在抬木头的劳动结束即完成了这一经验后,为了快乐情感的体验而模仿这一劳动的形式,创造出音乐、文学或综合艺术。他们要么在回忆中升起欣赏之情而产生快乐情感,要么在艺术的形式中直接产生快乐情感。其中的形式可能没有任何记录留存但却“等于出版”,可能“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而成为最初的艺术,但无论如何,在其中都有快乐情感、审美愉悦的留存。
普列汉诺夫记载土著部落巴戈包人从事土地耕种的场面:“在种稻的日子里,男人和女人一大早就聚焦在一起,着手工作。男子走在前面,一面跳舞,一面把铁镐插入地里。”男子边劳动边跳舞的情形类似于前述“邪许”与“杭育杭育”例,艺术与劳作在其中似乎是一体的,但它还不是真正的艺术,即便其中存在着快乐情感,却也是与劳作混沌不分的。就劳作者而言,虽然它是一个完整的经验,却不一定是审美的经验。只有这种劳作在其事后以艺术的形式留存下来,形成丰富而整一完满的“一个经验”,快乐情感、审美愉悦才得以呈现出来。
格罗塞详细地研究了舞蹈与快乐的关系,他认为,藉外表的动作来发泄内心的郁积,总是快乐的,舞蹈因激烈的运动少而规则的动作多而具有审美的性质,演者和观者注意到的是舞蹈的合节奏的规律,他们能够从舞蹈中能够得到节奏的享乐,“原始人类无疑已经在舞蹈中发现了那种他们能普遍地感受的最强烈的审美的享乐。……澳洲人围绕着他获得的战利品跳舞,正和儿童围绕着圣诞树跳跃一样的。”在情感性质的角度上,如儿童般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发展阶段,原始人围绕着获得的战胜品,激烈而不超过一定限度(不至于疲劳)地的庆祝的动作(还不能称为跳舞,而只是舞蹈的准备)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是实用性的快感而非审美愉悦。随着人类由“儿童”至“成人”的向前发展,这些动作慢慢脱胎出来,积淀为形式而成为舞蹈后,他们作为“成人”在有节奏地重复这些形式时也仍然是快乐的,无论是操舞还是观舞也都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不再是实用性的快乐而是审美的享乐了。从关系上说,前者(第一个经验)是对后者(第二个经验)的触发,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升华和质变。
二
普列汉诺夫以北美红种人用油脂擦身体的习俗为例讲装饰的起源问题,并引封·登·斯坦恩《在巴西的原始民族中间》的分析:“快乐是装饰的基础,正如过剩力量的积聚是游戏的基础一样;不过,那些用作装饰的东西最初因为它们有用才被人知道。”普列汉诺夫总结说,原始人用彩色黏土涂抹身体的习俗最初是因为这是有益的,如具有避免蚊子咬伤等功用,“后来逐渐觉得这样涂抹的身体是美丽的,于是就开始为了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起身体。”至于是如何从“有益”转向“美丽”和“审美的快感”,普氏在这里没有进行详细阐释,倒是斯坦恩的说法很有启发性。综合起来并运用于一般情况,其转向和发展的内在线索可作如是描述:第一步,有用使人产生实用性的快乐即快感;第二步,由于快乐本性的驱使,实用性的形式慢慢积淀下来,形成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装饰;第三步,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形式的功用性慢慢消融,实用性的快乐同样也慢慢消融;第四步,形式完全成型,成是审美的形式,积淀下来的实用性的快乐成为审美的快乐。因此说,“快乐是装饰的基础”,并且前者先于后者,只是在后续阶段,在审美的形式(这里指“装饰”)中,这种快乐(实用性的快感)已经不为人知,悄然转变成了审美愉悦。
同理,“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就是有力的人。”获得丰富的猎物后,以其皮、爪、牙齿、角等轻便而直观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灵巧、有力,不管是为了威慑、吓退敌人的目的,还是为了以之宣示勇敢的战斗精神而取悦妇女或获得更高地位的目的,在这些行为中,特别是在取得成功后,他们必然是快乐的,这些装饰也就慢慢地演变为美的装饰、美的形式,这些劳动的、实用的快乐也慢慢地演变成审美的愉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内容的积淀,其实用性的目的逐渐转变为审美的愉悦或者说为其所取代,进入后人们的潜意识里。格罗塞所述以很多条白兔子尾巴为腰饰,不仅是动人的、叫人欣羡的,而且还象征着佩戴者的技能,同理可证。
中国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较早,故而在文化源头及其影响上,中国农耕文明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大于狩猎。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中国在那个时代的显著标志。古人在第一次偶然发现火堆中熔凝的硬泥,受到启发而烧制出陶器的时候,当然是快乐的,但这并不完全是审美愉悦;同样,在因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而最多只能生产出仅具备基本实用功能的陶器的阶段,古人制作陶器和观看陶器均停留在实用阶段,他们或许是快乐的,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审美愉悦。陶器具有盛水蓄水、存物储粮、炊食饮食等功能。以盛水为例,在未发明陶器之前,古人只能用双手掬水饮用或以其他比陶器更简陋的方式盛水,在这种情形下或更早之前,水这一自然物在他们眼里是不可战胜的。席勒甚至认为,内容对精神起限制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只有在沉重的和无定型的物质占统治地位、晦暗不明的轮廓在不确定的界限内摇摆的地方,畏惧才有它的地盘。自然中的任何令人惊恐的东西,只要人懂得给它以形式,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对象,人就能胜过它。”或许,以手掬水等方式也是一种形式,但只有发明陶器之后,水才被完全地赋予了形式,成为人类认识和审美的对象而不再是“令人惊恐的东西”。
人类未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与宇宙自然这一母体处于混沌的和谐状态;从这一母体里分离开来后,他们天然地具有修复这一距离甚至隔阂、向母体回归的心理趋向,对原始和谐、对大地母亲的回忆成为一种“乡愁”。农耕先民们向土地获取生活资源,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最为亲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生夏长实秋收冬藏,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节律无不息息相关、和谐相应。据考证,古代“樂”字在结构上与谷物、食物有关,是对农耕收获的庆祝和喜悦,而且,“‘樂’字在远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已不单单是表面上获得一种谷物成熟的视觉印象,而是对耕种、收获的不易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一种喜悦心情。”除此义之外,其原初义众说纷纭,或云地名,或云养蚕栎树,或云祭祀乐舞,或云乐器或音乐,但无论哪一种,都是从原初的人类活动特别是农耕活动引向喜好、快乐、愉悦的心理情感。
仍以古人联系大地母亲的典型形式陶器为例。通过陶器这一形式,古人与大地母亲的联系和和谐关系更近了一步。有了这一形式,与其实用性相关的自然物不再与人对立,不但不再是“令人惊恐的东西”,而且是与人和谐统一的对象。神秘而不可知的自然对象被装进这一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的“形式”之后,人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不再受其压制,而是通过这一形式和谐运行,紧张、压抑甚至恐惧、刺痛等情感不再。因而从广义上说,无论原始阶段的陶器多么简陋,由于其“形式”的定型及其定型对于和谐关系的反映,它的发明、制造、使用和观赏本身就有着审美的愉悦。
从“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一阶段看作第一个经验,那么向着完美形式发展的阶段便可看作第二个经验。在第二个经验中,人们在意识到第一个经验里的陶器的“和谐”内容时必然是快乐的,虽然这种快乐不一定是审美的愉悦;人们在意识到第一个经验及第二个经验里的陶器形式时必然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一定是审美的愉悦。第二个经验以第一个经验里的内容为的铺垫、积累和背景,在第二个经验中人们或许可以从美的形式直觉到第一个经验的朦胧的内容,或许甚至连朦胧的内容都意识不到,因为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已完全积淀在或消融于美的形式中,如水之在盐、花之在蜜,此亦所谓“集体无意识”。同样,面对美的形式,认识与情感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在这种交织中,认识已浸润在情感之中,被情感所融合。换言之,第二个经验是审美的经验,虽然它基于第一个经验,却不必认识它而只要面对美的形式就够了。
可以看出,第一个经验和第二个经验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整体经验。“情感是运动和黏合的力量。它选择适合的东西,再将所选来的东西涂上自己的色彩,因而赋予外表上完全不同的材料一个质的统一。”杜威所说的这“一个经验”,对人类整体经验即前述两个经验的融合来说也是合适的。在这两个经验中,所有的或相同或不同的材料和内容因情感而达成“一个质的统一”,情感成为这两个经验的一以贯之的力量和红线,由此形成一个丰富而整一完满的经验。就陶器而言,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材料和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因审美情感而合成为一个整体,而且这一个整体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材料和内容在其各自历史阶段的特性,只是或显或隐而已:美的陶器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材料与内容,主体所感受的是这些材料与内容以及隐于其中的甚至感官感受不到的快乐情感,最终形成审美愉悦。
总之,在第一个经验中,原始人把某种自然物装进某个“形式”里,就已经开始把握这个自然物进而把握这个世界,就已经开始产生快乐情感和朦胧的审美意识;当这个“形式”积淀下来成为抽象的形式,在这第二个经验中,实用性的快感逐渐消融而审美意识逐渐凝结并最终突显出来,其中,审美意识是明确的、有序的,而功利快感是朦胧的甚至是不能觉察的。一般形态的陶器与快乐情感的关系如是,陶器上的纹理、图案等装饰以及其他艺术的装饰形式同样如是,只是形态上更为抽象、更为复杂,在源头上也更加难以探索。一般形态的陶器的形式,如前所言,取决于泥土这一物质,取决于与大地母亲的亲和内涵;其上的纹路、图案,或如格罗塞所言,来自对编织物的模仿。更先进的陶器如彩陶上的形式以及除陶器外的其他美的艺术的纷繁复杂的形式,取决的物质当然亦各有不同。“羊大则美”与“美人为美”从味觉快感与视觉愉悦中透视出美的形式及其中的社会意义内容和善的意味;“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一上古歌谣本就是对先民狩猎场面的描述,对艰辛的回忆、“乡愁”的治愈本就是快乐的;史前岩画的鲜明物象,青铜器纹饰饕餮的“狞厉”之美,石器由粗糙到光滑再到装饰造型的历史绵延,汉字由“上古结绳而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到书法的独特演变,无不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感性形式中、在形式与意味的双重规定和辩证关系中蕴涵着无尽的审美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