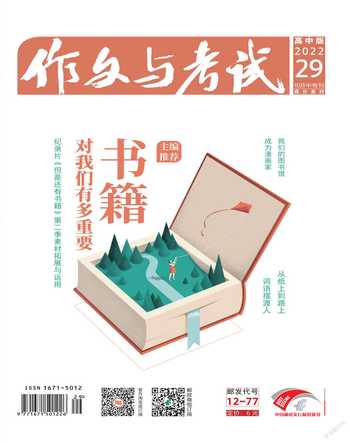书籍对我们有多重要?
2022-03-20刘小俊李木西
刘小俊 李木西
策划:本刊编辑部
日前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数字化阅读倾向明显,受访人中有77.4%进行过手机阅读,71.6%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27.3%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随着数字终端不断承载人们的阅读需求,传统出版业似乎越发艰难。所幸,仍有许多爱书人坚守于此。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便记录了那些可敬可爱,对书籍怀抱热忱的编著者、创作者、爱书人,展现出他们丰饶有趣的精神世界,定格下这个时代烂漫动人的阅读风景。
当“阅读神器”Kindle退出中国倒计时正式开启,当实体书店纷纷倒闭,当读屏成为大众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依然相信深度阅读的力量。就像纪录片里讲述的那样:“时代的浪潮被一个个具体的人所吸收,成为命运,成为文学。”读书,有着让我们与时代共振的力量。
我们的图书馆
图书馆,是一个城市最安静的角落,却踊跃着最活跃的思想。它保存着文明的火种,也滋养着未来的新知。它是一些人休憩心灵的桃花源,另一些人眺望世界的窗口。
“书是水,我是鱼”
版本目录学家“古籍活字典”沈燮元,退休三十年后仍在为自己未尽的事业忙碌着。他形容自己和图书馆的关系是“鱼和水”,他像鱼一样在图书馆里“游”了一辈子。善本编纂枯燥且需要极大的耐心,但沈老甘之如饴,一做就是十八年。在全靠手工的年代,沈老与四十位研究员整理了几十万张古籍卡片,认真查阅修改错漏。2008年,他们编写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索引》出版,成了 “最具权威性的古籍善本联合目录”。之后,闲不下来的沈老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新工作计划——整理出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题跋集。如今的他已经98岁,除了睡觉、吃饭、喝茶,剩下的时间都手捧着书。他说,他的生命是和书连在一起的。
让草原孩子看到未来的更多可能性
对身处四川甘孜的孩子们来说,书籍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还是他们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在外游学多年的藏族僧人久美,回到家乡后发现这里的孩子们往往从小辍学,复制着祖辈的生活轨迹。2014年,久美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了一座藏式图书馆“纳朗玛”。藏族女孩拉姆是图书馆的常客,她最喜欢看《巴黎圣母院》,觉得书中主角卡西莫多很像自己。阅读让拉姆与百年之前、千里之外的作家雨果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在此激励下,她坚持用藏语写作,并如愿考上了大学,一直为她的翻译和写作梦而努力。一座图书馆,打破了知识的疆界,消弭了阶级的壁垒,成为孩子们望向更广阔未来的窗口。
微评:读书改变命运,不应该作为功利主义的简单解读,而是内心深处的觉醒导致视野的改变,从而走向更大的世界。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潜心读书是一种坚持。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成为漫画家
漫画里有侠客,有怪物,有未来世界; 漫画外只有一个人,一支笔,一张桌椅。用方寸大小的格子,创造出整个世界的人,被称为漫画家。
初心不改,终能创造奇迹
许先哲从未接受过正统美术绘画训练,决定创作漫画之后,他练习了4年。26岁的他以一无所有的状态,开始筹备《镖人》漫画。他通过翻阅《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在历史中寻找根基。他的创作方式属于角色对话式的分镜法,需要很强的专注力,这也是《镖人》受欢迎的秘诀:角色在许先哲手下,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因此显得有生命感。为了让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许先哲的更新速度越来越慢,但他宁愿被读者抱怨,也要选择那条更艰难的路。凭借严谨的态度与过硬的质量,《镖人》漫画已发行10本单行本,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并且以国漫崛起之姿强势输出到海外,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级水平的中国漫画精品”。
坚持创作,只是因为有趣
匡扶,是漫画自媒体“匡扶摇”的创作者,出版了漫画合集《回答不了》与《纳闷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漫画家,“只是恰好做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像漫画”,故事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作”。热爱生活的他,總是喜欢从普普通通的日常中,找到出人意料的闪光点。那些日常的琐碎,被他细腻地描述时,就拥有了各自的意义,也吸引了许多有共鸣的读者。除了花费心思设计故事情节,他还会细致地去琢磨文字,研究画面细节。正是因为他对这些小细节的严格把控,才创作出了那些独立而充沛,有生命力的人物角色。在他看来,创作不是因为有多强的表达欲,或者要传递给这个世界什么,只是因为它“有趣”。
微评:真正地去“成为”——不管是漫画家或是别的什么——都需要一个人有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的信念。这是一种匠人式的执着,可能甚至是带了傻气的执着。
词语摆渡人
翻译,词语的搬运工、文化的摆渡者,他们被誉为盗取天火救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也被视为文学界的苦力,他们在一字一句的爬梳中,更新着语言的艺术,重建起打通世界的巴别塔。
在书中享受魔法乐趣
从《绿山墙的安妮》,再到《彼·得潘》《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绿野仙踪》等等,作为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马爱农将翻译做为一种心灵上的享受,她不断用翻译的方式重塑着纯真的感动。她的《哈利·波特》中文译本陪伴了无数人成长,让许多中国孩子也期盼能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在翻译《哈利·波特》过程中遇到过很多难题,她都仔细求证。她说:“翻译需要很严谨,把心灵放得很平静,深入到作品中去。”翻译是将不同语言的伟大文学作品连接起来的桥梁,也是全世界的读者心心相印的凭依。作为译书人,马爱农用勤恳踏实的态度,为作品负责、为读者负责的情感,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真梦境。
读书是忘我而无用的专注
如今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的包慧怡,业余进行诗歌翻译。她真正的翻译之路,其实是从一本诗集开始的。在经历一次巨大的精神危机时,她意外读到了诗集《爱丽尔》,产生了巨大共鸣,于是开始尝试将其译为中文,一做就是七年。从事翻译所需要的专注,让她体会到了一种“完全没办法被剥夺的幸福”。后来,她又翻译了十多部巨作,在这个过程中,她自身如一颗矿石般,在冶金炉中得到锤炼。包慧怡常常问自己,“我的翻译可以为我的母语带来什么”?她说,“白话文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语言,我们可以从文言文里汲取源泉,我们也可以从西方的翻译文本里面为它汲取不同的风格和新的动量,看看它能在我们的中文里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对包慧怡来说,翻译工作是发乎本心的专注,是对时间本身的克服。
微评:中外互鉴,语言为桥,美好的作品离不开译书人的努力。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建立在译书人的辛劳和智慧上。
从纸上到路上
时代奔涌向前,每个人都昂首面向未来,但总有人时时转身朝向过去。从纸上到路上,他们从废墟上重拾记忆,召回那些已经消逝的风景和声音。
重历联大西迁,写书才能安放自己
2018年,作家杨潇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以徒步为主,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南迁长沙。1938年,他们决定分三路再迁昆明。其中“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迁校的学生们面对内心的煎熬:读书还是参战?留守还是西迁?杨潇带着当年数位同学的日记重走这条路,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内心转换的过程,“我去不了战场,但是我走1600公里的路,然后到后方坚持我的学业和研究,来日方长,这也是一种救国。”重走这一路,也是杨潇在自我困境中思考人生道路的过程。回来后,他用了两年多时间写成《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在战火纷飞下,那代青年通过行走解决了内心困顿,而杨潇通过行走,解决了自己当下的种种顾虑与彷徨,“最后发现,可能还是要写书才能真正安放自己。”
《海错图》,穿越时空的对话
清代画家聂璜绘制的《海错图》,以生动的图画和文字记录了三百多种海洋生物。初中时张辰亮看到《海错图》,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年,他开始了还原一个科学版《海错图》的计划:从生物学的角度解读清代图谱中的生物密码。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他一次次踏上旅程,远赴辽宁、福建、广东、广西、天津甚至日本、泰国等地搜集素材、实地考证,编写成了《海错图笔记》。这个《海错图》的疯狂读者,还有另一个身份,微博知名科普账号“博物杂志”的运营者——无所不知的“博物君”。在考证《海错图》的时候,他没有一味介绍古代人,而是关注现代人跟海洋生物的关系,“我们老说中国就没有什么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其实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沿海。”在写完第4本《海错图笔记》后,这段破译之旅告一段落,但后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仍在继续。
微评:我们对书籍的理解,从来不只是文字的简单堆砌成册,而是一个延伸自我、延伸生命,找寻人类的思想、边界与可能性的乌托邦。
模拟文题
阅读下面的 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朱光潜《咬文嚼字》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
一切经得起再度阅读的语言,一定值得再度思索。——美·梭罗
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马南邨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东晋·陶渊明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南宋·陈善
关于读书之法,古今中外有许多警言灼见广为流传,读了以上六句,你有怎样的感触与思考?
写作指导
围绕“读书法”,第一则材料强调“严谨”,第二则强调“苦吟”的严谨和刻苦,第三则强调深思,第四则强调与固执一点相对的融会贯通,第五则强调发乎性情的喜好与会意,第六则强调出入法。前五则都好理解,第六则的出入法有一定的难度。第六则 “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中的“亲切”似乎是“深入、准确”的意思,强调读书时的专注和深入,共情共鸣,入乎其内;“用得透脱”里的“透脱”是“灵活”,强调不呆板,举一反三,出乎其外。甚至可以认为,第六则是对前五则的总结。
行文中,考生不应该拘泥于读书方法,应依据自己对读书活动的理解,表达当今时代下读书的意义,探索合乎时代潮流的读书方法,也可以针对当今读书风气或不良的读书方法讨论解决之道。
例文
熟读深思子自知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 严婉匀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经济发展方兴未艾,读书不再以“颜如玉”“黄金屋”等狭隘目的为唯一追求,而是我们触摸时代脉搏,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眼球经济”的裹挟下,在“全民读屏”的潮流中,“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不再是仅与自己有关的簡单选择题。我认为,今日读书,应选择经典,既要在熟读精思中“入乎其内”;又能于融会贯通后“出乎其外”,将阅读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读书要选择经典。以装订成册的纸张为媒介承载的语言文字材料都可称为“书”,而读书活动本质上是通过文字媒介与作者进行超越时空的交流,或轻松“闲聊”,或获取知识,或碰撞思想……所以,读书其实是读“人”。现实生活中我们尚且注意选择交往对象,读书活动中又怎会对制造文字糟粕的“人”敞开心扉?
“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读书应“一字不苟”,精读细品。一本好书不仅是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其本身更是语言艺术的精品。而对文字品味的深浅,不仅影响对语言魅力的领略,还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否充分领略其知识和思想精华。“谨严”的阅读态度和方式,影响着我们敏锐的文字感受能力和洞察能力。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才敢说对人生“从心所欲,不逾矩”;易中天也是在一番“咬嚼”后才能畅品《三国》,妙语连珠,发人所未发。精读,才是阅读经典应有的打开方式;“精读”,才能真正地“入乎其内”。
“一切经得起再度阅读的语言,一定值得再度思索。”读经典,应在推敲词句中浸润与沉潜,还应思深义,明大理,披沙拣金,对书籍意蕴作深入的思考。翻开《红楼梦》,除了对人物形象的准确把握外,你是否真的读懂了曹雪芹对世态人情切身体验和对“情天孽海”的无奈与悲悯?感叹祥林嫂命运的凄惨时,你又是否悟到了人物命运背后所影射的“吃人”的社会本质?深思,才是阅读经典“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
“见得亲切,用得透脱”,读书还应灵活应用阅读成果,以求“出书之道”。读书是读“人”,阅“世”也是读“无字之书”。阅读,不仅是一种积极有益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生活智慧的不竭源泉。若能在“入乎其内”之后“出乎其外”,在广阔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力证读书所获之“道”,方不失为读书的终极目的。
“书如甘蔗,渐入佳境。”互联网时代,让我们一起捧起墨香,在熟读深思中自由“出”“入”吧!
评点
文章立足材料而不囿于材料,在吸收材料中古今名家关于“读书法”观点的基础上,较充实地阐述了自己对“读书”的价值与“读书法”的理解。作者先阐述了选择经典的必要性,接着分别从“一丝不苟,精读细品”“思深义,明大理”和“灵活应用阅读成果”三个方面探讨读书的方法,中心突出,不枝不蔓,且由“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线贯穿,构思上别具匠心。而且充分注意到“读屏”时代和“眼球经济”对读书风气的冲击,针对各种读书法的误解等现实问题层层深入地表达观点,有一定的针对性。
(编辑:王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