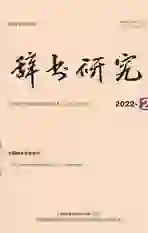论四川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变
2022-03-19张耕



摘 要 文章主要讨论四川洪雅方言复杂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变,由当前不规则的元音交替重建早期规则的词法结构。文章分析指出: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是从人称代词一般式与家义词“屋”组成的词法结构,经过合音、复元音韵腹低化、类推等音变演化而来的。结合跨方言的调查材料,文章进一步指出:定语领属结构中家庭领有者的语法化是汉语方言领格人称代词的重要类型。
关键词 洪雅方言 西南官话 人称代词 领格 定语领属
一、 引 言
(一) 四川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复杂性
四川洪雅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相比于以往关注较多的成渝片方言,其人称代词系统更为复杂。张耕(2019a)描写了洪雅方言人称代词做定语的领属结构,指出除一般三身代词“我、你、他”外,洪雅方言还有一套专用于领属的内部交替形式。这里分别称之为一般式和领属式,总结如表1:
张文主要描写了洪雅方言人称代词一般式和领属式在用法上的差别,但是这种相对异常、不规则的词形区分为什么会产生?人称代词的领属式为什么会用元音交替的形态手段表達?-əu、-ɑu又何以具备表达领属范畴的句法语义功能?洪雅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些是张文尚未回答的问题,本文则试图给出解释。
而且据笔者调查,洪雅周边方言如名山、丹棱等,人称代词同样存在相应的一般式和领属式的词形区分。赖先刚(2000)18研究乐山方言,也曾述及类似现象。这种复杂的人称代词系统应是川西南方言的共性,所以解决了洪雅方言的问题,相关方言的问题也可举一反三、迎刃而解。
(二)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洪雅方言的复杂人称代词系统,即单个语言(方言)内部的不规则词形变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是词形归一拟测法(unitary wordform reconstruction)。词形归一拟测法是内部拟测法的狭义表述。王洪君(2014)126区分了内部拟测法的广义、中义和狭义等三重内涵:广义的内部拟测法是与历史比较法相对的概念,指在单个语言内部进行的拟测方法;中义和狭义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材料,中义的内部拟测法利用的材料包括音位系统中的空格和不规则的词形变化,而狭义的内部拟测法只研究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即词形归一拟测法。
虽然内部拟测法有三重不同的内涵,但其研究理念是一致的,都认为应从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来考察演变,排除社会、文化、移民等非语言因素;异常的形态交替是由有规律的语音变化造成的,共时的不规则现象是探知历时规则演变的窗口。(徐通锵 1991;王洪君 2014)这种研究理念继承了新语法学派的规则音变论(陈忠敏 2013)57,研究任务就是找到不规则的表面下隐藏的规则。词形归一拟测法认为,当前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在历史上都是有规则的,因而不同的词形可以做语素归一处理,重建早期整齐的词法形式,并由此分析后期发生的各项音变,来解释现今可见的复杂变异。
在具体操作步骤上,Campbell(2013)199指出了运用内部拟测法的四项程序:(1) 找出存在变异的交替形式;(2) 给各种变体提出一个共同的早期形式;(3) 给出从共同来源到不同变体的变化规则;(4) 检查这些规则是否符合该语言内其他项目所共有的演变。就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张耕(2019a)实际上已完成了程序(1)的任务,本文第二部分的第一小节主要对应程序(2),第二小节主要对应程序(3)和(4),第三节则考虑更多汉语方言的材料,对问题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考察。
二、 洪雅方言复杂人称代词系统的演变
(一) 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来源及理据
我们认为,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的一般式和领属式是同源的,并非两套异源的人称代词。领属式的早期形式为“*我屋、*你屋、*他屋”(*号表示构拟的早期形式,下同),是一般式“我、你、他”与“家”义词“屋”[u35]组合而成的词法结构,当前的元音交替形式是早期的词法结构的演化结果。
这是基于词形归一拟测法分析材料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首先,提出人称代词领属式早期形式是“*我屋、*你屋、*他屋”,后期的音变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系统具体的语音演变过程待下一小节详细论述。其次,这符合“语义和谐”(semantic harmony)的要求。陆俭明(2010)指出,语言中存在“语义和谐律”,即句子成分之间存在语义制约关系,构式内部的各个词语之间在语义关系上要处于和谐状态。例如,现代汉语只有“拔出来”,而没有“拔进去”,便是因为“拔”这个词本身就含有[抽出]的语义要素,需要和趋向补语“出来”相和谐。
领属范畴包括定语领属、谓词领属和外部领属三种表达形式。(吴早生 2011)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通常只用于定语领属结构中,即“人称代词领属式+(的)+名词”,也就需要和其后被领有的名词性成分在语义关系上保持和谐。张耕(2019a)梳理了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的一般式和领属式在定语领属结构中所领有成分的不同种类,归纳如表2:
不难看出,人称代词领属式所搭配的被领有成分,都具有[家庭]的语义要素。不同人称代词搭配同一被领有成分,在语义上也会有区别:以第一人称为例,在洪雅方言中,“我的电脑”是指我个人的电脑,而“ɑu223的电脑”则是指此电脑属于我家庭的财产。由此可知,因为需要和被领有成分共同的语义特征相和谐,人称代词领属式理应含有[家庭]的语义要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əu223/ɑu223、ȵiəu223/ȵiɑu223、nɑu223只能够与亲属关系、家庭财产和家(“屋”)等成分搭配,构成领属结构。洪雅方言固有的表达“家”义的词是“屋”,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人称代词领属式的早期形式是“*我屋、*你屋、*他屋”的词法结构。
再者,这也符合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Hopper & Traugott 2003)。单向性即由实到虚,从独立词变为附着词,再变为构词语素、形态成分,这是句法独立性逐步弱化的过程。语言中很多句法功能词、形态成分,都是由语法化而来。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早期形式为“*我屋、*你屋、*他屋”,是用词法结构来表达不同的领属意义。而后因为代词是封闭类,容易发生弱化、合音等特殊音变,“屋”与前面的三身代词融合为一个音节,便是现在可见的元音交替形式,其来源、理据也就不再透明。“屋”从独立词到“*我屋、*你屋、*他屋”中的附着词、构词语素,再到əu223/ɑu223、ȵiəu223/ȵiɑu223、nɑu223中的准形态成分,符合语法化学说的单向性假设。
总之,“屋”最初仅仅是独立使用的“家”义词汇项;在语境表达的要求下,“屋”后置于三身代词“我、你、他”,表示“我家、你家、他家”义,领有亲属关系或家庭财产,逐渐凝固为特定结构中人称代词的附着词;最后,经过合音的重新分析,成为表示定语领属范畴的准形态成分。虽然在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中,“屋”字已不具备语音独立性,但“家”的语义对被领有成分的限制却依然保留至今。这种特殊的句法、语义分布,为我们提供了追溯其来源的线索。
(二) 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系统的语音演变
1. 类推音变与人称代词一般式的读音
讨论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的语音演变之前,首先要说明人称代词作为高频封闭词类在音变上的特殊性。陈忠敏(2016)在讨论吴语人称代词时,指出了人称代词三条特殊的音变现象:(1) 抗拒外来侵蚀,形成与主流读音相异的层次;(2) 是滞后音变,读音滞留在演变的早期阶段;(3) 常常发生弱化、合音等特殊音变。
这三条概括都是准确的,但我们认为,还应再补充一条:(4)系统内部的类推性,三身代词之间容易发生类推音变。这是因为人称代词系统是一组词形变化聚合范式(paradigm)(Bhat 2004)153,聚合范式的成员内部虽有意义的区分,但却表达的是同一个整体功能。具体而言,人称代词系统内部虽然要区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但表达指代人物的整体功能却是相同的。人称代词系统的成员数量极少,但在交际中却被高频使用,出于经济性的要求,整体功能相同的同一组聚合范式在词形上很容易趋同,仅保留核心的区别特征。因此,如果多数成员的某个语音特征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在不影响相互区别的前提下,其他少数成员便可能会放弃劣势项,直接改用优势项,使词形变化更为整齐、易于预测,所以也就发生了类推音变。
类推音变这一机制在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称代词一般式的读音便是类推音变的结果。洪雅方言人称代词一般式“我o42、你ȵi42、他nɑ44”与目前普通话的读音基本相同,但“他”的声母却与普通话不同。“他”是透母字,声母按音变规则本应读tʰ,例如同小韵的“拖”字,在洪雅方言中便读tʰo44。洪雅方言的“他”声母读n,不合音变规则,这就是类推的结果。第一人称代词“我”是疑母字,洪雅方言疑母字的声母ŋ消失,变为零声母,是相当晚近的音变,目前不少字仍有鼻音声母,如硬ŋən223、咬ŋɑu42等。“我”的声母早期就是ŋ,而“你”的声母是ȵ,三身代词中有两个都是鼻音声母。在洪雅方言人称代词的系统中,鼻音声母是优势项,由于系统内部类推性的作用,“他”的声母便也变为了与tʰ同部位的鼻音n。类推在音变上是不规则的,但却导致了规则性的结果,使人称代词的词形变化更为整齐划一。
2. 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音变过程
如前所述,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早期形式是“*我屋、*你屋、*他屋”的词法结构。“*我屋、*你屋、*他屋”结构发生的第一步音变就是:“屋”字与前面的三身代词合音,变为一个音节。第一人称“*我屋”快读极易合音,所以有*ŋo+u>*ŋou。第二人称“*你屋”合音,并在i、u之间增生了过渡的滑音ə,所以有ȵi+u>ȵiəu。第三人称“*他屋”合音,所以有nɑ+u>nɑu。
第二步,合音后的复元音韵母经历了韵腹低化的音变。这是一项跨语言普遍存在的音变,Labov(1994)116提出了著名的元音链移三通则,即长元音高化、短元音低化、后元音前化。其中,短元音低化还有一条细化规则是前响复元音的韵核(nuclei)低化。此音变的动因在于,如果复元音中韵腹(即韵核)与韵尾的舌位过于接近,那么发音就较为含混,听感上不易辨认为复元音,所以要加大韵腹和韵尾的滑动距离,使复元音“显化”,因而造成了复元音的韵腹低化。
就洪雅方言而言,第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读音非常显著地体现了这一条音变规则。合音后的复元音音节*ŋou,韵腹o与韵尾u的舌位相当接近,出于“显化”的需要,前响复元音的韵腹o便发生了低化,所以有*ŋou>*ŋəu>*ŋɑu,并同时经历了疑母字鼻音声母消失的音变,所以有现今的读音形式əu/ɑu。
同理,第二人称代词领属式合音后的音节ȵiəu,也经历了复元音韵腹的低化,所以有ȵiəu>ȵiɑu。
第三人称代词领属式合音后的音节nɑu,韵腹ɑ与韵尾u的舌位相隔较远、滑动距离大,也就没有“显化”的需求,未经历复元音韵核低化这项音变。
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的音变过程可以列表总结如表3:
从第一人称əu223/ɑu223和第二人称ȵiəu223/ȵiɑu223新旧层次并存的事实来看,复元音韵腹低化的最后一步音变əu>ɑu应发生较晚,大概仍处于扩散的过程中。不过据笔者调查,变体əu223、ȵiəu223目前的使用人群相對较少,发展趋势可能是被ɑu223、ȵiɑu223替代,洪雅方言三身代词领属式的词形变化最终形成ɑu223、ȵiɑu223、nɑu223的整齐格局,其深层根据也在于语言使用者的类推心理。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声调的演变。洪雅方言的单字调系统为:阴平44调、阳平21调、上声42调、去声223调、入声35调。(张耕 2019b)洪雅方言三身代词领属式均读去声
223调,既不同于“我、你”的上声42调和“他”的阴平44调,也不同于“屋”的入声35调。这是“合音变调”的表现,即“合音字的声调大多是原有各音节声调的加合”(王福堂 1999)176。既然是加合,由于三身代词与“屋”的调类不同,因此变调也就与二者都不相同。虽然现在已经很难直接断定在合音之时,三身代词与“屋”的调值、调型是怎样加合的,但从演变的结果可以推知,合音变调确实已经发生。其中也不排除有类推音变的作用,因为“我、你”与“他”的调类不同,它们的合音变调模式按理也应不同,但最后三身代词领属式的变调却都相同。
三、 汉语方言的共性
洪雅方言人称代词一般式和领属式的基本人称语素,都是“我、你、他”。人称语素加上家义语素“屋”,构成“*我屋、*你屋、*他屋”的词法结构,表示“我家、你家、他家”义,而后经过合音、类推等音变,成为了一套专用于领属的人称代词内部交替形式。换言之,演变中“屋”(家)语法化为了表示定语领属范畴的准形态成分。
在世界语言的语法化中,“家”义成分发展为定语性领属标记,是较为常见的演变路径。例如卡比伊语(Kabiye)、阿科里语(Acholi)和恩吉提语(Ngiti)等,都是“家”义名词或副词发展为领属标记;又如祖鲁语(Zulu)、科萨语(Xhosa)等的定语性领属标记,也都来源于原始班图语(Proto-Bantu)的“家”。(Heine & Kuteva 2004)175洪雅方言的“屋”(家)所经历的这种语法化过程,符合世界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
汉语方言中,也不乏“家”义词语法化为领属标记的现象。这些方言的“家”义词,在“三身代词+家义词”结构中,一般是与前面的三身代词合音,在共时层面上显示为变韵、变调等内部交替形式。例如:
湖北团风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三身代词一般式为ŋo44、ni44、tʰa22,但有一套特殊的入声形式ŋo213、ni213、tʰa213,表示“某家、某家的”义,来源于三身代词与“屋u213”字声调的合音。(汪化云 1999)
湖南长沙郊区的南圫、洞井等地方言(湘语长益片)。“我屋里、你屋里、他屋里”在做定语构成领属结构时,表示“我家的、你家的、他家的”,其中的“我屋、你屋、他屋”合音为ŋəu24、ȵiəu24、tʰəu24。(鲍厚星等 1998)7
湖南衡山方言(湘语长益片)。三身代词的领格变调形式ŋo33-34、ȵi33-34、tʰɔ33-34,也是来源于三身代词与“屋”的合音。(刘娟,彭泽润 2019)
广西玉林方言(粤语勾漏片)。三身代词ŋɔ23、ni23、kʰi32与“屋ok5”的合音ŋok5、nok5、kʰok5,成为表示“我家、你家、他家”义的特殊人称代词;并且在方言俗字上也有证明,合音字的写法正是三身代词的文字与“屋”字左右拼合而成。(梁忠东 2001)
广西三江六甲方言(西南官话桂柳片)。三身代词使用“我屋、你屋、他屋”的合音形式,指“我们、你们、他们”,表达亲属称谓的领属。(韦玉娟 2006)
而在另外一些方言中,表达“家”义的词形不是“屋”而是“家”,同样有类似的演变现象。例如严修鸿(1998)列举了众多客家话材料,认为客家话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如梅县方言的ŋa44、ȵia44/ȵie44、kia44/kie44,来源于三身代词与“家”的合音。[2]
还有不少陕北晋语,如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等方言中,第二人称代词的领属式nie213、niɛ213、niɛ412、niɑ412等也是“你家”的合音。(邢向东 2006)41
由此可见,洪雅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来源于“三身代词+家义词”,在汉语方言中并非孤例,是相当常见的演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共性。
汪化云(2008)总结了汉语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领格)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种:(1) 助词型,如“人称代词+的”;[3](2) 量词型,如“人称代词+个”;(3) 变韵、变调型。最后一种类型,在共时层面表现为形态交替,其来源大多也是合音,汪著所举例证也主要是上文提及的黄孝方言和客家话。本文主要讨论的以洪雅方言为代表的川西南方言,人称代词领属式在表面上也是变韵构词,但其来源是三身代词与家义词“屋”的合音。由上文列举的材料可知,这种构词方式在汉语方言中有一定普遍性,用例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认为,应更明确地提出一种类型:家义词型,即“人称代词+家/屋”。因为汪著分类的前两种——助词型和量词型,都是根据语素来分类的,而变韵、变调型似乎是按语音形式的剩余分类法。提出家义词型,可以解决部分变韵、变调型人称代词领属形式的构词来源,更严格地与助词型、量词型并列。
更为重要的是,家义词型的普遍性反映出:家庭领有者的语法化是汉语方言领格人称代词的重要类型。领格人称代词一般用于定语领属,一个定语领属结构的构成要素为“领有者+(助词)+被领有者”,家义词型领格人称代词是领有者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
目前对汉语方言人称代词领有者的调查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数范畴的区分,如“我”和“我们”的差异。王聪(2020)结合跨方言的调查材料指出,家义词属于汉语方言复数标记来源的一种类型。但需要辨析的是,“家庭”义与“复数”义并不是等同的,“人称代词+家/屋”指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概念时是单数,而指“家庭”集合内部所有成员时则是复数。“人称代词+家/屋”表复数的语义其实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并不是在每一种汉语方言中都会发生的。本文讨论的洪雅方言即为一例,表示“我家/你家/他家”的əu223/ɑu223、ȵiəu223/ȵiɑu223、nɑu223并未发展出“我们/你们/他们”的用法。而在陕北晋语中,“你家”等词有表领属和表复数的双重用法,邢向东(2006)42进行考察后也认为应当先有表领属的用法,而后才兼用为表复数。
家义词的本义是表示家庭(家族),定语领属结构中作为领有者的“我家/你家/他家”与“我们/你们/他们”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强调领有者为家庭,后者强调领有者为集体。由上文可知,很多汉语方言中都有专用于表达家庭领有者的语法手段,即家义词型领格人称代词。此现象的深层根据则在于汉语文化中家庭(家族)观念的重要性。对家庭(家族)所有权的表达,是汉语口语交际中的重要事项,因此“人称代詞+家/屋”在定语领属结构中被高频使用,最终在很多汉语方言中凝固下来,语法化为表达家庭领有者的专属手段。
四、 结 语
正如引言部分所指出的,洪雅方言复杂人称代词系统的问题,其实是川西南方言的共性,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洪雅周边方言相关问题的解释提供参考。特别是目前的四川方言词典,如《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等 1986)、《成都方言词典》(梁德曼,黄尚军 1998)等,主要关注的是四川方言的代表方言(即成都方言)。但是川西南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与成都方言存在诸多差异,人称代词系统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今后四川方言的研究及词典编纂,需要给予川西南方言更多关注,反映其特殊性。在词典编纂中,不仅要列出川西南方言的特殊人称代词,还可以对词条进行解释,指出它们的来源及演变。
除讨论四川方言的问题外,本文也讨论了人称代词的特殊音变规律,在陈忠敏(2016)三条规律的基础上,补充了“系统内部的类推性”,认为人称代词系统的成员之间容易发生类推音变,本文考察的洪雅方言就是一个例证。
本文还讨论了汉语方言领格人称代词的类型,在汪化云(2008)的基础上提出了“家义词型”,包括“人称代词+家”和“人称代词+屋”两种形式,认为定语领属结构中家庭领有者语法化为领格人称代词,是汉语方言人称代词系统中具有库藏特色的一种重要类型。
附 注
[1] 张耕(2019a)未提到洪雅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领属式有əu223这一变体。根据笔者的最新调查,此变体的确存在,但使用者相对较少,可能是老派的读音。
[2] 此说也有争议,参见项梦冰(2002)、温昌衍(2019)。因论题相关,故暂备一说。
[3] 汪化云(2008)单列的“用l系声母的助词表示领格”这一类方言,从构词上看也属于助词型。
参考文献
1.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等.长沙方言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 陈忠敏.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陈忠敏.吴语人称代词的范式、层次及音变.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六辑),2016.
4. 赖先刚.乐山方言.成都:巴蜀书社,2000.
5. 梁德曼,黄尚军.成都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6. 梁忠东.玉林话的代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1(2).
7. 刘娟,彭泽润.衡山方言人称代词领格变调现象的实质.湘潭大学学报,2019(4).
8. 陆俭明.修辞的基础——语义和谐律.当代修辞学,2010(1).
9.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 汪化云.团风方言三身代词的入声形式.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99(5).
11. 汪化云.汉语方言代词论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
12. 王聪.汉语方言人称代词的复数表达及其来源的类型学意义考察.辞书研究,2020(6).
13.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14. 王洪君.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5.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6. 韦玉娟.三江六甲话的代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學校学报,2006(3).
17. 温昌衍.也谈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的语源.中国语文,2019(1).
18. 吴早生.汉语领属结构的信息可及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9. 项梦冰.《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读后.语文研究,2002(1).
20. 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1. 严修鸿.客家话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语源.语文研究,1998(1).
22. 张耕.四川洪雅方言人称代词定语领属结构.方言,2019a(3).
23. 张耕.洪雅方言同音字汇.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b(1).
24. Bhat D H S. Pronou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 Campbell 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3rd 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26. Heine B, Kuteva T.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7. Hopper P, Traugott E.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 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 1: Internal Factors. Cambridge, MA: Blackwell,1994.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刘 博)
351250058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