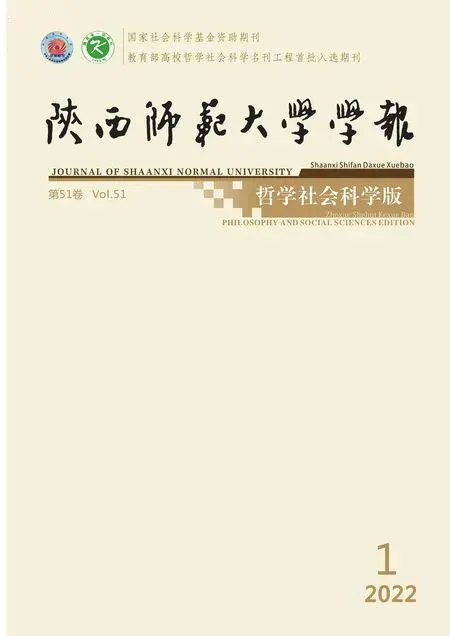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自主性难题
——兼论德雷福斯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性
2022-03-18李日容
李 日 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众所周知,在当代英美哲学中,德雷福斯因其对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哲学)的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展开批判而闻名,其所提出的以“熟练应对”或“涉身应对”为核心的技能获得模型理论以及由此所揭示的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特征,被认为是对老式有效(Good Old Fashioned,GOF)的人工智能即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有力批判,并使其发展式微,进而促进了海德格尔式(Heideggerian)人工智能的复兴和发展。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几乎涉及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模式。[1]xlv就此而言,他的人工智能批判无论如何都体现了哲学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深刻和内在的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哲学的理论与逻辑功用在经验领域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效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虽然涉及人工智能发展中所面临的根本难题即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问题,但他并没有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道路,而其主要原因便在于他的人工智能批判过于依赖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资源[2]230,而没有看到海德格尔对人之智能本质的完整揭示。即因归属于存在本身而可能的此在乃是一个时间性的整体存在,而非像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所主要依赖的那样,只是突出了其中的此在日常操劳在世的维度,并由此导致他的熟练应对或涉身应对技能理论饱受诟病。鉴于此,本文将从作为时间性整体存在的此在出发,廓清此在的存在“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德雷福斯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性,进而为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难题提供某种启示。
一、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与“人”之“本质”的存在论揭示
众所周知,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有关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分析而对基于主客分立和人类中心论为基本理论前提预设的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主体性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由此提出作为通达世界之初始基础的“我”,并非是意识主体,而是生存在世的此在[3],由此真正突破了意识哲学的藩篱,从而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深入到了对于存在意义问题的追问和探索[4]。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之所以能够通达存在本身乃由于其源始地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阐发的基本思想。时间性作为此在生存论结构整体即操心的存在论意义,包含着将来、曾在与当前3个相互共属、不可分割的向度,并分别对应着此在“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物)之存在”[5]361的生存论基本环节。而时间性的3个向度都有其本真与非本真的到时样式,如“曾在”对应的是本真的“重演”和非本真的“遗忘”,“将来”对应的是本真的“先行”和非本真的“期备”,而“当前”对应的是本真的“当下即是”和非本真的“当前化”。因而本真的到时即意味着此在能够先行着重演曾在并当下即是地开放出处境,而非本真的到时则意味着此在以遗忘着存在的有所期备的当前化的方式生存(如操劳的时间性基础便是何所缘之期备、遗忘存在的用具意蕴之居持以及当前化之操作的绽出统一性),两者分别构成了此在作为存在或存在者层面上的存在方式。
而当此在以本真的方式生存时,并非意味着它“摆脱”了其非本真的存在方式,而是说它能够将其非本真的存在筹划到其本真的生存中去。这是因为存在总是存在者之存在,即常人作为此在首先和通常的存在方式,是此在必须承受而不可选择的被抛状态。而此在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则必然已包含着其本真性的生存方式于其自身之中了,否则此在作为存在者层面的常人存在便不可能,因为存在者之存在总是有其存在层面的生成基础。
这表明,源始地看,此在的非本真存在是建基于其本真的生存之中的,但后者又必须通过前者才能够体现出来,尽管是以被遮蔽的方式显现出来。鉴于此,此在的存在便是一个本真与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共属于一体的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便是此在的存在乃是其时间性之绽出境域图式的整体到时,即此在作为将来、曾在与当前的3个时间性向度及其本真与非本真的到时样式,在此在的任何存在中都一起到时、共同在此。只是要么以显现的方式,要么以隐藏的方式来到。而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此在本身。概言之,时间性到时,此在存在。否则,此在便没有它的存在。至于此在为什么必然会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这是由此在的本质有限性以及其对于存在本身的归属性决定的。
因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的本真与非本真存在同样源始,只是前者通常被后者遮蔽着。而此在作为常人的非本真存在不仅包括此在与上手之物融为一体的操劳在世的层面,而且也包括此在作为“好奇”的理论性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称其为此在极端的沉沦样式。而此在的本真存在和整体存在则必须通过此在生存论的死亡决断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而在后期哲学中,海德格尔由存在者之存在转向对存在本身的探讨,表明此在的本真存在以及整体存在的“发现”或被揭示,不再仅只通过此在“向死存在”的方式,而是通过此在对于存在本身的归属性而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显示。海德格尔由此揭示了此在作为可能性之在的更深层的存在论根基,也使得此在的本质有限性得到了更为彻底的显露。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因为此在是时间性的存在,所以它的“本质”不能通过其“是什么”而得到规定,而只能通过其“怎样去是”即其作为可能性存在的种种样式来廓清它的存在。[5]50如果说在前期哲学中,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分析仍然着重于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话;那么在后期哲学中,海德格尔则深入到了对于存在本身的探索和追问。但这一转向并不表明海德格尔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毋宁说它是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或方向的探索,而这事实上都离不开作为通达世界之“初始基础”的时间性此在。因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唯有此在才领会并追问着存在的意义,而此在从根本上说乃是以时间性的整体方式生存的。
二、 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及其对此在本真性的探讨
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主要依赖于海德格尔对日常此在操劳在世的分析以及梅洛·庞蒂的经验身体意向弧(intentional arc)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熟练应对或涉身应对技能理论,由此揭示了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或无表征的特征,从而有力地批判了老式有效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以及具身人工智能。
在技能获得模型进阶理论中,德雷福斯先是与其弟弟斯图亚特探讨了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精通到专家的5个阶段[6]16-36,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阶段即驾驭和实践智慧阶段[7]40-46,但其核心思想并无改变(只是对原来的观点作了深化和推进),即都强调经验身体在熟练应对技能获得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由此揭示出一种无表征的实践。在德雷福斯看来,技能从低级到高级的获得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逐渐摆脱与语境无关的规则的限制(这些规则最初通过指导手册或师傅教导等途径而获得),从而融入真实情境或局势(这些情境或局势展示了比既定规则所能展示的更加丰富和复杂得多的东西),并获得熟练应对技能的过程。规则在学习者技能习得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从“完全与语境无关”到“部分与语境相关”再到“完全与语境相关”即无规则的语感敏感期的阶段特征。
当学习者达到技能的高级阶段(即专家、驾驭和实践智慧阶段)时,便彻底地摆脱了对规则的依赖,完全凭借身体的技巧实现与世界的流畅交互。在德雷福斯看来,作为梅洛·庞蒂式的经验性身体,在实践的具体情境中能够通过身体的“直觉”来操控和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最恰当或最协调的谐和状态,从而能够自如地“穿梭”于种种特定的情境中并不断地“作出”应对环境的“熟练行动”。因此,它不可能是理性审思的结果,毋宁说是经验性身体响应环境召唤的一种自动的“反应”。换言之,此时主体与其所处的情境并没有距离,毋宁说“两者”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的连续的整体而存在。
鉴于这样一个由人与物共同构成的中间没有任何缝隙的常识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日常此在操劳在世的周围世界,在梅洛·庞蒂那里就是基于身体意向弧的最大掌握而得到呈现的统一世界),由于其并非是通过此在对世界的表征(即预先把世界看作是外在于此在自身的,然后再通过概念或符号表征的方式通达它)而可能的,毋宁说它是主客共同涉入其中并由此而显现出来的统一世界,因此它无法被还原为孤立的原子事实而被恰当地把捉。
德雷福斯由此断言我们储存经验的方式并非通过储存一堆相互独立的经验事实并赋以其一定的联结规则而达到,即并非是以“知道是什么”(knowing-that),毋宁说是以“知道如何做(knowing-how)”即是以涉身应对的技巧的方式储存起来的[1]xxvii-xxviii,而它是无法通过形式化的符号表征来达到的。总之,德雷福斯认为,在熟练应对技能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涉身投入,它是直觉思维(而非理性思维)、情境应对(而非理论表征),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以鲜活的身体作为基础。由此,德雷福斯认为,了解技能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6]30
而鉴于在熟练应对技能中所体现出的人与物融为一体的世界无法被形式化和符号化,因此基于表征与计算的老式有效人工智能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GOF人工智能的研究计划最终失败了。我首先认识到心灵的符号信息—处理模型的内在困难是我们的关系感是整体的,并且需要卷入持续性的活动之中,而符号表征是原子式的,并且总体上与这些活动分离开来。”[1]xi而事实也表明,德雷福斯的批判是成功的,其直接的后果便是老式有效人工智能的式微和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包括人工神经网络和具身人工智能)的复兴和发展。而后者相对于前者来说,其总体趋向便在于都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式的内在表征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认知是‘嵌入的和具身的’”。[8]251
作为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的人工神经网络并不以信息储存和逻辑运算的方式来工作,而是通过神经元之间的连结强度来识别模式和泛化类似的情况。因而,它考察的是认知者与世界间的相互作用,而非两者的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而这种交互关系并非像哲学的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体现了领域的本质结构,而毋宁说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智能根本便“不需要技能领域理论的抽象特征”[1]xxxvi,即“不需要全能的教师,而只需要世界的反馈”[1]xxxix;并且“新条件会自动导致强化的变化”,并由此“促使装置作出恰当的回应”。[1]xxxix在德雷福斯看来,这种非表征的模型无疑更加接近于海德格尔对日常此在操劳在世方式的描述。[9]437它表明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并非通过符号表征与规则操作来实现,而是体现为两者间的一种或否定、弱化和同化的关系。
但德雷福斯认为,常识问题依然出现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并威胁其进一步发展。监督学习模式自不待言,因为它仍然需要设计者预先告知装置“每种局势的正确的应对行动”[1]xxxix。但“在真实世界的场景中,大部分的人类智能是以适合于特定情境的概括方式出现的。如果设计者将神经网络限制在预先定义的恰当的泛化类型的输出中,则网络将展现为设计者为特定情境而内置给它的智能,但不会拥有常识而使它能够适应其他特定情境,就如真正的人类智能那样”[1]xxxviii。而得到改进的强化学习模式虽然并不采取特定情境的特定反应策略的模式,而是能够“逐渐从经验中学习不同情境中的最优行动以实现长期的目标”[1]xxxix,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当新增的局势数量远远超过其最初接受训练时所遭遇到的局势数量时,它便难以作出精确的回应。究其原因,乃在于人工智能缺乏人的全局感(global sensitivity)。而人的全局感的形成涉及人的过去经验的沉淀,当下所处的实际情境以及基于此的动机、情感、目的等参数的改变,而这些都决定了事物当下呈现的方式。[1]xlii-xlv鉴于此,德雷福斯认为:“神经网络如果要分享我们恰当的泛化感(appropriate generalization),就必须共享我们对世界的常识性理解。”[1]xxxvi而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必须共享我们大脑的尺寸、结构和初始连接配置”[1]xxxviii,亦即它必须有一个像人那样的身体。
因此,尽管人工神经网络并不通过信息储存和符号操作的方式来实现人的智能,但毕竟其并不以鲜活的身体作为基础,从而无法像人那样学习如何熟练应对世界。而其主要问题便在于人工神经网络虽然能够模仿人与环境的交互模式,但却无法产生像人那样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无法根据变化了的情境来维持系统自身的演化和进化。
而具身人工智能的进路虽然不同于人工神经网络,毋宁说它是以建造能够自主地与世界充分交互的机器为目标的,而这种自主“交互”的实现灵感或依据正是来源于梅洛·庞蒂的以身体为基础的非表征性智能的启发,或海德格尔对于上手之物的功能指向性特征的揭示与论述,由此试图使机器以非表征的方式自动地实现与世界的交互。[8]251-257但具身人工智能同样面对的问题在于,它只能响应可被客观化的或固定的和可孤立的规范与特征,而非不断生成和流变的实际语境或情境。而上手之物的功能指向性也并非是固定的和可以客观化的,而是会随着其所处的工具意蕴整体的变化而变化。“海德格尔的上手并非是一个可被固定的函数,在预先得到规定的情境类型中运行,并触发有关成功或失败的预定回应。”[8]256对于德雷福斯来说,具身人工智能虽然同样通过模拟人与环境的互动而非人对环境的表征来实现人的智能,但它同样并非是真正海德格尔式的,因为它们的系统并非是开放和动态的,而是封闭和静止的。亦即,它要么只能响应固定的环境特征,要么预先便规定了相关性的情境,而非让机器学会响应新的相关性。因此,具身人工智能的研究最终也以失败告终。[8]257
由此,无论是人工神经网络还是具身人工智能都无法真正解决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即人工智能中的框架问题(frame problem)。所谓框架问题即是指计算机无法像人那样随着情境的变化而自动地维持系统自身的演化与进化,从而作出有效的应对。鉴于事物的意义总要基于某种框架才能被理解,因此为了确定事物的意义,我们得先要确定一个框架,但为了确定这个框架的意义,我们又需要预先确定另外一个框架,如此循环往复就会导致框架的无穷倒退。[8]251而德雷福斯认为,人工神经网络和具身人工智能之所以无法解决框架问题,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虽自诩为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事实上却是“不够海德格尔”的,即没有在机器中真正实现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或不可表征性的特征。而毋宁说它们都要通过将世界情境或特征进行某种程度的固化才能达到,因此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囿于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无法真正创造出能够在可能性与开放性的环境中自主地与世界交互的机器。
为了给此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启示,德雷福斯展现了弗里曼(W. Freeman)的神经动力学思想,认为其恰好从生理学的角度印证了梅洛·庞蒂的以身体意向弧为基础的人之智能的非表征性的特征,由此展示了一种真正非形式化的海德格尔式的人工智能是如何可能的和怎样的。[8]262-272尽管德雷福斯展示了弗里曼的神经动力学是“非线性”[8]263的,并且是“自组织”[8]267的,但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人类智能的非形式化特征与其形式化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与人的创造性与自主性之产生或形成的关系如何,而只是单方面地强调了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特征无法通过形式化的手段来实现的观点。而之所以会如此,乃由于德雷福斯对时间性此在的内涵缺乏整体的把握,也没有看到此在对于存在本身的归属性,进而对此在的本真性(创造性)与自主性的产生与形成缺乏清晰的认识所致。
在晚期哲学中,德雷福斯不再只停留于海德格尔对日常此在操劳在世的非本真维度的分析,而是重新关注了《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即海德格尔对此在本真性的描述,并由此区分了此在本真性的两个层次。亦即,由此在对被抛处境的畏所开显出来的基于日常平均理解的熟练应对技能,以及由此在对可能性死亡的畏所开显出来的对日常沉沦状态的彻底“离弃”。并且认为前者所造就的是在某个领域中拥有熟练应对技能的“专家”,而后者则是能够革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文化大师”。因此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的存在理解无疑更加本源,德雷福斯也称其为此在彻底的(fully)本真性理解。[10]44因为专家虽然能够识别一定领域里的相关性情境,并能够对其作出超出于常人的精妙的回应(否则熟练应对技能便不可能),但其存在理解在德雷福斯看来毕竟仍然是大众、平均的日常理解,即它没有提供比这更多的新的可理解性。从这个角度上说,熟练应对技能并非如德雷福斯所理解的那样是此在的本真性理解,毋宁说它仍然属于此在操劳在世的非本真性的层面。而“文化大师”则能够将文化积淀里处于边缘性的东西带到中心处,并由此揭示一个可能的新世界,进而彻底改变事物来显现或呈现的方式。[10]44由此可见,德雷福斯在晚期哲学中已经触及此在的本真性或创造性问题,但他并没有将此观点进一步带入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中,而毋宁说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探讨。[11]而这也导致德雷福斯错失了从此在作为时间性的整体存在(而非此在的操劳在世之维)来考察真正解决人工智能发展的自主性难题的可能性。
三、 德雷福斯对时间性此在理解的偏颇及其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性
由上述可见,德雷福斯对熟练应对技能理论的探讨主要基于海德格尔对日常此在操劳在世的分析,而他对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弧概念的挖掘与运用无非也是秉承了海德格尔所提供的这一基本思路,只不过是突出了其中的身体的视角。而尽管他晚期探讨了此在的本真性维度,并区分了“专家”与“文化大师”,认为后者是更为彻底和更为本源的存在理解,但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从专家过渡到文化大师,或者说此在更具本源性和创造性的存在理解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究其原因便在于德雷福斯并没有在一开始时便将此在作为时间性整体存在的视野纳入他的整个人工智能批判之中,由此导致他并不关注也无法深入解释熟练应对技能如何能够产生,人之形式与非形式化的智能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等这样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将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明晰人工智能发展的局限以及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的不足之处,从而为我们找到解决人工智能发展的自主性难题的途径提供某种启示。
事实上,非表征的操劳在世只是此在整体存在的一个层次,根据时间性之绽出境域图式的整体到时,此在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都意味着时间性的3个向度及其本真和非本真的到时样式都一起到时、共同在此。只是在熟练应对技能中,或在此在操劳在世的生存中,此时此在理论性的生存方式(即视物为“现成在手存在”的方式)及其更本真的存在方式(套用德雷福斯的说法)是隐而不显的,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根本不起作用。如前所述,德雷福斯认为当人的技能达到高级阶段时,人只是通过“知道如何做”即非形式化(非表征)的涉身应对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此时此在是以不再有“我”的,即是以非意识的方式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当你成为一名专家时,你完全融入到情境当中,并且,以不再有‘你’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其中。”[12]鉴于此,德雷福斯认为,熟练应对技能是“非概念的、非命题的、非理性的和非语言的”,一句话,即“非心理内容”的。[13]而在技能习得的初级阶段曾经起到指引作用的规则,此时(无论以何种方式,哪怕是以“无意识”的方式)也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应该怀疑认知主义的这种假设:当我们成为专家时,我们的规则变成了无意识的……为了成为专家,我们必须从脱离情境的遵守规则转换到更加受具体情境影响的应对方式。”[14]“没有理由认为在技能获得时起作用的规则在其后的应用中也会起作用。”[1]xii-xiii
然而问题在于,“规则”的作用或存在并非是必然脱离情境的,亦即非形式的并非意味着它就是非概念或非表征的,毋宁说规则也可以以情境依赖的方式存在或起作用,即作为现成的、既定的规则能够被此在筹划到其本真的生存中去,从而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中被注入新的可能性,并实现其进化。但德雷福斯认为,当人完全沉浸于情境中的应对时只有基于身体意向弧的最大掌握的运动意向内容,而没有任何基于理性表征与计算能力的概念意向内容。即此时只有涉身的领会(embodied understanding)而无心智的表征。毋宁说在德雷福斯看来,后者反而会对熟练应对技能本身造成损害。“如果学习者感觉到,只有当他们有理由来引导时,他们才能行动,这种态度将会妨碍他们获得技能。”[14]由此可见,德雷福斯仅只把现成性的对象性或概念性的心灵表征视作心智内容的惟一表现形式,而没有看到其也可以以非现成性的方式存在或起作用。就此而言,虽然此在操劳在世的整体情境无法被还原为孤立的原子事实而被把捉,但这种非本真的存在仍然是存在者而非存在层面的存在——德雷福斯本人也承认,熟练应对技能虽然是此在的本真性存在,但它实质上并没有超出大众、日常的平均存在理解(因而如前所述,它事实上并非是此在的本真性存在)——因此仍然是一种概念性或对象性的存在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是潜藏着的,即并不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表明非形式化的并非如德雷福斯所认为的那样必然是非概念的或非表征的,毋宁说“概念”或“表征”一直是以潜藏着的方式存在着的。“普通生活里头的吃饭、穿衣,你都是在边缘域里完成的,你根本不是拿它当个对象,根本不去注意它,它自动就出来了。一句话,对于观念化的东西、对象化的东西,我不计较它,我无视它,但是我并没有消除它,它潜藏着。”[15]222
鉴于此,概念意向内容(即“知道是什么”)并非是与运动意向内容(即“知道如何做”)不可兼容的,而非意识的也并非意味着它就彻底地是“非心理内容”的。毋宁说,意识与非意识乃是由概念意向内容在熟练应对技能中的参与是否被主体明确地注意到来加以区分的。“概念理性普遍渗透到我们的人类行为中的主张可以意味着我们并非总是注意到这些事情,但没有声明我们就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之中。”[16]并且“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无论它是意识的还是非意识的)都“负载语言”,[17]并且也需要一种区分事物的概念能力。而这里的语言与概念并非是行动的“恒常伴随物”,毋宁说它是“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17]。舍此便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人类行动,也无法将其与动物的本能性活动区分来。
而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本真性存在的阐述,也并非意味着此在此时“失去”了它的非本真(即存在者层面)的存在,毋宁说“常人”作为此在首先和通常的存在方式是此在无法选择和摆脱的被抛状态。故此在的本真存在只是意味着此在能够将它的非本真存在筹划到其本真的生存中去,从而能够“当下即是”地打开处境,而非彻底地去掉其非本真的存在之维,从而仅只保留其本真的维度。由此事物必然会以潜藏的方式被此在概念性或对象性地把握或区分。否则,此在与物融为一体的操劳在世便不可能。事实上,如果“对象”不是预先以某种模模糊糊的方式被此在所领会着了,即如果它不是预先以“潜藏”着的方式存在着了,那么便无法解释当手头的工具变得不合用或付诸阙如时,其如何能够突然地以现成在手的方式,即以作为此在的明确的理论静观的对象而呈现出来。并且,如果熟练应对技能只有身体运动意向内容,而无概念意向内容,便无法解释人如何不会像动物那样,当这种自动地应对环境的状态被打断时,何以会有自我意识的产生,并由此使得人类的整个文明成为可能。
此外,如果只专注于熟练应对技能的纯粹的“身体技巧”的层面,或如果只专注于此在作为时间性整体存在的非形式化的操劳在世层面,那么我们便无法看到其背后使其可能的此在的整个时间性基础。用约翰·塞尔批判德雷福斯的话来说就是无法解释行动的“实际满足条件”是什么,亦即“得不到所发生事情的逻辑结构”。[17]“如果你认为,我刷牙的行为只是减少形态失衡,而不是保护口腔,那么,你将永远不理解我刷牙的行为。”[17]
因此,在熟练应对技能中“知道如何做”与“知道是什么”并非是分裂的,而是源初地融合在一起的。尽管这里的“知道是什么”并非必然以一种现成性的可被人当做理论静观对象的普遍性规则(如德雷福斯所理解的那样)而呈现出来,毋宁说它是行动“指示或索引”的倾向,从而必须在活生生的情境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体现出来。[18]因此,熟练应对技能的真正本质可被归结为一种“知道的倾向”[18]。它意味着“知道是什么”构成了“知道如何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之亦然。亦即并非只有“我认为”即只有当我将行动本身当做一个反思的对象时,才有“知道是什么”参与进来。[19]毋宁说熟练应对技能总是已经有概念意向内容参与其中(而非仅只是一种运动意向内容),尽管其并不必然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也表明熟练应对技能的获得是一个完整的和连续的过程。即为了达到这种技能,应对者需要同时运用其表征和非表征的能力,而非一种绝对的“有你无我”或“有我无你”的情形。在熟练应对技能的生成中曾经起到“指引”作用的规则,在技能获得时并非“不再存在”了,毋宁说它早已作为技能的一个部分而内嵌于技能之中。如果否定这一点,则意味着德雷福斯人为地割裂了事物生成的连续性过程,从而也与其所强调的熟练应对技能的形成,最初总是从遵循规则开始的观点不相符。事实上,现成性的规则或概念必须被置回到其所从出或其所生成的存在情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进而才能解释其演化与进化的状况。而由德雷福斯所揭示的技能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规则重新回到存在情境,并被人在其中重新理解和领会,并由此实现规则的更替和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熟练应对技能的过程。这表明熟练应对技能作为一个生成的整体,始终不能排除“知道是什么”(包括“规则”在内)的一以贯之的作用。只是这里的“规则”是情境依赖的,而非现成和凝固的,即其并不必然以作为主体的理论静观的对象而呈现出来。
事实上,当德雷福斯强调在熟练应对技能中,学习者的直觉思维只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时[20],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的某种不可分割性。并且,当他在晚期哲学中强调此在“公共、平均和日常”的理解是此在任何本源性存在理解的存在论前提条件时,他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非形式化熟练应对技能背后的某种不可脱离的“形式化”的基础。只是他对这种“形式化”基础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人类智能的非形式化特征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探讨,由此也导致他无法进一步深入阐述从专家的一般存在理解过渡到到文化大师的更彻底的存在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
由此可见,熟练应对技能并非如它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只是一种非表征的身体“技巧”,毋宁说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非表征的身体“技巧”,它背后总是“预设”了比这更多的,亦即使其可能的作为存在论前提或条件的东西。而德雷福斯之所以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乃是由于他在此在作为时间性的整体存在中,只突出地强调到了此在日常操劳在世的非形式化的层面,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整个时间性基础或根基所致。而这个根基实质上表明了此在的存在乃是其形式与非形式化生存的内在融合与统一。
在此在的非本真存在中,此在作为常人操劳在世的存在即视物为“上手存在”的方式是非形式化的,但其理论性的生存方式即视物为“现成在手存在”的方式则是形式化的。因而此在的形式与非形式化的生存与其非本真与本真的存在方式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此在的非形式化生存事实上包含了两个层面,即此在操劳在世的存在和此在本真的生存方式,但前者仍然是此在存在者层面即概念性或对象性层面的存在(尽管其并不必然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后者则是此在存在层面的存在。因此,当德雷福斯认为作为具有熟练应对技能的“专家”的存在理解并没有超出此在平均、日常的存在理解,却又是此在的本真性存在的层次时,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的本真存在即是指此在能够将其非本真的存在(即视物为“上手存在”和视物为“现成在手存在”的方式)筹划到其本真的生存中去,即能够提供超出日常此在之存在理解的新的可理解性。因而,真正来说,德雷福斯所强调的“文化大师”的更本源的存在理解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本真的存在理解。
故当德雷福斯强调,海德格尔认为“所有的应对都是在其所称的‘在—世界—之中’的应对背景中发生的,而这种背景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表征”[8]258时,这里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表征”并非是此在沉浸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全部,即它并非意味着世界是纯粹非形式的,而毋宁说它同时也是形式的,即它是介于形式与非形式“之间”的领域。因为只要存在本身唯有通过此在的存在才能开显和通达,而又因为此在总是以时间性的整体方式生存,那么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那个世界就并非绝对地是非形式的,也并非绝对地是形式的,而是始终界于形式与非形式、概念与非概念、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领域”。
而德雷福斯的问题恰恰在于他未能清楚地看到世界作为“之间”领域而存在的本质特征,而尽管德雷福斯曾洞察到人之行动的目的并不必然以现成性的心理表征的方式显现出来——“行动可以是有目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有一个目标或目的在他的心灵中”[1]xxxi——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看到行动的“理由空间”,源初地看乃是此在“响应”存在本身之召唤,即是此在形式与非形式化生存之内在融合与统一的结果。亦即此在不只是操劳在世的存在,而是以时间性的整体方式生存,因而其存在者层面即对象性或概念性层面的生存方式同样构成了此在存在之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它并不必然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由上述可见,德雷福斯主要通过强调世界的“非形式化”特征来完成他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及基于其上的老式有效人工智能的批判,以及通过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的不够“非形式化”来揭露其失败。但他未能真正洞察到世界的形式化与非形式化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此在的本真性与自主性如何借由这种动态关联而得以可能或生成,并由此而能够在变化了的情境中实现自身的演化与进化,从而不会面临机器所遭遇到的框架问题。就此而言,无论是形式化还是非形式化的人类智能都要基于此在的时间性根基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而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失偏颇。概言之,正因为此在归属于存在本身并以时间性的方式生存,它才能作为可能性和开放性终结的存在,并且实现其形式与非形式化生存的内在融合与统一。鉴于此,无论是形式化的老式有效人工智能,还是非形式化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都无法真正解决机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机器无法通过“虚假”的“自身”来自动维持和实现系统的演化与进化。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由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此在所揭示出来的人之智能的“本质”既非形式的,也非非形式的,而是界于这两者“之间”的,即都有其此在作为时间性整体存在的根基,而此在的存在也要基于其对于存在本身的归属性来理解。但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单纯地强调了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的特征,并且它将这种非形式化等同于非概念的或非表征的,而没有看到此在的生存同时也是形式化的(即是概念的和表征的),尽管其并不必然以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德雷福斯的重要在性在于他通过现象学的视角与方法揭示了人之智能的非形式化特征,进而推动了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的复兴和发展,并由此揭露了老式有效人工智能形式化进路的本质局限性。但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道路应该是要看到人类智能形式与非形式化特征之内在融合与统一的本性,并基于此而对人工智能目前发展所面临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瓶颈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这种内在的融合与统一并非通过两者的简单相加便可达到,而是要呈现形式与非形式化“之间”的“关联领域”,由此便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所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