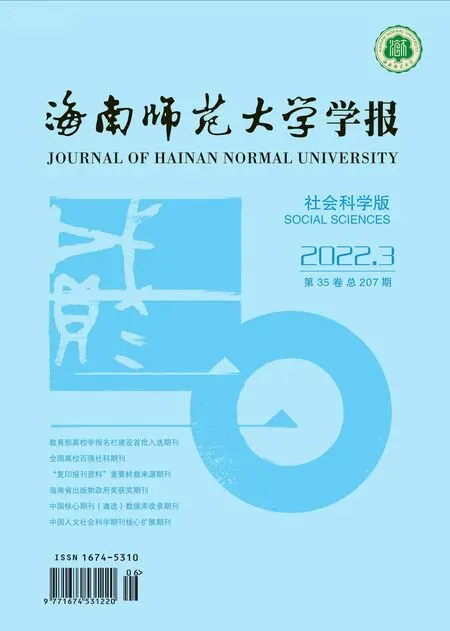“超市”内外与乡村现代性的一个侧面
——论付秀莹《陌上》中的“超市”书写
2022-03-18李保森
李保森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4)
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是近年来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它绕开了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社会更迭等重大主题,而以具象丰饶的细节、微妙复杂的关系、绵密缠绕的心思,对时代作一侧面的回应与再现”(1)曹霞:《美学的自觉与“陌上中国”的建构——付秀莹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在这部小说中,居于北京的付秀莹把经由和父亲通话、自己返乡等途径获得的感性经验进行了文学的熔铸,从而完成了对“芳村”,也即当下中国乡村的素描和塑形,并凸显了本人独特的美学经验和审美创造,如古典美学和抒情风格等等。在写作内容上,付秀莹延续了贾平凹《秦腔》中“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2)贾平凹:《秦腔·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18页。。不过两者又有差异,付秀莹有意打破了章节前后的时间联系,不是“流年式”的连续,而是跳跃的、自由的,不以事件为纽带,而以人物为中心,章与章之间仅仅有人事上的微弱关联,而无时间上的彼此呼应,从而形成了“桔子”式的结构特征,而“芳村”正是包裹这些桔子瓣的果皮。这一特性使叙述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也使文本获得了开放性,乡村包括外在空间变迁和内部肌理嬗变等在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在文本中得到显露和呈现。因此,可以说,在写作主题上,《陌上》和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写作保持了一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3)雷达:《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而在这部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超市”被重点展现和书写,从而使“超市”书写得以成为考察处于社会变迁中的村庄、文化群落及其生存状态的一个有效视角。
一、《陌上》与乡村的现代性进程
《陌上》中茂盛、驳杂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其叙述的主要部分,作为日常性事物的超市自然也被纳入了其中,并在文中多次出现。超市是一个携带着现代文化信息的物质空间,因而也可以被视作现代性的表征。如此,当超市进入乡村并作为一股隐而不显的力量参与乡民的生活运转、乡村的文化重构时,正构成了乡村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一种具体体现。付秀莹在《陌上》中的超市书写,不仅是对当前乡村的时代状况进行呈现时所借助的途径或意象,还以具象的方式接续和展示了乡村的现代性进程。在这个意义上,《陌上》嵌入到百年乡土文学叙事谱系中,并以自身的当下性而涌动着鲜活的气息。
有学者认为,“从20 世纪40 年代解放区开始的‘农村题材小说’实际上就是表现新的现代性秩序对自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介入、整合、改造的过程,这类小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乡村现代性叙事’”(4)王宇:《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其实,这一进程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起步之时,就已经在进行了。更准确地说,是在晚清遭遇西方列强时就已开始,“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既有以大炮为表征的强暴的一面,也有以新奇的洋货为表征的诱惑的一面”(5)王一川:《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不过,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不够显著,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群体差异。与之相比,肇始于20 世纪40 年代的新的乡村现代性体现出更为整体、明确的特征,且有更为一体化的政党政权、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理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参与其中,从而使整个的中国乡村和民众都卷入其中,相继出现了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等生产和生活组织形式。这些社会主义实践使农村发生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时期的差别,鲜明地体现在“乡村现代性叙事”(6)在“五四”时期,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在文学作品中借助现代文明之光对乡村进行了照亮,着重展示了农村的愚昧状况,揭示了农民的精神污垢。但这种启蒙叙事,忽视了乡村民众的物质处境,脱离了民众的生存体验,因而显得格格不入,造成了启蒙的悖论。进入延安时期,农民的社会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认可和推崇,写农民、为农民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命题,因而在题材、人物塑造、主题安排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性、地方性特点,如赵树理等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乃至生活方式都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将这些实践作为创作主题,论证实践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李准等人的创作。中。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调整,尤其是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乡村现代性的路径和目标也有所变动——以追求个人或家庭致富为主要动力。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自主权,实现了对劳动力的解放,从而解决了吃不饱的历史难题,农村贫穷面貌逐渐得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市场和商品贸易日渐放开,对农民而言,追求和积累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的愿景。在这里,财富不仅是指货币积累,还包括对现代物质的有偿消费和使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灵体验。例如刘庆邦《到城里去》中,宋佳银的购买自行车,并用心保管,引来了村人的羡慕之情,满足了宋本人的虚荣心,生动表明了消费具有在使用价值之外的意义生产功能。
随后,规模日渐宏大的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进程也把乡村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或者成为劳动力输出地,或者作为消费市场的开拓地,或者成为特定资源的提供地,又或者是某种后果或代价的承受者。这些力量持续地改写着乡村的面貌。可以说,从新时期农村改革到20 世纪90 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延续至今的乡村现代性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仍然作为主导性因素,又加入了城市、商品、商业、技术等新兴因素。主导性因素与新兴因素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当日新月异的现代物质、技术开始重塑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时,也在瓦解着乡村的旧秩序,同时建立着新秩序,如电视、手机、洗衣机、电脑、汽车(7)关于这些物质的文化功能分析,可参见南帆《双重视阈——当代电子文化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徐敏《消费、电子媒介与文化变迁——1980年前后中国内地走私录音机与日常生活》(《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等等。,以及本文所论述的超市等等。这些新事物便利了民众的生活,扩展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与想象力。因此,这些具体的物质、技术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在参与、影响着乡村秩序的建构,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
通过上述简单的梳理,可以说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先后经历了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和物质现代性等三个历史阶段。虽然乡村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变化广度与深度不一,但都搅动了“超稳定结构”(8)参见金观涛、刘青峰:《盛兴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的传统乡村社会,整体上使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稳定走向变动,踏上了艰难而沉重、幸福而苦涩的变革之路,也使乡村文学叙事在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时代主题。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乡土文学不断滋长的重要动力。乡村在种种外部力量的介入下不断被塑形,而“乡土”的语义随之发生着嬗变,乡土文学也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内容、风格和主题。付秀莹《陌上》即是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为百年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叙事,书写了当下的中国乡村。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文学叙事并非简单地对乡村的社会主题进行呼应,而是在某一时代背景下,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写出个体成员的命运轨迹和悲欢体验。对此,付秀莹有着自觉的意识:“写芳村的各色人物,写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命运和悲欢”(9)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08月04日第08版。。相比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宏观分析而言,文学始终在对个体生命的遭际给予及时的回应和关怀,从而始终拥有自身的魅力和独特价值。
二、超市与乡村的耦合
在《陌上》中,许多现代性的事物出现在乡村中,并已然在乡村落地生根,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汽车、手机、微信、服装等等。例如小说中的服装,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许多颜色丰富、样式各异、四时不同的衣服、饰物,如素台的“葱绿小衫儿”“鹅黄软坎儿”“茶色薄呢裙”“奶白的高跟鞋”“浅粉色丝绸裙子”,春米的“浅黄裙子”“藕荷色小夹袄”“靛蓝色灯芯绒肥腿裤子”,建信媳妇的“鹦哥绿薄呢裙”“桃红高领小毛衣”“嫩黄水纹丝巾”“草绿暗花的大丝巾”等等。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色彩斑斓、样式各异、分类细致的衣物,不仅是对人物的生活水平、装饰风格和审美观念等的显现,以及对乡村的点缀,还有着丰富的社会学意味:现代商品已然开始组织着甚至支配着乡村民众的生活,乡村民众同样在共享商品社会和物流通达的福利与便利。
但无论是服装,还是手机、汽车等,这些现代性事物都主要附着于私人之上,鲜明地体现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和经济状况,是乡村现代性程度在单个个体或家庭上的体现。而超市则与上述事物有着不同的特征:它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的、流动的场所,是群体交往的中介,因而也是展示各色人物言行举止的窗口;它以展开商品买卖为主要内容,具有现代交易的相似特征,是乡村现代性进程的直接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中所论述的“超市”实际上起着“认识装置”的作用。
超市,是超级市场(super market)的简称,是一种规模大型的现代零售业商店。超市内一般会按照一定的秩序,摆放不同品牌、种类和价格的商品以方便消费者自由选购,并在出口处统一结账。这种自助式的商业经营模式保证了消费者的购买自主权,满足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超市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 年代的美国纽约。“二战”后,特别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超市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20 世纪90 年代,超市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它们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中国内地确立了零售业新的经验理念与方式,并且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消费者习惯的购物方式”(10)孙骁骥:《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412页。。随后,大陆本土的超市经营公司开始出现。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性进程的深入,超市也日渐进入乡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乡村的商品买卖主要是通过供销社(11)949年11月,中央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合作事业;1950年7月,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生产、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1982年,在机构改革中,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商业部合并,但保留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设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保留了省以下供销合作社的独立组织系统;199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在总结供销合作社过去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了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入新世纪后,该机构再次做出调整。实现的,而且还要凭票购买。物资短缺、供应不足、购买能力不足、服务人员态度不好,是其时商业制度的主要弊端。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型,私人经营的商店开始成为乡村商业活动的主流,供销社日渐失去国家庇护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上尽显落魄之色。超市进入乡村后,凭借在经营模式、商品规模等方面占有的优势,开始成为新的主要商业经营方式。
在日常性的商店交易之外,乡村还有另外一种交易方式作为补充,即集市,乡民称之为赶集,“乡村集市不仅融入村民生活之中,且在其发生、发展中带有鲜明的乡村烙印”(12)韩茂莉:《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50页。。这种集市通常是露天的,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定期举办,早期主要以美味小食、生活用品、农产品、农具、农畜为主,后来交易内容日渐扩展,也有许多现代商品。《陌上》中就描写了喜针在农历八月十二这一天去青草镇赶集的场景。
对于乡村而言,超市是外来的新事物。超市在乡村的运营,既是超市适应乡村特征的一个过程,又是乡村接受超市的一个过程。乡村的超市,在商品的规模、种类、质量、价格等方面,以及消费的层次、频率、数量等方面,都难以与城市中的超市相比。同时,由于乡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特征,两者的差异影响了超市的具体经营方式。乡村的地理空间有限,且处于相对静止的文化状态,民众的生活方式相似,人际网络又是主要建立在血缘、婚姻、地缘等基础上,人们在长时期的接触和交往中,彼此相当熟悉了解,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13)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113页。。城市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与它的空间繁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处于流动状态有关。在城市中的人彼此互不认识,除了工作、生活等相对固定的交往空间外,有的即使是邻居也因为安于自己的屋内而互不相识,在其它场合上基本是临时性、一次性的交往。
超市的出现适应了城市人的生活和交往的需要,提高了购物的效率,保护了顾客的隐私,免除了遇到熟人时可能会有的尴尬、不便等顾虑。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挑选,商场的服务员仅仅提供向导的作用,双方互相不知根底,自然无从交流。但在乡村则是另一幅不同的情形,且不说顾客在超市遇到熟人的概率极高,开超市的人就是熟人。这样,彼此之间打招呼、聊天、问询等就经常发生,这时候的超市提供了社交的场所。这种熟人相遇与交谈的场景,具有两面性:既使买卖增添了人情味,得到店主的主动让利,又可能给顾客带来不便,造成某种负担(如耽误时间、影响选择等),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所需。
郑也夫曾针对我国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不同人群特征,提出了“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两个概念。“人格信任”建立在熟人之间的彼此熟悉这一前提下,“系统信任”则是在陌生人之间展开合作时生长而成的。(14)可参见郑也夫:《走向杀熟之路——对一种反传统历史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学术界》2001年第1期。在社会向流动性、开放性的转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系统信任”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对于以等价交换、自愿买卖为原则的商业活动而言,“系统信任”显示了买卖双方的平等地位。但在由“人格信任”占据主流地位的乡村社会,既有可能增强、滋养“系统信任”的生成,又有可能破坏、干扰“系统信任”的生长。这一点在《陌上》的几处场景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三、“超市”内外: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博弈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超市既是一个物质空间,又是一个观念载体,是乡村新秩序(现代秩序)建构的一块基石。超市的功能不仅在于提供民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还由于它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携带着现代社会的相关准则,进入乡村后,起着传递新的价值观念的功能。那么,当它在有着深厚文化惯性和特定伦理规则的乡村中出现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场景呢?
芳村中的超市有好几家,但小说中的几处场景都是围绕秋保家的超市展开描写的。这首先与这个超市的地理位置有关:秋保家的超市位于芳村大街的正中央,是村委会小白楼的临街门脸,附近还有难看家的小饭馆、耀宗的医院,人来人往,一片热闹景象;其次,可能是作者在叙事上操作简便的考虑;再次,还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借助这个现代性空间展现乡村的人情物理,“乡土小说里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造:日常生活诸因素变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件,并且获得了情节的意义”(15)[苏]M.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在秋保的超市里,既有其乐融融的乡间温情和民间意趣,又有现代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冲突。这也就是说,秋保家的超市虽然是构成乡村空间秩序的日常部分,却具有症候式效应,在乡村现代性的过程中起着“磨刀石”的作用。因此,对这些场景的关注和考察,可以具体地透过乡村现代性的一个侧面,探讨乡村现代性的现实境况,具体内容如下文所述。
(一)温情:熟人社会的交往特征
在城里“开发廊”的香罗回到了芳村,去秋保家的超市购物。秋保一看见她,就喊着“婶子”,赶紧招呼起来,并互相开起了玩笑,还夹杂着颇有暗示性的性话语,这就惹恼了香罗,形象地展示了乡村的民间性。香罗在超市里挑了一箱酸奶、一箱六个核桃、两盘鸡蛋、一只白条鸡、半斤咸驴肉和一些零嘴。秋保开心地算账收钱,帮着香罗装袋,又让自己的媳妇国欣把香罗送回家,还拿了一个保温杯作为赠品。(16)付秀莹:《陌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6页。同样,当兰月来到秋保家超市时,秋保便问道:“啊呀,人民教师下班啦?”接着,还是用性话语“挑逗”对方,引来了兰月既恼又羞的责骂。一番口舌后,兰月挑了一袋豆奶、一袋芝麻糊和一箱方便面。秋保跟在后面,说兰月连二斤肉也舍不得割,一方面是在逗趣,另一方面也有想要扩大自己生意的意图。(17)付秀莹:《陌上》,第241页。
在这两个场景里,叙述者首先展示的是乡村中的熟人交往特征,商家和顾客彼此之间总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关联。秋保对顾客的职业、收入、个人品性等情况都有所了解,因而能相应地和她们展开对话,并获得对方的回应。这一点显然不同于城市中单纯的超市购物行为。其次,从香罗和兰月所购物品来看,这些商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必需品了,而具有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侧面展示了她们各自的生活水准和经济状况。在这里,现代商品的符号作用在乡村已有所显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当代物品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纵”(18)[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再次,从秋保让媳妇国香帮着香罗提东西,送她回家这一行为来看,这固然是秋保对香罗在自己这里高消费后的服务延伸,有秋保对利益的衡量,但也可以看出乡村超市的空间辐射范围是有限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同村的居民,鲜明地体现了乡村超市的在地性。
当然,更主要的是,这些看似无聊又无趣的笑谈,虽然仍是乡村民间性的一种体现,但在销售与购买的商业行为之间,显示出了乡村特有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在人与人之间都可能出现,但在熟人之间更具有天然性。同样,尽管如今的商业活动,也越来越强调销售人员对顾客的尊重,追求服务的贴心,体现温暖与关怀,但对于乡村而言,这种人情味首先是内生的,是人们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而不仅是基于服务水平的提升。
在这两个场景中,与其说购物和那些商品是主要的表现对象,还不如说秋保和他们之间的笑谈是主要内容。超市在这里仅仅提供了一个交往的空间,却鲜明地体现了乡村人际间的交往特征。乡村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为现代商业活动抹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使买和卖这种冷冰冰的事情有了一定的温度,反过来又进一步维系了这一人际网络。
(二)冲突:对商品观念的不同理解
在秋保家超市门口,还有几个小动物形状的电动摇椅,可爱又好玩。这种小玩意儿,主要是用来吸引小孩子的,既能够增加商店的收入,又可以聚积人气。使用者需要投币,一次一元,使用时间固定。玩一次后,使用者若想再次使用,需要再次投币。这天,凤奶奶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在这里玩。孩子玩了一次后,哭着表示还想玩。凤奶奶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认为这种机器是在坑人。另外一个老太太也附和说,这种玩法太费钱。这时,秋保媳妇走了过来,回应道这是自愿的事情,又非硬拉着你们玩。那个孩子还在哭,凤奶奶一时火起,骂道:“愿意挨刀子的东西,有钱还不如买块糖,还能甜一甜嘴呢。非得犯贱给人家送钱来”(19)付秀莹:《陌上》,第207页。。接着,双方就吵起来了,凤奶奶指责对方坏了良心,秋保媳妇诘问对方,什么叫坏了良心;凤奶奶指责对方,两口子红白脸配,赚了村里人不少钱;秋保则拿凤奶奶的儿子说事,越扯越远。围观的人群中,有说秋保不是的,有说凤奶奶不是的。
在凤奶奶看来,在这种机器上面花钱是不值的,进而把责任推到放置这些机器的秋保夫妻,认为是他们在诱惑孩子玩。的确,“玩”是一种服务性商品,主要满足个人的游戏快感,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还不如一块糖带来的口腹之欢。这种成本考量,显然不是一个孩子所能具备的,他也就不能理解凤奶奶的苦衷。凤奶奶在这里的指责,除了有老辈人的勤俭、节约、朴素等惯习在发挥作用外,也与凤奶奶对现代商品社会的契约精神不够理解有关。周围人群之所以站在凤奶奶的一边,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与传统两种观念在商品交易中引发的冲突。
契约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商品交易建立在交易双方共同认可并遵从的契约之上。这份契约未必是以书面方式呈现的,大多时候是观念性的,却同样含有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作用,是开放社会建构“系统信任”过程中的有效支撑。秋保夫妻的做法是一种商业行为,消费者则本着自愿原则,对这些游戏娱乐产品进行消费,并无什么不妥。就此而言,凤奶奶的指责实在是冤枉了秋保夫妻。不过,在以“人格信任”为主要基础的乡村社会,建立在等值交换基础上的商品买卖行为,让金钱参与了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使人与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利益的面纱,并在实际上代替了传统观念中强调的利让于义等道德观念。习惯了传统观念的民众对由金钱为主导的现代买卖,尤其是非明显的商品买卖(货物交易),自然难以理解和接受。当凤奶奶用“一心赚钱,坏了良心”指责秋保夫妻时(20)付秀莹:《陌上》,第207-208页。,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物质主义挤占乡间淳朴民风的不满。
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整个时代的宏大主题,乡村也奔上了致富之路。人们一心扑在赚钱上,漠视、拒绝甚至是否定了乡村熟人之间应有的情感联系。凤奶奶对于这种情感联系的道德化维护,既是对情感联系的肯定和珍视,但同时又是对它的混淆和误用,这正是这场冲突发生的主要缘由。
(三)馈赠: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护
当秋保夫妻和凤奶奶吵架的时候,军旗媳妇臭菊也在围观的人群里。小闺和她打招呼,问她来干嘛,臭菊说买点东西去看看脚崴了的傻货他娘。小闺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一看,还说她太讲究礼法了。臭菊解释说,傻货他姥爷跟军旗他爷是亲堂兄弟,应该去看看。进入超市后,臭菊拎了一包点心、一袋芝麻糊和一袋豆奶粉。付了钱后,臭菊感到心肝儿疼,这种疼显然不是生理上的疼痛,而是心理上的,表明了花钱后的一种情绪,即既必须买东西又不愿高支出的复杂心理。(21)付秀莹:《陌上》,第209页。臭菊的解释说明了自己为何要去看傻货他娘,显示出传统礼法在现代乡村的延续以及它们的效力。费孝通认为我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对个体和社会具有支配作用,“从社会观点来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22)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6卷,第132页。。臭菊去看傻货他娘,正表明了她对乡村道德伦理的服膺。只不过,随着乡村的发展,维护私人网络的成本已经有所增长。从臭菊对花钱的心疼,可以看到乡村的商品现代性在丰富了乡民的物质享受、便利了乡民的购物行为的同时,也无端增加了乡民的支出和负担。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谁都可以自由参与和享受这种便利的。
无独有偶。春米在芳村见到了同村的缨子,两人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了起来。缨子的丈夫在储蓄所工作,她就自己在家做贷款业务,凭亲疏远近,利息有高有低。春米家开饭馆的时候,就是从缨子那里贷的款。缨子在利钱上对春米有所照顾。对此,春米抱有感激,于是执意要留缨子在饭馆吃饭,却未如愿,又赶忙抱着孩子去秋保家的超市,买了一堆吃的玩的送给缨子。缨子嘴上客气着,心里却十分受用。(23)付秀莹:《陌上》,第263—264页。此外,大全媳妇去超市“买了一只烧鸡,半斤咸驴肉,一大块牛腱子,总有十来斤。一些个营养品,牛奶鸡蛋八宝粥等营养品……”并将自己的衣物,送给嫂子(24)付秀莹:《陌上》,第158页。;从外地回来的小梨在超市买东西,也是去串门(25)付秀莹:《陌上》,第438页。;小鸾带礼物去看生病的二婶子(26)付秀莹:《陌上》,第86页。,喜针在集市上碰到了自己的亲家即儿媳妇梅的娘,内里心疼却又不得不故作热情地买羊肉和香蕉,送给对方(27)付秀莹:《陌上》,第222页。等等,都与上述行为有着相似的功能,即维系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乡村社会中私人网络的培养既是一种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关系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28)[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这些人购买的商品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所需,而是将自己的道德、情感和目的等都注入其购买的商品之中,赠给对方,而对方也通过商品,感知和接受对方的心意。这种沟通方式,有利于乡村私人网络的再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秋保家的超市只是作为购物的场所而出现,但在沟通人际关系上起着物质支撑的作用。一方面表明了乡村仍然遵从旧有的社会交往逻辑;另一方面又因为超市的出现而增添了新的馈赠内容,提高了维系人际关系的成本,可谓“水涨船高”。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超市正在重新组织乡村的生活秩序。
尽管都是礼物馈赠,同样都是为了维持乡村社会中的人际网络,臭菊和春米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出于对传统道德观念的遵从,主动而为之,体现的是乡村人情;后者则有理性计算在其中,被动而为之,体现的是现代功利。这种差异也可以视作是代际之间的。这一迹象表明:旧的道德观念仍然在乡村起作用,新的价值观念也开始逐渐地覆盖乡村。新的价值观也预示着,在乡村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和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中,新的乡村人际关系正在慢慢涌现和成型。
(四)“杀熟”或者“欺生”:乡村商业的“恶之花”
如果说秋保在凤奶奶不公允的评价中,是受到了传统观念的“侵害”,那么他在对待小梨时却利用了传统人际关系提供的便利,显示出乡村商业丑陋的一面。春节期间,小梨从北京回到了芳村。在乡民对城市的想象中,小梨也被想象为事业有成、赚钱甚多、生活优越的一员。当青嫂子见到小梨时,让小梨感到的并不是熟人相见的脉脉温情,而是一种不适。她一直在问小梨的月收入,大有问不出来不罢休之势。直到然婶的到来,才解除了小梨的尴尬。看到芳村的日益丰盛,小梨不禁感叹道芳村的年味不比从前的了。(29)付秀莹:《陌上》,第430页。
当小梨来到秋保家的超市时,秋保表现出了极大地热情,小梨也叫了他一声哥。两口子和小梨聊了一会儿后,小梨说自己来挑些东西去串门儿。显然,小梨也是通过礼物馈赠的方式来维系她在乡村的人际网络。秋保让媳妇囯欣帮小梨挑东西,还有意地挤了挤眼,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幅场景:
她一口气挑了一大堆,一箱六个核桃,一箱蒙牛鲜牛奶,一箱露露,一只烧鸡,一只鸭子,一大块驴肉,半个酱肘子,两盘鸡蛋。小梨忙说够了够了,国欣哪里肯听,又把一些个酸奶火腿杂七杂八的零食塞过来。小梨只好拿出钱包结账。(30)付秀莹:《陌上》,第438页。
这幅场景极具画面感,国欣的卖力和小梨的无奈都在其中淋漓显现。作者不厌其烦地展示这些商品,与其说是在表现乡村和城市的物流共享,不如说是为了近距离地显示秋保夫妻的心机和贪婪。尽管如此,秋保还是责怪国欣给小梨挑的东西太便宜了,故作夸张地说:“小梨北京来的,还差那几个小钱儿?”(31)付秀莹:《陌上》,第439页。这话表面上是在埋怨国欣不会挑东西,实际上是说给小梨听的,意在卖出更多更贵的物品给小梨,颇显强卖之姿。当小梨把这件事告诉其大姐时,大姐忍不住骂道:“秋保这两口子,穷疯了,见谁都想咬一口。六亲不认,狗日的”(32)付秀莹:《陌上》,第439页。,同时责备小梨在花钱上大手大脚,数落她讲究礼数有些过了。大姐的“骂”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以粗鲁的方式揭穿了秋保的行为动机——拐弯抹角地揶揄小梨是为了卖出更多的商品,指出了乡村商业活动中丑陋的一面。当然,这种现象在城市也会发生,但出现在本以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的乡村,就显得格格不入,暴露了乡村在现代性进程中对自身传统的摒弃。这虽然只是秋保的个人行为,但仍然可以表明物质主义对乡村的侵蚀。
芳村是小梨的故乡,是她生命的起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开始了成长,并在长时期的接触中认识了许多乡亲,感受到了乡村的质朴。在离开芳村后,小梨就中断对芳村的参与,原先对乡村的熟悉也就停留在记忆中,她本人成为了“在而不属于”的过客,仅仅是在特定时期回到故乡,且不会久留。这两种形态,使得小梨和芳村形成了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对于秋保而言,小梨既是归来的熟人,又是短暂停留的陌生人。那么,秋保两口子的所作所为,既像是“杀熟”,又像是“欺生”。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对“杀熟”“欺生”这两种概念和现象的辨别,而是这些现象在乡村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这里当然有人性的自私、势力、贪婪等因素在作怪,但同样也与此时乡村所处的环境有关:既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又渐被现代社会风气所浸染。针对如今的乡村社会状况,有学者提出了“半熟人社会”,认为“社会变迁中,农民的熟悉和亲密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也在剧烈变动中减弱甚至丧失了约束力,农民的行动逻辑因而表现得非常理性”(33)陈柏峰:《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页。。这个概念脱胎于费孝通的“熟人社会”,点明了现如今乡村的过渡和转型状态。
尽管如今的乡村已经逐步走向了开放、流动的状态,但由于自身各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在城乡秩序中处于低位,它仍然处于相对封闭、静止的状态,保留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特质。在这种社会中,熟人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际关系状况。对“熟人”的亲切和熟悉的另一面,就是对“陌生人”的辨识更为敏感。在秋保看来,小梨的工作、生活都在北京,大多数时间不在芳村,那么小梨在大城市的收入具有被“宰”的价值,只是偶尔回到芳村则免除了“宰”熟人后会经常面对被宰者而带来的愧疚和担忧。因此,秋保乘机利用了熟人关系提供的便利,为自己谋利。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品交易是自由、平等的,并应充分尊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但在乡村社会中,由于特有的人际关系脉络,属于消费者的这种权利并未得到全面的尊重和践行,因而出现了上述让人感到惊讶和气愤的一幕。
《陌上》中的这些场景,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超市”内外的人情物理,揭示了如今乡村的社会变化和文化状态,从中除了可以看到乡村物质的丰富,还有乡村传统伦理的失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场景中的小说人物,既有臭菊的心酸、凤奶奶的无助、小梨的无奈,也有秋保的八面玲珑等多种姿态。这些姿态其实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对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不同回应,因而生动展现了乡村现代性的复杂面向。
四、结语
通过对《陌上》中与超市相关的场景的论述,可以发现,尽管以“超市”为代表的现代性事物和为表征的现代性已经进入乡村,并具体地参与到了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中,但诸如平等、自愿、自由等这些指导并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理念并未在乡村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也并未完全转为民众的自觉实践。传统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并未随着乡村内外空间的变化而全然失效。现代性的市场理念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遇并引发一系列冲突,反映了乡村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斑驳复杂的过渡和转型阶段,乡民们在此期间演绎着新旧相掺的喜剧、闹剧或悲剧。付秀莹通过书写乡村超市这个具有现代外观和传统内在的场所,不仅呈现了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描摹了生活在其间的乡民生命个体的隐秘心事。
对于有着久远历史和深厚文化根基的乡村社会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晚清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中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等饱含文化意义的差异序列,不仅影响和塑造着民众的观念、心理、情感与价值观,更直接地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逻辑上。《陌上》中的“超市”内外,即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生动描写,无论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时间流淌中的现代性进程仍然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超市嵌入乡村,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超市因此成为一个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双重物质文化空间,展现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渗透、磨合等复杂关系。芳村中的“超市”与超市中的“芳村”就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样本,正如曹文轩在《序》中所说,“芳村不小,芳村很大。它几乎就是整个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更大,大到整个人类社会”(34)曹文轩:《序》,付秀莹:《陌上》,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