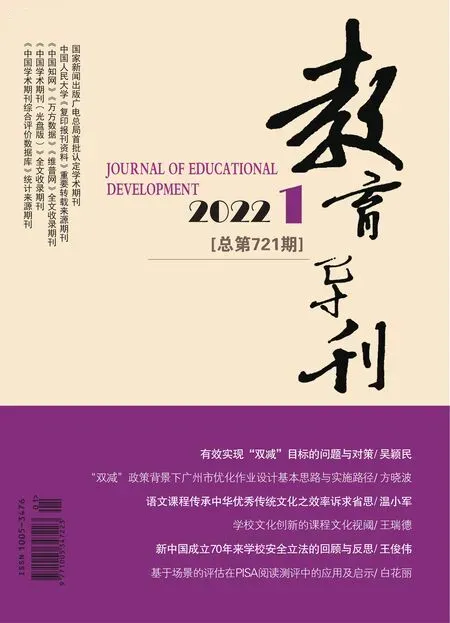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效率诉求省思
2022-03-18温小军
温小军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民间,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成为当前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颁布,更是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中小学具体学科的深度融合。语文学科作为一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事关“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等关键问题,在立德树人这一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因此,新时代的语文教育应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独特学科优势,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抓手,通过“以文化人”,实现“文化育人”。然而,语文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效率诉求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对其进行揭示并剖析其实质,进而提出相应的化解路径,显然有助于语文课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诉求之分歧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教育日渐备受关注的背景下,语文课程也自觉地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部于2014年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要求,应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语文等课程标准的修订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并且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具体规定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甚至提出要“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2017年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又进一步提到要修订中小学语文等教材,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基于这一目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说到:“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也把“文化传承与理解”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在教材方面,众所周知,统编版语文教材不仅大幅度增加了传统文化内容的篇目,在体裁方面也努力覆盖。这些都共同表明,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的自觉之举,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要如当前一些研究者所主张的那样进一步提高其效率。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发现,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语文课程有其自身的目标,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渗透其中,而不能喧宾夺主〔1〕。他们更主张采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水到渠成地实现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2〕。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学生精神生命奠基的一项工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短期内达到速成。他们反对“片面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应摒弃追求短期功利的浮躁心态,多问耕耘,少问收获,持之以恒,方有所得”〔3〕。
那么,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诉求在当前为什么会产生分歧?究竟如何理解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同样也从根本上关系到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
二、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诉求分歧之实质
为更清晰地把握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分歧的实质,我们不妨用发生学的方法追本溯源,去把握产生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分歧的思想源头。
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会出现效率诉求,主要是源于现代教学对效率的自觉追求。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条件下逐步确立、发展并不断完善起来的现代教学,效率是其固有之义,这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自从教育产生以来,如何有效地教?怎样做一个成功的教师?教师如何教得轻松而学生可以学有所成?历来是教学实践的基本追求。在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社会,‘效率’意识尤其得到强化,与之相应的教学活动也随之更加重视‘效率’。”〔4〕正是源于现代教学对效率的自觉要求,国家才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强调和进一步落实,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语文课堂也进而努力采取切实行动以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的分析可发现,“效率”一词主要出现在物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物理学中,效率指的是在一个单位时间里,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做了多少功,如果在相同的时间单位内,某一个过程、某一个物体做的功多,那么,这一个过程的效率就高。反之,该过程的效率就低。经济学领域里的效率,则指的是投入成本与回报之间的关系,如果投入成本越低,回报越高,效率就越高。教育学领域中的效率,主要取自经济学领域的含义,或者说,主要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来把握教学效率。它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即在规定的课堂时间内,通过既有的教学投入与最终获得的课堂产出。“课堂教学效率=有效教学时间/实际教学时间×100%。这表明,有效教学时间与实际教学时间之比值越大,课堂教学的效率越高;比值越小,课堂教学效率就越低。”〔5〕从这一角度来看,教学效率主要是一个科学教学论范畴内的概念。它体现了人们试图用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来把握教学。而众所周知,这一科学主义的思维最初主要来自西方,这可从现代语文教学这一角度得以具体认识。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改良、戊戌变法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废科举兴学堂,语文学科也走向独立和现代化,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语文课程从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评价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诸如单一化的教学目标、程序化的教学过程、模式化的教学方法、标准化的教学评价等,无不打上了西方科学主义的烙印。也有研究者将此称之为“科学主义的泛滥”〔6〕。正是从这一点来看,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诉求体现了来自西方科学主义思维下的现代教学对效率的固有追求。
那么,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又会出现对效率诉求的质疑呢?这主要是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汉语言文字为途径,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对象所致。众所周知,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理性、逻辑、分析见长,而是强调天人合一、以伦理为本位,在思维方式上则重综合、整体、灵感和感知。这也导致我国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一系列的教学方法与经验,诸如多读多写、熟读精思、重体悟等,以及以“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为集中表征的习得性学习过程。所以叶圣陶先生也曾说:“学习语文不能要求速成。”〔7〕吕叔湘先生则把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比作农业而不是工业。同样,以“人文化成”为目的的传统文化教育则具有“延迟满足”的特征,即它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外显效果,而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其效果逐步体现出来。
正是从这些特点出发,一些研究者质疑甚至反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诉求,甚至认为其带有过于明显的“功利性”。他们希望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水到渠成,不要追求“轰轰烈烈”,“不要操之过急”,要“耐心等待”,静待花开。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当前人们在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诉求之间的认识上出现分歧,是来自西方科学主义思维下现代教学对效率的自觉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汉语言文字)所固有的特征之间的矛盾。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化解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诉求的困惑,合理认识、理解与把握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诉求,便也需要在来自西方科学主义思维下现代教学对效率的自觉追求与传统文化(以及汉语言文字)的固有特征的双重视域下进行。
三、化解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诉求分歧之路径
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的认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为效率标准的确立,二为评判方式的建构。
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标准的确立即为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标的厘清。因为从本质上说,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是人们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主观反映。
当前,关于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在整体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以实用性目标为主,他们认为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渗透在语文课程之中,应坚持语文课程自身的独特的本体性目标,即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有一些研究者因此还直接将提升口语表达、阅读和写作能力水平等作为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在文化目标下把握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主张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以精神层面为主。这正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所说:“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8〕
如前所述,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标的厘清也应在双重视域下进行。这也体现了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科学人文主义的基本诉求。关于此,叶圣陶先生在阐述文言文教学时也曾说到:“对于‘文学名著’,似乎该偏重在涵泳和体味方面(通解文意当然是先决条件)”“对于‘近代文言’,似乎该偏重在基本训练方面”〔9〕。这表明,因文言选文特点的不同,可分别基于实用目标与文化目标提出不同的要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多年来各种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课程标准对文言文实用目标方面的规定也特别强调“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本文以为,其中的“浅易”二字值得注意。这似乎表明:对于一些浅易的文言文,可以从实用目标的角度加以把握,对于一些非浅易的文言文,则可以从文化目标的角度加以把握。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在实用与文化的双重目标下把握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说,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不仅应包括属于实用目标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也包括属于文化目标方面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如此,其效率标准亦同理。
鉴于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既包括实用目标也包括文化目标而具有综合性,那么,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的评判方式也应实现多元化。
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用目标,诸如知识与一些简单技能等,可以通过及时效率来体现,而且也应当努力提高其及时甚至外显的效率。从这一点来看,当前一些研究者所主张或实行的通过诸如考试、比赛以及相关活动来评判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的做法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值得继续提倡。
但是,对于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的文化目标,较之知识与简单技能之类,显然更为复杂,因此,对于这类目标,不仅应关注其结果,还应注重其过程。应用表现性评价的方式来考察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以评判其效率。同时,诸如情感、态度、价值观之类的文化目标,其效果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是通过累积的效应为他们日后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也就是说,其效率是滞后的,那么,对其效率的评判则应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如可对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效果进行不断追踪式的增值评价,将学生日后的成长和发展纳入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效率的考察范畴之内。如此,才可能对语文课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率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