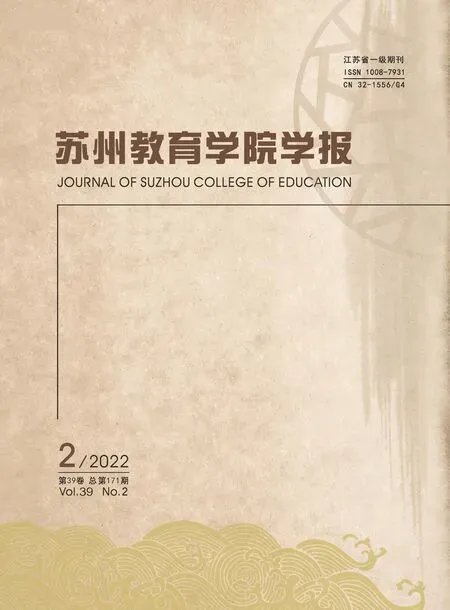新发现王鲁彦佚简及佚文
2022-03-18戚慧
戚 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王鲁彦,著名乡土小说家,原名王衡,又名返我,浙江镇海人,1944年8月因病在桂林逝世。“王鲁彦的一生,是旧中国一位富有才能的文学家在社会压迫和贫病交困中过早夭折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1]王鲁彦的小说师法鲁迅,被鲁迅亲切地称为“吾家彦弟”。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鲁彦文集》收录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但仍有不少文章散佚于民国大小报刊中。笔者搜集资料时,辑获王鲁彦佚简五通、佚文数篇,为了进一步推进王鲁彦研究,现择要介绍并略作梳理考证。
一
据统计,王鲁彦书信现存二十一通,即致史济行四通、致汪馥泉两通、致赵景深两通、致杨和风一通、致姚蓬子一通、致《广西日报·漓水》编辑一通、致周贻白一通、致靳以一通、致茅盾一通、致王西彦七通①参见鲁彦:《紫竹林中小札》,《人间世》1936年第1期新,第28页;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上海书店出版社1936年出版,第9—11页;赵景深:《纪念两个朋友:王鲁彦·谢六逸》,《新文学》1946年第1期,第33—36页;赵景深辑注:《现代小说家书简—现代作家书简之一》,《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5页;编者:《答杨和风先生》,《文艺杂志》1942年第3期,第41页;鲁彦:《致蓬子》,《文坛》1942年创刊号“作家书简”栏目,第4页;周春英:《王鲁彦的佚文及佚事》,《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第188—194页;鲁彦:《遗墨(手迹)》,《文艺春秋·朝雾》1945年第4期,第47页;王西彦:《一个朋友的病和死》,《文艺春秋》1946年第6期,第9—23页。致靳以手稿现藏天一阁博物院;致茅盾手稿为孔海珠所收藏。。新发现的有致郭青杰两通、致汪以果一通、致孟十还一通和致蹇先艾一通。
(一)致郭青杰
王鲁彦致郭青杰的两通信,第一通刊登在《西京日报·明日》1933年4月13日第8版,题名为《你还活着》。兹照录如下:
老戈:
我们隔别太久了。不通消息,也打听不出消息,正像我们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样。上海别后,应该还不满十年吧,但在我像是过去了几世纪了。我们的艺术家特夫,在我毫不知道的时候死了,天可怜,他死了两年,我才得到这个消息。然而,我们的哲学家诗人还活着,我又是多么的愉快呵!
有三个朋友告诉我,我们的哲学家诗人已经坠落长久了。据说在济南的时候,香烟里要裹着什么毒物,这是腐化。据说在西安,被人叫做“铁公鸡”,是一毛不拔的个人主义者。
然而,我不以为这是坠落,我以为我们的哲学家诗人已经进步到了顶点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习常地生活着的,我以为只有缺少灵魂与天才的常人;真正的诗人是必须用吗啡来迷醉自己的,在这样的人类中,抱绝对个人主义者才是参透了宇宙的神秘的哲学家。因此我非常喜欢听到了我们哲学家诗人的消息。
我依然是一个庸凡的人,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生活的重担。音乐家的梦已经打销了,做小说家也觉得没有资格,政治家又怕做,革命家觉得可笑。思想没有归宿,也不想有归宿。未来的希望的梦是没有的,幸也不陷入绝望的悲哀。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可笑的,但在我倒也觉得没有什么。
西安应该是缺少趣味的吧,但因为老朋友们在那边,我很想来玩一玩。而尤其希望的是我们的哲学家诗人青杰老哥能够南来,和我久住一下,或者至少同在南京的我们的太平洋①王鲁彦在《我们的太平洋》(《文艺月刊》1933年第11期,第1576—1580页)中,提到他十年前曾在南京住了将近半年,太平洋是“被我们中间的一个同伴,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同伴所首先发现,所提议而加衔的”,这里的“诗人兼哲学家”指的便是郭青杰。中洗一次脚。
请常常给我一点消息,我最渴望地思念的老哥。
愿平安永久和你一起,愿你活得和我一样长久。
你的老弟鲁彦。
信的抬头为“老戈”,这是郭青杰的笔名。郭青杰,生卒年不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聂尚宣、高盟萍、徐国馨等人共同创建西安生存分社,创办《生存》周刊,曾为《西京日报》编副刊,1933年创办《青门日报》,写有不少诗歌、散文。覃英说鲁彦的作品曾发表在郭青杰主编的《西京日报》副刊上,笔者查阅《明日》和《文学周刊》等副刊,发现除已披露的《人类的喜剧》《汽笛》《〈阿斯巴西亚〉引言》《阿斯巴西亚》等文,还有书信《你还活着》《又是标榜》《凡美信笺:鲁彦寄自镇海》和散文《我的春天》,未见她所说的“其中不少是诗,用笔名发表的”[2]。
身在南京的鲁彦收到郭青杰从西安的来信,感到很高兴,这是两人多年未见面后的一次通信,他们共同怀念着两年前病逝的好友赵特夫②赵特夫,原名荣鼎,字铸生,江苏沛县人。工书画,写有不少诗歌。他曾参与开展狂飙戏剧运动,还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不幸患肺病逝于北平。王鲁彦在《给海兰的童话》(西皮尔雅克著、鲁彦译,开明书店1933年出版)扉页题曰:“译呈肖眉和特夫。”。鲁彦称郭青杰为“哲学家诗人”,得知他还活着的同时,还听闻他堕落的消息。他认为“只有缺少灵魂与天才的常人”才能习常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诗人是要用吗啡来迷醉自己的,“抱绝对个人主义者才是参透了宇宙的神秘的哲学家”。对于自己的现状,鲁彦认为自己是一个“庸凡的人”,肩负着生活的重担,音乐家的梦已打消了,他自认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又怕做政治家,他已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书报检查机关的工作,做革命家则觉得可笑。他称自己“思想没有归宿,也不想有归宿。未来的希望的梦是没有的,幸也不陷入绝望的悲哀”,可见王鲁彦此时的心态,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的矛盾与悲哀,陷于痛苦之中,欲逃避现实而不能,只好做一个看似玩世不恭的无心之人。他想念西安的老友,于是邀请郭青杰再同游南京玄武湖。
1933年4月17日,郭青杰的《复鲁彦》刊登在《西京日报·明日》上。他在信中介绍了自己在西安的情况,远离现代都市、单调而无变化的生活使他很容易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怀念着从前的朋友们,与鲁彦“共度了那青春燃烧正烈时的困苦而又欢快的时间”也令他难忘。对于自己堕落的传闻,他表示也许正是“最烦闷的时期”:“诗人的梦是破灭了!这饥饿倒毙的人众,是不能无视的,即令只有这,已足以改变我整个的生活了!”还提及所见到的几位未名社诸友的情况:“他们除了努力产生了些作品外,生活上很少变更,静农多了几孩子,几架线装书,两本作品,仍是一边闻着脚臭一边谈笑,丛芜、霁野小白脸上多了些胡子,多了些洋装书。”[3]他希望鲁彦能够到西北来,“这里有广大的原野,有惊心动魄的悲剧,这不仅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同时以你熟练的技巧,正可以完成一部不朽的杰作”[3]。
1934年2月下旬,王鲁彦离沪赴陕,应友人党修甫之邀到郃阳县立中学任教。致郭青杰的第二通信便写于同年4月21日,即刊登在《西京日报·明日》1934年4月28日第5版的《又是标榜》。
老戈老哥:
到此后无日不思西来,乃为道路所困。日前有汽车开潼,当欲趁便,又为老党所阻。奈何奈何?此间寂寞殊甚。闻长安多故友,愈增相思矣!老哥乎,一别十年,何日得不复吟“长相思,在长安”,①原文如此,此处“,”似多余。之句耶?时因风便,乞惠佳音,以舒积怀。
老弟鲁彦拜启,四月二十一日。
信中,王鲁彦说想去西安,未能成行的原因是困于道路,交通工具缺乏,偶有汽车路过,却为老友所阻。相对于此地的寂寞,他更加思念西安的故友。王鲁彦到郃阳后为何急于离去?1934年5月12日,他在致周贻白的信中写道:“学中情形殊坏,经济亦困难,修甫颇狼狈,下期恐难继续。弟亦在此厌烦,下期决不敢再来矣。”[4]《西京日报》上的《王鲁彦去郃阳的前后》[5]也对此有所说明:党晴梵担任郃阳中学校长后,致力于校务改进,与党修甫共商发展之计。而学校经费已不足以支持办学,加之地方劣绅的破坏,所请教员被称为“下等人”。倘若政府不设法补助,学校恐有关门之虞。“鲁彦在此状态中精神非常痛苦,几次欲来西安,均由学校及学生的恳切挽留,不能成行。如眼前再无办法,鲁彦即来西安友人处小住。”[5]不久后,鲁彦在暑期离开郃阳返回上海。同年8月底,他携妻儿前往西安,在省立高级中学执教。在西安期间,他参与组织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担任指导,还计划筹办《文学杂志》,与党修甫、郭青杰、汪以果等人共同推进西安世界语学会的成立。
(二)致汪以果
1935年12月18日,《西京日报·明日》刊登了《凡美信笺:鲁彦寄自镇海》。兹照录如下:
凡美:
我们到家一星期了,没有尽先写信给你,想你也能猜想到我们有不少的琐事忙着的。
我们一路都好,过沪时勾留了五日,见到许多久别的朋友。等待着我着手著译的工作很多,这半年内可以作一个自由的人了。
在西安住了一年,似乎并没有见到天空。只有故旧的天是特别大,变化特别多。我们的屋子在青山与绿水的围抱中,一到晚上遍地起了音乐。水面的萤火与天空的星光映辉着。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唉唉!西安归来,真想江南老了。
乌鸦又该成群的在你头上飞过,哇哇地叫着了吧?苍蝇少了吗?年青人为什么要在那样的地方多年作客呢?请多多保重,好好保重。
鲁彦 月 日
信的抬头为“凡美”,即汪以果,他是《西京日报》的撰稿人之一,并在《西京日报》上开辟了“凡美信笺”栏目,刊登朋友们寄给他的信。1935年底,王鲁彦离开陕西,在上海停留五日后返回故乡镇海,这一通信便寄自镇海。信中,他告知友人路上一切都好,在上海见到了许多久别的朋友,等待他的著译工作可使他半年内做“一个自由的人了”,不用再为生计四处奔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他感慨在西安住了一年,没怎么看见过天空,如今回到故乡,这里的天空特别大且变化多,屋子置于青山绿水中,一到晚上,萤火与星光交相辉映。这样的世界与西安的成群乌鸦、满地苍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安印象》[6]中,他笔下的西安便是乌鸦的领地、苍蝇的世界。他反问汪以果年青人为何要在这样的地方客居多年,并让他好好保重。
(三)致孟十还
王鲁彦致孟十还的信,刊载在《大时代》1938年第13期的第197—198页,题目为《快要插秧了》①此文的部分内容刊登在《同仇》1938年第6期,第8页,题名为《伟大的农民》。,文中有孙福熙所作插画《后方将士》。全文如下:
十还兄:
来信读到了,我最近到外县旅行了一次,所以迟复。这次旅行得到了从来未有的快乐,为此赶快写信告诉你,并请你将此信刊登,希望全国的同胞都能知道这好消息。我回来后曾把这好消息首先告诉了春苔兄,我看见这位艺术家感动得只是连连点头,说不出话来,快乐得眼角湿润了。过了许久许久,当我告诉他,我要把这好消息带给全国同胞之后,他立刻自己提议说他就给我画一幅《后方将士》的插画寄给你同时发表,而且答应第二天就画好。你应该认识这位画家的吧?他有着一个最易感染的心灵,温和得像处女一般的性情,但同时却又非常沉着,不轻易动笔,不轻易发表作品的。自从他到长沙后,许多人请求他作画,他都没有动手。无疑的,他和我们一样,因了关怀整个民族生存的抗战,他的情绪常常难得平静下来。而今天则不然,我觉得他似乎把一切忧虑全忘却了,环绕着这位艺术家的心灵的仿佛是一幅和平安静的自然的图画;整洁的田野,平静的池塘,碧绿的稻秧,用新黄的泥土修筑过的田滕②原文如此,似应为“塍”。以下同,不另注。,以及那从容不迫地工作着的农夫和骑在牛背上歌唱着的牧童……
是的,这一切最使人愉快的图画全映入我的眼帘了,当我这次旅行的时候。这是一幅好伟大的图画呵!在前方,日夜听见枪炮声,我们忠勇的将士无时无刻不在冲锋肉搏,为国家民族作壮烈的牺牲,而在后方的农村,却依然和往日一样的安居乐业,呈露着和平的景象,毫无战时的意味。
为什么只有和平的景象,而没有战时的意味呀?难道后方的同胞到现在还是醉生梦死吗?不,决不!后方的民众,连妇女一起,都早已受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了,只要给他们枪弹,他们就会对着我们的敌人瞄准。他们中间已经有不少的兄弟和儿子自动的或被征发的上前线去杀敌,因着这关系,他们所受到的痛苦,所感到的愁愤是最为深切的。他们决不会醉生梦死。他们现在能够安居乐业,正是他们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在支持抗战,在为国家民族尽最大的义务。在前线完全忘记了个人的一切,努力杀敌的同胞是伟大的,但在后方,随时随地可以触引起人生最悲痛的生离死别的,而我们的同胞却能自己抑制情感,更加辛勤而又从容不迫的尽自己的责任,这伟大是多么值得我们颂扬呵!又是多么值得我们感谢呵!抗战的必胜,民族的复兴,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铁一般的信证了!
在平时,湖南人原是当兵最多的,自从抗战以来,应征的也可以说是最多,很久以前,许多人曾因此对于田作起了很大的忧虑,因为湖南是产米最多的区域,丰歉关系着全国的安危,尤其今年是与抗战的前途有极大影响的。最近蒋委员长通令保护春耕以后,一般人忽然给提醒了,常常显得非常忧虑的说:
“今年谁去耕种呀,不是许多壮丁都上前线去了吗?”
但是我这次从城市出去旅行,所见到的怎样呢?我是坐火车出发的,坐汽车回来的,经过的地方不同,来回凡六七百里,所望见的几乎全是田野。
那些田野什么样了呢?贮满了水,仿佛湖沼一般发着明亮的光。底下是早已犁过了的松散的泥土,正游泳着成群的黑色的蝌蚪(有些地方已经听到了蛙诗人的歌声)。许许多多水田里这里那里划着方的,长方的,或圆的肥料圈,整齐得仿佛用仪器画出来的一般;有少数的水田已经开始在耙了,但大多数的却还静静地躺着,在等待稻苗的成长,这里那里插着一根短短的竹子,竹梢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红布,仿佛旗子似的,那就是曾经播了种子的地方;也有少数的地方已经密集地长了一二寸的嫩绿可爱的稻苗了,农人们现在正是休息的时候,很少出现在田野里,但他们第一期的工作时做得非常完善的,不但看不见一小块荒田,他们甚至把所有的田滕全修筑过了,田滕的两边全是新黄的泥土,田滕上面的两边长着碧绿的短短的野草,而中间则是一线黄色的行人道。这些美丽的田滕曲折纵横,使单调的水田变成了错纵复杂的图案,在迅速地游行着的车中望去,仿佛卡通画家所添加的线条,处处有生命,都在水田里活动着,跳跃着。这真是至高的艺术,同时也就证明了我们的同胞不但能耐劳,能克苦,而且也沉着从容,足以担负天下最艰难的困厄,中国民族的伟大,恐怕就在这一特性上吧。中国是农业国,现在在前线浴血抗战保卫国家一寸一尺的土地的将士大半是农民,而在后方不荒废一寸一尺的土地,支持长期抗战的将士也是农民,谁说抗战的最后胜利不属于我们呢?
看吧,漫天遍野的碧绿的秧田就要出现在眼前了!在我们后方的将士的辛劳的手里,培养生命的粮食就会很快的成熟了!感谢而且祝福呵!
鲁彦敬白
(四月二十日)
这一通信写于1938年4月12日,正是王鲁彦在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副刊期间。收信人孟十还,原名孟显直,又名孟宪智,笔名孟咸直、咸直、孟斯根、斯根,辽宁人,曾留学苏联,翻译过不少苏俄文学作品。1937年12月,《大时代》周刊在汉口创刊,由孟十还主编。信中,王鲁彦说这次旅行“得到了从来未有的快乐”,想将这“好消息”分享给孟十还以及全国的同胞,因而请他将此信刊登出来。他已将这“好消息”告诉了正在长沙的孙福熙,孙福熙听后很感动,主动提议画一幅《后方将士》附文发表。而这“好消息”指的是他在湖南农村所见到的安居乐业的景象。战士们正在抗战前线奋勇杀敌,后方的民众并未醉生梦死,而是“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在支持抗战,在为国家民族尽最大的义务”,王鲁彦赞赏他们能“抑制情感,更加辛勤而又从容不迫的尽自己的责任”。作为产米大省,湖南粮食的“丰歉关系着全国的安危,尤其今年是与抗战的前途有极大影响的”,壮丁们虽然上前线了,但农田并没有荒废,春耕正有序开展着。旅途所见,田野中充满了生机,泥土已被翻松,种子撒下,嫩绿的稻苗正在生长,修筑过的田滕“曲折纵横,使单调的水田变成了错纵复杂的图案,在迅速地游行着的车中望去,仿佛卡通画家所添加的线条,处处有生命,都在水田里活动着,跳跃着”。王鲁彦称这为“至高的艺术”,不仅表现了同胞们能吃苦耐劳,而且沉着从容,能担负起天下最艰难的困厄。他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热情地歌颂农民的伟大。
(四)致蹇先艾
1945年3月6日,《贵州日报》增办了文学副刊《新垒》,由蹇先艾主编,设有“作家书简”栏目,刊登了沈从文、齐同、王西彦、鲁彦、朱雯和罗洪夫妇等人的书信,信的抬头均被隐去,代之以“××兄”和“××先生”。鲁彦的这通信刊登在《贵州日报·新垒》1945年3月26日第4版,题名为《作家书简(四)》。全文如下:
××兄:
承赐两稿,甚感。《春酌》已发排在五期,《父母》可编入六期,不久亦将送审发排。弟病年余未痊,近又入院开刀,迄今满二十三日,尚难起床,情形甚苦,故久未函复,乞谅。四期三五日内可出版。五期开始校对。印刷殊坏,下卷始能调整,殊觉对作者与读者抱歉。因老板只想赚钱,弟无法过问也。二卷一期拟在六月十日送审发排,因印刷迟缓,不得不提早。仍希兄有稿赐下。读《春酌》与《父母》感慨殊深;然另有一种儿女则殊有希望也,愿兄稍自慰。贵州生活如何?兄已在彼住久了,有意到这边来过一些时候否?西彦现在本省省立平乐高级中学任教,兄如有意,随时可去该校,弟与西彦当为接洽。广西省中任两班国文,目下待遇每日约×百××元。由贵州来路费亦可交涉由校方负担。此间米价新秤百斤××××元,火柴每盒××元,物价奇昂,但不知比贵州如何?请斟酌,草草祝好。
弟鲁彦 五月十三日
根据信的内容,可知“××兄”为蹇先艾。信中,王鲁彦感谢他寄来《春酌》和《父母》二稿,告知前者已排在第5期,后者可编入第6期。查《春酌》载《文艺杂志》1942年7月15日第5期。因此,可知此信应写于1942年的5月13日。《文艺杂志》于1942年1月在桂林创刊,王鲁彦任主编,为了办刊他向友人多方邀稿,住院养病期间仍在编排杂志。蹇先艾在《悼鲁彦》中写道:“三十年的上半年,他开始筹备他的《文艺杂志》。因为各方面寄稿的迟缓,及登记手续的麻烦,十月才着手发排第一期。他为了多年的痔疮,九月初,便在医院开刀了,一面他还躺在床上,写信给他的朋友,报告近况兼催索文章。他对于朋友的热情太可感了。他对于自己的事情和杂志的不能顺利进行,常常心里不痛快;对于朋友的不平的事情,也一样的着急,不分彼此。”[7]这与信中王鲁彦所述心境一致,他在入院开刀后,近一月“尚难起床,情形甚苦”,杂志办得也很辛苦,“印刷殊坏”,对作者和读者感到抱歉,而出版社老板只想赚钱。
蹇先艾先后寄来《孤人》《春酌》和《父母》三篇小说,实际只刊登了前两篇,《父母》并未发表在《文艺杂志》第6期,蹇先艾对此事有记载:“为了我的小说《父母》被扣,在《文艺杂志》上预告了而不能发表,也引起过他极大的愤慨。”[7]查蹇先艾文集、年谱、著作年表均不见小说《父母》,至于为何被扣,囿于资料,难以考证。笔者推测可能是因小说揭露国统区种种黑暗、腐败的现象而被查,因已发表的《孤人》和《春酌》便是此类题材。信中,王鲁彦问候蹇先艾在贵州的生活状况,告知他王西彦正在平乐中学教书,询问他是否有意来广西,如有意将代为接洽,还详告广西当地的物价情况。
二
新发现王鲁彦的佚文有《我的春天》《怎样纪念鲁迅先生》《鞭炮声中》《我渴望见到故乡》《鸽子》等,现依作品发表时间介绍于下。
1935年2月13日,《西京日报·文学周刊》第9版“春之特辑”刊登了王鲁彦的散文《我的春天》。文中,他回忆起奔波在外的父亲每年回家过年时,总是会在立春这一天命他写“立春大吉”“新春如意”等大字,并张贴于门上。父亲对立春始终怀着虔诚的态度,深信吉祥会来,一切都会如意。而鲁彦长大后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不再相信,之后的二十年,他总是让父亲独自去写、去贴,有时还表现出批评的态度。然而父亲却始终这样相信着,依然年年这样做着,“他虽然渐渐的老了,每次一到立春,他的希望便生长起来,他的生活也似乎显得更有意义,更有力量了”。这份仪式感让父亲对生活充满了信念,而作者的生活却渐渐地阴暗了,没有希望,也没有信仰,季节的变化引不起一点兴味。文末作者感慨道:父亲和他的时代都离去了,现在是“我”的时代,在这春天“我拿什么教养我的孩子呢”。
1938年底,王鲁彦辗转到达桂林,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活动。他在桂林《扫荡报》副刊《瞭望哨》《星期版》《现代文艺》等上发表了《怎样纪念鲁迅先生》《我渴望见到故乡》《鞭炮声中》《鸽子》等散文。1939年10月19日,正值鲁迅逝世三周年,王鲁彦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并写下纪念文章《假使鲁迅先生还活着》和《怎样纪念鲁迅先生》,前者已收入文集;后者未见披露,其最初刊登在桂林《扫荡报·瞭望哨》1939年10月19日第4版“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中。两篇文章都围绕着“团结,抗日,反汉奸”主题,在《怎样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他谈到以往纪念鲁迅时,想到的是怎样继续鲁迅先生的工作与发扬他的精神,如今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怎样与抗战配合起来”,并称“倘使他现在活着,一定是站在这一战斗的最前线的”。他说鲁迅活着的时候,便明确指出当时的任务是抗日、反汉奸,现在抗战两年多了,纪念鲁迅应该要“检讨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团结统一,文艺界各派别作家都做到了;其次是抗日,文艺界也有不少人在前线与敌人拼杀,在后方参加活动;最后是对于反汉奸工作做得还不够,应该检讨,他认为“所谓不够,并非是对那已经公开成为汉奸的人的讨罚不够,而是平日对那些潜伏在我们抗战阵营里的汉奸和动摇或投机分子,批评太少,创作也少”。他以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被敌人利用后被认为是不妥的作品为例,呼吁“为了加强抗战的力量,我们的文艺界必须正视现实,反映出忠勇壮烈的严肃的抗战和荒淫无耻的汉奸及动摇投机的行动,而且对于后者,正是应该加以猛烈的抨击的时候”,继续发扬鲁迅先生不妥协的精神,坚持“团结,抗日,反汉奸”。
《我渴望见到故乡》载桂林《扫荡报·星期版》1942年1月11日第4版。王鲁彦为了谋生而远离家乡,长期过着漂泊的生活,他写有不少关于故乡的回忆性散文,多取材于乡土,文字也充满了怀旧与乡愁,成为他心灵的慰藉。在这篇散文中,身在异乡的他怀着无限爱恋的心情回忆故乡的风土人情,那里有紫云英、菜花、松林、河流、萤火虫、云霞与朝露,他怀念除夕前后故乡的种种习俗,想念勤劳淳朴的乡亲——田野里的农夫、打桨的船夫、挑柴的樵夫、捕鱼的渔夫、挑海味的贩夫、抽烟卷的老者和扎四角辫的小女孩。父亲的墓前应该长满了荆棘与草莽,他想赶紧回到故乡,而故乡正遭受敌人的蹂躏,“愿新年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带着希望与祝福来到人间,跟我们千千万万离乡背井的同胞,一齐打回故乡去吧”。这无疑表达了作者对野蛮侵略者强烈的愤怒,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抗战。
《鞭炮声中》①此文曾被叶苍岑等编辑、叶圣陶校订的《初中精读文选》第5册(文化供应社1947年1月初版,第129—133页)收录,其中“题解及文体”写道:“本篇写述在鞭炮声中,新境与幻起的旧境间之对照,因而生出无限感触;为抒情文。”载桂林《扫荡报·星期版》1942年2月15日第4版“春节专页”。同期还有熊佛西的《我之旧历年观》、龙朱的《年关》、欧阳予倩的《似序非序》、蒙复的《送旧》和符浩的《人世》。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作者梦见四年前在上海的寓所内,卢沟桥炮声响起,收音机里传来救亡图存的呼声。他从梦中醒来,站立在桂林寓所的窗前,回想着梦境中同胞们在鞭炮声中举着龙灯游行庆祝胜利的到来。朋友的来访打断了他的思绪,将他拉回了现实,眼泪涌了上来。朋友忙安抚他,说有一天他会听见更热烈的鞭炮声和壮烈的场面,顿时他流下了希望与欢乐的泪水。借助梦境和幻觉,作者渴望战争胜利的心情跃然纸上。
《鸽子》载桂林《扫荡报·现代文艺》1942年12月21日创刊号第4版。这篇散文主要记述了在作者屋顶上空生活的一群鸽子,它们的声音和平又安详,略带几分悲苦之感。作者的记忆被这声音带回了遥远的北方,在这个小小的寨子里,他与住在屋顶上的鸽子和谐相处,默默关注它们的觅食、游戏情况,大部分时间里是和平、安静的,望着这些可爱的动物,会让人忘记一切烦恼。三个月后这份平静被打破了,一位无知的童子向它们下了毒手,鸽子受到袭击,叫声变得不安、惶惑。作者难以忘记一对老鸽子盘旋在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鸽子身边的场景。此后屋子周围很难再见鸽子的踪迹,悲苦的叫声永远留在了他的耳膜里,成了无法忘记的可怕记忆。此文表现了作者对弱小生命的同情与悲悯之情。
三
此外,王鲁彦的佚文还有《全世界庆祝的今年:世界语产生四十周年纪念》(《民铎杂志》1927年第9卷第2期,第1—4页)、《介绍狂飙演剧运动》(《中央日报·青白》1929年2月28日第3张第3版)、《爱》(《草野》1930年第2卷第11期,第91—92页)、《难去之物》(《民钟日报》副刊1930年7月16日、17日、18日第10版)、《买米归来》(《前线日报·战地综合版》1941年1月19日第7版)、《破铜烂铁》(《文风杂志》1944年第1卷第2期,第66—67页)等。以上佚文、佚简的发现,希望能裨助于王鲁彦研究。王鲁彦的佚文尚有可辑佚的空间,在他逝世后,桂林文艺界曾计划整理出版《王鲁彦全集》,2005年浙江省也曾策划出版《王鲁彦全集》,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鲁彦文集》较为完备地收录了其大部分作品。希望在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王鲁彦全集》能够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