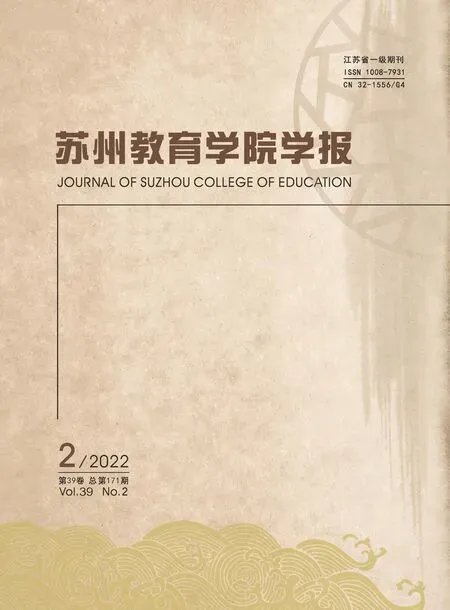轻重之间:叶弥小说的“调和”叙事
2022-03-18王亚惠
王亚惠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65)
叶弥一部分属于城市,一部分属于农村。6岁之前,她生活在苏州市区;6岁到14岁,她随父母下放至苏北农村;后又回到苏州工作、结婚、生子。叶弥在苏州生活了很长时间,但她始终觉得这座城市“不适合放置灵魂”[1],又逢位于古城区朱家园的家被盗,于是叶弥告别了城市,回到了农村,这一次,她在农村寻到了长久往地—太湖边上的临湖别院。地理位置的不断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叶弥心灵与心性的不断变化,她一直在寻找自身存在的最佳位置。叶弥的写作是随性而简单的,有灵感就写,没灵感就养养植物,照看照看动物,内心倒也闲适安然。这一生活和写作状态体现在叶弥小说上,就是无所谓大悲痛,更无所谓大欢喜,一切都是淡的、平的与“调和”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小说中的故事与故事、人物与人物之间,像潺潺流水一样自在流动,不知去向,任何矛盾、冲突、灾难都能以其调和之笔举重若轻地将其过滤和消解。叶弥的这种“调和”叙事,避免了尖锐刺激,只留下淡淡的空白。然而,由于叶弥小说重在调和,缺少调和之前的铺垫,这就导致其存在“调和”叙事下矛盾冲突潜隐和张力不足等问题,小说深度及批判力度均有所减弱。
一、“调和”之一:人与物
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关注和书写动物。莫言、贾平凹、迟子建、叶广芩等作家都在小说中通过描写动物或者以动物视角来表述对世界的隐秘看法。叶弥秉承了书写动物的传统,除此之外,叶弥在临湖别院的家里养了许多鸡鸭狗猫,她和动物相处超过了十年,可以说,她对动物的理解更生活化和细节化,因为她介入了动物们的生活,给它们取名字,给它们安个家。她晓得低着头不吠叫的流浪狗的小心思;她不厌其烦地给无主的小猫滴眼药水,甚至像亲人一样照顾它们……她与动物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她认为动物教会了她许多,也滋润了她的心灵,[2]她甚至更直白地说道:“这个世界的人不能被真心爱恋,因为人的心太复杂。但是你尽管放心去迷恋动物或者植物。我爱动物和植物。”[3]127于是,身陷现实生活的压力和紧张的人际关系中的叶弥,从动物身上找到了某种缓和的途径。动物于她,早已超越物种之间的差异,建立了稳固而深刻的情感联系。她在《风流图卷》后记中写道:“不说为了什么写作的理想而奋斗,光说住到乡间九年,收留了无数没有生存能力的猫狗等小动物,我给予它们重生,它们也助我‘养性’,我深信它们还替我消前世之业和今生之罪。与它们打交道久了,会明白什么才是最自然的生活态度。”[4]438
《市民们》[5]1-49是叶弥的初期作品,这在叶弥的整个小说创作历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奇怪的是,评论家们似乎选择性地将其遗忘。《市民们》以南北街发生的三个荒诞的故事展开,由此有了居委会老许的故事,老许在工作上雷厉风行,但在生活上却不如人意,女儿精神有问题,丈夫陈忠良假装阳痿,虐待老许,于是心理扭曲的老许便转而去报复猫,不让猫怀孕,使猫发出瘆人的嚎叫。丈夫与老许、老许与猫,都处于虐待与被虐待的对立关系。但猫生活在最底层,它无处发泄,也不能够报复,最后,只能“干瘪的”“毫无生机”地困死在深井里。细细考量困死在深井里的“猫”就会发现,猫的处境与人类相似,其代表的是身处牢笼且无法挣脱的人类,也暗喻人与人之间无尽的相互折磨、相互摧毁的真相。由此,再去看叶弥的《猛虎》[6]就有了某种承继关系。用叶弥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女人杀死一个男人的故事,在叶弥看来这似乎没什么大惊小怪,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表面来看,由于女人给男人喂药不及时,导致男人死去,女人似乎是在间接杀人。然而,故事的主题是女人在无爱的生活中耗掉了所有的一切,变得冷酷而麻木,呈现出一种枯死的状态。所以从另一种意义来讲,也应该算是男人杀死女人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女人对自己女儿的暗示,当女人去忏悔的时候,她拉着女儿一同前往,似乎在向女儿“传经布道”,这是否隐喻女儿将来会重复母亲的悲剧,我们不得而知。叶弥用淡然的语言娓娓道来,仿佛这里的一切都无关痛痒,只是生活中的常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更易刺痛读者。小说《猛虎》中的“猛虎”二字,代表着血腥和力量。叶弥的笔端总是透露出一种坚定的力量感,她能看到并直面生命中的冷冽,展现出生活中不忍直视的一面,同时又在不经意间流淌出一股温情。“猛虎”虽猛,但其内心深处是柔弱的,仍会不可避免地遭受伤害,她既要面临着各种对抗,也要在残酷的生活中努力保住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美好。
叶弥爱写蝴蝶。《小女人》[3]185-252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被雨水打湿翅膀、撞到窗户上的“蝴蝶”,凤毛之于蝴蝶,蝴蝶之于凤毛,偌大的世界似乎只有她们能拥抱取暖。评论家张立、孙宏波曾对《小女人》中的“蝴蝶”意象进行专门讨论,其结论是:“迷失的蝴蝶暗示了凤毛晦暗不明的蝴蝶运命。”[7]凤毛和丈夫离婚,抛弃了世俗意义上的美满生活,游离于胡老师、董长根之间,后又在夜晚归途中遭到身高一米六的小偷强奸,一个女人所有的若难都被她遇到了。这本属于很沉重的遭遇,是女性和家庭的双重不幸,但叶弥却用一种与此相悖的轻松、调侃式语言进行叙述,比如,当“一米六”打劫凤毛时,凤毛竟然觉得穿了厚底鞋的“一米六”无比英明,因为“用目前这个姿势性交的话,是最恰到好处的”[3]245。从这个角度去看贯穿文中的蝴蝶意象,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蝴蝶本身是轻的、飞翔的,但因被雨水打湿翅膀,变成重的、危险的。卡尔维诺谈到小说的轻与重问题,借用瓦莱里的诗句说:“应该像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8]这样的“轻”才是有重量的。被打湿翅膀的蝴蝶之“重”,亦是轻飘之“重”,是本质而非外力施压之重。《香炉山》[3]105-124中亦有蝴蝶意象,这时候的蝴蝶翅膀已经躺在地上,彻底不能飞翔,“我”与苏就在这样的境遇中相识。“我”因蝴蝶心存芥蒂,苏却纯净如水。最终,“我”被苏感染,苏给了“我”享受生活的勇气。小说中虽然未再提及蝴蝶,但蝴蝶似乎早已翩翩飞舞。
叶弥认为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在她看来,人和动物浑然一体,能够互相陪伴和安慰,就如同其小说《风流图卷》虽着力于表现时代之伤痛,却更致力于描写时代、环境及其“物”对人本性的掩盖乃至于遮蔽。因此,她从不孤立地看人,而是将之放在与动物、植物的交往互动之中。叶弥沉潜到动物心中,寻找其内在秘密。猫被囚、蝴蝶翅膀被淋湿、猛虎被杀死、苍蝇懒得飞动,等等,叶弥营造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意象,呈现出动物世界的悲欢离合,同时也借动物的视角观照人,究竟是动物可悲还是人可悲?他们如何更好地相处?叶弥在深究这些问题时,也是在拉近、调和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
二、“调和”之二:谎言与真实
叶弥爱写谎言,对谎言不具批判态度,并将谎言当作现实生活中温暖的留存。在其小说中,说谎者或是无意、或是有心地营造出“真实”的环境,说谎者并不孤立存在,与受骗者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虚伪和谎言充斥了人们的一切关系”[9]357-358。因此,在叶弥这里,真实和谎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彻底了解谎言,才能懂得真实的奥秘,谎言有时比真实更有力量,也更能接近和还原生活本身。
在《父亲和骗子》[3]19-38中,叶弥塑造了一个经典的骗子形象—老冯。老冯博取了“我”的父亲的信任,骗走了父亲十万元现金,而后便不知所踪。父亲知道被骗后,并没有表现出有多悲伤,只是他在与老冯走后出现的骗子们屡屡交手后,颇感失望,因为他们行骗的伎俩与老冯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叶弥颠覆了传统的骗子和被骗者形象。骗子老冯温文尔雅,步步为营,有足够的耐心和温情,在他行骗成功后,还为父亲准备好服用的药物,在留给父亲的信中提出了三条暖心的建议。父亲对骗子老冯不恨不怨,还时常怀念与老冯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对父亲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老冯欺骗了他,而是老冯离开了他。巴赫金认为骗子形象是由“笑点”构建起的“人生存在外在化”[9]355,具有公共性的特征。许多经典的骗子形象莫不如此,如《西望长安》[10]中的栗晚成,就是极为可笑的。栗晚成伪装成“党员”“英雄”“干部”等身份,他利用这些假身份行骗,居然还成功了。叶弥小说中的骗子形象极具内在性和个人性,如父亲对老冯的怀念乃至痴迷,这固然与父亲的执拗有关,更重要的是,父亲在与老冯的交流中体会到了精神的纯粹。叶弥借助旁观者视角叙述父亲和老冯的交往,再次强调了父亲迷恋老冯这一事实。“我”看到父亲朝老冯的那边斜坐着,“我”也知道,“父亲是依恋老冯的,他不在乎表现这人性脆弱的一面,这是父亲的幸福”[3]27。叶弥运用略带戏谑的手法,呈现出人心灵空虚的悲凉,在这样的空虚和无人依靠中,谎言竟成为骗子慰藉受骗者心灵、情感的一剂良药。
真实生活是残酷的,是令人窒息的,唯有谎言,或许能为生活增添些许色彩和温暖的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骗子,何尝没有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撒过谎,或欺骗过自己和他人。是否撒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撒谎,撒谎的初衷和动机是什么,因为这些人物的“存在是另外某种存在的反映,并且不是直接的反映”[9]355。《现在》[5]151-189中的全金,她的一生与其说是被战争摧毁了,不如说她活在了别人的谎言里。她相信谎言,回家乡开证明,是为了再次确认谎言不是谎言,是真实的。《霓裳》[11]178-192中要饭的老葛,她从乔麦婶身上看到了她所艳羡的一种生活,于是她与乔麦婶相处的夜晚,她不停地说谎,仿佛从谎言中得到了生活对自己的补偿,从贫苦而无望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丝满足与希望。《郎情妾意》[12]中的范秋锦,她用尽各种法子挑逗王龙官,当王龙官对她动了心思时,她又隐藏起对他的爱,决绝地离开了王龙官,而后在浴室里当了小姐。《草上的竹筷》[11]77-89中的季罗氏为了生计去卖竹筷,她哄骗老妇人,谎称竹筷是自己亲手削出来的,季罗氏的女儿为此瞧不起她,再后来,不堪重负的季罗氏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在作家看来,谎言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总是心存恐惧”[13]。全金、老葛、范秋锦和季罗氏等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恐惧而惴惴不安,为此,他们只有逃避,用谎言将自己安置在虚妄的世界里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其实真实的世界对于她们来说早已无可留恋,谎言倒可以成为她们的精神享受与心理慰藉。
叶弥对谎言悖论的描写揭示出人性的荒诞,体现了作家的深刻思考。在现代机器和权欲社会的统治之下,人或许早已面目全非,只剩虚伪的面具,谎言覆盖或消解了生活的真实。叶弥于此很敏感,于是借助谎言和真实之间的巨大冲突剥开生活和自我本身。布斯在谈到《洛丽塔》时说:“在模糊不清的镜子中所反映出来的多雾的背景中,我们已寻觅了这么久,以至于我们自己也已经喜欢上雾了。”[14]那么,叶弥在乐此不疲地讲述谎言时,也让人物和读者沉浸于谎言之中,全然忘记了现实,喜欢上了谎言。《父亲和骗子》中的父亲、《现在》中的全金、《霓裳》中的老葛等,他们都甘愿沉溺于谎言之中,谎言成为他们避世的一种方式,也成为他们获得短暂快乐的源泉之一,这种谎言是心酸的真实,也是更有震撼力量的真实。
三、“调和”之三:个人与时代
对作家而言,个人与时代有时是相互包容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个人与时代相互对抗,时代凭借强势力量压制个人,而个人只能以微弱之力来对抗时代,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相较而言,第一种包容状况具有和谐之美,第二种对抗状况则具有崇高之美。初登文坛的叶弥就有与时代对抗书写的初心,到创作《风流图卷》时,她对时代之中的个人遭遇有了更深切的体认,并以自己的“风流”去触碰时代。她说:“中国当代作家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就是没有与社会里的黑暗相对抗的能量。”[15]38同时,叶弥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终究不能对抗时代,她缺少与之相匹配的力量,于是她巧妙地提出:“在当下,作家的责任还不在于承担多少社会的义务,因为还不具备那么大的能量,作家要做的首先是解放自己。”[15]38阅读叶弥的小说则会发现,她对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处理是很微妙的,她虽然对对抗感兴趣,但其关注又不持久,稍不留意就会滑向平庸;她虽然也关注个人与时代对抗之下的无所适从,但对其情感空间的开掘往往又是缺乏的;她虽然想在个人与时代的缝隙中“到达现实”,理解世界,但又总是把自己游离于作品之外,虽然这容易使人看到丑陋、原始的一面,但是缺少了沈从文式作家的怜悯之情。
1997年,叶弥的《成长如蜕》[3]253-315一经发表便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提高了叶弥的知名度。小说讲述了弟弟的成长历程:弟弟有个美好愿望,就是让天下人都幸福,为此,他反抗既定的从商之路,远走西藏,寻找心灵的救赎,而在他的救赎梦破灭之后,他怀着仅存的一丝希望,去了钟千里所在的城市。钟千里是个骗子,他骗走了弟弟的钱,还害得弟弟进了监狱。出狱后,弟弟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愿望,开始经商办企业,他经商的天赋和才能得到展现,很快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作者借用“我”的视角写道:“我弟弟已经能轻松地胜任了工作,大到签订合同组织生产,小到扣掉工人的一个加班费。”[3]314可以说,弟弟已经得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已被世俗社会认可。但从另一维度来看,弟弟的成长之旅亦是精神溃败之旅,他的放弃以及最终的接纳,何尝不是人的一种异化。但叶弥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的思考显然是缺失的,她将此称为命运的必然,其必然性表现在:一是弟弟年少时用宝塔糖、牙刷和手帕换取了于大妈的金耳环,这种不对等的甚至带有掠夺性质的商业交换,显示出弟弟天生就具有不平凡的商业头脑。二是弟弟的经历与父亲的经历是一一对应的,弟弟无论是在朋友面前炫耀财富,还是进监狱,都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父亲的脚步。这种带有命运色彩的设置,无疑削弱了弟弟无效反抗的悲剧性。《两世悲伤》[5]190-235亦采用此种叙事,上学时,李欧和孙超是对手,若干年后,无论他们多想握手言和,也终究只能是对手。叶弥着迷于描写摆脱不了的宿命,《成长如蜕》也好,《两世悲伤》也罢,都在时代与个人的抗衡之中,套上了宿命的魔咒,这就让其人物沉浸于悲伤的氛围中。
叶弥后期的小说虽没有直接书写时代,但其背后仍能寻觅出时代的影子,她用一种云淡风轻的笔法揭示了时代与人的隐秘关联。她不经意地提及时代,巧妙地点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如《天鹅绒》中的“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中国”[3]168,《独自升起》中的“这是一九七六的事”[3]85,把时代埋在故事深处,成为起源和症结所在;比如,借助时间变化勾连起时代,《月亮泉》[11]193-208也罢,《逃票》[3]39-70也好,都用村子/个人的变迁,隐晦地表达了时代的风流云散;再比如寻根溯源、查阅地方志,在《市民们》、《晚风轻拂落霞湖》[11]103-116、《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11]160-177等小说中都有类似的句子:“南北街形成于什么年代,已无从考查。”[5]3通过这种不断溯源的方式,所有事情的发生有了根据。可以说,叶弥的内心深处始终藏有时代的情结。《风流图卷》选取的是1958年和1968年这两个时间展开:上卷中,作家描述的是柳爷爷在1958年的故事。柳爷爷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之中而与世无争,悠然自得,却因嫉妒与谎言被陷害,他于假山底下自焚而死。下卷中,作家描述的是“我”(张燕妮)的奶奶高大进在1968年的故事。高大进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都是荒诞不经的,她雷厉风行,暴戾乖张,但她自杀的方式却是极温柔的,她和“老丝瓜”喝下砒霜后,脸贴着脸相拥而死。这是否表明高大进内心存有深处柔弱的一面,我们不得而知。政治和生活代表了高大进的两个生命维度,也意味着时代对人本身情感的遮蔽。“我”作为见证者,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代发生的故事。同时,“我”还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若干男人,如杜克、张风毅、林纳德等。他们是怎样塑造“我”,时代又是怎样塑造我们。叶弥在创作后记中说:“时间是小说的背景,只限于时间的价值。对于我小说中那些奋斗者来说,时间只是水,混浊的清澈的、湍急的平缓的,都挡不住他们追求幸福的船舟。”[4]436叶弥显然轻视了时间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但追求的方式和姿态千差万别。这种千差万别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时代,也只有在时代的潮流之下,个人的奋斗才能显现出自身的悲壮。
与许多同时期的作家相比,叶弥能洞见时代的阴暗面,以及在此背景之中挣扎和跋涉的个人。但由于缺乏与时代相抗衡的力量,她找不到突破的途径,只能以草草的命运来解释时代悲剧,或者轻率地将小说的重心移到“趣味”之上。这种“以轻避重”或“轻重交错”的调和写法,使其小说本该有的重量变轻。
四、结语:无处不在的两面性
叶弥不是一个风格恒定的作家,她是善变的,经常徘徊在两个极端事物/状态之间,叶弥自己也说其性格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太阳,另一面是月亮,这直接导致了“叶弥的作品存在两面性”[15]35。除了对人与物、谎言与真实、个人与时代的书写之外,还有诸如轻和重、梦和现实、思想和趣味等也是她所关注的内容。基于此,叶弥从1994年开始创作以来,一直让评论家们眼花缭乱,始终找不到稳定的审美态势予以描述。李敬泽最初注意到这一点,坦言这也是“一病”。
纵观叶弥的创作历程,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她都在寻找一种有效的弥合途径。更何况,叶弥从来都不会将生活与创作截然分开,生活即创作,浑然一体。她总是带着包容心和同情心去看待一切,所有的差距都可以被消弭,所有的悖谬也都可以被调和,这大概是叶弥生活及创作的智慧所在。季进说:“叶弥在此将感性之优美和理性之严酷作了一种较佳的协调平衡,不会让读者太受打击,亦不致过分乐观。”[16]换言之,无论是小说风格,还是具体到对人生的开掘,叶弥总是摇摆于两端,缺少向前掘进的力度,不忍将人生最残酷的真相撕开。叶弥小说的结尾处通常会陡然出现诗意之美,使持续已久的对抗悄然化解,进而消解了故事本该有的深度意义。
叶弥认为当代作家缺乏与黑暗相抗衡的力量,只能先解放自己,这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策略,她喜欢简单,注重趣味的表达,认为小说之道在于做减法。叶弥不断剔除文学身上的重量,单纯地将文学看成梦,看成“一种会走路的梦,你不知道它将带你到何方去”[17]。叶弥的这种“调和”叙述拉开了与当代美女作家、先锋作家的距离,而暗合了沈从文、汪曾祺式的闲适笔法,但这些作家在调和中的挣扎、闲适中的苦难、平淡中的批判等,显然被叶弥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如对人与物的书写,叶弥过多关注人与物的调适,而忽略了人与物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以及人的孤单、宿命等终极问题;在谎言与真实的叙事上,叶弥的谎言总泛着诗意的调子,真实与谎言的边界常被抹掉,这就导致其叙述缺乏直指人心的震撼力,谎言如真实一样,犹如隔靴搔痒,抑或只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于命运;在个人与时代的处理上,叶弥总疏离于时代之外,但又不能形成与时代相抗衡的力量,缺少了时代的厚重感和悲剧感,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克尔凯戈尔曾说:“我决心只读死囚犯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18]这种说法不免极端,但也并无道理。对作家来说,应当怀着对人类和世界的热爱写作,不仅要参与,更要审视和洞察,对生活批判也罢,否定也好,总是要拿出点勇气来。对叶弥而言,这点尤为缺乏,也尤为重要。
叶弥小说的这种“调和”叙事,既上承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又与当代文化中的某种“暧味”和“妥协”相关。因此,从她的“调和”叙事中,可窥探其小说的恒定性因素与潜藏的当代精神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