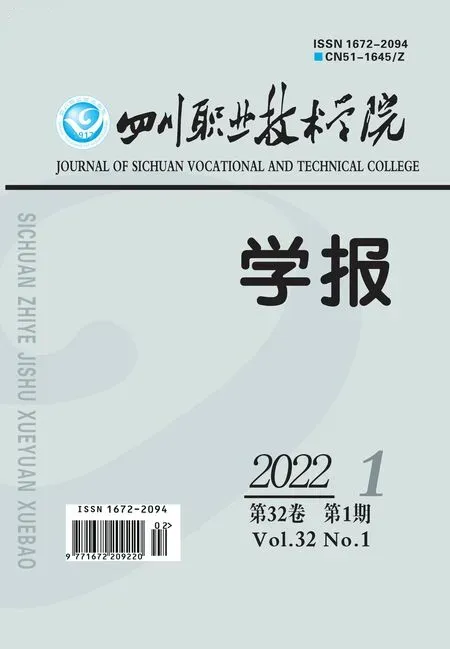《白毛女》的革命文艺特点探析
2022-03-18雷家军
蒋 翠,雷家军
(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一、革命文艺和文艺革命相结合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文艺革命的“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文化有了更普遍动员的趋势,向文艺大众化迈进。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下,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产生了一大批新文艺人才,他们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将文艺大众化的理念最大限度地融合进《白毛女》的创作中,从而推动革命文艺向更深层次的大众化迈进,实现了革命文艺与文艺革命的内在统一,为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98,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同时,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个是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853凝练了文艺革命的根本问题,即以文艺革命为渠道,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实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推向大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彻底的思想精神的解放和变革。由此可见,文艺革命从来不是为文艺革命者圈地自营的狂欢,而是真正意义上大众化的文化改革运动。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663“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1]699创作于文艺革命时期的《白毛女》,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深受压迫的苦难境遇。它以民间“白毛仙姑”为素材结合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以现实人民生活现状和诉求为基准,以犀利的描述突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事实,这种对现实尖锐的刺破和呈现是《白毛女》作为一部革命文艺所特有的毁坏旧世界、旧秩序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定。同时,其具有的转化为现实革命力量的能力展现出革命文艺的作用。“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旋律对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状、对人民群众意识形态观念的觉醒都具有积极意义。
《白毛女》作为一部经典革命文艺作品在多重意义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一方面它实现了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作为集体创作的产物,《白毛女》的成功不仅归功于革命文艺人才创作团队的付出,也依赖于群众在观看演出时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创作的行为,这种创作组织形式是他们在既定意识形态指导下所进行的一项自我教育。另一方面,《白毛女》语言运用、歌舞编排等都实现了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851的要求。张庚曾指出,“我们的剧作者在语言方面,多数是不完全的,他们只有知识分子的语汇,这种语汇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从理论中来,这种语言只有说明力而没有表现力。”[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革命文艺者们抛弃了过去他们自成一体的生活圈子,真正参与到大众的生活中去,熟悉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生活。在文艺工作中,内容上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形式上力求能为群众所接受。
此外,自“五四”文艺革命以来,文艺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争议不断。毛泽东深刻洞察了民族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706,“民众就是革命文化地无限丰富的源泉”[1]708。民族文化是历史洪流中人民智慧的积淀和结晶,是数千年来人民群众对人生、对生命最淳朴表达方式的凝结。中国历史文化与人民群众之间牢不可分的关系深刻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不能绕开民族文化,抛开民族文化空谈实现文化大众化是根本不切实际的。《白毛女》借助歌剧的表现形式,融合中国特色的地方民歌、梆子、戏曲唱腔和身段,既反映了群众的思想感情,又表达了内容的真实性,使其普及至全边区乃至全国,更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繁荣起来,最终在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中获得人民对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
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和拓展,后二者影响着革命文艺的前进趋势。《白毛女》在文艺革命的影响下不仅实现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打破了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的文化壁垒,更做到了对大众物质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怀,在演出传播的过程中既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斗志,又为新社会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稳固做出重要贡献。《白毛女》创作的成功使得延安文艺界更进一步深化了对文艺革命正确性及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认识。
二、革命文艺和传统艺术相结合
革命文艺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人民大众为主体,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文化信仰为基础,不断深化民众的革命意识、革命觉悟和革命精神。要实现这个革命目标必然要以人民大众长期浸染并被广泛接受的传统艺术为载体。只有将革命文艺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紧密结合,人民群众才能从情感上迅速认可。如果不能和传统艺术实现内在统一,革命文艺将很难走进广大群众的内心深处。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认同感,更好地推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继而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民间革命话语权构建,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秧歌作为陕甘宁地区民间传统艺术,是人民群众情感的宣泄和精神寄托,在百姓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人民情感为契合点的秧歌运动,以传统民间艺术为起点,是革命艺术融合进本土文化土壤使其“合法化”的一次有效尝试,最终成为鼓舞、影响人民的宣传工具。联结革命艺术和传统艺术的秧歌运动成为孕育《白毛女》的地基和土壤,新秧歌为《白毛女》的创作提供经验和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而进一步稳固社会价值风向、为新社会做准备则需要更新、更有力量的艺术表达。此时,“白毛仙姑”恰好传入延安,它以符合时代需要和群众审美的契合性成为创作蓝本,“民族新歌剧”被提上日程。
《白毛女》作为民族新歌剧重要里程碑,它的成功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革命文艺与传统艺术相互竞争、相互交融的结果。创作初始,革命艺术的现代化追求和传统艺术的激烈碰撞不断发生。首先,从前线返回延安的西站团的同志们没有经历过秧歌运动,对于已经取得人民认可并被人民所期待着的秧歌歌舞剧非常陌生,几近一无所知,这也就导致他们所设想的剧本和情节不符合当时文化秩序重组与建设的需求,更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其次,在延安亲自参与过秧歌运动的革命文艺人才被限制在了对民间传统艺术追求的束缚中。为了尽早满足文化政策的要求,他们急于改造文艺,而秧歌运动的成功却让他们过度依赖于传统艺术,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忽略了他们对革命艺术现代化的追求。机械地照搬秧歌运动成功的模式使得第一次创作宣告失败。
毛泽东曾表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以中国自己的形式,即民族的形式来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是有别于任何别的民族、而特属于中华民族的形式。文艺创作中要有选择地剔除和保留各种传统,要将革命艺术和传统艺术有机结合,提高革命文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发掘传统艺术的民主性元素并通过其表现出革命艺术的色彩是《白毛女》剧组迫切的追求。“民族新歌剧”说来简单,但要在革命艺术和传统艺术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在固有的文化秩序中实现突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先不说延安的文艺家们有多少真正接触过西方歌剧,就单在歌剧上实现一个既体现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性革命艺术追求的“新”,着实让文艺家们摸不着头脑。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交稿日期的迫近让创作团队压力剧增,而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通晓现代音乐形式的张鲁在河北民歌《小白菜》的启发下创作出了《北风吹》,将表现人民情感的民歌曲调改编成深沉、哀婉极富内涵的歌剧曲目,奠定了新歌剧《白毛女》的总基调。重新创作的剧本吸取秧歌运动的经验,谨记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在扎根传统艺术的情况下,摒弃对旧时戏剧的依赖,大胆地整合创新,打破文艺表现形式的界限,将群众熟悉或陌生的多种元素创造性地糅合,产生一种奇妙的共鸣。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698《白毛女》是无产阶级在构建新文化体系时重要的文艺成果,是民主的、大众的。“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4],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白毛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情感作为审美导向和基础,兼收并蓄地融合了传统艺术民主性的精华,在传统艺术中寻找革命艺术发展的可能性,在追求革命艺术现代化时不忘传统艺术,实现了革命文艺和传统艺术的紧密结合。《白毛女》所体现的革命性和民族性不仅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革命文艺永葆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更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只有立足于人民的需求,才能塑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三、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5]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1944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存,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成为人民面临的两大危机。为了战胜这两大危机,革命文艺作为协助中国革命的文化武器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蓬勃发展,以坚定的态度同一切反革命、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白毛女》作为一部经典的革命文艺作品,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以一种文化力量,切实而有力的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前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白毛女》是“五四”文艺革命以来革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实验成果,是延安新文艺的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延安新文艺的革命实践性和社会发展性。在这一阶段,阶级斗争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白毛女》所呈现的特有的“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不仅表现了革命实践道路的美好前景,也映射出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殷切期盼。《白毛女》作为“民族新歌剧”对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整合和重组时,对民间话语权的估量和革命话语权的把控、对革命斗争需要和人民审美需求之间的衡量进行了多次反复的斟酌,这种“旧”与“新”的矛盾、“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纠缠,究其本质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在文艺作品中反映现实的革命任务,从而使文艺能更好地服务于革命,进而推动新中国、新社会的诞生和建立。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革命文艺不仅能够反映并作用于时代风潮,而且还能激动鼓舞人民群众勇于反抗的革命思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的中坚力量。《白毛女》以真实性为纽带,将革命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在最大程度再现现实社会人民苦难的同时充分激发人民参与革命的渴望,而正是这种由革命文艺激发出的人民内心的渴望才能促使人民踏出抗争的第一步。胡绳表示,“知识分子和群众结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决定因素。”[6]尤其是在民族战争走向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多次修改下,《白毛女》已然成为展现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喜儿慢慢脱离了单纯的女性身份,代表受压迫的阶级;黄世仁则站在整个受压迫阶级的对立面,成为实施压迫的阶级主体,个人恩怨上升为阶级对立,现实生活中也必然引向革命。因此,《白毛女》不再是简单的文艺作品,而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增强了人民反抗压迫的斗志,鼓舞了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士气,军民齐心为革命前进道路扫除了障碍。
无产阶级最终想要取得国家政权,单靠武力斗争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武装全党并领导人民群众同一切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做彻底的不妥协的反抗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的共同合作最终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的文化力量同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政治力量一样都是革命的力量。延安时期,面对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双重压力,中国共产党基于现实革命斗争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方针政策和纲领路线。在这些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延安革命文艺人才们共同创造出了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这不仅是一种革命文化的实践,也是党和国家革命方针、革命理念的实践。革命文化的理论也必须和革命文化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瞿秋白认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连接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白毛女》作为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战线”理论部署的指挥下,它的革命叙事将一个单薄的民间传说改编成符合群众需求、革命需求、时代需求的民族经典。与此同时,《白毛女》在革命时期对于意识形态领域观念的宣传和普及力度的成功,使共产党更加确定文化战线部署的必要性,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争取文化主动权、稳固后方革命话语权的重要武器。
《白毛女》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经典,就在于它超越于一般革命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它是革命文艺理论实践的产物,是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重要纽带,是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作为革命文化总战线中一条重要战线,它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反作用于现实革命斗争的典型代表——能够广泛地联系群众、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反抗的斗争中去,成为推动革命进程重要动力。
《白毛女》作为实现了革命价值、政治价值、文艺价值等多种价值为一体的革命文艺作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情怀为导向,其革命性和文学性的多重交融既真实反映了人民生活苦难,又能在敏锐觉察人民诉求的同时引导社会意识形态走势,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力量作用于现实革命。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白毛女》以多种样式的表现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范围,在文化部署过程中成为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革命经典。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以《白毛女》为例探析革命文艺的特点不仅是对革命文本创作历程的探究,更是对延安新文艺革命性、实践性以及革命文艺经典化构成的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