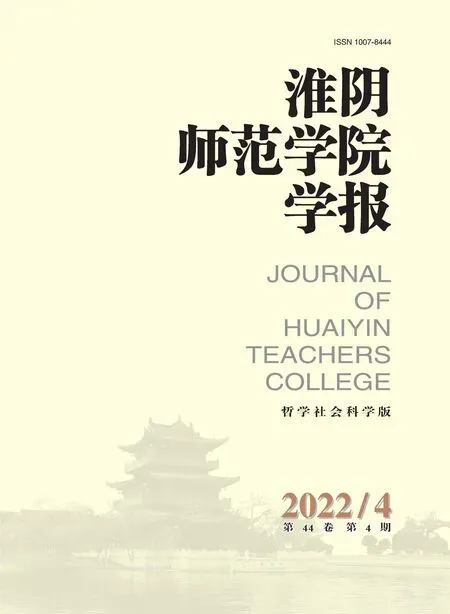论钱锺书学术著述文言语体的生成及意义
2022-03-17焦亚东
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在钱锺书的学术著作中,文白兼用是一个突出的文体特征。《谈艺录》《管锥编》《容安馆札记》等著作中典雅凝练的文言,与《宋诗选注》《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中规范流畅的白话,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在同一个作者手中转换自如,发挥各自的语言优势,达成不同的学术目的,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1]。如果说,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学人,钱锺书选择白话作为书写工具是一种势所必然,那么,在白话的畅行已势不可挡的时代里,他为何还要“逆”潮流而动,以文言写就自己几部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他的这种文言语体的考量与选择又有何学术意义?
一、“勿以繁简判优劣”:语言观念的影响
发端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时已成浩大之势,经由不同思想和观点的激烈碰撞,这场语言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白话逐渐得到官方、民间和知识界的普遍认同,从而取代文言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而在白话文运动一路高歌猛进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教育,对这场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变革尚懵然无知,更谈不上发表什么看法。然而,十几年后,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白之争的意见,这就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1期上的《与张君晓峰书》。在这封写给学衡派重要成员张其昀的信中,钱锺书对文白之争主要谈了这样几点看法:
其一,认为文白之争还有继续检讨的空间。钱锺书认为,当年文白之争的结局从表面上看似乎早成定论,“已由时代代为解决”,但个中的经验、教训是颇值得反思的:昔日新旧两派大起争端,“以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深闭固拒,挟恐见破,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唯有等时过境迁,对立的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才有可能对文言、白话的“异量之美”做一番客观辩证的思考。
其二,指出文言、白话各具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不应偏废。钱锺书提出了三个考察文言、白话功用的角度,他说:“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驔比美,正未容轩轾。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这是从文艺审美角度对文白之争的思考。又云:“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这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展开的思考。又云“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ri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一笑”。这里提到的“应用”,即当初在文白之争中“激进派”与“保守派”从社会政治层面考辨语言功用的视角。不难看出,钱锺书在信中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文艺”“文化”这两个角度讨论文白之争这一问题的:“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是否深赜难解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存在即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而简单地从政治宣传、文化教化的角度主张推行白话文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非所思存”,“可发一笑”的,这就婉转地批评了将语言变革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功利主义取向。在此基础上,钱锺书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故以繁简判优劣者,算博士之见耳。”可见,与新旧两派在论争中的偏狭立论相比,钱锺书审视文白之争的立场要全面得多,态度也更持正、平和。这其中当然也和讨论问题时的语境大不相同有关,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持正与平和的重要原因。
其三,指出文言、白话互渗互补的可能性。从上述讨论出发,钱锺书进一步指出:“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吾侪倘能及身而见之欤。”[2]这里完全摈除了新旧两派以偏概全的思维定式,对文言、白话没有轻言“去取爱憎”,而是坚信“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强调了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互渗互补的可能。
由此可见,在如何看待文白之争这一问题上,审视的角度不同,思考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不同。在钱锺书,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冷静客观地审视新旧中西的关系,是其一贯的立场,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如果卸下语言承载的政治宣传、政治教化的重负,文言和白话并不是决定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优劣高下的原因,也不是制约文化传播的决定性因素,“文言白话,骖驔比美,正未容轩轾”遂成为他在这封信中的着力阐发点。钱锺书在青年时代写下的这些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确实少有人像钱锺书那样同时使用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进行言说活动:在文学创作领域,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以典范的白话写作,挥洒自如,全无彼时很多作家西化或泥古的痕迹;而收录于《槐聚诗存》中的旧体诗,则以古色古香的文言写就。在学术研究领域,以白话完成的论文《七缀集》、选本《宋诗选注》,随笔《写在人生边上》,与以典雅的文言书写的《管锥编》《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使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人之手。“《谈艺录》中,有意识的精致的文言,与《写在人生边上》中实验性的形式,成为鲜明的对照,并令人更加相信钱锺书在后一部著作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以古典文体的流畅表达,来充实粗浅的白话。”[3]就是说,文言、白话在钱锺书这里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套语言系统,而是“骖驔比美”的言说工具,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钱锺书在学术著作中选择以文言语体进行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文言在意义表达效应上的价值认同。
二、“不如径用文言”:研究对象的制约
钱锺书文白兼用的语体特点,与其学术研究的特定对象有一定的关系。在言说活动中,言说对象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言说形式的选择,这就是刘勰说的“因情立体,即体成势”[4]159。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对象、内容,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体式、语体,如此方能做到“去留随心,修短在手”[4]262。
总体而言,进入钱锺书研究视域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尽管钱锺书在学术研究中也大量征引西方文学典籍,但这主要还是服务于他的古典文学研究。钱锺书曾多次表示他感兴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1978年在意大利的两次对欧洲汉学家的演讲中,他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5];“我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6];他还称自己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比较文学只是“余兴”[7];坦言自己对诗歌是“偏袒、偏向它”[8]。杨绛也这样评价:“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领会的。”[9]在钱锺书重要的学术著作中,《谈艺录》是诗话,讨论的重心自不必说。即便是内容庞杂的《管锥编》,古典诗歌仍是作者最关注的对象(1)1983年,钱锺书在填写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登记表时,在《管锥编》后写上“文学、哲学、历史研究”等字。此表复印件见吴泰昌《不愿重印〈谈艺录〉》一文,收入其所著《我认识的钱锺书》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管锥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文化典籍。其中,《毛诗正义》《楚辞洪兴祖补注》无疑属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太平广记》虽是类书,但取材多为野史、笔记、传奇,尤以神怪故事所占比例较大,许多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全赖此书得以流传,因此被视为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周易正义》《焦氏易林》虽属《易》的注疏,但钱锺书阐发主要还是从文学角度切入的。据笔者粗略统计,《管锥编》论《周易正义》共27则,除第三(泰)、第九(睽)、第十(损)、第十二(革)、第十七(系辞一)、第二十二(系辞六)、第二十四(系辞八)、第二十七(说卦二)这8则未直接论及文学外。其余19则都针对特定的文学问题而发。例如,“二、乾”讨论文学之“象”,“五、观”讨论李商隐诗歌,“八、大过”讨论“诗文常喻”、元人院本及《西游记》,“十六、归妹”探讨“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这一文学修辞现象等。至于《焦氏易林》,钱锺书称此书“有明中叶,谈艺之士予以拂拭,文彩始彰”,“成词章家观摩胎息之编”[10]535-536,充分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因此对此书的讨论也多从文学角度展开。而《左传》《老子》《列子》三书,原本就是先秦散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尽管不全是文学之“文”,但钱锺书关注的主要也是文学或文学色彩较浓的文章。正因如此,周振甫在审读《管锥编》时才有如下结论:“这部著作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但以文学艺术为主。”[11]敏泽也称:“《管锥编》是《谈艺录》研究内容、旨趣和原则的一种延伸,中心或重心仍属谈艺论文。”[12]由此可见,《谈艺录》《管锥编》主要的批评对象是中国古典文学,钱锺书之所以选择用文言语体进行书写,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即,研究对象的语体制约了研究者的语体,使他有意识地要去维持二者在语言形态上的一致性。
对钱锺书来说,一方面要在《谈艺录》《管锥编》中大量征引古典文学作品、古代文化典籍;一方面还要在征引过程中随时作出言简意赅的述评,如此一来,如果所引之文多为古雅的文言,而评述之语又转用白话,就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著作在语言形态上的统一感,并且这种影响还会因文言引文的稠密叠匝而显得格外突出。张隆溪曾回忆,有一次他问钱锺书为什么《谈艺录》《管锥编》不用现代白话,却用大多数读者觉得困难的文言,钱锺书的回答是:“引文多是文言,不宜处处译为白话”,“不如径用文言省事”[13]236。作者本人的这一解释虽然很简短,但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他对文言的使用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二是之所以选择文言是考虑到语言文字的协调感、统一感。那么,这两部著作涉及的大量的西文典籍何以没有制造应有的麻烦呢?这其实应归功于钱锺书以文言翻译西文的高妙境界,使得出自西方典籍的引文也与整部著作典雅的文言融洽无间。有学者指出:“钱锺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14]钱锺书自己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5]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消除异质语言的生疏感,使其最大程度地归化于全书的语言类属和语言风格,这是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毫无顾忌地使用文言的一个重要前提。试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各举一例:
古希腊诗称美人:“不太纤,不太秾,得其中”(not too slender nor too stout, but the mean between the two);拜伦诗称美人:“发色增深一丝,容光减褪一忽,风韵便半失”(one shade the more,one ray the less,/Had half impair’d the nameless grace/Which waves in every raven tress,/Or softly lightens o’er her face)。与宋玉手眼相类,均欲示恰到好处,无纤芥微尘之憾。[10]873
瓦勒利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le but de communiquer à quelqu’un quelque notion déterminée),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entiêrement remplacée), 意之既达,词亦随除(cette idée s’étant produite, le langage s’évanouit devant elle);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la forme conser vée comme unique et nécessaire expression)。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16]282-283
这两段话,一征引西方文学作品,以古希腊诗歌、拜伦诗歌为例,来讨论宋玉《好色赋》的描写手法;一征引西方文论著作,以瓦勒利(今译“瓦雷里”)的观点来说明中国传统诗学命题。在行文过程中,钱锺书以他一贯的阐释策略,在征引文献的同时不忘插入自己精当的点评。由于讨论的重心和征引的目的是论述中国古典文学,外文资料只为满足说明问题之需,所以钱锺书对西文的翻译是比较简练的,译文能传意达旨即可。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外文均以古雅的文言译出,显而易见,这样的处理避免了中西引文及钱锺书的点评在语言形态上可能出现的文白相杂的情形,无论是对作者的表述,还是对读者的阅读,抑或对全书全篇的语言风格而言,都有顺畅妥帖之效。
三、“旧书上的眉批”:学术文体的限制
在钱锺书用文言完成的学术经典中,《谈艺录》是诗话体,《管锥编》是札记体,而我们知道,相比于研究对象,文体类别对语言选择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我们很难想象用白话写成的诗话、札记会是什么模样的原因。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的文体样式,诗话、札记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所使用的语言应是典雅的文言语体。首先,从内容上看,诗话的主要功用是点评诗作、臧否人物、追源溯流、辨彰清浊、指摘利钝以及记录诗人言行、诗坛轶事,札记的重心在于读书摘要和阅读心得。这些内容在表述上,讲求的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谈笑之间,传神写意,这就使得文言的优势得以凸显,成为钱锺书考量的一个因素。其次,从形式上看,诗话、札记均属笔记体文体,不追求严密的体系结构、严格的范畴界定、严谨的论证法则,而是结构松散,长短不拘,以便更好地契合传统诗文评论重个体感悟、轻逻辑论证的思维特点,因此语言的要求也自然倾向于语法结构、语词组合更为灵活的文言,这显然又是钱锺书选择文言进行书写的原因。第三,从功能上看,撰写诗话的目的是自娱自遣。蔡镇楚说:“宋人于政事之余,茶余饭后,谈诗,论诗,评诗,已蔚然成风。此风之兴,于诗话这一新的论诗体裁的诞生,是相当有益的。”[17]事实也如此,欧阳修就称自己写《六一诗话》的缘起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8];近人王逸塘在《今传是楼诗话》的自序中也称“欲为诗话以自遣”[19];钱锺书自己在《谈艺录》序中也说“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16]序1。都很明确地点出了撰写诗话的用意。与诗话一样,札记作为读书笔记,体现的是传统学人熟读精思的治学习惯,“不要求行文之前有完整的构思,可以随想随写,随见随录”[20],也是很个人化、随意化的文体。以《〈宋诗纪事〉补正》为例:该书是钱锺书利用40多年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完成的札记体著作,杨绛曾这样描述钱锺书的写作状态:“他半卧在躺椅上休息,就边看边批,多半凭记忆,有时也查书。”[21]批完此书,钱锺书还在第一册扉页写下“随笔是正之”之类的话,可见札记的写作状态与诗话一样,是非常从容、闲适的。诗话和札记这个特点自然也会影响到钱锺书的语言选择。钱锺书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22]而与白话相比,文言的特点更契合诗话、札记“以资闲谈”“随笔正之”的写作状态,倘若采用白话,非但难以得心应手,而且语言形态也显得过于规范庄重,这就多少与作者所追求的“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不那么协调了。与之相对照的是《七缀集》中收录的那些学术论文,钱锺书采用白话进行写作,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论文的文体样式是典型的现代西学范式,在内容上主要围绕一个特定的命题展开论述,在形式上篇幅较长,在结构上层层推演,逻辑严密,论题的提出、范畴的界定、论据的使用、论证的过程、结论的产生甚至参考文献的列举,无所不有。如此一来,文言显然很难满足这种文体在表达上的这些需要。有研究者指出:“文言在组合方式上极其自由,这样的语言特征与不长于逻辑思辩的批评话语有密切关系。”[23]晚清、五四以来,白话文之所以在西学东渐的浪潮推动下渐成大势,“恰是因为现代理性的逻辑系统难以用文言文圆满显现,甚至连西学的一些概念都无法在文言中找到对应物”[24]。文体的特点制约着语体的选择,而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中将文言、白话转换自如,则无疑显示了一种高超的毫无滞碍的语言驾驭能力。
当然,关于为何用文言撰写《管锥编》《谈艺录》的问题,钱锺书本人及学界也曾有其他一些解释。按余英时转述钱锺书的话,“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25];按启功的说法,文言就像“木耳”一样,写出来都是干货,“你看《管锥篇》,……看起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稍微加点水,就能发出一大盆真货来”[26];按张隆溪的观点,钱锺书用文言是为了驳斥黑格尔鄙薄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谬论[13]236;而按柯灵的回忆,钱锺书曾说可以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容纳新思想[27]。如此,则大致有四种解释:一是为避祸,“毒素”云云,与杨绛所谓“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可相互印证[28];二是增强容量,“木耳”“真货”云云;三是欲证文言亦宜于思辩,“驳斥黑格尔”云云;四是以旧文字传达新思想,“检测旧文体”云云。上述几种说法有些虽不无道理,但或是作者调侃之语,或是学者一家之言,缺乏足够的资料支撑,本文不做深入讨论。
钱锺书在学术著作书写语言上的选择,现在看来是非常通脱和明智的。有研究者称:“钱先生对白话文有极深的造诣。但是在他从事学术创作时,他还是舍弃了它。考虑到钱锺书学成于五四新文化的氛围中,考虑到文言文几乎成为消亡的语言,他的举动格外耐人寻味。”[29]事实也如此。赵毅衡在题为《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的文章中说:“如果吴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见好就收,论文用文言写小说改用白话(钱锺书就是一佳例),二十年代怎么会让汪静之享情圣大名?三十年代也能给何其芳等指拨迷津,而他的长篇肯定让海伦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誉文坛。”[30]他的意思是说,当年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并没有像钱锺书那样领会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旨”,缺乏对中西文化会通的透彻认识,不能真正做到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多元选择,而斤斤计较在文白之争中的阵营和立场,以至于应该写出好诗佳作的吴宓最终还是放不下对白话的一偏之见,没有根据实际写作的需要在文白之间作恰当的选择,白白失去了享誉文坛的机会。叶维廉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有“过度情绪化的发挥”,他说:“在当时的激流中,要停下来不分新旧只辨好坏完全客观而深思熟虑地去处理文学者实在不多,而且亦非当时的主流。”[31]如今,文白之争已曲终人散,但反思不同的人在此问题上的不同选择,我们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在处理新旧中西的关系问题上,钱锺书客观持正的立场是何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