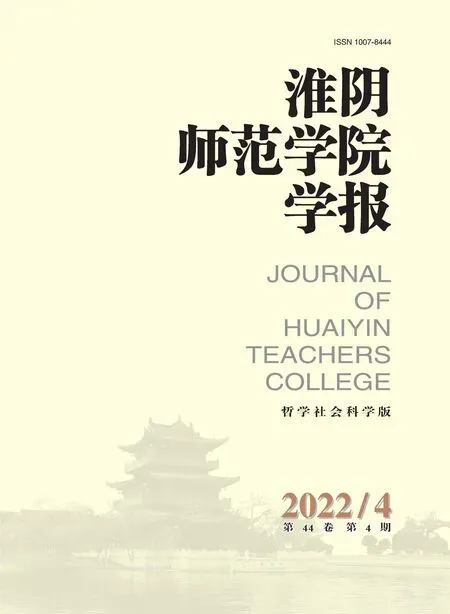《湘绮楼日记》所见王闿运史学研究
2022-03-17舒习龙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号湘绮老人,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在国学的多个门类都有较高造诣。他的《湘绮楼日记》(下文简称《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名日记之一。《日记》撰写时间从同治八年(1869)到民国五年(1916),跨越近半个世纪;总字数约250万,内容颇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日记》中有许多史学批评和历史编纂方面的内容,零散分布在历年日记中,需要研究者仔细梳理,才能发掘其精华。近年来,史学界开始认识到学人日记的巨大价值,并尝试运用学人日记对一些颇具影响的史学家或历史现象展开研究。桑兵对学人日记的价值有颇为精彩的揭示,他说:“以当时人的日记为凭借,……探寻历史的发生演化,一方面可以补充大历史的视野所不及,丰富历史的影像;更有助于改变认识历史的方式,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差异与活跃之于历史和史学的应有之义。”[1]12本文以《日记》为主要史料,在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时代思潮下研究王氏的史观、史学批评和史学编纂实践,以期反映其成就与不足。
一、王闿运的史观与史学批评
晚清社会进入急遽的转型时代,近代史学在接受传统史学观念和话语的同时,也在时代催生下有所变革。作为儒家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王闿运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深受传统经学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其经学主《春秋》而尚《公羊》,“通经致用”观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和前提。王氏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天人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五经五纬以备奇正、通神变者,圣之用也。自儒生不达天道,术家但知诡妄,谶秘之学有类妖符。盖圣学所传,唯期致用。若其自运,必合阴阳。至人不死,岂关天祐?……自非体自精深,要亦等于远泥,无劳探索,以扰神明。”[2]497“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诸子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春秋》“公羊学”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王氏认为,儒生不识“五经五纬”,方士、术士以迷信的神秘主义演绎天人关系,皆没有将儒学的通变致用发挥出来。王闿运提出将天事与人道融会贯通,强调史学家治史、论史皆需本此旨趣。王氏承认天人之间有联系,但反对“天人感应”理论。他说:“天人之际,神鬼之灵,其理灼然,而情或爽。谓相感应,则有全无验者。”[2]498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离不开恰切地处理“天”与“人”的关系,历史观决定了史书的撰著和方法的自觉。
王氏从经学家的角度来推阐史学的功用,指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世之人事,皆非情理,谬正经。如以经义绳之,则自入荆棘矣。……汉、宋诸儒自成党祸,其亦不知史学之咎与?”[2]514晚清经史关系的探讨进入新时期,传统经史关系强调“经尊史卑”,而晚清时期,经史同源、“六经皆史”成为学界风尚,经学逐步边缘化而史学逐渐走向中心。然王氏坚守经学对中国史学的核心价值。王氏认为经学和史学皆有裨于现实政治,在经学指导下史学能更好地发挥资鉴和垂训的功用。同时,他指出经学与史学的作用有差别,经学是用以致治的“大义”,而史学则为资鉴和垂训的“成例”。他认为世事应合乎经,但不能受制于经,由此他提倡经史互证,在分析和解释历史时,他能援经释史或以史证经,使经学和史学互为例证解释史实。
王氏的史学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影响其史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成为其评判史家撰史得失、体例篇目设置合理与否、叙事是否简洁工巧等尺度之一。王氏接受了传统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与话语体系。他对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提出自己的理解,“史以识为先,源出《尚书》”[3]222,特别强调“史以识为先”的重要性,以此来评判古代正史修纂的得失:“如欲修史,乃言三长,则平昔论之屡矣。班书有学而无识。范书有识。南齐书亦有识。宋书最芜,而范仲淹传独有识,金史亦不足言,而食货志有学。明史无学识,而文独雅,是亦有才。宋、魏书成于一人。”[2]522-523以此评判历代正史修纂的得失,可算得上王氏的“一家之言”,是其阅读历代正史所得出的认知。
王氏虽认为范晔《后汉书》具有史识,但对其中某些篇章提出质疑:“西汉论政,学者皆对策上书,足以裨治。东汉王符、崔寔、仲长统诸儒,动作数万言,以诱民俗,则著书自任,其文必繁,范史载之,未为通识矣。”[3]10诏令奏议类对于王朝行政治理非常有价值,班固《汉书》多载有用之文,为乾嘉史家赵翼所推崇。然东汉儒家王符、崔寔、仲长统奏议皆篇幅巨长,全载于传主之下,无疑会割裂叙事的连贯性,造成篇幅冗长,影响编纂者对史事、人物见解的提炼和总结。王氏的批评似有一定道理。王氏利用“史家三长”论批评陈寿《三国志》,指出:“观陈书叙次,诚非佳史,而后颇推之,以其所采词采犹近古耳。史才不易,亦何容滥予人名,若以鄙人秉笔为之,当不在班、范之下,因慨叹久之。”[3]13陈寿善叙事,颇有良史之才,后世学人大多服其善序事理。然而王氏并不推崇陈书的叙次之法,可能在于陈寿受正统史观影响,存在为曹魏和司马氏回护之嫌,史料搜集方面也受制于档案文献史料不足。如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指出的:“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4]1363从叙事角度而言,陈寿可称为良史,却是有愧于史德与史学的。王氏批评其史才不足,有失公允,且王氏对自己的史才太过自负,任意诋毁前人,不能视为史学批评应取的态度。王氏对沈约《宋书》新创志目“符瑞志”评价甚高:“沈约作《符瑞志》,文意深曲,有良史之风,而今人多訾之。凡古人新创一事,必有意义,如《史记》‘封禅书’、班‘古今人表’、范‘皇后纪’、宋‘符瑞志’、唐‘世系表’、赵宋‘道学传’,皆深眇之旨也。”[3]26-27沈约处于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尖锐对立的时代,以刘歆建构的新五德终始说为理论指导,论证出身寒门的刘裕代晋的政治合法性,此为其编纂《符瑞志》的“深眇之旨”。许多学者批评《符瑞志》不经且无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志目是从时代思潮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创制的,是编纂者独具特识的另类表达。王氏能抓住其历史编纂从现实关怀的角度谋篇布局、紧扣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创制新体例,由此来高赞新创体例的价值,可视为史学批评抓住问题核心、提出独到见解的范例。
王闿运早年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后又结识长沙大儒彭嘉玉,经史百家,无不诵习,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王氏对传统史书体例运用得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故对史学的鉴赏和批评往往能击中要害。纪传体正史绵延二千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重视。作为一种“综合体”体例,它的编纂得失关乎纪传体正史的质量。《日记》对纪传体各部分编纂得失多有批评。他以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纂《新唐书》为例,批评他们不知本纪编纂之法:“宋、欧作《唐书》本纪,茫然不知其事迹,惟见封官杀人而已,是断烂朝报之不如,不知何所取也。总为孔子《春秋》所误耳,阅之恨恨。”[3]65又说:“欧、宋尤不善作本纪,均为春秋书法所误,真千古不寤之愚也。”[3]72宋代史书编纂仿效《春秋》之义例,主要包括一字寓褒贬、纪年上“冠王于正”、常事不书或讳书,在内容选择上则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春秋》的微言大义。欧阳修、宋祁等人皆是“春秋学”的主将。由于《新唐书》本纪编纂过于重视褒贬,删削了很多重要内容,使得帝王编年纪事脉络不够清晰,有违史书秉笔直书实录的传统,因而遭到王氏强烈的批评。对正史中的“志”书部分,王氏比较新旧《唐书》,也提出了辩证的批评:“刘史《志》虽阙略,而事详悉可览。宋、欧词人,固不知史,《新唐书》直可焚也。”又说:“阅《旧唐书》志八本,又以校《新(唐)书》‘百官志’。新书详于官职,而略于阶级,卅品官阶不明。然史殊于礼,诸职掌略具而已,不必详也。”[3]123又说:“大概《新唐书》、《新五代(史)》皆文人志传之书,不谙史体,文笔较健耳。《新唐书》人皆訾之,而不敢议《五代史》,可怪也。”[3]70正史中志书部分最难撰写,也最能体现史家的素养。王氏批评后晋刘昫《旧唐书》“志”内容较简略,对《新唐书》“百官志”的编纂更是颇有微词。唐朝官员品级分正、从、上、下共九品三十级,包含官爵、文武职官、勋位等品阶。职官制度只叙官制不叙官阶,很难反映一朝官制的实况。王氏认为,“百官志”不同于“礼志”,官职略具即可,官阶更要列明叙述。王氏在深入理解唐代官制特点基础上提出的批评,应该说是颇为中肯的。王氏对史书论赞亦有批评:“阅《唐书》两本。刘作赞颇参差,不重用四字句,盖知《史》《汉》赞体,如张路传赞甚合例也。”[3]149王氏对《唐书》史表也提出批评:“检《唐书》表九本。唐宰相本不皆名族,宋子京为作世系表者,阴仿萧、曹世家以重宰相耳,然甚无谓。”[3]70《新唐书·世系表》由宋祁编纂,宋祁(字子京)不识史书编纂的正理,编纂史书惟求异求简,导致事实不明,有乖本意,所以后世有人指出史书不能取宋子京的编纂之例。关于历史编纂的语言叙述,王氏以欧阳修《新五代史》为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卢多逊等以七言绝句入史,其理万不可驳,而其体缪丑可笑。世之言文者,必欲纪实,大要如此,故欧阳起而改之,乃至全无史实,弊又均也。”[3]74王闿运曾对史书中的语言叙述做过阐释:“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辞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5]189史之无文,传之不远。刘知几非常重视史书语言表述,提出史书表述应尽量简洁周详,叙述以反映实情为宗旨,摈弃浮华矫饰的语言,且最好能用一些口语。王氏批评卢多逊等以七言绝句入史,将史体与诗体混合,不利于反映历史;他还批评欧阳修虽改掉卢氏“七言绝句入史”之弊,但放弃了追求历史真实、反映历史实情的宗旨。
王氏正史批评颇见其史学批评的旨趣和力度。对其他史体王氏也能依据其观念和原则,结合史体的特征加以批评和评论。王氏对编年体史书《左传》编纂的批评,则是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发声,具有强烈的门户之见:“《左传》可笑处极多,亦荒唐文也,而二千年尊之如经,则吴懈、廖平又不足道。”[3]1549-1550《左传》价值颇高,是先秦时期较为成熟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王氏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指摘《左传》的学术价值,至为可笑,也不是平情之论。对于司马光(字君实)等人编纂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评论,王氏则基本为平实之论,能扬其大端,抉发其微瑕:“《通鉴》当昔未点群史时,讶其浩博,知君实特专补宋人唐、五代二史之略,自唐以下采稗史为证,有裨欧九等阙误不少。自唐以上,尚有可增删也。凡一代奉敕书出,必有人阴纠之,《通鉴》其最也。”[3]90他指出《资治通鉴》卷帧繁复,唐以后采稗史入史,颇能补益欧阳修等人《新五代史》《新唐书》之失,但对唐以前的编纂提出批评,认为有进一步搜采史料使其完备的必要。至于说奉敕之书,后人对《资治通鉴》纠弹最多,则为夸大之词,无足为据。王氏对后世典志体的名作亦有批评,如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批评道:“《文献通考》‘舆地考’,未为佳作也。凡作地理当明沿革改易之本,历代郡县省并为最要,而但举州郡大纲,不过供对策之用耳,惟叙五代得州多少,甚明晰有益。”[3]58王氏是沿革地理的拥趸者,故他批评马端临“舆地考”过重州郡大纲,忽视州郡改易,确有通识。王氏对章学诚的方志体例也提出批评辨析:“还阅章书,言方志体例甚详,然别列‘文征’一门,未为史法,其词又过辨求胜,要之以志为史,则得之也”[3]192。章学诚被后世称为“方志之圣”,因他对方志编纂既有理论建构,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章氏认为,方志编纂既要“圆而神”,又要“方以智”,要满足这样的编纂意图,必须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二为一,尤不可也。”[6]191他认为“文征”一门不可或缺,借“文征”来保存地方上艺文方面的文献史料,“文征”并非徒炫档案史料的繁富,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整理加工来体现史料的条理性和连贯性。章氏用“文征”保存史料的思路具有创见,但将正史之传及诏谕录于“文征”则受到后世的批评。从以上角度出发,王氏的批评似无道理。王氏批评章学诚将地方志作为地方史来编纂,从而造成史志不分的局限,有一定道理。
明季清初王夫之开创的船山学派,以张载思想为源头,批判地汲取程、朱理学的合理成分,创造出具有强烈批评意识的哲学体系,成为清初“三大家”之一。船山学在后世的流传和接受至为艰辛,没有取得与其学术地位相匹配的荣光。王闿运在日记中完整地记录下他对王船山著作和学术思想批评的历程,反映了其主观立场和心态。王闿运一直自视为湖湘之学的大儒,为学尊“春秋公羊学”,鄙薄宋学,其学术见解与王夫之异趣,故他对船山学批评尤烈。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的日记中,他批评道:“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3]1995王闿运一直看低船山史论,其思想一以贯之。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能从错综复杂的古代社会矛盾中抽绎出某种规律,熔铸众理,断以己见,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王夫之的史论不是“自诡特识”,而是确实具有别识洞见。王闿运批评船山论史局限于宋明理学的标准,这也是对王夫之学术立场的误读,实际上,王夫之对周、程、朱、陆、王各家理学思想皆持批评态度。王闿运批评船山史学,根源在于他想在晚清湘学知识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力求剔除湘学之陋,可见他的批评不是立足于客观的立场,而是从学术门户和话语权的角度攻讦对手所擅长之处。对王船山及其作品,王闿运的整体评价也不高。在同治八年的日记中,他批评:“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百诗、顾亭林也……至康、乾时,经学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3]15他认为“船山学”不及顾炎武、阎若璩的学问,在清代经学中只能居于二流的地位,这样的评判与后世学者主流意见不相称,也不能反映“船山学”的真正价值。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日记中,他仍然批评船山著作:“看船山讲议,村塾师可怜,吾知免矣。王、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3]2662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之说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王闿运贬低王夫之的著作和议论,对船山的经学成就一再挑剔。学术批评强调客观中立的立场,不能前置条件,批评要基于主客观条件,只针对文本,而不涉及其他。显然王氏的批评有悖于此。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同时代其他学人的日记和文集,就可以看出王闿运骨子里鄙薄“船山学”的缘由。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孙宝瑄在其日记中将“亭林、梨洲、船山”与“国朝经世硕学”等相提并论[7]。张謇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的文集中,曾专列“船山亭林梨洲学术同异论”[8],是将三人并列的。由此可见,晚清时期,将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相媲美,已经成为当时知识界的通识。
二、《湘军志》编纂的成就与缺憾
《湘军志》是王闿运的成名之作。该书最初写于光绪三年(1877),一年后完成初稿,后又经多次修改完善,最终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共计有10多万字。为编纂该书,王闿运查阅方略以及湘军统帅和高级将领的文集、奏议等,还参阅《湖南褒忠录》《平浙纪略》等,并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档案,雇人制作地图,历时7年终于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被指为“谤书”。王闿运被迫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
光绪元年(1875),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光绪三年(1877),在编纂伊始,王闿运就编纂宗旨致信两广总督刘坤一,云:“军志近始创稿,大约东杪可成,其意不在表战,而在叙述治乱得失之所由。节下鸿筹所及,虽未施行者,不妨相示,非欲闻斩级擒渠之功也。”[3]551王氏编纂《湘军志》,并不是为了表彰湘军的战功,而是为了梳理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胜败的缘由,总结战争和政治成败对清朝统治的影响。这一编纂宗旨与湘军将帅请其编纂志书的意图背离,因此也埋下了被毁版的命运。
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胜在史书编纂体例多元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氏对传统史书编纂有较为深刻的体验,但是在如何表述湘军历史上经过了思想的转变。湘军活动舞台遍及咸同之际多个行省,战争在南北多地进行,所以最初他想仿效“史传地志”体例进行编纂。光绪四年(1878)日记中记录他的忧思:“熟思《军志篇》之局法,颇难见长,反不若史传地志之有纲领,亦甚闷闷。”[3]635典志体史书普遍运用于静态的典章制度,对于场面宏大的湘军历史的记述,采用典志体编纂难以反映事件的首尾经过,更难总结战争成败得失、梳理经验教训、总结因果规律。在经过一番摸索后,他觉得运用纪事本末体来反映湘军历史更为妥帖,而这与其编纂宗旨也是自洽的。光绪七年(1881),王闿运总结《湘军志》编纂体例时说:“分置日历,纪事犹难明晰。此志自以纪事本末为易瞭,但非古法尔!”[3]1035纪事本末体最便于反映大事件,也能从中总结历史变动的规律。《湘军志》体例采用“非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原因在于初期融入了地方志的编纂元素,《湘军志》篇目基本以省志区域命名体现出这一特征,但又区别于地志专叙一地的沿革地理和人文地理,而重在叙述军事战争;其后,参酌古代典志体,专设营制篇、筹饷篇来记载营制、饷械方面的制度,营制篇比较清楚地解读了湘军军事体制,筹饷篇则着重阐释了湘军军费的来源和开支情况,对湘军军制和经费制度积弊多所揭示。王氏撰著此书,还兼采纪传、编年的优点,如书中专设“曾军篇”和“曾军后篇”,表彰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贡献,在篇目初设时曾计划写“胡军篇”,后考虑全书统一,将“胡军篇”改为“湖北篇”。书中其他篇章,对彭玉麟、罗泽南、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言行与事功多有表述,体现了编纂者对人物功业的重视。梁启超在梳理近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时评价:“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9]124将王氏《湘军志》评为杰作,并不在于它是否为典型的纪事本末体,而是表彰他融会多种体例的优点,用高朗之文笔,将头绪繁杂的战争实态呈现出绵密的条理,其“史裁之丽密”超越了同时代其他纪事本末体的著述。
宗旨与体例既立,接下来的编纂工作自然就是搜集和整理排比史料。史料搜集贯穿于《湘军志》编纂的始终。《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是清朝同治年间官修的档案汇编,收录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形成的谕旨、奏章和各类文书,由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任总裁、朱学勤任总纂。全编共420卷,选辑档案5 000余件,涉及交战双方的情形及军队部署与调拨、粮饷筹备、奖惩抚恤等一手文献,对研究湘军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氏深知其价值,故急欲一观。光绪二年(1876)七月四日,他在长沙得知《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已经发售,“《方略》已由驿发到,曾、胡嗣子各一部。……过洪井问之,云尚未到。取道欲迎会看之,竟不能得”[3]499-500。光绪三年,他买到此书后认真阅读,厘清湘军从创始、发展壮大到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脉络。清朝官修史书虽有美化统治者的弊病,但因拥有官方权威,采集大量一手档案史料,是史书撰写必须凭借的依据。王氏《日记》记录,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七日,“阅《方略》二十本,检江西军事”[3]650;六月七日,“看方略,欲作江西后篇,翻四十本止”[3]666;十月二十二日,“作《平捻篇》,翻《方略》,头绪纷繁,未皇他及”[3]698;十月二十七日,“重阅川陕事,翻《方略》八函,至暮毕”[3]705。日记中关于检阅方略的记载还有多条,表明王氏撰著《湘军志》诸篇都会参考《方略》。
郭嵩焘等编纂的《湖南褒忠录》记载了湘军将士的事功。该书虽存在不少问题,但编纂者在搜集当事人口碑和档案史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王闿运知悉该书在叙次和编纂观念上有瑕疵,但因其征引了不少一手史料,故编纂《湘军志》时曾多次参考该书。如他说:“次咸丰五年军事,殊不明晰,因念《褒忠录》虽断烂,既有成书,不可不详观。因为钞撰营官之可考者,此书毕,将遍阅曾、胡集而摭拾焉。”[3]635“检忠绿二本,颇不若昨日之条晰,知其无益而不可不为者,此是也。为之则当有文理,今日殊草草,明当改之。”[3]636“看《忠录》一本,河南马德顺者,前为湘军马队将,予在祁门从问牧马,方别十九年,遂不相闻,以为留江浙补镇将矣。及阅阵亡册,乃知其于十二年前战死甘肃。愕然伤之,为作一诗。”[3]636王氏对《湖南褒忠录》的利用去其糟粕、汲其精华,且能将《湖南褒忠录》与其他书籍对照,考证湘军将领的存亡情况,“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史料运用中的一种境界。
同治十二年(1873),秦湘业、陈钟英著《平浙纪略》,根据当时奏疏、公牍、闻见等资料,以纪事本末体专记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的大事。王闿运认为《平浙纪略》“并浙略一部,多谀颂左公之词,其序他事,则颇有关系”[3]558。对于这样一部刚出的史书,王氏作《湘军志》时多有利用。《日记》记载,光绪四年(1878)五月朔,“作《浙江军事篇》末两叶,不称意而罢。缘《浙纪》颇详,未能裁割也”[3]657;五月二十六日,“《浙江篇》草草成,中多未窍,依怀庭书,略去其铺张者而已”。王氏用近一个月就初步撰成《浙江篇》,其速成与《平浙纪略》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和基本框架有关。在编纂实践中,王氏将《平浙纪略》中阿谀之词尽量平实加以表达,不铺张扬厉,坚守传统史学求真务实的精神。
王闿运编纂“平捻篇”时特别关注湘军平捻的记载,查阅过赵烈文的《平捻记》。赵烈文为曾国藩幕僚,熟悉湘军事迹。王氏对《平捻记》较为重视。《日记》记载,光绪三年(1877)七月二十七日,“得怀庭书,送赵惠甫《平捻记》,阅竟乃过松宅”[3]590;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四日,“作《平捻篇》,看赵惠甫《平捻记》,自胜王定安”[3]698。因赵烈文熟知湘军掌故,其所撰《平捻记》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王闿运的这一评价颇为中肯。
湘军集团代表性人物的日记、笔记、文集、奏疏和年谱等,既能反映他们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能见其功过是非,故有必要加以认真搜采。在编纂《湘军志》之前,王闿运就注意搜集曾国藩的日记与书信。《日记》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五日,“阅曾侯日记,殊草草不足观”[3]373;二十七日,“观曾侯与次青书札,无甚可取”[3]374。王氏对曾氏日记、书信的评价不高,但叙述湘军历史无法绕过曾氏的个人史料。接受编纂任务后,更需要对曾氏的文集、奏疏等加意搜集与阅读。光绪四年(1878)二月十一日,“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3]635。《日记》中还有多处“看曾集”的记录,记录了王闿运阅读曾氏奏疏与年谱的情况:“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3]653光绪二年(1876)闰六月十九日,“阅《曾年谱》毕”[3]496。对湘军主帅之一的胡林翼,王氏最初评价其作用不如曾国藩,后逐渐转变为扬胡抑曾。这一转变是在深入阅读曾、胡二人的私人著述过程中发生的。《日记》记载,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3]644;三月十六日,“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3]648。
对湘军其他重要将领,王氏亦精心搜集史料,以便全面反映湘军实态。比如他向曾任贵州巡抚的刘岳昭借阅资料,刘氏奏稿成为“援黔篇”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日记》记载,光绪四年五月六日,“刘前抚送援黔奏稿十本来,检抄竟日”[3]648;五月七日,“检援黔奏稿毕”[3]659。在搜集史料的同时,王氏要确定其价值,并对其纪年书法进行辨析。比如,王氏对骆秉章的《骆文忠奏稿》纰缪之处有所指正:“和合处送《骆文忠奏稿》一部,内有误编者,盖其家唯案时月,不看年分之故。苏赓堂遂据以作碑,然则谓碑志可补史,其说殊谬。”[3]670史家修史惟求真实,史料有误必然会影响史书的价值,严谨的史料考辨态度是史书质量的重要保障。
咸同之时,湘军势力遍布各行省。实地考察得到的故老传说等口碑史料,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甚至有时可以据此改写、重写相关叙述。《日记》中包含大量王闿运与时人谈论湘军史事的记录。他非常重视访谈所获得的史料,希望发挥其纠偏补阙的作用。1879年,他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故能十分便利采访蜀中战事的相关人员。《日记》记载,光绪六年(1880)八月二十四日,“鄂生来,久谈蜀中战事”[3]947-948。唐炯,字鄂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咸丰年间历任四川南溪知县、署绵州事,同治元年(1862)向四川总督骆秉章献计建言,协助剿灭石达开。其人知悉蜀中战事,故王闿运与唐炯讨论蜀中战事,可以说是采访得人。其后,他还采访了经书院监院薛丹庭。光绪七年(1881)七月三日,“翻《钞报》,作《援蜀篇》,请薛丹庭来,略问寇始末”[3]1029。以上口碑史料是王氏撰写“川陕篇”的重要史料,成为书面史料的重要补充。
王闿运在搜集整理史料上用力甚勤。有关湘军部分的史料搜集较为全面,但是在史料利用上过于重视私家文献和口碑史料,而对官方档案史料不够重视,此为缺憾之一;叙述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过程,还应搜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档案文献,然而,审阅《湘军志》,不难发现其利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档案文献较少,此为缺憾之二。王氏史料利用上厚此非彼的态度与其史料观一脉相承。他说:“惟此书端绪颐乱,传述异同。私论官书,均当兼采。……以官书本不尽精详,且此志又不资公家言也。”[2]804一方面,他申述撰写《湘军志》当兼采私论官书;另一方面,又指责官书“不尽精详”,对湘军历史的叙述不资官方的书写。王氏史料观上的矛盾态度,可能限制了他深入挖掘官方史料,从而影响《湘军志》的价值。
《湘军志》成书后,王氏对其充满期待,自视可以和《史记》《后汉书》比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期望时人有赏音者。出乎意料,湘军将领、士绅,如曾国荃、刘坤一、郭嵩焘等人阅读《湘军志》刻本后,众口喧腾,讥其为“谤书”“秽史”,甚至引得曾国荃发誓要杀掉王闿运,章寿麟要对其“饱以老拳”。《湘军志》之所以成为湘军将领和士绅批评的靶心,即在于王氏的撰著宗旨是客观记录湘军历史,以求其“兴坏成败之理”,这与曾氏兄弟及郭嵩焘等人要表彰湘军功业的旨趣背道而驰。郭嵩焘评价该书:“朱香荪晚过谈,因论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命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气习,不足怪也。”[10]455他指责王闿运文人之笔修史,缺乏史德,史料征引有失,对湘籍将领的功绩着墨不多,表功不足,伤害有余,是非功过颠倒黑白。他还批评王氏:“壬秋自命直笔,一切无所忌避,而颇信取委巷不根之言,流为偏蔽而不知。又其性喜立异,匹夫一节之长,表章不遗余力;其名愈显,持论愈苛,或并其事迹没之;其所不欢,往往发其阴私以取快。此其蔽也。然亦未尝不服善。”[10]374郭嵩焘批评王氏喜欢标新立异,对湘军统帅和将领名声愈著者批评愈烈,议论不具公正之心。郭氏的意见代表了不少湘军将领和士绅的意见,许多人都给王闿运压力,王氏《日记》中对此均有记录实态,物议沸腾最终迫使王闿运将《湘军志》毁版。
湘军周围人的评论反映了他们对湘军的情怀,而晚清和民国其他人的评论则相对客观中肯。如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姚永概评论该书:“连日舆中看湖南王开[闿]运《湘军志》,虽间有过于尊己抑人之处,而文笔酷似班固,可爱也。”[11]366姚氏赞赏其文笔模拟班固,但对其评论颇有微词。晚清藏书家贺葆真父亲贺涛评论该书:“王壬秋《湘军志》,其文学《史》,无公牍语,其事则取之见闻。此其佳处也。然不实处亦所不免,且喜毁谤人,人亦以是多怨之”[12]44。贺氏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为平实可取之论。民国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在比较《湘军志》和《湘军记》之后,给予《湘军志》较高的评价:“阅王定安《湘军记》,此书为驳《湘军志》而作,然笔力卑弱,叙次无法,直不中与湘绮作舆僮……末又有王定安日云云,不自量度,竟若以此与湘绮相抵,正如丑女弄姿,其丑弥甚。据予所知,定安本不能执笔,倩江淮间二三等秀才代为之,定安加以绳削,复经郭嵩焘兄弟润色,宜其笔墨猥下,文气不贯。然亦有一得,即人、地、时之误,较《军志》为少。考其事始末者,得以据依,其书终不必废。但《军志》之失,未必真失,则此书之为得也,亦未必真得耳。”[13]128他认为王定安笔力卑弱,叙述没有章法,完全不如王闿运驾驭语言和历史叙述艺术的能力,王氏之失并未真失,其批评具有辩证的观念。
结语
晚清学人日记有别于普通人日记,它除了记载日常生活见闻和对历史事件、家国情怀、复杂人性、社会巨变的思考外,更多的是记载日记主人购书、读书的体验与思考,是研究学人学术思想、学术变迁的史料渊薮。以学人日记为主要史料,并与时代情势相关照,会激发出以往不曾关注却又很重要的新问题、新领域、新见解。学人日记所体现的史学观念、史学批评、史学成就评价等,都值得深入探讨。与官方文献相比,史学学人日记形式更质朴、内容更真实。官方文献以官方的视角和话语构建“正面”的史学叙述,史学学人日记则为我们提供史学的“另面”。以往的近代史学研究,在研究路径、视角、话语言说上,重视官方文献、史学名著等,这部分遮蔽了史学的“另面”。
王闿运的《日记》记事时间跨度大,记录了他阅读正史和其他史体的感悟与评论,以及他纂修《湘军志》和地方志的始末经历。关于其史学观和史学批评,《日记》中有的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长时段的跟踪并提出系统的评价,有的则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捕捉这些见解和批评,对于全面理解王氏史学有重要的意义。王氏不是以史学名家的,他一生虽编纂了大量湖南地方志,但也不能算是地方志名家。他为后世部分史家所推崇的史学编纂实践就是撰写了《湘军志》。日记中对该书修纂缘起、编纂宗旨、体例设计、篇章布局、史料来源、改写重写、成书反响等进行了系统记录,这是在其他体裁文献中无法看到的,所以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王氏《日记》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氏史学深受今文经学的濡染,史学观念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氏的史学批评借鉴传统史学批评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在近代新旧转化的大背景下,未能有效地吸收西方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其史学批评仍是传统史学批评话语的再阐释,缺乏深度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阐释。观其史学批评,主要集中在王氏的《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基本上是丛残琐碎的片段,缺乏专文探究。王氏的史学实践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湘军志》,但是该书也不能算是一流的史学撰述。从日记视角检讨王氏史学的“得”与“失”,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细节与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