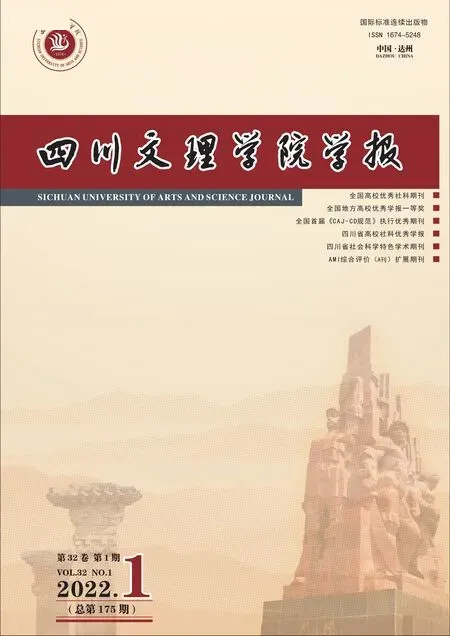从大地伦理到大地生命:现象学之生命显现思想进路
2022-03-17彭凌玲
耿 阳,彭凌玲
(大连理工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长期以来,伦理自然主义坚信伦理学与自然世界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自然事实和自然规律能够为人类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提供辩护。20世纪初,伦理学家摩尔则站在对立的立场批判伦理自然主义的思想进路,通过“自然主义谬误”划分了伦理的非自然属性和自然陈述之自然属性之间的区别,根据休谟法则否定根据自然事实推断伦理之价值判断的逻辑有效性。对应自然主义谬误提出的挑战,部分进化论伦理学者声称“进化使人类将行为目标指向社会福祉”,立足于进化论的事实陈述能够解释人类的道德行为、动机和确立相关规范。[1]20世纪30年代初,以利奥波德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家从进化论的角度解释伦理演化机制,将人类的社会伦理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扩展为关怀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地伦理,驱动伦理演化的内在动力乃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2]“大地伦理”的基本原则依据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事实来论证“自然的主体性”,进而作出人类与自然处于“对象性关系”的推衍,人类群体进化之最高级的目的在于大自然之整体的善。
然而,“大地伦理”之理论困境在其所描述自然作为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主体在陈述中被描述为客观事实,而陈述语言的优先性所赋予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同自然作为大地伦理的道德价值主体并非是处于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之中,主体意识活动的自明性并非必然通过观察外部客观世界所做出的事实陈述而得以确认。回溯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阐明此在寓居于世界之共存关系的局限性,唯有剥离意识活动的意向性,摒弃其与事实陈述之真实性的争执,才能回到共同面对的实事本身。在生命显现自身的模式中,作为生命的自行触发(auto-affection)优先于意向性意识,大地和生灵在纯粹的情感中内化于大生命现象之中,进而为从人道主义出发理解生态中心论提供可能的思想进路。
一、大地共同体与大地伦理的可能性
20世纪30年代初,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备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学科。利奥波德将生态学“食物链”“生态系统”等概念引入生态伦理的研究中,“所有的伦理学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之上:个体是一个其部分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一个成员”。[3]203利奥波德强调共同体乃是理解生态伦理的重要概念,共同体即由一个相互依赖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扩展为土地。“土地并不仅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过一个由土壤、植物以及动物所组成的环路的源泉”。[3]205利奥波德融合生态学所提出的大地共同体概念,不仅助推伦理学向大地有机地扩展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沿着哲学中自然与精神关系这一古老的线索,尝试探索在道德向度上提出人与自然融合的大地伦理能否克服自然主义道德观所遭遇的逻辑谬论。
利奥波德吸收了以大卫·梭罗和沃尔多·爱默森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对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洞察,从伦理角度提出人和自然同属于大地共同体。爱默森在《自然沉思录》中坚持依据整体主义原则论述人与自然之统一,“一片树叶、一滴水、一块水晶、一个瞬间,都同整体相联,都分有整体的完美。”[4]人类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包含于自然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自然和人具有共同的精神构造,唯有将人的存在同自然关联起来才能探究自然之精神构造的存在抑或是理解人自身的存在。“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从其他每一样事物中发出的启示之光都照向他。若无这些事物,就不能理解人;同样,若无人,也无法理解事物。自然史中的所有事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结果的,就像单性的植物。但若将它与人类历史相结合,它就充满了生命”。受到爱默森的影响,梭罗凭借其对自然的同情和关切,颂扬大自然内在美学价值独立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所创作的工业文明。通过描述了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梭罗立足于自由思想阐释了个体的完善和发展经历从原始野性向着追求精神演化的重要规律。个体发展的初级状态即追求原始野性的生活,“处于胚胎状态的人,要经历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5]238“而且还继续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5]243梭罗认为人拥有原始的野性和探索精神活动这两种本能,个体自我的完善和发展唯有通过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才得以实现。“他必须不仅限于自然——甚至超越自然的。并非自然通过他说话,而是自然与他同在。……他是另一个自然——自然的亲兄弟。他和自然彼此友善地各行其职,都在宣示另一方的真理。”[5]29据此,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共同演化,人在同自然的关联中演化为更高层面的精神性存在,自然也在这种关联中获得同样绝对的精神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共同演化承诺着对彼此之精神结构的完善,这意味着个体的自我演化超越了认识论的范畴而具备了道德的向度,而自然也从孤立状态演化为与人类和谐共存的有机统一体。
沿着卢梭在道德向度上探索人和自然共同演化这一路径,利奥波德融合生态学视角对自然演化的伦理价值这一问题加以系统论述。然而,道德向度的自然演化作为一种与人之精神性存在共生的精神结构,它是否能够通过基于生态学的生物进化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加以描述呢?在《沙乡年鉴》收录的《像山一样思考》一文中,利奥波德描述在看到狼垂死时眼睛发出的绿光时,他领悟到到狼和山之间隐藏着充满深刻含义和沉重情感的关联,“没有狼的地方就意味着是猎人的天堂,……而失去狼的山将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正如梭罗所说,“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只有这座山长久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听取一只狼的嗥叫”,而狼和山之间这种隐秘的关系却极少被人类所领悟。通过阐述狼和山之间的情感和隐藏的生存关系,利奥波德将客观自然描述为具有意识现象的主体,因而并未超越梭罗所提出作为精神主体的自然范畴。继而,面向如何通达客观自然之精神现象这一问题,利奥波德从梭罗所提出的自我演化转向了人类演化的道路上来。“我是有意把土地伦理观作为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来论述的,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一种曾经被‘大书’过的道德更重要的了。”[3]191利奥波德吸收了生物进化论提出道德向度上的人类社会演化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伦理演进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向着人类环境扩展的大地伦理。
毫无疑问,利奥波德立足于生物进化论提出人类社会向着大地伦理演变的观点,必然面临来自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和休谟法则的批判。对此,利奥波德对其观点的辩护则基于自然主义伦理学蕴含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助于扩展伦理知识的可能性,进而为新的和不同的伦理规范提供辩护。在进化论视角下,道德则应当关注实践行为中所诉诸的客观事实,考量目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包含价值判断的伦理决策。“道德向人类环境中的这种第三要素(大地)的延伸,就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行为上的必然性。”[9]192这意味着自然事实和伦理价值之间并非是逻辑演绎关系,而是基于客观事实做出评价规范行为的实践决策关系。然而,正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最后一章写道,“大地伦理的发展,是人类智力上的发展,也是人类感情方面的新进展”,大地伦理的可能性并不能通过否定道德的“是”而得到有效的辩护,而是仍需要通过探讨道德和自然之间内在的精神性关联,对二者之间同结构的精神现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探究。
二、世界共同体与大地言说
正如休谟断言“这种‘应该’和‘不应该’体现了经过确证的某种新关系,只是这种新关系如何从其他的关系中推导出来?”[6]道德意识乃是先天的和内在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经过推理演绎来论证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决策无法解释道德的存在,由此否定了理性的演绎通达先天道德之可能性。据此,摩尔通过“自然主义谬误”批判道德的自然主义观点,指出根据事实陈述的自然属性无法定义非自然属性的“善”。然而,与其说“自然主义谬误”归因于逻辑推导产生的谬误,倒不如说这一谬误从未正面审视爱默森和梭罗在超验自然主义思想中引入自明性的道德前提,即道德乃是对人的精神性存在同自然的精神结构之共存现象的觉察和洞见。在此,海德格尔立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重建此在形而上学,反思人之精神性存在与德性之间关联,试图重构以存在论为基础阐释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共同体概念,从大地关联着此在、世界以及语言出发阐释大地的哲学意蕴。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批判传统形而上采用主客二元论来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导致人成为孤零零的主体,抽象化的世界被当作客体化的对象,人与他者和世界相割裂。“在存在者范围内人成为主体,而世界则成了人的图像。”[7]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通过下决心去生存而被抛入世界,“此在”(Dasein)和世界的关系还原为“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整体性生存结构。[8]47在生存结构中,世界乃是由器具所构成的整体性指引关联,作为生存活动的终极境域先行向此在敞开。此在向着“向来属于我”的世界自行决断,先行领会世界这一源初境遇的有限性。在这种先天被给予的此在之“在世共在”的先天结构中,自我和他人的分离重新通过其所信任的世界得以关联。正如科柯尔曼斯所述,“‘共在’不必然意味着和睦相处……此在和他人的每一种关系,每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都已经以共在为条件。”[9]根据海德格尔对此在之“在世共在”的阐释,世界从作为由器具关联的整体性存在指向为了生存而操劳的自我和他人共同构成的世界共同体,否定了传统主体形而上哲学以精神性存在为前提所预设的共在结构。
20世纪30年代后期,海德格尔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经历了重要的转向。在《艺术作品的本原》中,海德格尔提出了与世界相对的大地概念以及二者相互争执又相互庇护的共生关系。世界不再是那个“向来属于我”(jemeinig)的终极境域,而是归属于一个更加本源的境域——锁闭的大地。世界代表敞开和显现,而大地意味着遮蔽和隐匿,存在通过敞开的世界得以开启自身,又通过大地得以自行隐匿。“世界”与“大地”之“争执”具有“开端性的本质”,此在之时间性并非是流俗时间,而是回到在历史的“另一开端”处通过“争执”来保存和守护存在自身的显隐二重性。“必须针对其遮蔽作用的对此在历史的流俗的解释作斗争,才能博得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8]426在“世界”与“大地”之“争执”的间隙中开启出非流俗的历史时间,此在以一个民族方式实现其整体性生存,其既是历史的开创者同时又是制造者。在认清人的有限性后,海德格尔将“生成”从“此在的生成”转向对根源于“物之聚集”的“世界生成”(Weltgeschichte)的思考之中。“我们把这种无声地召唤者的聚集——道说就是作为这种聚集而来的世界关系开辟道路——称之为寂静之音。它就是本质的语言。”[8]151大地作为此在在世的终极境域,不断涌动生长的大地便揭示着语言的本质乃是寂静的道说。
海德格尔在其晚期思想的语言转向中将大地称为“自行锁闭者”。“制造大地的意思就是: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10]制造大地是让大地在制作中的存在(In-Herstellen-Sein)凸显出来,大地作为存在者根基于更为源始的运动存在中,这也就是古希腊所理解作为“运动根基”即“自然”,“自然”让锁闭的大地自行开显。艺术是“制造”的根基,艺术的形式让作为此在的人和世界自由开显和隐蔽。在艺术世界中,沉默无言的大地躲避着世界的开敞和显现,而唯有经过此在的聆听,锁闭状态的大地同开敞状态的世界进入到聚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场所,天地神人四元在语言机制中相互运作形成通达存在自身的世界共同体。换言之,天空和大地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自然聚集到此在的“林中空地”,作为此在的人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世界之中。在此在之去-存在的途中,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让“作品让大地成为大地”,让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11]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此在和大地共同属于语言所构筑的艺术世界,在更为原初的自然之自行开启和锁闭状态中相互依存而共属一体。
在追问存在的途中,此在将根基置于自行锁闭的大地之上,大地既是水、土壤、树木等一切存在者整体,也是此在之“在世共在”的世界根基。在海德格尔中后期思想中,大地不再是此在操劳在世中显现的世界境域,而是同开敞的世界构成争执的遮蔽状态,并与天地人以及存在者处于生成性的涌动之中,大地构成了终有一死者的终极境域,其自身在等待着存在之自行涌现的充盈中同生命的密切关联。正如哈贝马斯说说,“使我们摆脱自然的唯一事物便是语言”,当海德格尔将此在的栖居之所以及开显天空和锁闭大地的纯一性均置于语言之前,大地同生命的运作之间的关联显现于语言所构建的诗意世界之中,大地语言所建构意义世界中向着整体性表象世界显现自身。[12]
三、生命共同体与情感化的大地
海德格尔将语言看作诗意栖居的家园,语言所构筑的意义世界“贯通”天地“聚集”万物,“形象的诗意道说把天空现象的光辉和声响与疏离者的幽暗和沉默聚集于一体”。语言与大地共属一体,此在在聆听大地的言说中先行领会存在的意义,进而再经过述谓活动而成为语言的含义。[8]174海德格尔将语言同存在意义之间的关联比喻为“生长”(wachsen),“言辞吸取含义而生长,而非现有言辞物,然后配上含义。”[8]188在“生长”之构造的意义上,语言并非唯有通过此在才能把外在化的表象世界引向存在的意义,而是在源初的主体性的生命显现自身中言说自身。[13]区别于海德格尔让存在意义经过语言转换而显现自身的外在主义思想路径,亨利则强调作为源初本质的生命在自身纯粹的内向性中自行展现,“是即刻地、无距离地感受自身的纯粹实事。”[14]据此,生命乃是不可还原的源初现象,向着生命的给予这一源初事实,人以及天地万物都在生命中形成生命共同体,不可见的大地在生命悲惋的情感映射机制中显现自身。
聚焦于现象学对象的生命之自我显现,亨利清晰地指出沿着意识和对象区别考察语言的意义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的复杂性之中。[15]“生命分裂了现象学对象和进入其中的方法之间的同一性”,[16]生命之自我显现乃是其他现象的根基,其显现的源初模式就是生命的言说。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中,生命的自我显现具有内在性,是一种绝对内在的自我感触(auto-affection),也就是说只能在生命自身中被经验,内在性的生命自身与经验自身相同一。因此,生命乃是纯粹的内在感受,是源初显现的根本形式,这一绝对的自发感触不可能还原为任何别的经验,也不会在外在世界中显现。尽管生命显现自身绝对内在性特征,但是,这种内在性的生命显现并未否定在意向性表象中呈现的对象,“准确地说,内在性在其本质中给与了超越性的可能性,在这一个意义上,前者揭示了后者。”[17]在亨利看来,他人的经验被给予“我”的经验通过意识所构造的对象-身体进入“我”的场域,这种意向性的渗透篡改了单子的自身性,乃是通过排除生命自身的内在性转而将其转化为表象世界而构成的。在生命之自发感触的意义上,生命的被给予性通过内在的纯粹的情绪自行显现,它与外在化世界完全无关,而仅凭自我的经验而连续不断地展现自身。生命个体共同存在于生命内在的纯粹情绪之中,从根本上超越了现象学的距离和构造的感知对象,消除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获得或未获得回应的欲望、由此欲望的互给性而胜出的情绪,在场或不在场的感觉、孤独、爱、憎、怨、恼、宽恕、狂喜、悲、欢乐、惊奇”源于生命的自行触发而具有内在性,我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作为“情感间性的生命的具体物质”在情绪表达中共享生命内在的无距离的本质。
面向生命这一实事,生命的绝对内在性让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得以显现,生命个体的主体既通过内在的感受确认其绝对自我性,同时在情绪间性中产生了超越意义上的自我。亨利将具有自我性和超越性的绝对生命个体称为生灵(vivants),生命自身显现的内在结构就包含了由诸多生灵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亨利强调生命共同体及其具有绝对个体性的生灵成员并不存在等级差别,生灵作为共同体成员并非从属于这个整体的存在,生命共同体也不会高于或者低于作为成员的生灵,生命共同体及其诸生灵共同享有生命本质的个体性。在生命共同体中,栖居于大地之上的生灵内在地感受着自我与大地共存,不可见的大地在生命的充盈中显现出生命的个体性。“你所占据的土地不可能大于覆于其上的双脚”,[18]“此地”(Hic)是不可见的,它并非属于外在化世界,“我”与“此地”处于绝对等同的地位。“我忍受不了看我周围土地上的东西的那种费劲的感觉”,[19]“我”对“此地”的感受并不能通过现象学的“看”而被还原外在化的土地,让“我”与“此地”之间亲密无间还原为在意向性中由此在和诸多存在者所组成的世界共同体。所以,“我们就像雪中的树干”根基于“此地”之中,“此地”自身的不可见性向着自身显现,在它的遮蔽下一切现成存在者失去了各自的边界,作为“此在”的大地在生命的充盈中确立其自身绝对的主体性。
既然生命自行触发而显现自身,那么生命显现何以通达语言,或者说语言或者文本该如何言说生命自身?言说意味着使其显现,对语言的聆听让存在者及其表象世界作为述说之物向我们显现,“听是世界言说的模式,这种言说模式在我们之外,在世界之中述说着它自己。”[20]在亨利看来,生命的绝对内在性乃是不可见的,生命自发感触向着生命显现自身,也就说生命显现自身就是生命言说的方式。“生命的言说不仅能让生命,而且能够生成它言说的现实。”[21]据此,亨利区分了世界的言说和生命的言说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生命的言说拒斥以聆听的方式所展现外在化世界,在世界言说中“我”同外在于我的指向物发生关联,而这种关联缺乏生命的内在力量而不可避免陷入虚无。生命的语言根源于内在性的无场域的生命之自发感触,根源于生命发自感触的情绪通过映射的方式在感性物质中得以延展。抽象艺术乃是生命言说的一种独特形式,它拒斥了让外在化世界在意向性活动中显现自身的这一言说方式,转向寻求对不可见的生命之源初显现的自我表达。在内在生命显现自身的超越性结构中,非意向性的纯粹情感躲避着可见性的言说,而以抽象的点、线、面、色彩以及形式来表达自身,如同光线投射在遮蔽着天空的云朵之上,为其勾勒出抽象的轮廓。抽象所关联不再是在次级构造中存在的对象之本质,而是根源于生命显现自身的力量,不断自我展现的纯粹感情相关,大地上的诸生灵以抽象表达的方式触及彼此的内在情感,在无距离的情感中共同构成具有绝对主体性的生命共同体。
结 语
利奥波德吸收早期的超验自然观奠定其有机整体主义的立场,通过描述大地以不同运作方式来维持其自给自足的状态,及其孕育着人类以及多样性的物种这一客观事实,论证大地的创造能力使其成为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有机体,“种种趋势和迹象表明,土地就像人的身体,症状表现在一个器官而原因在另一个器官上。”[2]195以自然和人之精神性存在的同一性结构为理论前提,利奥波德结合生物进化论提出“大地伦理”乃是人类的道德决策与实践不断演化以实现大地共同体这一整体的“善”。然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无法回避“自然主义谬论”的批判,难以解释基于自然的客观事实何以同伦理价值的判断发生关联。面对“大地伦理”与先天的道德意识之逻辑悖论,与利奥波德处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拒斥传统哲学中将先天的道德意识视作人类的整体追求,从而避免了传统哲学的绝对精神和超验自然主义的历史意识,指出存在论视域下大地乃是此在在世的终极境域,人聆听大地的语言以领会存在的意义,天空、大地、人以及万物在语言之中显现自身而生成相互依存的世界共同体。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从大地关联着的此在、世界、语言出发,赋予大地以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的哲学意蕴。在海德格尔看来,大地并非任何物质性或者可感性的东西,而是此在作为终有一死者的终极境域,诗意栖居的此在以聆听的方式领会存在的意义;在存在的意义上,大地作为遮蔽着存在而具有语言性,大地的言说向“世界生成”(Weltgeschichte)聚集而来世界关系开辟道路,通过语言所构造外在化世界构造让自身得以显现。区别于海德格尔让大地在外在世界中显现的思想进路,亨利提出了不可见的生命的显现模式优先于可见的世界。在生命自行触发的意义上,大地既不是处于外在化的世界之中存在者整体,也不是在此在聆听中向着终有一死者显现的终极境域;大地作为不可见的“此地”同与诸生灵处于亲密无间关联中,它在自身中自行显现而具有绝对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在无距离的持续性的情绪关联中,“此地”和诸多生灵共同构成了无差别的生命共同体。生命自行触发在纯粹的生命显现自身的情绪之中,情感投射乃是大地言说生命本质的方式,唯有在情感的投射机制中不可见的“此地”既是道路终点也是起点,将自身扩展向根植于大地的整体性生命共同体,在不可道说的生命悲惋中显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