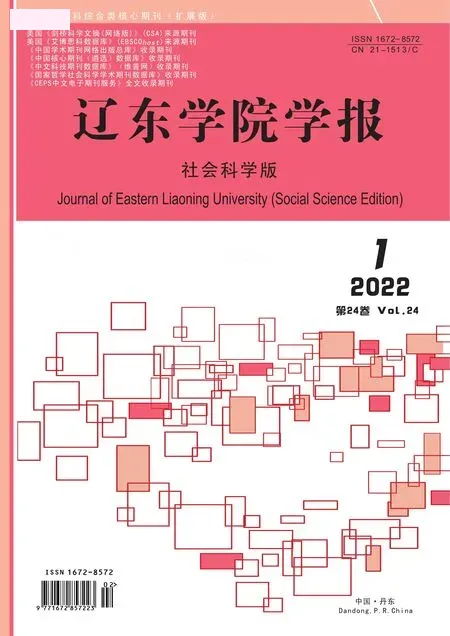索隐发微 注屈明志
——马其昶《屈赋微》的注解特色及现实意义
2022-03-17马群懿
马群懿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家、经学家,桐城派著名作家,被誉为桐城派的殿军。1894年,马其昶再一次参加乡试失败,加之恰逢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深觉从政艰难无望,于是,彻底放弃了科举之路。是年冬天,自京城南归,退而授书治学。在此期间,他的楚辞著作《屈赋微》[1]57-180一书刊行。目前,学界对《屈赋微》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总体评价与综合介绍《屈赋微》,考察其在楚辞学史中的价值;第二,深入研究该书的注释特色,主要围绕注释体例和注释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展开。《屈赋微》产生于清末,其时列强入侵、清政府统治日薄西山,马其昶在民族危亡、家国倾覆的关头注解楚辞,显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因此,我们更应关注其注解特色并考察其现实意义。
一、清末剧变与《屈赋微》的“索隐式”特征
马其昶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初社会的种种剧变,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事件都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影响,马其昶著述《屈赋微》与他的这些经历息息相关。
甲午海战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其昶对社会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抱润轩文集·李泌论》中说道:“今有分盗以财,丐其生者,财不尽,盗之欲不止。何则?彼所以窥吾之隙,而生其欲利者,固不仅如是遂已也”[2]20。马其昶于此说明,面对列强的侵夺,一味退让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马其昶还注意到,陷入外患困境的清政府,也处于内忧境地,内忧外患交攻之下,民生极其凋敝。《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民脂民膏被搜刮殆尽,富人尚且难以立足,贫苦之人更是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破败、社会困顿的场景不止马其昶一人遇到过,两千多年前的屈原面对相似的境况,也曾发出长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77。此时的马其昶翻开楚辞,思接千载,一对异代知音于此相遇。马其昶对屈原的理解,体现在他对屈原所面临的处境的理解。他在《屈赋微》中对《九歌》《九章》的阐释,就是典型体现。
总体来讲,马其昶对《九歌》《九章》的阐释具有“索隐”的特点。索隐,即探索幽隐。《红楼梦》研究中有“索隐学派”,他们善于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马其昶在对《九歌》《九章》的注解中就运用了这种“索隐”的做法,将诗歌的注解和楚国史实结合起来。
《九歌》解题当中,马其昶先引何焯的观点,以“其昶案”的形式进一步阐发义理:
何焯曰:《汉志》载谷永之言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则屈子盖因事以纳忠,故寓讽谏之词,异乎寻常史巫所陈也。其昶案:怀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则《九歌》之作必原承怀王命而作也。推其时,当在《离骚》前。《史》称“原博闻强志,明治乱,娴辞令,怀王使原造宪令,上官大夫谗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为。”虽非其实,然当时为文,要无出原右者。彼怀王撰词告神,舍原谁属哉?案:怀王十一年,为从长攻秦;十六年,绝齐和秦,旋以怒张仪故复攻秦,大败于丹阳,又败于蓝田。吾意怀王事神,欲以助却秦军,在此时矣。[1]91
从这则释题中可以看出,马其昶认同何焯所引谷永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解释《九歌》是屈原的应诏之作,屈原所作《九歌》即是怀王祭祀鬼神的文稿。按马其昶所引谷永的说法,这份祭祀文稿还包含着屈原的讽谏之语,表现出屈原对国家的忠心。马其昶还根据史料记载,认为《九歌》应当作于蓝田大败之后。因此,他注解《九歌》诸篇时,和丹阳、蓝田大败后楚国的境况相结合,并强调屈原的讽谏之意、爱国之情,甚至有的诗句的注解索隐至丹阳大战前后的细节当中去。比如,马其昶对“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1]94(《湘君》)等句的注解:
其昶案:秦使张仪来,诈楚绝齐,赂以商於地六百里。怀王信之,使一将军西受地,张仪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怀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六里。”怀王大怒,伐秦。自是兵连祸结,旋和旋战,卒以亡国。所谓恩不甚而轻绝也。交不忠,谓绝齐;期不信,谓张仪称病不出。此盖述其事,以求神之听直也。[1]94
从上述对《湘君》的注解中可以看出,马其昶几乎将每一句的注解都和丹阳大战前楚国的历史相对应,他认为这几句诗是楚怀王向云中君述说秦楚大战的原委,并祈求神灵助楚军的陈词。从马其昶的解读来看,屈原确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十分相似,楚怀王不以国家为念,在秦、齐之间反复摇摆,而且攻秦是愤而出兵,最终导致兵祸连天。
在马其昶看来,屈原面对这样的局面,内心痛绝,但不可胜言,于是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份事鬼神的祭词中。比如,从马其昶对“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1]99(《东君》)等几句的注解便可以看出来:
声色,即下所陈纟亘瑟、箫钟,祭神之乐舞是也。夜中作乐,观者顾怀声色,且太息日之将上,娱乐未极,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却敌,其可得乎?原意存讽谏,言之痛绝。[1]99
由这段注解可见,马其昶将《东君》中该句诗索隐至丹阳、蓝田惨败后朝野上下的反应。楚军在秦军的打击下,士气低落,损失惨重。然而,朝野上下却沉溺于声色享乐,无法自拔。马其昶认为,屈原面对战场上楚国兵挫地削,庙堂上夜夜笙歌的景象,心中忧愤痛绝,因此,借此句讽谏君主,表达自己的心迹。楚国惨败之后,朝野如此景象,再怎么取悦神灵来退强敌,恐怕也于事无补。马其昶在此能够深入屈原内心,与他对时局的感同身受是分不开的。
除了《九歌》之外,《九章》中也有大量对史事的索引。
秦在楚之西,楚屡被秦兵,则当时之转徙避难者,必东迁江夏。疑此是怀王三十年陷秦时事,故有天命靡常之感。[1]135(《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句注)
《史记》:秦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此曰“西思”,思咸阳也。[1]136(《哀郢》“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句注)
怀王十七年,怒伐秦,秦大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虏屈匄,取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魏闻之,袭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和,王曰:“不愿得地,愿得仪而甘心焉。”故曰“冯心未化”。[1]145(《思美人》“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句注)
怀王十八年,仪至,囚之。赂郑袖免,因以连横说王。是时,原使于齐,反,谏曰:“何不杀仪?”王悔之不及。“隐闵寿考”,谓饮恨终身。“变易”,谓复与秦和。[1]146(《思美人》“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句注)
怀王二十年,齐湣王恶楚之与秦合,乃遗楚书,于是怀王竟不合秦,是“知前辙之不遂”也。二十四年,又倍齐而合秦,秦来迎妇。至是三次与秦合,故曰“未改此度”。[1]145(《思美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句注)
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来伐楚,楚使太子质于秦。二十七年,太子亡归。二十八年,秦与诸侯共攻楚,取重丘,杀唐昧。二十九年,秦取襄城,杀景缺。故曰“车覆马颠”。和、战皆不可,惟有自强以俟时。改辙异路,独原有此怀耳。[1]145(《思美人》“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句注)
如上列举,马其昶引入诸多史事来解读《九章》,尤其是所列的《思美人》的注解,完完全全将诗句落实到史料中去。当然,《屈赋微》中这种索隐式解读屈赋的例子不仅限于《九歌》《九章》,在《离骚》《天问》等篇目中也有,只不过相对零散,在此提出,不再赘述。
马其昶所使用的这种注解方式,事实上不一定完全正确,目前学界也认为这种索隐式的注解方法难免存在穿凿附会的情况[3]。但是,在清末强寇入侵,尤其是甲午海战后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唯一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马其昶于此时著述《屈赋微》,考之于史事,最终通过注解屈赋,看到屈原和他的时代也曾面临国家危亡的时刻,然而即使国家败亡,屈原也始终不曾离母国而去。对于清末屡受打击的国人来讲,他们正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因此,《屈赋微》的出现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马其昶从屈原所处的时代出发理解屈赋,最终将屈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之下。这样的注解方式置于清末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考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清末学风与《屈赋微》的义理阐发
有清一代,乾嘉考据学的学风影响深远。清代乾嘉考据学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但是全盛之后,逐渐流于细碎,往往为了注解一字,旁征博引,多至万言。对此,焦循批评道:“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4]248。后来,桐城派的创始人姚鼐推崇宋学,以程朱为尊,并对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如毛奇龄、李塨、程廷祚、戴震等人大肆攻讦[5]333-337。这种乾嘉学术的汉宋之争在晚清时代的桐城派内部也存在,马其昶曾师事吴汝纶、方宗诚、张裕钊等人,吴汝纶要求马其昶:“多读周秦两汉书,毋作宋元人语”[6]18;方宗诚则曰:“文不衷理道,则其用亵,宜本经史,体诸躬,旁及大儒名臣论著”[6]18;张裕钊认为:“宋学重义理,侧重阐发圣人之道;汉学重考证,有助于通向圣人之道。二者固有本末、精粗、重轻之别,但治学中不容厚此薄彼。”[7]411从吴汝纶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吴汝纶对宋元时代重视义理阐发的做法是颇有微词的。但是,方宗诚没有一味排斥宋元人语,他主张“文以载道”的观点,同时他强调为文以经史为本。相比前二者,张裕钊汉、宋兼重。
马其昶对汉宋之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学、宋学各有特色,但极力为宋学辩护,认为“《汉学商兑》一书,反复数千万言,以正其违谬”[8]397,并且深觉汉学流于破碎,于圣贤义理的阐发毫无发挥,“乾嘉诸儒一变而崇尚汉学,其流弊所极,至掇拾丛残,讳言义理,已失圣贤明体达用之旨”[2]118,这大致反映了桐城诸儒宗宋的基本倾向。桐城派后期陷入讲求义理,坐而论道的弊端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桐城派又将汉儒的考证加入其主张,但考证只是文字训诂方面的实务,仍旧改变不了空疏的毛病[9]。这个问题的解决直到马其昶才算有了转机,他面对清末乱世,主张匡世救俗,为文、著述也应当和救亡图存的主题相符,“古之人持说立教,不一其端,要皆为发愤救时而设。文能观其大通,气息亦厚”[2]22,具体的做法便是“日取先圣遗经,发愤研诵,务明大道之原,存已坏之人纪,期至老死不悔”[2]94。他的著述观念很明确,在晚清世变面前,作为文人,要想救亡图存,能做的就是通经致用,匡世救俗[10]。因此,马其昶注解《屈赋微》不同于乾嘉考据学时期的研究特点,他注重对屈赋义理的阐发;同时,受桐城派后期加入汉儒考证以求实的影响,在阐发义理时表现出“求实”的倾向,而不是空谈义理。
《屈赋微》注重义理的阐发在马其昶所作《屈赋微·自叙》中已经得到明确:
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欷歔感泣。然真知其文者盖寡,自王逸已见,谓文义不次。今颇发其指趣,务使节次了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赋微》,人之读之者,其益可兴起,而决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区区文字得失间也。[1]72
具体来看,马其昶阐发屈赋义理表现在解释诗篇题旨、划分诗篇层次、疏通诗篇章句等三个方面,形式上或直陈义理,或引前人语,或加注按语以申述己意。
(一)解释诗篇题旨
马其昶在每篇的篇题之下对该篇的主旨进行阐发。比如,《离骚》下有释题:
《史记》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乃忧愁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1]73
这段内容其实是马其昶对《史记·屈原列传》的概括与转写,其目的在于借《史记》表达自己对《离骚》创作动机的认识。他认为,《离骚》是屈原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愁而作。国家前途堪忧之际,马其昶著述的心境正与屈原为文时的幽怨相同。前文引《屈赋微·自叙》说:“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欷歔感泣。”[1]72马其昶于此体会到屈原之忧,《国殇》的释题中,或许可以窥见马其昶深察屈原之恸了。释题如下:
洪兴祖曰:谓死于国事者。姚永朴曰:《九歌》终于《国殇》,亦因兵挫于秦,死者众也。其昶案:怀王怒而攻秦,大败于丹阳,斩甲士八万,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又大败。兹祀国殇,且祝其魂魄为鬼雄,亦欲其助却秦军也。原因叙其战斗之苦,死亡之惨,聆其音者,其亦有恻然动念者乎?[1]102
马其昶在解《国殇》篇题时,先引用洪兴祖和姚永朴的说法。洪兴祖寥寥数语点明《国殇》是为为国而死的人而作;姚永朴在洪兴祖的基础上继续申说,指出“死于国事”[1]102即秦楚交战,楚军为秦军所败,伤亡惨重。马其昶为阐明此篇旨意,对洪、姚二人的说法进一步具体化,指出“兵挫于秦”[1]102的历史事件为丹阳、蓝田大战,楚军大败,因此,《国殇》为祭奠楚军亡魂而作。他认为,楚军连遭大败,屈原心中哀恸,故祭祀战死的英灵,愿其魂魄化为鬼雄,帮助楚国力退秦军。此外,他略述《国殇》内容,“叙其战斗之苦,死亡之惨”[1]102,末尾直抒胸臆,听《国殇》之音,人皆为其情打动。在马其昶看来,《九歌》诸篇是屈原在楚国连遭大败,兵挫地削,见欺于秦的背景下,承楚王之命的祀神之作,其目的即“怀王事神,欲以助却秦军,在此时矣”[1]91。《国殇》当然也不例外。
ERICA程序是欧盟提出的电离辐射对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的框架程序,其来自于2004—2007年的欧盟“电离污染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ERICA)项目。
马其昶对篇题的解读从形式上来看往往先引前人的观点,在按语中对前人所说不足之处继续申述。无论何种形式,他对篇题的解释都是围绕屈原是爱国主义者的角度展开:《离骚》是屈原为国心忧之作;《九歌》是为了让怀王事神以退秦军的承诏之作;《天问》是屈原讽谏楚王的长诗等。因此,在对篇题之下章句文义疏通的基础上,马其昶呼应对篇题的解释。
(二)划分诗篇层次
如序言所讲,马其昶为了阐明屈赋的义理,对内容做了分层,使节次了如秩如。他在《离骚》的解读中,引述张惠言的观点,认为全诗可依“愿俟时乎吾将刈”“延伫乎吾将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五句为层次[1]89-90。但这种分层方式在《屈赋微》中并不普遍,一般地,马其昶会在疏解文义时,以“其昶案:以上(言)……”“以下(言)……”的形式来阐明该层所表达的主旨。这种分层阐述义理的方式遍布各篇,比如在《天问》篇中就有很明显的体现:
以上皆问天象。……自篇首至此,问天象、地理、物变,以下皆言人事。……以上言寿命不恒,富贵佚欲之乐不可久据,故宜及时自修,讽顷襄也。……以上论亲亲之道,以舜及泰伯、仲雍为法,以象为戒。……以上论用贤则兴,不用贤则亡,一法一戒。……以上论虞、夏之得失。……以上论商周之兴亡。……以上论天命之无常,覆举商周之兴亡证之。《传》所谓近己而事变相类也。天命罚佑之效,明白如此,而主曾不悟,遂以死自决。《史》称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观其论列三代兴亡,如指诸掌,诚命世之伟才矣。……以上言武功不可不厉,国仇不可不思。己虽与世长辞,而秦之贪利忘亲,终不能不痛切言之,史公所谓“冀幸君之一悟”也。以下再举楚事而切言之。[1]106-126
由以上胪举材料可以看出,马其昶总结屈赋各层主旨,将《天问》梳理得层次分明,而且往往会掺杂自己的评价。他认为及时自修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讽谏,并于此总结出王朝兴衰的规律,即用贤则兴,不用贤则亡。针对《天问》中商周历史的变迁,他结合楚国的情况,认为屈原为命世之才,但君主不明屈原之心,故其只能以身殉国。“武功不可不厉,国仇不可不思”[1]126,既是屈原对楚王的苦心劝谏,也是马其昶历经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的心声。
(三)疏解诗篇章句
马其昶注解屈赋,疏解诗篇章句的形式最为普遍。这种方式既有对字词的解释,也为阐发义理而服务,最主要的还是对章句义理的申发。从疏解方法来看,马其昶疏解章句有时会引述前人说法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时也会在前人说法不到位或自己持论之处下按断。这类疏解诗篇章句的例子如下:
(1)王逸曰:虽获罪支解,志犹未艾。王夫之曰:此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复设为爱己者之劝慰,以广言之。明己悲愤之独心,人不能为谋,神不能为决也。姚鼐曰:以上言欲退隐不涉其患,而不能也。[1]79(《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句注)
(2)王逸曰:愍,病也。其昶案:《说文》:“惜,痛也。”惜诵,犹痛陈也。《诗》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1]129(《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句注)
(3)吴汝纶曰:“江与夏之不可涉”,述其谏入秦之言也。“九年不复”,则未报此国仇耳。其昶案:怀王失国后三年,卒于秦。此文之作,又后六年。“忽若去不信”者,言不信其去国忽已九年也。仇耻未复,故含戚益深。[1]137(《九章·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句注)
(4)朱子曰:恐其离散之远,而或后之,以致徂谢。其昶案:“恐后之谢,不能复用”二语,乃微言也。此必怀王已死于秦,屈子恸之,不忍质言其死。因古有皋复之礼,北面三号。《礼》疏云:“三号者,一号于上,冀神在天而来;一号于下,冀神在地而来;一号于中,冀神在天地之间而来也。”故本此义,作为《招魂》之篇,亦史公所谓“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者也。生归无望,今望其魂反,其痛更深矣。以上为通篇立案。[1]169-170(《招魂》“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句注)
由上所见,马其昶注解《屈赋微》时,义理的阐发占据大部分内容。字音、字词的训解在义理阐发的前面,如第(2)例所示,“愍”“惜”“诵”三字的解释,第(1)(4)例中“惩”“用”二字的音注。从形式上来看,马其昶注解屈赋广采诸家之说,上举四例中采用王逸、朱熹、王夫之、姚鼐、吴汝纶等人的说法,并且在自己持论之处有“其昶案”,这样的情况在《屈赋微》中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3)(4)两例中马其昶阐发义理时将屈赋同楚国的史实结合起来,第(3)例中,马其昶先引吴汝纶的看法,之后又下按语,按语部分其实是对吴汝纶之语的进一步申发。第(4)例中,马其昶将礼俗与怀王之死相联系,“生归无望,今望其魂反,其痛更深矣”[1]169-170,于注中凸显自己对屈原的情感体会。
总体来看,马其昶注解《屈赋微》以阐述义理为主,间有对字词音义的训解,这与马其昶力诋汉学之破碎、崇尚宋学是分不开的。但马其昶并非彻底地回归义理之学,他在阐发屈赋义理时,往往有无信不征的考据痕迹在里面。比如:《离骚》的释题考之于《史记》中屈原的本传;《九歌》的释题和楚国丹阳、蓝田大败的史实紧密结合;《天问》《九章》诸篇的义理阐发也是结合楚国历史,并且字义的训释引《诗经》《左传》等文献,本之于经史。如本节开头所讲,马其昶看待汉宋之争,在宗宋的同时,也看到汉学的特点,又受桐城派求实思想的影响。因此,马其昶阐发屈赋义理时,在阐发的同时加入考据的成分,或考之楚国史实,或本之于经史,或引前人旧说以辅证自己的观点,使义理的阐发有所依傍。
三、马其昶对屈原之死的认识及《屈赋微》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马其昶对屈原之死持肯定态度,并且对屈原为国舍生赴死的精神给予极大的理解和赞扬。他在《屈赋微·自叙》中明确表达了对屈原之死的看法:
悲夫!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岂与夫匹妇、匹夫,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气,储与扈冶,为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间条缕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紊。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宗国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潜之他族,冀绵须臾之喘息。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气既绝,斯无能独存也。事可为,则单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即吾之气不有亏乎?事不可为,则返其气于太虚,太虚不毁,彼其浩然者,自旁(磅)礴而长存,吾又未见屈子之果为死也。性与性相通于无尽,是故屈子书,人之读之者,无不欷歔感泣。[1]71-72
马其昶在此段文字中首先定性,屈原之死绝不同于一般人的因一时愤怒而自寻短见。这句话事实上是有所针对的,俞樾在《宾萌集》中对屈原之死有质疑,他认为:“彼屈原者,一为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谗,则幽愁憔悴,继之以死,何其小也!”[11]12-13并且评价道:“如妇人女子失意于人所为者。”[11]12-13俞樾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来看并不少见,其原因跟当时的学风有一定关系。杨国强认为,明末清初以后,激荡在宋明之世的学风和士气逐渐消散,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杨国强引章太炎语对此总结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12]35该过程使读书的士子在精神上日渐蜷缩,并且和两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逐渐疏离[12]35。于是,以俞樾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在汉儒的饾饤之学中将自己的时代使命感消磨殆尽,他们认为屈原之死和常人不忍一时之愤自杀身亡并无区别。
马其昶否定屈原泄愤自杀的说法后,进一步指出,屈原死于宗国倾危之时,生为宗国士,亦当为宗国而殒身。唯其如此,屈原的精神能够浩然长存于人间,至于那些贼臣篡子,最终的下场只能是失其祖气,断绝其生存之根,难存于世。马其昶认识到,个人的命运其实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惜诵》“愿侧身而无所”句下其昶案:“君蹈危机,则己亦侧身无所,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也”[1]131。像郑袖、靳尚、子兰这样不为家国计的人,最后自己也会无处容身。因而,从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来讲,屈原最终的抉择值得肯定,千载之下,读屈赋者都为其精神所动。屈子精神如此鼓舞人心,只可惜“真知其文者盖寡”[1]72,屈原之精神不彰于后世,这便成为马其昶著述的动机。
在具体注解屈赋的过程中,马其昶通过罗举各家说法、间下按断的方式,从多个方面对屈原之死的精神予以阐述和肯定。《离骚》末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1]89的注解,针对屈原之死,罗列各家之说。钱杲之点出“从彭咸所居”乃学古圣先贤,为国殒命。王夫之则对屈子之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屈原的进退生死绝不是临时起意,殉国之决心也是经过一番沉淀的。《悲回风》“心纟圭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1]156句注解也引王夫之说:“君不闵己之死而生悔悟,则虽死无益,心终不能自释。盖原爱君忧国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愤世疾邪,婞婞焉决意捐生而已。”[1]156由此可见,“决意捐生”也是经过犹豫的,屈原深明若君主不体察自己殉国的用意,只是白白舍弃了生命,但心中爱君忧国的心终究无法放下,最终选择走向生命的终点。《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1]150句注说道:
朱子曰:不死,则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如此也。识,记也。设若不尽其辞而闵默以死,则上官、靳尚之徒,壅君之罪,谁当记之邪?其为后世君臣之戒,可谓深切著明矣。其昶案:以上历数古人遇合之无常,见士不遇不足惜,独己所立之法度,实兴亡治乱所关,故虽死而犹欲毕其辞也。[1]150
马其昶引朱熹这段话是对屈原爱国忧君之心的解读,即便是决意赴死之前也要“毕其辞”,不能对上官、靳尚之类的宵小之徒听之任之。本段话最后,马其昶下按语“所立之法度,实兴亡治乱所关”,虽死也要明确振兴国家的关键。振兴国家、追求美政是屈原毕生的追求,《离骚》“乱”辞部分注解,马其昶引龚景瀚语:“‘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1]89。屈原寄希望于美政可以振兴宗国,美政受阻,希望断绝,不得已使其殉国。
总而言之,屈原之死是为国而死,为宗族而死,他的选择是爱国忧君的选择。马其昶通过肯定屈原之死,彰示屈原为国家、为宗族献身的精神。历经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屈辱的国人,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与屈原所处的境况何其相似。马其昶在此时肯定屈原之死,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世人,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现出其在国运衰败时期的责任与担当。因而,从马其昶对屈原之死的认识来看,《屈赋微》是一部明志之作,它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反映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误解和历史使命感。
纵观楚辞研究史,诸如南宋末年、明末清初、清末、抗日战争时期等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学人对屈原与楚辞的研究总会勾连国家命运。人们通过注解屈赋、阐发屈赋义理来表现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此砥砺国人,成书于1905年的《屈赋微》即是这样的著作。清末国家衰败,强敌入侵,马其昶首先在时局上和屈原有共鸣,因此他在解读屈赋时索隐楚国史事以发微;清末易代之际除了社会的剧变外,清代学风的变化也对马其昶著述《屈赋微》有影响,马其昶宗宋儒之学,以广引前说、间有按语的方式对屈赋义理进行阐发,这也是对《屈赋微·自叙》中“真知其文者盖寡矣”[1]72的回应。同时,马其昶又受桐城派“求实”思潮的影响,阐发义理考之于经史。屈赋义理的阐发是认识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而如何看待屈原之死是理解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关键点。马其昶高度认同屈原之死的价值,认为屈原之死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死,绝不是不忍一时之愤的自裁。在国家破败,屡受欺凌之时,马其昶著述《屈赋微》以明己志,并且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国人,展现了士人对世运的担当。因此,《屈赋微》产生于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是一部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砥砺国人的注屈之作。周祖谟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中说:“古人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研究前代历史,自当明鉴戒,励节概。作者(余嘉锡)注此书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既‘有感于永嘉之事’,则于魏、晋风习之浇薄,赏誉之不当,不能不有所议论,用意在于砥砺士节,明辨是非。”[13]3-4余嘉锡先生著述《世说新语笺疏》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周氏的这段话来看,不唯马其昶的《屈赋微》,国家易代存亡之际的楚辞研究,甚至国家危亡的特殊时间节点,人们对旧典的注解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