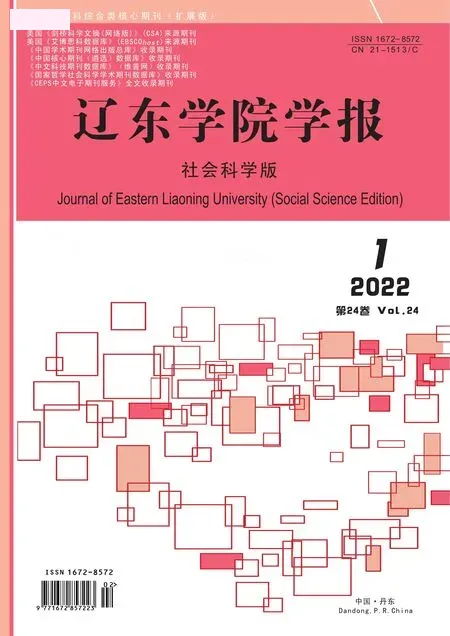《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及其引发的文体焦虑
2022-03-17宋扬
宋 扬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茅盾等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和叶以群的组织下,由香港转移到桂林。《劫后拾遗》是茅盾到达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却一直没有得到与其独特性相匹配的研究,其中很大原因与它的文体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速写”借助中篇小说体式,生成战争视域下破碎凌乱的文体美学,引发了茅盾本人及研究者共同的文体焦虑与言说障碍。对《劫后拾遗》文体的重新梳理与深入探究,关涉《劫后拾遗》的价值重估和对茅盾创作整体认识的再出发。
一、焦虑之象:从局部到整体的文体认知流变
《劫后拾遗》最早的文体说出现在局部篇章发表的时候。《劫后拾遗》中的部分篇章曾先后四次发表过。1942年6月15日,《最后一次防控演习——〈劫后拾遗〉中之一节》发表在《野草》第四卷第三期。1942年6月20日,《〈扭纹柴〉——〈劫后拾遗〉的一段》发表在《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二期,在封面和目录页均题为《扭纹柴》,并在括号内标注“特稿”,在正文页题为《〈扭纹柴〉——〈劫后拾遗〉的一段》,加注了副标题,正副文本均未注明文体,也没有发表在与文体相关的栏目。1942年7月15日,《闪击之下——〈劫后拾遗〉之一段》发表在《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五期,位于目录页第一篇的位置,题目《闪击之下》后括号内注明“小说”,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劫后拾遗》局部篇章的文体划定。正文页以《闪击之下——〈劫后拾遗〉之一段》为标题,没有设置与文体相关的栏目。1942年8月15日,《偷渡》发表在《创作月刊》第一卷第三号,在目录页上以《偷渡》为题,位列小说栏目第一篇,这是《劫后拾遗》的局部篇章第一次出现在专门的小说栏目中。
在最初的发表过程中,《劫后拾遗》一直被作为文学文体的小说来传播与接受。从中长篇作品中截取局部就可以作为短篇小说,这种处理方式,显得草率,但它代表了编辑的一种文学眼光和审美直觉,那就是《劫后拾遗》是文学文体,是艺术创作。《创作月刊》主编张煌在《编后记》中说:“茅盾先生的《偷渡》虽然是他近作中篇《劫后拾遗》中的一段,四千余字的篇章却展现给我们怎样一个森人的天地!如若读者失足跨进这个故事的氛围,恐怕‘神经就是钢铁绕成’,也会心跳,也会战栗。”[1]这种说法即着眼于小说三要素之一的“环境”而展开,关注的重点在“故事”“氛围”这些典型的小说叙事特征。就是说,《劫后拾遗》在其自身与刊物、市场、读者的互动过程中,首先是以“文学性”矗立的。
《劫后拾遗》“新闻性”得到放大,是在评论者以《劫后拾遗》作品整体为阅读、批评对象的时候,文体被划归为报告文学。1942年6月,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劫后拾遗》,这是最早的完整作品版本。在初版时,无序言和后记,只有正文,所以未关涉文体问题。《现代文艺》第五卷书评栏目刊发谷虹的《劫后拾遗》书评,在正文页栏目位置标注“新书介绍”,可知谷虹阅读的是《劫后拾遗》单行本。这篇评论在第一部分结尾明确提出“茅盾先生的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第二部分开头再次将内容与文体结合在一起,提出“《劫后拾遗》是关于香港陷落的一本报告文学”[2]。矢健《香港陷落的记录》也将《劫后拾遗》的文体划归为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的“新闻性”在传播过程中被逐渐突出。
不仅当时的评论界看重《劫后拾遗》的“新闻性”,倾向于将其归入报告文学,茅盾本人也在《劫后拾遗》出版后多次形塑其“新闻性”,称之为报告文学。1946年11月底,茅盾在应苏联塔斯社驻中国社长罗果夫之约而写的“自传式资料”中明确说:“报告文学有《如是我见我闻》(今改名为《见闻什记》)及《劫后拾遗》(写香港战争的)”[3]。1958年,茅盾在《新版后记》中评价《劫后拾遗》“像是一些‘特写’,又像是几篇大型的‘香港战争前后的花花絮絮’”[4]262。这一评价虽然没有以报告文学命名,但依然突出《劫后拾遗》的“新闻性”。1985年发表的《桂林春秋》再次明确称“《劫后拾遗》是一中篇报告文学”[5]。
历史现场文学评论的文体导向,特别是茅盾本人的三次文体自述,奠定了《劫后拾遗》“报告文学说”的可靠依据和权威定论,至今仍为研究者沿用。如《茅盾年谱》《抗战时期旅桂作家创作综论》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茅盾条目都持“报告文学”说。另外一些学者虽未明确称《劫后拾遗》是报告文学,但认为它的新闻性、纪实性远胜于文学性,对其采用了其他偏重“新闻性”的命名,如李建平在《抗日战争的历史呈现与影视剧创作——以桂林抗战文化为例谈谈抗日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历史把握》中称其为“纪实文学”[6],徐苑琳在《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出版业发展概况——以成都、桂林、昆明三地为例》中称其为“长篇特写”[7]。第二类观点与局部篇章发表时的“小说”说相承接,王卫平的《茅盾在小说文体建构上的独特贡献》将《劫后拾遗》与《路》《三人行》《多角关系》《少年印刷工》《走上岗位》等并称为“中篇小说”[8]。第三类观点则认为难以认定《劫后拾遗》的文体,林焕平的“杂文”[9]说,夏志清的“旅游杂感”[10]说,不约而同地以“杂”作为《劫后拾遗》文体命名的权宜之计。无论茅盾的文体自述还是研究界的观点分歧,都显示了《劫后拾遗》的文体焦虑及言说障碍。
二、焦虑之因:“纪实性”与“即时性”的文体“伪装”
《劫后拾遗》文体焦虑的焦点在于对“报告”抑或“文学”本质属性的认定,而文本的材源和面貌是左右这种认定的两个关键要素。
对于《劫后拾遗》材源的真实性,茅盾及早期评论者起了重要的形塑作用,使之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研究基础。茅盾在《新版后记》中强调《劫后拾遗》“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4]262,许多研究者也列举了《劫后拾遗》中遍布的“真人真事”痕迹,以此作为文本“纪实性”的重要依据。这里涉及我们该如何确立纪实边界的问题——对文学研究而言,这种边界主要体现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是否会进攻香港成为时局的关键。当时在港的三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此一直争论未果,史沫特莱作出“日美战端一开,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11]的判断。如果说这一段相对客观的回忆可以称为历史真实,那么在《劫后拾遗》中茅盾对这一段材料的运用与敷衍就是艺术真实。首先,三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文本中高度典型化为一位罗先生,这是小说艺术的处理手法。其次,史沫特莱的判断化身为周小姐的意见,而史沫特莱本人并未出现,这是移花接木的语言嫁接。《劫后拾遗》的“纪实性”主要体现为这种经过艺术处理后的“真人真事”,这就与报告文学等新闻文体所追求的真实具有本质区别。
谷虹认为《劫后拾遗》“是以作者在香港沦陷前后所经历和搜集的素材为基础,加以作者的选择和整理,然后给以客观的纪录”[2]。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很多研究者与读者也是据此突出《劫后拾遗》的“纪实性”,从而将其认定为报告文学的,所以有必要对这种貌似正确的观点加以厘清。这里的“纪实性”指涉两个层次:一是“实地考察”的素材来源的真实;二是“客观的纪录”的文本面貌的真实。为了更好证明素材来源真实的说法,我们不妨将《劫后拾遗》与毫无争议的报告文学经典之作《包身工》的素材来源做一比较。夏衍为了写《包身工》,不仅连续两个月“坚持每天早上三点多起床,步行十几里路,去杨树浦路福临路的纱厂附近实地察看包身工上班下班的情景”,而且“换上工装,先后两次设法混入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实地考察”是报告文学必不可少的写作方式,并不是“搜集材料”[12]可以置换的,而后者恰恰是小说的生产方式。茅盾的创作以搜集素材、记录新闻、列出大纲的现实主义操作方式著称,但若以此来理解《劫后拾遗》的“真人真事”,从而判断它的报告文学性质,那么《蚀》《子夜》《清明前后》在题材和人物上与“新闻”的距离更近,写作大纲更详细,难道都是更为出色的报告文学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客观的纪录”也是不少研究者的观点,与之近似的说法还有“纪实小说”“特写”等。在王德威看来,茅盾小说客观的文本面貌中“不乏目的论式的操作”,这种“客观”带来的“真实”“不会自我产生”,“‘真实’之所以可被理解,有赖意识形态与叙事动机等力量的共同勾画”[13]15。由此看来,素材来源的真实与“客观的纪录”的文本面貌只是在小说的芯子外建构起报告文学的外壳的错觉。
太平洋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劫后拾遗》1942年5月1日即脱稿,这种对材源处理的“即时性”也是“报告文学说”的一个论据。很少有顾彬这样敏锐且细心的识见者,他将这种“即时性”放置在小说艺术框架内来认知,认为“茅盾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的、可以构成他的风格的特点,是对于当前事件的描写与评析,这些事件甚至还没有在报告文学中失去价值”[14]。王德威更多地从文本面貌的角度来看待茅盾小说的“即时性”。他认为“时间的急迫感”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上的操作,“茅盾以近乎新闻报道的急切态度,将最新的消息与议题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由此创造出历史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临场感”。“即时性”是茅盾小说的写作策略,“快速捕捉人们记忆犹新、尚未褪入过去的事情”[13]31,“为现在作史”[13]38是这种策略的核心宗旨,目的是建构或虚构历史的脉络与秩序,获得对历史的解释权。
与似是而非的“纪实性”和策略操作的“即时性”相比,“文学性”才是《劫后拾遗》的内质。《劫后拾遗》中遍布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与心理描写,而且都采用细腻、形象的小说手法。“蜜黄色轻绡西服的一位女郎,上身加一件黑丝绒的短外褂,两颊喷红,半睁着水汪汪的一双眼睛,低垂了头,爱走不走地拖在他的男友的身边。”[4]182这段描写突出颜色的对比与搭配,将颜色与人物神态、动作和心理有机结合,立体塑造人物形象,而且渗透着叙述者的观察、揣摩、想象与态度,显然是小说家的手法。“报告文学是介乎新闻与创作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15],它在文学手法的选择和运用上自有取舍标准。报告文学的成分,“要让‘新闻’占得多;那艺术性的描写,只有加强对读者诱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新闻的重要地位”[16]。茅盾在抗战时期高度关注报告文学文体,1938年曾在《文艺阵地》上连续六期发表系列关于报告文学作品的书评,描写手法运用的技巧与比重被他视为报告文学一个重要的文体特征:“许多通讯员不正面的集中的去描写分析事件的经过发展,关系,反从侧面的来描写,如过分琐碎的描写风景,个人的感情,以及不必要的与报道事件本身无关的议论”[17]。以此标准反观《劫后拾遗》中的一段景物描写,不难发现在他的理论与创作之间存在的巨大裂隙:“十一月下旬的阳光晒到下午三时,海水似乎也温暖宜人;海浪的白沫一阵阵舐着沙滩,像热的在喘气。沙滩上的反光刺人眼睛”[4]188。既然如此,茅盾为什么要努力剥离《劫后拾遗》与小说的关系呢?其他研究者又为什么会轻易地被“纪实性”与“即时性”的“伪装”蒙蔽呢?背后显然隐含更为复杂的文体美学与作家的深层心理。
三、焦虑之隐:“速写小说”的文体美学
通观《劫后拾遗》,笔者认为用“速写小说”来概括其文体美学是较为贴切的,对于释放其文体焦虑也是更为有效的。“速写小说”的命名并非挑战既有文体格局,也不是对小说类型的节外生枝或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建立茅盾小说与新文学文体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体谱系的角度概括某种具有一致倾向的小说美学,从而标识茅盾小说体式演变扩展的图谱,深化对茅盾创作的再解读,同时也是对文体反思思潮的一种回应。
“速写小说”的命名缘起于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的“速写”。与其在西方的词义流变过程相似,作为文学体裁的“速写”在传入伊始就与美术学保持着难以剥离的亲缘关系。胡风认为“速写”是轻妙的世态画,田仲济认为文学上的“速写”和绘画上的“速写”,“除了表现的手段不同外,一切是完全相同的,一种是用文字,一种是用线条”[18]。茅盾在《桂林春秋》中对自己的创作思路与审美诉求表述为“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十五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5]。可见,在“速写”文体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变的是与美术源头的关联。在《劫后拾遗》出版不久即有评论家朦胧感受到这种文体美学:“全部作品由于时间的进展和战事的演变,分为六个部分写出,而每一部却又由许多片断所组成,这些片断连接起来,则成为一部有系统的完整的作品。”[2]这里所言的“六个部分”即小说的六幅主体“速写”,“片断”即构成主体“速写”的若干局部“速写”,各个层次的“速写”以平铺、穿插、拼接等组织形式建构起完整的战争阴影下的香港时空。如,开篇第一幅“速写”是“罗便臣道”“几对男女”行走谈笑的画面,第二幅是“德辅道”“卖晚报的女人和孩子”与“胖绅士”组成的街景画面。两幅“速写”之间全无任何瓜葛,摒弃一切传统的起承转合的俗套,干净利落。阅读作品的过程,犹如翻看画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一页画作既统一于叙事整体,又各自独立,线索清晰。应该说,《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表现出了是对“速写”本源的回归。
“速写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持续进行了文体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速写”自20年代与中国新文学发生联系,甫一传入即形成强势的创作实践,同时,也与短篇小说发生了频繁的对冲与难解的纠缠。《文学》《太白》《中流》《光明》《七月》等刊物都曾是推广“速写”的文艺阵地,茅盾、叶圣陶、许地山、巴金、艾芜、丁玲、叶紫、萧军等新老作家以及一大批文学青年都涉猎“速写”的理论或创作,构成的庞大的“速写”队伍。茅盾在《春季创作坛漫评》《速写与随笔·前言》《关于报告文学》等多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一盛况,他本人是最持久的“速写”谱系的建构者。茅盾的“速写”谱系建构经历了20年代“速写”片断训练—30年代以“速写”笔法作短篇小说—40年代在中长篇作品中嵌入“速写”画面的流变过程。然而,茅盾的《速写一》《速写二》名为“速写”却与“新闻性”无关,专注点在于观察、捕捉、造型的迅速与勾画的写实。《速写》也是一篇名不副实的小说。这篇作品以房舱为空间,以元昌、金百顺、胡广生三个小商人构成对立的三方人物关系,情节发展围绕三个小商人可否进入房舱的焦点展开,人物性格简单,情节线索单一,投射的是对于描写场面和结构片断的能力诉求。茅盾对“速写”文体的实践一开始即搁置其“新闻性”,利用的是“片断”“写实”“即时”的一种面向。值得辨析的是,这里的“写实”并非将“真人真事”植入文本的纪实,而是如实刻画对象的一种艺术手法,“即时”强调迅速的落笔能力。这两者更像是一种对小说创作能力的训练。如前所述,“纪实性”与“即时性”是形成《劫后拾遗》文体焦虑的关键所在,虽然在内涵的理解上后世评论者有所错位,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文体美学正是伴随“速写”这一文体的固有特征进入《劫后拾遗》的。尽管“速写”理论拒绝想像,将纪实与虚构作为自身与小说的差异底线,但这种源自苏联的文学理论在30年代的中国“速写”——小说创作实践中往往无效。白尘的《打遞解》《肉》、顾和声的《夜店》等都可以看作包含了“速写”美学的短篇小说。它们之所以没有引发文体焦虑,是因为没有突破“速写”最直接可见的一种特征——篇幅短小,而《劫后拾遗》正是由于实现了“速写”与中长篇的嫁接,才引发了文本面貌直观的陌生化,进而积聚成一种文体焦虑。
对这种文体焦虑推波助澜的是30年代报告文学传入中国。它在原本已经难分难解的“速写”——短篇小说关系中又注入了明确的“新闻性”、长短各异的篇幅等更为纷繁的因素。报告文学的出现彻底取消了“速写”与小说的最后一道屏障——篇幅短小。报告文学进入中国之初就被文坛视为“速写”的关联性文体,由于报告文学传入较晚,为了说明其特征,辨析创作的高下,评论者常常引入“速写”作为参照,在对象化过程中生成报告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夏征农、周立波乃至茅盾都进行过这种比较。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认为“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19]。这种文体意识忽略了文学手法具体技巧和程度上的复杂分野,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文体边界,由此导致茅盾对《劫后拾遗》文体指认的困难——毕竟从茅盾的观念出发,《劫后拾遗》可算作报告文学,问题就在于他的观念与后来研究界和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认知与期待之间的错位。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三种文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足以使《劫后拾遗》因“速写”而生成的文本面貌被误认作“报告文学”。
既然茅盾认为报告文学与小说并非壁垒森严,为何又要在《新版后记》中特别强调《劫后拾遗》“不是小说”[4]262呢?这种曲折的创作心路和难抑的文体焦虑背后恐怕隐藏着茅盾对文体高下的一种价值判断。在茅盾的潜意识中,小说是更为正宗的一种文学样式,而“报告”于20世纪30年代才从西方传入,更多是应了时代和大众的需要。与小说相比,“报告”更多是一种功用性的产物。在此潜意识下,文坛多面手茅盾显然更加爱惜自己小说家的羽毛。“对新中国成立后仅有的两份创作类手稿”“亲手销毁”[20]即是茅盾爱重自己作品的典型表现。茅盾主张“小说必须‘做’,有计划地去‘做’”[21],而《劫后拾遗》显然“做”得不充分,没有在茅盾属意的构思路径上前进。“小说”的初衷与“特写”或“花花絮絮”的效果之间的鸿沟被茅盾视为“老大毛病”,因此茅盾宁愿放大其“纪实性”与“即时性”,作为“辩护”的“理由”[4]262。
《劫后拾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体焦虑背后投射的是“速写”与小说文体碰撞与融合的一段历史。“速写”文体美学建构的累积和《劫后拾遗》对“速写”美术本源意义上的回归都为“速写小说”的命名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能性。为了描摹“速写小说”谱系的整体样貌,把握最核心的一些美学要素,笔者试图对“速写小说”的内涵加以描述。首先,“速写小说”具有小说文体的本质属性——艺术性,它旨在对叙事负责,而不必对事实负责。其次,“速写小说”具有“速写”与小说交流互动的文体特性,在创作时间上往往距离本事发生较近;在结构上打破情节、人物、环境的连贯性,以单一片断或并置片断建构叙事整体,生成碎片化美学观感;在人物刻画、场面描写等手法上力求写实,抓住突出特征以点带面,不事铺陈与渲染,减少抒情和象征的介入;在语言上追求简练、精准、朴素的风格,体现迅速勾勒的质感。
四、结语
突然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给作家带来碎片化、片断式的生命体验,“速写”文体美学的优长与战争体验书写的需求之间的契合使“速写”进入茅盾40年代的创作视野。经济压力、政治观望、出版预估等多重因素的权衡促成了《劫后拾遗》的文体策略。作为“速写小说”在40年代的发展形态,《劫后拾遗》突破了“速写”篇幅的限制,存续了“速写”的风味,既是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速写”文体在消解自身独立性后发展的文学一脉,也是抗战时代语境复苏“速写”文体,催生美学新质的产物。“速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最终在茅盾手中完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