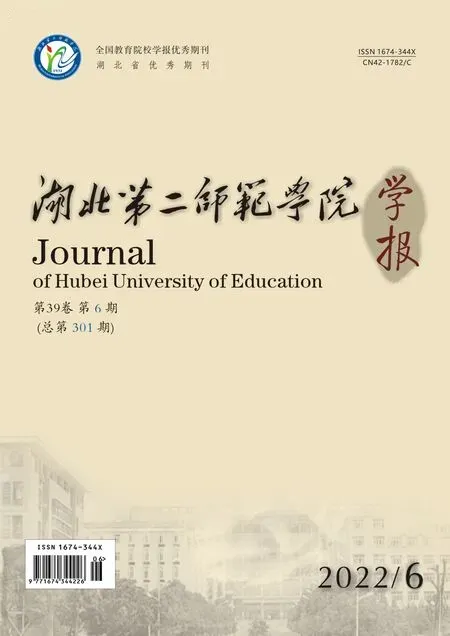明末清初闺秀词的传播
2022-03-17林静
林 静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361024)
从词学研究看,词的传播方式是不可绕过的研究角度。目前对词的传播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唐宋词传播的研究。对女性词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宋代,如宋代女性词传播方面目前有谢穑《宋代女性词作流传方式与创作主体的关系》,[1]还有从词的传播角度专门研究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史地位。[2]但是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中后期以后,词也由音乐文学转为案头阅读的徒诗,[3]传播方式大有不同。明词清词区别于宋词的一大特征就在于传播方式的案头化。同时,明代中后期开始,闺秀作词兴起,作为区别于青楼词人的伦理身份,它们的传播方式同青楼词人通过公共空间传唱词的传播方式有很大不同。目前对明词清词的传播研究,学者汪超有数篇论文与一专著《明词传播述论》,对明词案头化传播中总集、别集和普通书册传播均有详细研究,其中也涉及明词口头传播,但总体更偏向案头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汪超对女性词作的传播研究中,从文化场域角度区分了闺阁(闺秀词人)与青楼(青楼女词人)两种不同伦理身份的女词人词作的传播。虽未对闺秀词的传播作更深入与详细探讨,但也点明了闺秀词的私域性质。本篇的目的就是从闺阁这个私域出发,结合明词的案头化传播,通过细究明末清初时期闺秀词的各种传播策略,来考察这个时段的闺秀词,以充实明清女词人,特别是闺秀词人研究的观察路径。
一、闺秀的定义与时人对闺秀词传播的态度
对闺秀的定义可从“闺”的含义出发。《说文解字》对“闺”字的解释为“特立之户,上圆下方,有似圭,从门圭,圭亦声”。[4]《墨子》卷十五《号令》中对“闺”的解释为——“周还墙、门、闺者”。[5]可知闺,即小门、内室之意,所以说闺阁是一种私域,闺秀是私域女子。闺秀文人和男性文人、青楼妓女文人的不同之处体现在活动空间上有私域和公域之分。
词的传播分为口头传播(包括歌唱等)与书面传播(包括书写与印刷等)。词产生的初期主要的传播方式是乐妓口头传唱。但渐渐到宋元之后,通过书册传播(即案头化)成为词的主要的传播方式。所以唐、五代和宋初的词既是语言艺术亦是歌唱艺术,如欧阳炯在最早的词集《花间集》序中所总结的——“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6]刘光裕在《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中提及“词传播方式的转变在北宋中期开始,印刷和手抄逐渐取代乐妓演唱而成为传播宋词的重要渠道。虽然周邦彦、李清照、姜白石等人依旧倚声填词、浅吟低唱,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诸人仍时常与乐妓交游,但乐妓演唱在宋词传播中的作用日渐衰弱。”[7]再有学者吴大顺与王定勇论文《论词的传播与词的文化特性》更细致说明这种书面的传播是以词籍刊刻为基础的文本传播。这种词籍传播成为了南宋时期词传播的重要方式。南宋开始的词总集、别集、丛刻有很多,到元代以后更是到了以文本为主的传播时期。明清时期,相对于口头传播,文本书册是填词和词传播的主流。[8]回到明末清初时期的闺秀词人的词作传播方式讨论上,闺秀不是歌妓,并不在筵席之上,也不是男性文人。“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9],闺秀们囿于“内”这个私域空间,她们的词作来自“内”,必须从“内”的私域空间里向外衍生开来。
在对自身所作的诗词的传播方面,闺秀词人们抱有矛盾的心态,她们把写作当作不认真的“顽”行为,对自己作品传出家庭外感到“羞耻”。以下将利用明末到清代的文献对此分析:
清初小说《红楼梦》中有一段文字可以从细微处了解当时闺秀在家中所作诗词的传播状况,以及她们对其诗词作品流传的态度:
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若说我们认真作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10]
这一段中可以了解到以下信息:第一,闺阁私域作品的传播,是通过家中男性成员带出给朋友们阅读,然后这些交游的文人把其中的好作品进行刊刻。第二,《红楼梦》成书年代和作者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的(清朝初年到乾隆年间)男性文人对闺秀所作诗词的欣赏。以上《红楼梦》选段中贾宝玉的所言“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描述了当时文人对闺秀家中创作的诗词的好奇心与支持。当他们听见贾宝玉的姐妹们在家中发起诗社,便求家中男性成员(贾宝玉)将闺秀们的诗作带出来一起阅读。遇到让人“真心叹服”的好作品,这些文人便会“抄写”、刊刻“刻”了去。第三,从这一段还可以了解到闺秀们对自己的诗词作品的创作和流传的态度。她们都把写诗当作“顽”,是不“认真”的行为,至少言语上对作诗态度是如此。听到自己的诗词要被带出去流传,对此并非持有高兴的态度。探春和黛玉听说宝玉要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外传,都直接制止,说“胡闹”,自己的笔墨“不该传到外头去”。当时闺秀诗词若是外传,被抄写流传,被编入诗词选集中,大都在编排体例上放置于僧人道士诗词后,娼妓诗前。不知道是言语上的谦逊,还是真的不希望自己的诗词被流出,她们都认为自己诗词流出是“胡闹”。
类似贾宝玉外头有交游的朋友希望求得贾宝玉家中姐妹唱和诗词,事实上明末清初的确有文人喜欢收集闺秀作品,比如明末藏书家祁彪佳就喜欢收集。祁彪佳的《林居尺牍》中与沈君服信中记:“向所求小山题咏倘已有脱稿者,乞仁兄垂示,得名僧闺秀之作,尤为泉石生光。”[11]也有文人喜欢为家族中女性编辑作品,促进他们文集传播。祁彪佳妻子商景兰就有自己的文集,徐灿的个人别集《拙政园诗余》的编撰有其夫陈之璘的帮助,不仅为此书作序,徐灿的作品后常有其夫的纪事和点评。当然,除了鼓励外,男性文人和大众对于闺秀作品的追捧还有一个原因是来自对闺秀乃至所有女性诗文的好奇心甚至猎艳之心,这也导致女性作品的外传容易惹上“不栉之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让她们对自己作品的外传感到更加谨慎和不安。
虽然说家中男性积极为女性作品编撰成集,不少文人也积极收集自家和朋友家中的女性作品,当时的闺秀对于自己作品外传的态度却类似贾宝玉的姐妹们。有些闺秀把文编成文集却秘不示人,似乎是当时有些女性一方面希望作品得以保存,另一方面较为保守,怕作品流传带来不良影响。比如据汪超在《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中列举了明末闺秀词人李眺已作个人文集《鹃啼集》,却秘不传播。[12]
《红楼梦》中贾宝玉和家中姐妹对于诗文传播的态度也体现在当时文人王士禄在搜集上古至清初女性著述的总集《然脂集》中的自序所总结:“使诸书具在,当必徘然。惜也羽蠢劫灰,散灭略尽,即世所艳称,若班左钟谢诸媛,所存亦什百之一,而碎金片羽,复不足厌攀猎艳之心。推其缘故,岂非以语由巾帼,词出粉墨,学士大夫往往忽之,罕相矜惜,少见流传故或英华终朋于房闺,或风流旋歇于奕世,还使关家女士空传不栉之名,蜀国名姬独擅扫眉之号,不其惜哉。”[13]闺秀们往往囿于“内言不出于间”之俗见,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束之高阁,把文集密不外传。
综上,《红楼梦》中探春黛玉这类闺秀所说的:“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这句话就高度总结了她们对自己词作传播出闺阁的态度。而贾宝玉的友人所说的“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也体现了当时文人对闺秀诗词作品的提携,当然其中也不乏存在猎奇心态。值得一提的有宝玉的一句“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此话道出了闺秀词传播的真相,即闺阁笔墨必须通过传播才能传世。
二、闺秀词传播的方式
(一)庭内吟咏与书信传播
闺秀囿于闺中,闺秀的诗文作品传播需要从家族出发,走向对外传播。家庭内部的吟咏,然后与家庭外的家族成员唱和和书信来往,让词作走出家庭之外,才可以帮助闺秀词的传播。其中,书信往来的唱和与交游是传播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互动的主要方式。在闺阁内,闺秀们可以相互进行文学讨论,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闺秀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家庭、家族内外的唱和和交游不仅是她们创作的重要组成,更是传播的主要形式。书信来往不单单能够使得女性诗歌的创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还促进了女性朋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促使闺阁女性的交游走出家庭,扩大交际面,从而对女性文学创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学者魏爱莲在《十七世纪中国才女的书信世界》总结书信是“上层才女彼此支持鼓励诗画创作的主要途径之一”[14]魏爱莲的研究中叙述了十七世纪明清之际时,中国的才女们交换作品、彼此互相支持鼓励创作。她们或是通信或是聚会,同时以作者、读者、点评者的角色彼此沟通,产生互动。根据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考察,清初著名文人袁枚和他最知名且最欣赏的女弟子席佩兰一生中仅见过几面,而且都只是在席佩兰家中。[15]他们之间的交游和诗词交流必然都依靠书信方式,这很大可能就是得益于清初的交通邮驿的发展。
关于家庭内的唱和和家族来往(血亲、姻亲关系)中的唱和,清代中前期的小说《红楼梦》对贾府大观园内闺秀成立诗社、创作诗词等情节就反映了那时代闺秀家庭内的创作场景。学术著作方面,家庭内的唱和和家族之间的来往(血亲、姻亲关系),在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也有所总结:“明之季世,妇女文学之秀出者,当推吴江叶氏,桐城方氏。午梦堂一门联吟,而方氏娣姒,亦无不能诗文,其子弟又多积学有令名者。”[16]家中女性之间唱和交游之例甚多,梁乙真所举例的吴江叶氏(又称午梦堂家族,因其家族文学集名“午梦堂集”)就是其中翘楚,钱谦益在其编写的《列朝诗集小传》沈宜修传记就沈宜修所嫁的午梦堂家族庭内唱和“宛君(沈宜修)与三女相与题花赋草,镂月裁云,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宠,有逾左氏。于是诸姑伯姊,后先娣姒,糜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诸女红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役交作矣。”[17]还有明末山阴祁氏家族“夫人(商景兰)有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事。”[18]再有桐城方氏乃以理学名家闻名,才女辈出,方于毅《桐城方氏诗辑》的凡例中记录方氏一门才女:“彤管流徽,吾桐最盛。如环珠(吴令则)、棣倩(吴令仪)、壤芷(左如芬)、缄秋(姚宛),不可胜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方维仪)守志于清芬阁,与娣妇吴令仪以文史代织纫,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方维仪在弟妇吴令仪逝后承负起其子叶就是侄儿的教养责任,也与侄儿有书信《与密之侄书》往来。方氏才女与其他家族外的才女之间也有交游之作,《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张秉文妻方氏”条目记录有“三家妇独以篇咏相往复”的佳话:“含之(张秉文)举万历庚戌进士,同年生闽人孙昌裔、翁为枢携家长安邸中,孙之妇郑、翁之妇吴皆谙文墨。承平多燕,女子从夫宦游者岁伏腊以粳妆花胜相贻,而三家妇独以篇咏相往复。……崇祯初,含之官于闽,两家妇为如耀刻集,皆为其序。”说明几位才女不仅有唱和之作,这些作品还被结集成册。
除了家庭成员外,闺秀词人还有和家族外的非血亲姻亲关系的来往亲密的女性朋友交游唱和,比如闺塾师、女尼,但这也不属于公域传播,因为闺塾师往往被请到家中庄园内授课,女尼也可进出闺秀家中。上面所举例明末山阴祁氏家族夫人商景兰一家与闺塾师黄媛介有交游,商景兰作《青玉案·即席赠黄皆令言别》词赠黄媛介,商景徽也有《江城子·怀黄皆令》这种交游之作。黄媛介与商景兰还有商景兰三个女儿祁德渊、祁德茝、祁德琼等都有送别诗。她们皆作过写给黄媛介的送别词:如祁德琼《途黄皆令归鸳水》,祁德渊写送别诗《途黄皆令归鸳湖》,祁德苣为黄媛介写《途别黄皆令》。闺塾师外,商景兰与比丘尼亦有送别赠作,她的词作《忆秦娥·雪中别谷虚大师》和《诉衷情·雪夜怀女僧谷虚》皆是和僧尼谷虚的交游之作。
以上为闺阁私域内的闺秀词作传播,这种传播就如汉学学者魏爱莲(Ellen Widmer)以及高彦颐都所总结:“女性文化的特殊性,建立在女作家、编者和读者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基础上。女性创作或互相传递的诗集、序跋、随笔和版本,使我们在每日闺房生活的场景中,重构了一个爱情、性和友情的论述。虽然身隔异地,这些妇女通过交换诗歌来相互传递感情,就如同邮政交流时代朋友间的通信一样。”[19]
闺秀词人还有对于家族内男性成员的,比如和夫君、兄弟的诗词唱和来往。闺秀词人出嫁从夫后与娘家兄弟的唱和和寄赠之作,是帮助词作从一个家庭(婚后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原生家庭)的传播反思。这类词作全明词中所收录数不胜数。以清初康熙年间重要选本《众香词》为例,此选本所收和兄弟唱和词作就有周贞媛《如梦令·送铭九三弟》、任淑仪《金菊对芙蓉·送茹廷弟就婚广陵》、江淑兰《杨柳枝·和戴颍生表弟》《忆王孙·寄溯岷弟》、张桓少《谒金门·寄怀古容三姑时长君太史子千英表兄迎养京师》、许定需《如梦令·壬午秋留别兄竹隐》、钱凤纶《孤鸾·为林寅三表兄咏孤雁时嫂重楣新没》、纪松实《画堂春·送兄法乳北上》、吴文柔《谒金门·寄汉槎兄塞外》等。上文所提的午梦堂家族闺秀词人也不乏和家中兄弟有词作来往,沈宜修写给母家弟弟沈自炳多首词作如《更漏子·寄弟君晦》《瑶池宴·和弟君晦韵》《风入松·思弟君晦》《临江仙·对雪忆君晦寄六妹》《桃源忆故人·寄君晦》等。
以上唱和和交游之类词作是帮助她们词作走出家庭对外传播的方式之一,但是被收录后结集成册的书册是她们作品被保存下来可以“存史”的更佳方式。
(二)书册传播
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以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为主。明代中后期以来,印刷术和印刷行业发展,大大推动了词的书册传播,出版业的繁荣也进一步让词的传播从通过传唱传播到案头传播。词逐渐脱离演唱现场而走向案头化。书册的传播对于明末清初闺秀词的传播方面,主要体现在总集和别集上,同时名家文集中为闺秀所做的序和词评也助力了闺秀词的流传。
女性作品总集出版方面,“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20],到清代女性总集编撰依旧风行。随着对女性作品的喜爱和印刷术印刷行业的兴隆,明代中后期开始,对女性作品采集编撰的总集选集鱼贯而出。根据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与清代王士禄的《然脂集例》可知,明代女性诗文选集编纂工作从嘉靖万历开始,到天启崇祯年更为盛行。被载录在籍的有以下带有“彤管”“女史”“名媛”词的女性选集:名字中带“彤管”的选集如:《彤管新编》《彤管遗编》《新刻彤管摘奇》;带“女史”的选集:《诗女史》《古今女史》;带“名媛”的选集,如:《古今名媛彙诗》《名媛诗归》《名媛玑囊》,带有地域性质的女性选集《娄江名媛诗集钞》。青楼名妓诗文选集如《青楼韵语》《青泥莲花记》。此外还有《女骚》《玉薹文菀》《续玉薹文菀》《伊人思》等。这些选集在伦理身份上对名媛与名妓尽收,“名媛”代表私域的闺秀与公域“名妓”这两种鲜明的才女身份是明代才女们文集的重要分类。到清代,《燃脂集例》中的《缘起》提到晚明出版女性“故明以来颇有数家……《名媛诗归》一书,虽略备古今,似出坊贾射利所为,收采猥杂。”[21]所以相对于明代,清代女性总集不一定是商贾的获利之目的,不少为非盈利甚至官方编撰,比如一些御选词选。清三百年间,相对于名妓的文学,闺秀文学更日臻鼎盛,加上来自官方的奖掖和鼓励,闺秀总集的编选也远超前代。全国性选集有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珲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汪启淑之《撷芳集》、徐乃昌之《小檀奕汇刻百家闺秀词》,地方性闺秀选集如梁章拒《闽川闺秀诗话》等。
别集,是收录某个作家的全部或者部分作品的图书类别,属于古代图书分类法中集部的子目。[22]明代中后期开始到整个清代,闺秀别集的整理编撰成风。明末清初的闺秀词人别集的编撰支持大都来自家人。因为印刷术的发展,刻书事业也随之兴盛,个人文集别集较容易印刷,女性别集的刊刻在明代中后期开始逐渐繁荣。这种繁荣当然离不开女性文人自身在写作上的努力和参与传播,更离不开当时男性文人,他们对于促进女性文学传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对于闺秀词人,她们别集的刊刻和词作的传播的支持自然来自家族的父兄、夫婿和子女的帮助,此外家族外的文人也给予一定支持。别集的编撰常常是丈夫帮忙收集编撰妻子的文稿,父亲替爱女、兄弟为姐妹收集并刊刻她的个人文集,儿子也可以给母亲整理文集,不论是何种形式,在家族男性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有更多家族女性文人的作品被保存下来。明中后期受到夫君帮助整理个人文集的闺秀不胜枚举,如明末闺秀词人沈宜修(叶绍袁妻),陆卿子(赵宦光妻)等。她们的别集有些被当做“附刻”附在其夫文集之后,或被收录“家集本”别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吴江叶绍袁家庭的别集《午梦堂集》,本书收录了妻子沈宜修的《鹂吹集》《愁言》《伊人思》,长女叶纨纨的《愁言》,次女叶小纨的《鸳鸯梦》和三女叶小鸾的《返生香》等。为何家族要支持家族女性成员的别集出版,在第一章分析过家中的才媛也负担起家中的教育责任,即母教。有知识的女性是家族的引以自豪的文化资本和骄傲,这也是家族男性为家族女性刊刻作品出版传播的目的。正如高彦颐所说:“家庭资助妇女作品的出版,一面将才女视为家庭的骄傲,使其才华融进家庭文化资本中;一面也透露家族对女性才学的栽培与支持,进而透过这类作品的刊印与赠送,对于提高并群固家族的社会名望与人际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帮助。”[23]
值得一提的是,书册传播中,来自家族外的名人支持是闺秀词人作品传播的重要助力。名家的推荐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助力。闺秀词人的个人文集常请文坛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作序,如朱中楣的文集由“钱牧斋宗伯、李海公序”(即钱谦益、及其夫李元鼎);陈璘文集《藕花庄集》由王烟客太常作序(即王时敏)。丁瑜《皆绿轩集》由钱塘毛稚黄、孙宇台两征君序(毛先谦、孙治);季娴文集由钱塘陆云龙序;商景徽的文集由词坛名家陈迦陵序(陈维崧)。《乐集》中黄媛介文集《湖上草》由虞山钱宗伯作序(钱谦益)。除作序外,明末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陈维崧、毛奇龄等,都通过他们所做的词评对闺秀词予以鼓励,他们为闺秀作品命名、题序、品题。他们也在自己所编的诗话词话中对闺秀词记载和评论,如吴伟业《梅村诗话》、毛奇龄《西河诗话》、袁枚《随园诗话》等。到清代,闺秀文人也开始尝试写诗话词话,助力闺秀词的传播。这些词话对闺秀词起了“存人、存词、存事”的作用,在传词方面对闺秀词的保存和传播发挥了非常有效的助力,帮助闺秀词在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有效地传播。
(三)存史留念:地方志对闺秀才女的记录
除了总集别集之外,地方志里对闺秀才媛的记录也是闺秀词人词作保存流传的重要方式。
刊刻于清代中期(乾隆年间)的《绍兴府志》就有明末清初闺秀词人王端淑的小传“幼聪颖,喜读书,稍长益酣史传,古大家,工于诗,能临池,亦间游戏水墨诗,则标新探奥,敌体沈宋,其论断古人处,绝似龙门,毫无儿女口角”[24]康熙年刊刻的《杭州府志》也记录明末清初闺秀词人顾若璞,记录她用她的才能和知识在丈夫去世后撑起书香门第的重担:抚养子女发挥母教为子女授课“遗孤长者八岁,次者六岁,每从外傅入,辄为陈说诗书及秦汉百家言命之”[25],所以一家可以“炳乎于班氏同风”。在此地方志对顾若璞的记录中,对她的知识才能是赞颂的态度,无独有偶,对梁孟昭也是同样推崇。地方志记录她逝后不久便得到“孝慧女史梁氏之墓”这个称号。这种墓志有“慧”“女史”这种对知识女性的肯定之词。
存人外,地方志也有存诗词作品和存句作用,有些地方志在通过小传介绍才女的同时也对她的一些名句有所记录。比如这类记录:“张贞,字拾翠山人,庠生周树声室,二子一女皆能诗。家虽赤贫,唱和自若,句如‘鸟到春深娇韵减,人从病后道心多。麦晨糊饼聊充午,梅水煮茶正及时。酸偏有味齑充瓮,淡自声香水在瓢。汤沸竹炉医病胃,光分绩火读残书。’清贫景况风趣哂然,能不为境况所苦。’”[26]
(四)单篇传播的其他方式:题壁、扇面等传播
诗词创作在别集总集编撰前,不少文学作品通过单篇的形式传播。单篇传播可借助于一个特定的载体,比如题壁石刻书画等。
题壁是古代诗词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特别是针对单篇传播。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中就对题壁传播有所论述。王兆鹏认为石刻传播有其优势,毕竟口头传播(演唱、传诵等)受着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不仅容易传讹致误,而且容易失传。手抄传写,不仅费时费力,传播速度也相对较慢。题壁的诗词可以吸引过往行人自行拓印、传写。[27]明末清初的闺秀词人作品亦有通过题壁传播的。比如收录明末清初女性词人词作的选本《众香词》的凡例中就记录对这类单篇词作的收录:“或壁间、扇面、马上、墙头摭拾,若句调不工,平仄不肘,姑存其人以广大意。”此说明词选编者会收录在壁间、扇面、马上、墙头等地方的词作,即使不合格律的标准,甚至是艺术水平不高之作,编者都将这些词采选至选本中,以保存这些女词人的作品,所谓存其人。以此说明,题壁扇面是明末清初词作传播的重要途径。本选本中收录题壁词有尹氏《离亭燕·题润州鲍集店壁》、书集杨毓贞《如梦令·题羊留村壁》和王素音《减字木兰花》。尹氏的小传中也引了她叙说婚姻不幸借旅馆题壁写诗抒发情感的自序之言:“夫也不良,谁知煮鹤。既入宫而被姑……兹者随夫薄霞,弃女遐征,北望黄沙,闻道雄关百二。西连白草,愁瞻玉塞三千。金屋谁娇,长门有怨。马上琵琶,同昭君之远适,扇头鹭凤,叹捷好之弃捐。……独因旅宿,聊写愁怀。”[28]
出现在扇面画像等图画上的作品在明末清初也是不胜枚举,如明末词人张琮题汗巾词《满庭芳·题柴季娴姨母书回文汗巾》,此词是她赠姨母柴静仪汗巾之作,属交游书信赠作之类,亦体现题画词的交游社交传播功能。还有题画词方面,明末清初闺秀喜欢题咏画像,比如有不少闺秀都有专门题咏明末清初名妓陈素素画像的词如商景徽《月中行·题陈素素像》、王端淑《秦楼月·题陈素素像》、顾似《虞美人·题陈素素像》、商彩《巫山一段云·题陈素素像》、叶子眉《阮郎归·题陈素素像》。
三、结语
不同于青楼词人和歌妓们可以在公共空间演唱、题词、唱和或吟咏推动词作传播,出身文化家庭的闺秀们通过和家人们在家庭内吟咏和书信往来传播。她们的单篇词作或个人文集,或通过家人收集整理,或被当时文化名流们选入词选中刊印出版并辅以作序词评推荐等帮助闺秀词最终流传后世。除这些途径外,地方志对才女的收录,存人存作,也帮助闺秀词的保存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