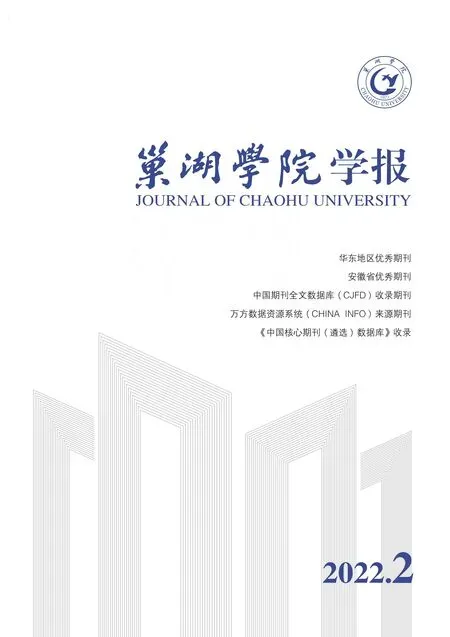复调合声与边缘重构
——《刑前一课》中边缘性的探讨
2022-03-17李向云
李向云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引言
《刑前一课》是非裔黑人作家盖恩斯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发表于1993年,奠定了盖恩斯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故事讲述了黑人杰斐逊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判电刑,而后社区为了让其有尊严地赴死,展开了一系列拯救其灵魂的行动。对于盖恩斯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盖恩斯笔下对于黑人男性气概的塑造。凯斯·克拉克[1]、威廉·T·马伦[2]、隋红升[3]等学者以男性气概为研究总基调,从性别、父与子的关系、黑人身份、宗教、社区意识和历史等方面深入剖析了黑人男性气概的危机以及建构路径,形成了盖恩斯作品中对男性气概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中,社区作为黑人成长的港湾,也是众多作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杰克·希克斯[4]、杰弗瑞·J.福克斯[5]、刘晓燕[6]等学者指出社区对于黑人个体与集体的意义,以及建构新型黑人社区的重要性。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都遵守了“危机—建构”的基本模式,但是没有分析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不论是黑人男性气概还是社区意识的书写,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征。男性气概的施展场所和社区的建构都是基于盖恩斯对于黑人所处边缘状态的承认。这种边缘状态既具有地理位置的社会边缘性,也具有心理结构的边缘性。但盖恩斯并没有以“抗议”的形式向“中心”进攻,而是思考在边缘处境中的救赎方式。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我不能呼吸”再次唤醒了黑人痛苦的记忆,意识到种族歧视从未离去,黑人依然生活在法制和社会的边缘。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边缘状态一直是过去、现在、甚至是在未来都有可能存在的状态,而对于边缘状态和边缘人物一直秉持消极的态度并不利于族裔问题的解决。因而,对边缘性的重新认知和书写对族裔问题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中通过叙事技巧体现了对于后现代语境中黑人种族边缘性的认知。《刑前一课》中言简意赅的直接引语占据了大部分篇幅,不仅让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展开交流,也使得读者可以直接听到不同人物的心声。这些声音表达着各自的观点和价值,不论是书中的女性,还是将死之人,作者都赋予他们平等的话语权。此外,小说结构之间、视角之间也存在对话性,使得全书整体贯通,一气呵成。通过对话,盖恩斯赋予这些人物主体性来作用于边缘性,这也意味着后现代时期少数族裔作者对于边缘性认知的转变:边缘的社会性状态会一直存在,少数族裔不应该以突破边缘为最终目的,而是接受边缘,在边缘中积极作为,发挥边缘的优势。
一、理论阐释:复调理论与对话书写
复调原本是音乐学中的一个概念,指两个或几个旋律同时结合,从而丰富音乐形象,加强音乐发展的气势和声部的独立性,造成前呼后应、此起彼伏的效果[7]。巴赫金借用音乐学中的复调来解析小说,形成了复调理论。利用复调概念强调小说是一个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世界。
(一)理论背景
复调理论指“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保持各自的独立,这种独立性又保持在一个统一体中,形成比单声结构更高一层的统一体。”[8]巴赫金认为,小说中存在独享权威的“I”使得小说中其他人物不能享有同等权利,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可以自如地应对这一现象。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成功地允许他笔下的人物具有“我(I)”的地位,对抗其他有权威的声音。巴赫金创造了“复调”这一特殊术语来形容这一现象[9]。
复调主义的核心之一是对话主义。复调的存在可以避免小说中一家独言的情况,也使得小说中众多意识能在思想观点方面相互作用,形成多元开放的局面。这个过程也是对话实现的过程。事实上,“我”不可能完全违背另一个活着的主体,他或她也不可能完全违背“我”。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局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8]。此外,巴赫金也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对话的重要性:“任何人都处在唯一不可重复的位置上,任何存在都是唯一性的。‘我’在时空位置上的唯一性存在形成了‘我’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我’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内核,是‘我’之为‘我’的个性,是‘我’的人生尊严和价值基础,有了它就能发出独一无二的声音,就有了和他人对话交际的资格。”[10]
需要注意的是对话性不仅包括引号所覆盖的内容,还包括小说在结构、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对话。由于对话的存在,看似貌合神离的小说会在实质上紧密联系,浑然一体。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他将对话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微型对话在大型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大型对话因微型对话的存在而更加深刻,因此,在分析文本的时候,两者缺一不可。
(二)《刑前一课》中的复调现象
复调意味着以对话的方式使人物认识其主体,这对族裔文学至关重要。一直以来,主流文化的小说家允许从属阶级的声音进入自己的文本,经过各种声音的对话和协商,最终产生出符合自己文本的意义,从而巩固自己的文本地位[11]。少数族裔的声音被主流社会的声音所淹没。因此将复调理论带入族裔文学的研究,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地与少数族裔进行对话。《刑前一课》无论是从叙事的结构、人物的关系还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对话,都呈现出复调思维,读者能够跟随主人公与作品中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人物进行对话,既从宏观也从微观层面了解族裔的生活。
从宏观而言,文章在结构和视角上体现出对话性。历史的记忆与当前的经历一直处于对话互动之中,黑人记忆中的残酷并没有随着黑人解放运动而消解,历史似乎演变成当下的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这种互动对话性体现了黑人边缘的状态。此外,即使在黑人民族的内部,女性与男性,不同阶级之间的男性也存在的地位不平等,使得“话语权”生效,人物之间的对位关系由此而来,强化了边缘的张力。从微观而言,故事中的几个人物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他们的认知各不相同。盖恩斯要做的就是让每个人物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让故事的真相以及黑人生活的境遇在一步步的讲述中真实起来:黑人民族的社会性边缘状态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黑人应对边缘性的态度发生转变。整部小说,对话一直持续,交叉进行。从这个层面上看,《刑前一课》无论是从叙事层面、人物关系还是人物间的微型对话上,都有独立而不相容的意识和声音,它们在小说中呈现、对话、冲突和交流,具备了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复调小说使每个人物意识到他们都有发言的权利,从而有利于打破主流社会的话语权威,有利于少数族裔表达自我,为少数族裔的权利抗争。
二、大型对话:黑人民族的“边缘”记忆
盖恩斯在《刑前一课》中巧妙地利用大型对话的形式,揭示黑人历史处境与当下环境中的边缘性状态。在复调理论中,巴赫金指出:“小说内部和各部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被当做‘大型对话’来结构”[12]。也就是说,大型对话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论述小说中的对话性,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它不像人物之间的对白那么直白,但却使各个部分之间前后呼应,形成潜在对话,使得小说紧密连接。大型对话体现在两个方面:结构上的对话性和人物关系上的对话性。结构上的对话性包括叙事视角的对话性、小说时空的变换;人物关系上的对话性主要指人物关系之间的对位性。作者利用大型对话从宏观角度揭开黑人种族的边缘记忆。
(一)时空的边缘性:叙事时间与空间的边缘性体现
小说叙述中时空体的变化属于大型对话的范畴。叙述时间的变化不仅是交代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也是人物对于事件重要性的认知。在《刑前一课》中,作者无论是在叙述时间,还是叙述空间的转变上,都可以体现黑人民族的边缘生存环境。
从小说叙述的时间来看,整个故事采用倒叙的方式进行。倒叙是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实践的一切事后陈述[13]。此外,作者在倒叙的回忆中又不断切换人物视角,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人物各自的经历,使得情节在叙述视角的变换中不断深化。小说是以倒叙的形式讲述的,但是,直到故事的结尾,读者才会意识到这一点。作者开篇写到:“我没去那,可我又在现场”,既是对于审判现场叙述者本身状态的描述,也是对于结尾叙述者状态的描述。因为,在审判现场,叙述者(格兰特)虽然身在审判现场,但是由于已经熟知了黑人罪犯的结局,所以他对于后面所有的事件都心不在焉;而在结尾的电刑现场,叙述者(格兰特)并没有出现,但是他的心却是被电刑现场的杰斐逊紧紧吸引着。从这个层面上看,开篇的话语表现出双层含义,既自然而然引出了下文法庭的叙述,又与结尾呼应。这样的开篇,突破倒叙模式的传统叙事方式。读者只有读到故事的结尾,格兰特最终流下眼泪时,方才发觉叙述在进行倒叙。虽然文章下文大体上采纳了符合时间顺序的布局,但是这个总体的方法不排除细节上大量倒叙的存在。
热奈特将倒叙分为外倒叙和内倒叙。如果将上下文称作第一叙事,那么任何时间倒错与它插入其中、嫁接其上的叙事相比构成一个时间上的第二叙事,在某种叙事结构中从属于第一叙事[13]。外倒叙则是指整个时间的范围在第一叙事之外,反之则为内倒叙,它处于第一叙事的时间场内。而在《刑前一课》中,盖恩斯的倒叙中大部分采用了外倒叙的手法,只有一处使用了内倒叙。笔者粗略地区分出8处外倒叙的叙述部分,它们分别分布在6个时间位置上,这些位置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祖辈、父辈岁月里男性的缺失;
(2)格兰特的童年时代(在亨利家的厨房时期);
(3)格兰特的拉大锯、抡大斧的童年时光和杰斐逊的童年;
(4)薇薇安大学里的爱情和格兰特的大学时光;
(5)格兰特外出求学期间探望启蒙老师;
(6)1942启蒙老师逝世;
(7)1948-04-08杰斐逊的死亡(内倒叙)
(1)至(6)的时间段属于外倒叙,不在第一叙事之中,它对于第一叙事起到补充作用。(7)属于内倒叙,在第一叙事的范围之中,之所以将这一个时间段与前面的6处时间位置放到一起,是为了说明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外倒叙和内倒叙作严格划分,也就是说这样的倒叙属于开放性的倒叙,读者很难找到叙述者结束倒叙的时间点,也就使得作品中时间段的划分不那么明显,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主题。纵观这些时间段,时间范围从奴隶制到南北战争后直至小说创作背景的当下,作者将“过去”与“现在”结合,甚至把“未来”也包含在内,“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段区分,因而使得主题上没有时间的区分。黑人父性的缺失、黑人教育的受限以及黑人司法、工作等不平等的问题既属于过去,也存在于当下,甚至会在未来持续上演,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黑人依然活在种族压迫的边缘地带。作者在倒叙中故意以开放性倒叙来讲述故事,体现了“过去”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甚至在“将来”也会一直存在,而白人为黑人所缔造的神话也不过是谎言而已。
倒叙的选择不仅是情节的需要,也是作者对于边缘性的认知。倒叙是叙述者的回忆。而在这些回忆中,纵观全部的叙事内容,都是对于处在种族压迫之下的黑人境遇的描写,有知识分子受到的排挤,有黑人逃离社区的回忆,有黑人无辜被处死的回忆,如此种种。对于这些回忆,叙述者一直没有书写可以走出边缘的方式。倒叙的主基调与顺序的主基调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对于黑人生存状态的无奈。故事如果以顺序的方式进行,读者或许可以等到案件最后的转机,因为对于未来的事情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在倒叙之中,对于案件的结果是没有期待的,结果最先被告知。
此外,对于空间的选择,作者也十分用心,并在叙述中采用移步换景的方式。小说中涉及到的主要空间有监狱、艾玛的厨房和学校,这三个带有象征意味的空间经常产生对话。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首次提出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区别。“故事空间”指故事发生的地点;而“话语空间”指叙述行为发生的空间。在《刑前一课》中,可以看到格兰特的叙述是随着故事空间的变化在不断发生变换。这里的故事空间不仅是构成小说人物行动的空间,也暗指黑人活动空间的边缘性。监狱是与杰斐逊谈话的主要地点;厨房是黑人群体聚集商量要事的地方;学校是黑人小孩受教育的地方。在这三个空间中,监狱和学校都属于白人的权力范围,黑人并没有话语权;只有厨房是黑人能够畅所欲言、表达观点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商量如何拯救杰斐逊、如何举行圣诞,厨房成为黑人实施话语权的重要场所。而厨房,一般而言,是女性专有的场所,是私密的场所,在《刑前一课》中,却成为黑人社区公开的话语场所。作者通过这三者之间的对话性暗指:尽管黑人运动取得一些成绩,但整体而言黑人的生存空间处在边缘地带。将黑人的生存空间与女性的生存空间等同,是对于黑人边缘性地位无力改变的认同。
(二)人物的边缘性:黑人男性的多重边缘身份
人物的边缘性主要通过人物关系来体现。大型对话之中,人物的关系通过“对位”来体现。“对位”也是音乐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各个声部之间都参与奏乐,且各自的作用都无法代替,也就说明对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参与交流的关系。巴赫金将对位的隐喻关系用到小说中,肯定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发言都具有价值和意义,将每一个人物都赋予了主体性意义。进入对位状态,意味着对话参与者均具备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意识”,促成了故事中人物关系的对话和交流。反之,人物关系未进入对位状态,则说明人物地位的不平等。在《刑前一课》中,黑人男性的边缘性即通过对位的失败体现出来,这种失败表现在代际交流和种族交流之中。
在代际层面,主要是老年女性和黑人青年男性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老年女性掌握了社区的话语权,而黑人男性则处于边缘地位。艾玛等老年黑人女性既是社区的守护者、年轻一代的培育者,也是黑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黑人男性无论是格兰特还是杰斐逊,则并没有表现出对于社区、种族和文化的责任感。格兰特想着逃离,对于黑人的教育应付了事;杰斐逊教育程度低,所从事的工作都无法满足自己的温饱,和他一样的同龄人背井离乡,也无一点音讯。寥寥数语揭示出黑人社区之中男性的缺乏。而黑人男性对于社区、传统文化也并没有责任心,黑人社区的存续由女性来负责,这在拯救杰斐逊的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灵魂对于一个民族至关重要,拯救灵魂的过程中格兰特作为知识分子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但是格兰特的初始行动是极不情愿的,是由艾玛教母和姨姥一手促成,包括与牧师的合力相助,都离不开艾玛的积极奔走。我们可以在第一次探监的情景中看出格兰特的消极态度。第一次探监中,艾玛教母的对话轮次有10次,而且都为艾玛主动发起对话。但是每一次的对话杰斐逊都没有回复。前8轮对话都是艾玛对于狱中杰斐逊的问候,杰斐逊没有回答;而后两轮对话中,艾玛教母的对话指向了格兰特,但无论是杰斐逊还是格兰特,对此都没有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在这10次话语中,艾玛教母收到的都是零回复或无效回复。而格兰特和杰斐逊的话语轮次在初次探监的时候共有3轮,值得注意的是在杰斐逊和格兰特短短的话语轮次中,杰斐逊是最先发起话语的人,而且在话语中带有逼问格兰特的意味,格兰特的两次回答都显得被动而冷漠,没有了之前教母话语中的关爱与柔情,甚至在最后一轮话语中,由于教母的打断,格兰特都没有参与进来。这与格兰特一开始对于拯救杰斐逊灵魂的态度是一致的:拒绝,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的,也是对于自己责任的无视和规避。在这种情景下,我们看到的是代际之间对位的失衡,老年女性在积极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年轻的一代却是被迫“对话”,并没有自己的主动性,黑人青年男性因此成为社区的边缘人物。
此外,在种族关系层面,黑人种族也是处于边缘地位,不受白人社会的接纳,这对于格兰特和启蒙教师尤为明显。格兰特和启蒙教师都是黑人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可以作为融入白人社会的一种途径。但是,格兰特第一次去亨利家是从无人问津的后门进入,然后被安排在厨房被迫等待两小时,可知这样的身份并没有改变白人对于他们的歧视;而在黑人社区,受宗主国文化的影响,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14],接受了白人教育的格兰特和启蒙教师都曾尝试逃离黑人社区,认为“抛弃自己的黑肤色,便越是白人”[14],而结果却使他们处在白人与黑人文化以及社会的边缘地带。
从时空的选择和人物关系的塑造上,作者意在表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看黑人边缘性的生存状态依然存在。而在边缘固化的世界里,想要打破这样的平衡非常困难。所以盖恩斯从宏观的角度肯定了边缘永续存在的状态,继而从微观的对话中来分析个体态度改变的重要性。
三、微型对话:个体的边缘体验
微型对话是在大型对话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微型对话指对话向内部深入,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之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之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这已经就是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风格特色的“微型对话”[12]。微型对话通过渗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从微观程度揭示人物的内心以及心理状态。微型对话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主人公与他人的对话和主人公与环境的对话。《刑前一课》中,以格兰特为主人公向外辐射,他和周围的关系以及对于自身边缘状态的认知展现在他与不同声音的对话之中。
(一)边缘的中心:个体与自我的对话
在《刑前一课》中,作者设置了诸多主人公(格兰特)内心独白的场景,让读者能够紧跟格兰特的思想。通过内心独白,我们看到格兰特循序渐进的自我认知:从对儿时伙伴客观的独白对话,最后回到自己对于刑场上杰斐逊的紧张状态中。当格兰特倚着篱笆墙看学生砍柴时,他脑海中回忆起了自己儿时的小伙伴:
他们也曾在这里劈柴。毕业后,有的同学到乡下种地去了,有的同学到小镇去了,有的到大城市去了,呆在一个地方直到生命的结束。不断有消息传来,某个黑人被杀死了呀,某个黑人因杀人而坐牢了呀。斯洛波尔,在艾伦港口的酒吧被人捅死了;克劳迪,在新奥尔良被一名黑人妇女杀死了;斯密特,因杀人被关押在安哥拉州立监狱了。其他人呆在家乡,慢慢消磨时光,等死而已。[15]
读者很难从格兰特的独白中读出对于儿时伙伴们的情感:对于他们的死亡,格兰特是否有过痛彻心扉的感觉?格兰特此时的独白略显客观,将悲惨的黑人生活以平淡的文字写了出来,读者很难在文字中感受到格兰特的温暖,像是在没有感情地读一则则远方传来的死亡讯息。这时候的格兰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这些外出的伙伴同呼吸、共命运,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社区的责任以及主体意识,他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在观看。
而到了小说结尾,格兰特在拯救杰斐逊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与所有的同胞心相连、共命运,他和每一个社区的黑人一样,应该对这个社区负有责任。在第31章中,格兰特的内心独白达到高潮。也是从他的内心独白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于同胞牺牲的惋惜。在杰斐逊被执行电刑的当天,格兰特没有勇气去刑场,安排好本校学生的祈福活动后来到教室外的坝子,仰望苍天,思绪万千。他既想知道刑场的情况,又想回避这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时刻他在哪里?在窗边,瞭望天空吗?还是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灰色的天花板呢?还是站在牢房门口,正在等待?他的感觉怎么样?他害怕了吗?他在哭吗?这个时刻,他们来把他带离牢房吗?他跪在地上,在哀求多活一分钟吗?他是站着的吗?我为什么不在那里?我为什么不站在他身边?我为什么不和他手挽着手?为什么?[15]
这一段独白中,格兰特内心的情感十分丰富,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格兰特对于杰斐逊的情感,他把自己与杰斐逊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杰斐逊的死亡也意味着自己一部分的死亡。这时的格兰特,不再是社区的旁观者,也不再因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排斥杰斐逊,他甚至将杰斐逊当作真正的民族英雄,因为他最后有尊严地赴死。他不再排斥这样的边缘社区,而是将自己作为边缘的一份子,接纳边缘,改造边缘。
(二)边缘的互动:个体与他人的对话
主体的发展与成长,离不开客体的帮助。巴赫金指出:“我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掌握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过他人的。这是由在世界上唯一不可替代的位置决定的:因为此时此刻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唯有我一个人处于这样的位置上。所有他人全在我身外。因而相对于‘他人之我’而言,他人所看到的也总有一部分超出我的视域。”巴赫金从“他人之我”的视角肯定了“他人”存在的必然性,也就肯定了与他人对话的必要性,由此看来,对话成为个体所在的必要条件[11]。
小说中,格兰特与其他人物的对话也不断促成其对于社区的接纳和对边缘的承认。小说伊始,格兰特在拒绝艾玛拯救杰斐逊的同时,也在策划着逃离这个黑人社区,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他应该去到北方的城市,应该与白人一起生活。格兰特对薇薇安说:“我想去一个能稍稍激发我活力的地方,我不想在这里过苟且偷生的生活,教一辈子窝囊书,终老农场小教堂。我想陪伴在你的左右,呼吸自由的空气,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这里,我感觉不到一点生命力,我成了一具行尸走肉。”[15]
在格兰特的描述中,黑人社区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的,他在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都在苟且偷生。这意味着,作为黑人教师的职业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在这里约束太多,周围的一切(除了薇薇安),都是枷锁,姨母与艾玛、牧师、学生以及白人;这里的人生道路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由他人控制的。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格兰特的厌恶之情。
但是在后续与不同人物的对话中,格兰特慢慢消解了自己内心的厌恶感。薇薇安告诉他:“我们是老师,职责所系,不能一走了之。”[15]在与艾玛和姨母等老人的对话中,格兰特渐渐感受到老人对于社区的情感和责任以及自己对于社区的责任,正如他所言“我不能弃危难中的艾玛小姐于不顾”,格兰特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了;在与牧师的对话中,牧师告诉他,“能够认清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认清自己意味着认清社区和黑人的真实处境,承担起自己身上的担子。在与杰斐逊的对话中,他不仅告诉杰斐逊白人神话是谎言所在,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言说,自己曾以白人文化为标准是错误的认知,黑人应该以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为榜样。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格兰特从一个旁观者成为了社区的参与者,深知自己作为男性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责任将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联系在一起,让“我”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成为一个主体就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实现生存谋划。因此个体在履行责任的时候,也是个体在确立自身的主体性[16]。
(三)边缘的优势:个体与环境的对话
个体与环境的对话在《刑前一课》中体现在叙述者与黑人社区的对话之中。格兰特与社区的对话体现出一种由厌恶到接纳、由悲观消极到主观能动的历程。对于黑人社区,格兰特最初表现出想要逃离的态度,他好几次和薇薇安表明心声:想逃离这里,想去真正属于他的地方。虽然作品中没有透露他想去哪里,但是根据格兰特的表述以及他对于黑人同伴的描述,笔者推断格兰特向往北方的城市。在与启蒙老师的对话中,更是表达出对于黑人社区的厌恶感。正如启蒙老师所言,生活在黑人社区,是没有“人生”可言的,剩下的只是“黑奴生活”,这样的字眼是永远的标签。因此格兰特在环境中的演绎是消极被动的。
转机发生在拯救杰斐逊时,拯救的过程是格兰特与社区不断互动的过程。作为黑人社区的知识分子,艾玛教母将拯救杰斐逊灵魂的大事件交给格兰特,这是对于格兰特黑人地位的一种承认,也是格兰特施展能力的场所。通过拯救,格兰特也渐渐认识到,黑人社区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大家齐心协力,黑人地位的改变才有所期待,这使格兰特重新反思黑人社区存在的合理性及意义。他想到那些逃离了南方社区的伙伴,大部分杳无音讯,消失在了他们所向往的北方。因此,对于黑人而言,逃出南方亦或是南方社区而在北方拥有一席之地,似乎是件比较艰难的事情,不如将目光收回到南方社区,将这里视作改变与反抗的地方。作品结尾,作者看到阳光下的村落,蓝天如洗,初日如金,这展现了作者心态的变化,是对社区的一种认同与回归,是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在欣赏社区。正如蓓尔·瑚克斯在结合自己的种族身份和女性身份对“边缘性”给出自己的见解一样:“我所说的边缘性不是要丢开、放弃的东西而是要在其中逗留、坚持使之平衡……对被压迫、被剥削、被殖民的人民来说,认识到边缘乃反抗之所非常重要……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17]在谈到边缘的优势时,她指出:“我们既从外面往里看,又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关注边缘也关注中心。我们二者都了解”[18]。因此,边缘中的人物要认识到其主体性,也要将边缘视作一个创造性的场所,并鼓励身处边缘的人进行创造。在这个层面,少数族裔可将边缘视作脱离统治意识形态而进行反抗的场所。
主人公代表个体在和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同理,其他人物也在对话的基础上表达观点,重拾自己的主体意识。黑人对于边缘的认知不再报以“逃出边缘”的极端反抗态度,相反是留在边缘地区,承认自己的边缘地位,重新将边缘作为自己的成长的场所,在边缘中积极反抗。
四、结语
对话作为研究文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案之一,不仅是人物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体现。人物间如何发起对话,如何使对话正常进行,得到问话者的答案,都是一门学问。此外,文学作品中的对话,不是一种面对面及时性的对话,而是一场面向大众,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对话,它受时间的限制相对较小。这种文学中的对话不仅局限于人物之间的对白,也包括作品结构和人物之间的一种对话性。在 《刑前一课》中,就作品结构、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与个体的独白形成对话性,让读者伴随着阅读揭开南方黑人生活的诸多问题,其中,边缘性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而盖恩斯利用对话表明,社会大环境中的边缘性依然存在且难以根除,因此,借主人公的话语表达出接纳边缘,重新认识边缘,意识到边缘可以作为黑人自己的反抗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