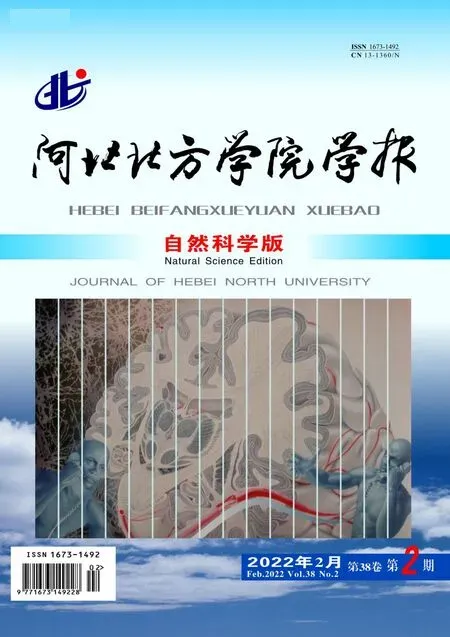CLK与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2022-03-17司文英孟宪勇董晓华
司文英,孟宪勇,董晓华
(1.河北北方学院药学系,河北省神经药理学重点实验室,河北 张家口 075000;2.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CLK家族是一组进化上保守的双特异性激酶,能够磷酸化丝氨酸、苏氨酸和酪氨酸残基上的蛋白底物,改变蛋白质底物的生理特性,从而在信号转导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CLK通过对富含丝氨酸和精氨酸(serine-and arginine-rich,SR)结构域的蛋白进行磷酸化,调控pre-mRNA的选择性剪接。异常磷酸化与许多人类疾病有关,近年来研究表明CLK与病毒感染、肿瘤、药物成瘾及神经系统疾病密切相关,现对CLK在抗病毒、抗肿瘤、药物成瘾以及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1 CLK家族的生理功能
CLK属于蛋白质激酶的一个小亚家族,包括CLK1、CLK2、CLK3和CLK4。最初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发现了CLK1基因,认为它是一种与长寿相关的基因,在秀丽隐杆线虫体内CLK1突变会使其寿命延长。CLK1在包括人类在内的真核生物中是保守的,其结构与酵母代谢调节剂Cat5p/Coq7p相似,CLK1突变体寿命延长可能是其细胞代谢减慢的结果[1]。已有研究通过广泛的自磷酸化证实CLK1和CLK3的激酶结构域在大肠杆菌中以活性形式表达。CLK1和CLK3的催化结构域呈现典型的蛋白激酶折叠,C端展示了一种独特而保守的“EHLAMMERILG”特征基序,CLK也因此被称为“LAMMER”激酶[2]。人类CLK基因由13个外显子组成,可选择性剪接表达全长或缺失催化结构域的截短蛋白。至少有两种剪接机制可导致截短的CLK1表达:外显子4的跳跃和内含子保留。CLK1的N端截断导致CLK1酶活性急剧增加,表明N端起负调控作用[3-4]。
CLK1在细胞周期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5],CLK2参与褐色脂肪组织中饮食诱导的产热控制,是肝脏糖异生的抑制因子,而CLK3在成熟精子中大量表达,可能在受精过程中发挥作用。此外,CLK对生理温度变化的敏感性是由激酶激活片段内的结构重排所赋予的[6]。CLK作为体温传感器,全局控制选择性剪接和基因表达。CLK的C端激酶结构域本身对温度敏感,并且该特征在不同哺乳动物中保持不变。
2 CLK与病毒感染
流感病毒感染会造成季节性流行病和反复发生的大流行,对全球公共健康构成威胁。流感病毒属于正黏病毒科,其核蛋白(nucleoprotein,NP)和基质蛋白M1的抗原差异使流感病毒可以分为A型、B型和C型。A型病毒进一步分型基于血凝素(hemagglutinin,HA)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NA)表面糖蛋白的抗原性。病毒的高突变率促进了其突变体的产生,使得针对病毒编码目标的疫苗和药物可能无效。相反,将宿主细胞决定因子作为目标,可以防止病毒逃逸。已有研究证实CLK1是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在体外和体内成功复制所必需的[7]。CLK1的选择性剪接丰富了基因组和蛋白质组调控网络中涉及的多种蛋白质异构体的结构和功能变异性。流感病毒利用宿主RNA加工机制启动选择性剪接,使CLK1与SR蛋白的RNA识别序列结合,调控IAV M基因的剪接变体(M2)RNA的合成,从而导致蛋白质组的多样性表达[8-9]。有报道称抑制CLK1基因的表达可以使流感病毒复制减少两个数量级以上,与病毒M2 mRNA剪接受损有关[10]。因此,CLK1被认为是治疗流感病毒的潜在宿主细胞靶点。
CLK1被发现影响COS-1细胞中腺病毒E1A基因选择性剪接[11]。CLK家族成员在调控HIV-1基因表达和RNA加工中的作用不同,CLK1过表达可增加HIV-1感染的HeLa细胞中Gag蛋白的表达,而CLK2过表达则抑制Gag[12]。CLK1对基孔肯雅病毒的有效复制至关重要[13]。
3 CLK与肿瘤
3.1 CLK与神经胶质瘤的耐药性
神经胶质瘤占所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30%以上,是迄今为止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神经胶质瘤分为Ⅰ~Ⅳ级,其中胶质母细胞瘤是最具侵袭性的胶质瘤。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手术切除并辅助化疗,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成为限制其预后的最大障碍[14]。CLK1是一种线粒体酶,其表达减少会影响线粒体功能。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突变在肿瘤细胞化疗耐药性中发挥重要作用[15]。近年来有研究探索肿瘤细胞中沉默CLK1与化疗药物耐药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神经胶质瘤细胞中减少CLK1表达可以抑制AMPK的磷酸化,进而激活下游mTOR信号通路,mTOR活化后可在基因和蛋白水平上调HIF-1α,提高糖酵解能力,抑制线粒体功能,通过Bcl-2家族抑制细胞凋亡,从而使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增加[16]。
3.2 CLK与乳腺癌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也是全球女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C-myc在多种人类癌症中过表达,可调节细胞增殖、代谢和凋亡等过程,其表达与不良预后相关。Myc调控pre-mRNA剪接,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剪接调节剂作为抗癌药物,治疗Myc介导的癌症。有研究表明CLK2和Myc协同调节pre-mRNA的生物合成和剪接加工,以提高癌细胞的存活率。富含丝氨酸和精氨酸的剪接因子1(serine and arginine-rich splicing factor 1,SRSF1)是CLK的直接底物,也是Myc的直接转录靶点,能够促进乳腺上皮细胞转化。在Myc介导的乳腺癌中,一种新型口服CLK2抑制剂(T-025)可诱导外显子跳跃突变,从而导致癌细胞数量减少。相反,CLK2过表达严重影响Myc扩增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而对非Myc扩增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仅有轻微影响。CLK家族激酶在Myc驱动的乳腺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18]。
三阴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即雌激素、孕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表达均为阴性的乳腺癌。癌细胞中CLK2的缺失导致上皮向间充质转化相关基因表达上调,表明CLK2可被用于调节上皮-间充质细胞剪接模式和抑制乳腺肿瘤的生长[19]。
3.3 CLK与肝细胞癌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发病率高。与非肿瘤对照组相比,CLK3在HCC组织中明显上调,其表达水平与HCC恶性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下调CLK3表达可在体外抑制肝癌细胞生长、迁移和侵袭,在体内则抑制肿瘤发展。CLK3是miR-144的直接靶点,在HCC中miR-144的表达与CLK3的表达呈负相关。过表达miR-144可显著抑制CLK3的表达,而过表达CLK3可部分逆转miR-144对肝癌细胞生长和转移的抑制作用,表明调控CLK3的表达可用于肝癌的诊断和治疗[20]。
3.4 CLK与胆管癌
胆管癌(cholangiocarcinoma,CCA)是起源于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临床上较少见。我国胆管癌患者数量较多,因此胆管癌的研究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CCA患者CLK3表达显著上调,被认为主要与核苷酸代谢重编程有关。CLK3使USP13在Y708位点磷酸化,促进USP13与c-Myc结合,从而阻止FBXL14介导的c-Myc泛素化,激活嘌呤代谢基因的转录。CCA相关CLK3-Q607R突变体诱导USP13-Y708磷酸化并增强c-Myc活性;反之,c-Myc上调CLK3的表达。CLK3表达水平与人类CCA标本中phospho-USP13-Y708、c-Myc和嘌呤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ATIC的表达显著相关。盐酸他克林已被证实可抑制异常CLK3增强的CCA侵袭性,这为含有CLK3突变的CCA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性治疗策略[21]。
3.5 CLK与其他肿瘤
CLK2过表达可以促进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NSCLC中miR-573表达减少有关[22]。一种新型肿瘤抑制剂SM08502可通过抑制CLK的活性来降低Wnt通路基因表达,抑制胃肠道肿瘤细胞生长[23]。另一种CLK抑制剂T3可以与Bcl-xL/Bcl-2抑制剂协同作用,诱导人卵巢癌A2870细胞和直肠癌HCT116细胞凋亡,使CLK抑制剂联合Bcl-xL/Bcl-2抑制剂为癌症治疗新选择[24]。此外,CLK还与胰腺癌、前列腺癌有关。
4 CLK与药物成瘾
药物成瘾是一种强迫性用药的疾病,可引起严重的公共健康和社会问题。药物成瘾与突触可塑性、奖赏机制、学习记忆、感觉和认知等领域有关。多巴胺(dopamine,DA)是大脑中参与奖赏系统的主要神经递质,在药物成瘾中发挥重要作用。多巴胺降解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酶降解,通常由单胺氧化酶介导;另一种是多巴胺通过多巴胺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DAT)跨质膜易位。钙介导的囊泡与突触前膜融合导致多巴胺释放到突触间隙,质膜DAT利用突触间隙和突触前神经元之间的离子梯度来驱动多巴胺的运输[25]。铁作为机体中一种重要的元素,参与机体诸多生理过程。机体中铁稳态受铁离子外排蛋白(ferroportin1,FPN1)调节,而铁调素(hepcidin)可以与FPN1结合,降解FPN1。CLK1的缺失可以导致线粒体呼吸链中电子传递受阻、线粒体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生成增加和HIF-1α表达上调[26-27]。HIF-1α与hepcidin结合抑制hepcidin的转录,hepcidin对FPN1的降解减少,细胞内铁离子外排增加,铁离子浓度降低可抑制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从而抑制DAT降解,因此突触间隙的DA浓度降低[28]可以抑制奖赏系统介导的药物成瘾。
5 CLK与神经系统疾病
5.1 CLK与阿尔茨海默病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也称为老年性痴呆,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表现为进行性记忆丧失、认知障碍、行为改变,并且多伴有人格改变。AD的特征性病理改变主要包括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沉积形成的老年斑(senile plaque,SP)和tau蛋白(tubulin-associated unit)过度磷酸化行成的神经细胞内神经元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AD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医疗卫生问题之一[29]。
CLK1是生物合成泛醌(ubiquinone,UQ)所必需的,UQ是线粒体电子传递链中的电子载体,此外还可以作为抗氧化剂发挥作用。Mclk1(小鼠的同源基因)的完全缺失导致小鼠死亡,但Mclk1+/-突变的小鼠寿命延长。在Mclk1+/-突变体中,线粒体外膜中的UQ越多,内膜中的UQ越少。UQ减少导致线粒体内ROS生成增多。有文献报道线粒体ROS生成增加有助于延长寿命[30]。最近几年的深入研究表明年龄是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和AD的最大危险因素。线粒体活性下降与年龄相关功能障碍的发生和进展密切相关[31]。有研究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D患者的尸检结果表明AD的病理过程中存在线粒体功能障碍[32]。综上,线粒体功能障碍可以提高生物体的适应性和存活率,超过阈值就会产生毒性,生存能力也会受到影响[33]。
AD病因尚不明确,且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有研究者在AD患者前额叶和海马的SP和NFTs中检测到大量铁离子,提示铁离子可能参与了这些病理特征的形成。氯碘羟喹(clioquinol,CQ)作为一种金属螯合剂,与铁离子螯合可阻断Aβ的聚集,还可以调控tau蛋白磷酸化的关键酶GSK-3,阻止tau蛋白过度磷酸化。此外,CQ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多种细胞和动物模型以及AD患者具有有益效果,其作用机制与抑制哺乳动物细胞中CLK1的活性有关。氯碘羟喹抑制哺乳动物中CLK1的活性,这种作用可被铁或钴离子阻断,说明螯合过程参与了CQ对CLK1的作用,但确切机制尚不清楚[34-36]。PBT2,一种基于氯碘羟喹化学结构的新型8-羟基喹啉,AD转基因小鼠模型经过11天的PBT2治疗,小鼠的认知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Ⅱa临床试验期,研究人员对78例AD患者进行了12周的PBT2治疗,发现PBT2可以降低脑脊液中的Aβ水平,且降低程度与PBT2用药量有关[34]。CLK1抑制剂氯碘羟喹及其衍生物有望成为治疗AD的潜在药物。
5.2 CLK与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以运动和非运动系统表现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特发性疾病。它是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PD的病理生理学改变包括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退化和路易小体的形成[37]。CLK1是自噬通路中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丝氨酸/苏氨酸激酶mTOR调节细胞存活和增殖,是自噬的主要负调控因子。AMPK激活调节线粒体功能维持能量平衡来保护神经元存活。CLK1可以调节AMPK/mTORC1通路,损害自噬-溶酶体通路,促进体内和体外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38]。此外有文献报道,在MPTP诱导的PD小鼠模型中减少CLK1表达后,小鼠大脑黒质部位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数量显著减少,同时发现星形胶质细胞内线粒体功能障碍,炎症反应增强,炎症因子释放增加,HIF-1α的表达上调,表明CLK1基因表达下调通过激活星形胶质细胞释放大量炎症因子,作用于周围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导致神经元变性和坏死,从而加重PD的症状[39]。因此,调节CLK1的活性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治疗PD的新方法。
6 CLK与遗传性疾病
Phelan-McDermid综合征(Phelan-McDermid syndrome,PMDS)是一种由22号染色体长臂末端缺失引起的先天性疾病,同时伴有SHANK3基因缺失,这种缺失与智力残疾和自闭症有关。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抑制丝氨酸/苏氨酸激酶CLK2可以修复SHANK3缺失的神经元突触缺陷,并且CLK2抑制剂使SHANK3基因缺陷的小鼠恢复了正常的社交能力。因此,研发新型CLK2抑制剂有望改善PMDS患者的自闭症[40]。
7 CLK与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全关节疾病,其特征为软骨退化、骨质改变和滑膜炎症,导致关节间隙狭窄、疼痛和功能丧失,是全球残疾的三大原因之一。Wnt通路抑制剂Lorecivivint可抑制CLK2介导的SR蛋白的磷酸化,抑制CLK2的表达,可促使早期软骨的形成[41];另一个Wnt通路抑制剂SM 04755对CLK2的作用导致Wnt通路受到抑制,促进细胞的分化,减轻炎症反应,作用于CLK2靶点后促使胶原酶诱导的大鼠肌腱损伤的修复[42]。因此,CLK2有望成为治疗OA和肌腱病的新靶点。
8 小 结
综上,CLK可通过调控信号转导、剪接因子与病毒感染、肿瘤、药物成瘾及神经系统等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近些年,随着CLK的分子机制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为治疗和寻找新的临床药物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CLK在神经系统疾病如AD的治疗中有很好的前景,现已有部分CLK抑制剂被证实是治疗AD的潜在药物,但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进一步了解CLK在神经系统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可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