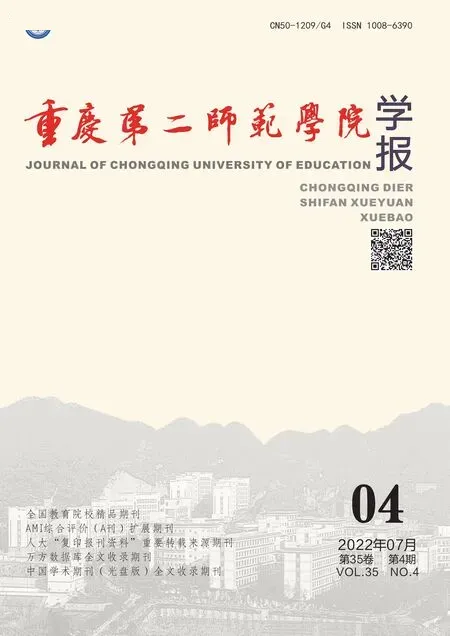《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莉莉·玛莲》女主人公的悲剧成因比较
2022-03-17钱宁
钱 宁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
享誉世界的中国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与德国电影《莉莉·玛莲》看似毫无关联,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发行于上海,1956年再版发行,由蔡楚生和郑君里编导,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主演,被赞誉为耗资巨大的“史诗影片”[1]。该片讲述了女主人公李素芬一家从抗日战争爆发到胜利这十多年的颠沛流离、生存抗争与悲剧结局。《莉莉·玛莲》发行于1981年,由德国编剧兼导演R.W.法斯宾德与M.普尔策根据该国歌唱家L.安德森的自传体小说《多彩的天空》改编,安德森演唱的流行歌曲《莉莉·玛莲》(1941年发行)描写了一个士兵的恋爱和离别之情。电影《莉莉·玛莲》讲述了女主人公维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追求爱情、生存斗争与爱情幻灭的故事。两位女主人公美丽、善良、坚强、勇敢,对爱情坚贞不渝,却都被爱人抛弃,而她们最终的悲剧结局又有所不同。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从战争、阶级、文化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方面分析电影文本,追溯二人悲剧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国家,即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大规模崛起之时。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2]5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能够相结合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剥夺的是对劳动关系的控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被剥夺的则是对性关系的控制,正是这二者从本质上界定了各自理论中关于权力缺失的概念。”可见,两者都揭示了两级关系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罗斯玛丽·佟恩(Rosemarie Tong)[3]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主张以阶级来解释女性的地位和功能,资本主义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主因,而资产阶级女性与普通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压迫。“女性受压迫与其说是任何个别人有意造成的结果,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及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联结后产生的结果。”[3]69女性自父权制社会起一直受到各种性别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更受到资产阶级和男性的双重压迫。《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莉莉·玛莲》的两位女主人公都成为战争、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牺牲品。
一些评论家认为电影与文学有相同之处,即采取的一些叙事手段相同,包括序幕、倒叙、预叙、视点和叙事者等[4]268-275。本文认为,电影文本相较文学文本的优势在于,电影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独特的电影符号,包括画面意象、音乐、音响、光影等效果,加上各种创造性的剪辑和组织手段,能更加形象生动地叙述故事、塑造人物。
一、战争:民族压迫
国家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导致两部电影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战争剥夺了女主人公的自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她们施加了沉重的打击,特别表现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两方面。
《一江春水向东流》取材于多部纪录片的战场、轰炸、难民逃难等实地场景,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军的惨无人道、中国老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英国记录电影学派的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5]135-136指出记录片是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能够表现真实世界中更复杂和更惊人的事件。日军肆意屠杀中国老百姓,主人公素芬的公公因反抗日军而被杀,素芬丈夫的弟弟参加了抗日武装。老百姓濒临绝境,四处漂泊。素芬的丈夫张忠良离家参加抗日救护队,家里丧失了经济来源,素芬不得不想尽办法艰辛劳作,靠洗衣服和在难民收容所做事养活孩子、侍奉婆婆,勉强度日。在精神上,丈夫的离家使素芬饱受思念之苦,处境艰难。影片中多次显现的典型场景是素芬在深夜独自仰望明月,大眼睛饱含思念和忧伤的复杂之情。镜头闪回到素芬初婚时与丈夫甜蜜仰望明月的情景,她那美丽的面庞满含幸福与单纯的喜悦。她始终把丈夫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生活的希望。这种强烈的对比震撼人心,突出了残酷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家破人亡的灾难,也为后来张忠良的变心埋下了伏笔。
电影《莉莉·玛莲》真实地展现了二战对普通民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摧残,特别是民族压迫:德国纳粹荒谬地把白人尊为雅利安人,把犹太人和东欧民族贬为“劣等民族”。身为德国雅利安人的女主人公维莉没有民族偏见,热恋瑞士犹太人音乐家罗伯特。罗伯特的父亲领导着营救犹太人的地下组织,担心维莉会影响组织的工作,于是设法使瑞士边境当局以维莉欠巨债为由阻止其入境,使她不得不留在德国以唱歌谋生,却被纳粹利用演唱歌曲以鼓舞德军士气。罗伯特冒险来到德国见维莉,离境时被捕。为了营救罗伯特,维莉接受了犹太地下组织的任务,设法弄到记录纳粹在波兰集中营中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施暴行的胶卷,这是纳粹灭绝种族的铁证。维莉救出了罗伯特,自己却被逮捕关押。战后,维莉历尽艰辛找到罗伯特,昔日的恋人早已另娶他人,维莉最终黯然离去。影片借古董店老板之口,间接叙述了战争开始前夕纳粹砸毁犹太人的店铺、火烧犹太人会堂的暴行,这暗示的是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发生的“水晶之夜”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大约3万犹太成年男性被逮捕送往集中营。战争是造成维莉与罗伯特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普通民众流离失所、饱受摧残的罪恶根源。
电影《莉莉·玛莲》间接展现了纳粹对欧洲其他民族的压迫。在二战初期,当火车站的广播宣告德军已占领贝尔格莱德时,德军士兵们欢呼高歌: “……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全世界将属于我们! ”可见,他们已经被纳粹灌输了称霸世界的狂妄迷梦。维莉对此表情木然,并不倾向于纳粹,但也不了解战争的本质。随着战争的推进,纳粹宣传部门迫切需要用音乐鼓舞德军的战斗士气。钢琴师塔斯纳道出了播放音乐的本质——“人们需要的是让大家不要老想着去死的”“有趣味性的”音乐。歌曲《莉莉·玛莲》受到纳粹头子戈培尔的批评,认为“一首散发出死亡气味的伤感曲”很难鼓动纳粹主义战斗的士气,却得到希特勒的好评。影片反复切换维莉演唱时的热闹场面、战场上狂轰滥炸的惨烈与军营中德军士兵的茫然、伤感。在战争后期,士兵们在俱乐部为莉莉·玛莲欢呼,却不理会希特勒的生日,表现了强烈的厌战情绪,鲜明的对比讽刺了用伤感歌曲鼓舞士气是何等荒谬。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发动侵略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之一,影片振聋发聩地表现了纳粹德国妄图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及其失败结局,发人深省。
二、阶级压迫
战争凸显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也呈现了复杂而尖锐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在于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的劳动来获利,广而言之,在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两部电影的女主人公作为无产阶级女性都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一江春水向东流》着力描写在抗日后方重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庞浩公为代表的大资本家以及各色富商相互勾结、垄断工商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丝毫不为抗日出力;以交际花王丽珍为代表的寄生阶层攀附权贵、生活放荡。这些是平民百姓深受压迫、贫困潦倒的阶级根源,也是道德沦丧的社会根源。抗战刚刚胜利的上海,依然是夜间戒严、社会动荡、通货膨胀、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素芬一家依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生活穷苦不堪,她只好去汉奸太太何文艳家当佣人,儿子去卖报纸。素芬厌恶资产阶级的奢侈和放荡生活,看到丈夫出现在何家更感到惊诧和悲愤。
《莉莉·玛莲》也反映了政治强权和阶级压迫。有评论家认为:“维莉并不具有任何自觉的政治意识,诚如她自己所剖白的:‘我只是唱了一首歌。’”[6]确实,维莉起初不关心政治,一再强调她只是唱歌而已,急于找到工作赚钱,以便回到瑞士与男友重逢。但是,她被纳粹军官选中演唱《莉莉·玛莲》,受到了作为统治阶级的纳粹的压迫。为了录制维莉的第一张唱片,亨克尔强迫维莉、钢琴师等人排练了18小时。维莉对战争和政治,从最初的一无所知渐渐转变到逐步认识,并付诸行动。她唱歌时的表情很说明问题,在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和嘉奖后她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陷纳粹圈套,因此演唱时表情欢快,载歌载舞。后来为了营救男友罗伯特而去波兰演出,她在舞台上表情呆板不自然,演出后匆匆离开,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弄到了拍摄纳粹在集中营中暴行的胶卷,从而使男友获释回到瑞士,这是对抗纳粹的充分表现。维莉后来因此受到审查,以自杀来反抗纳粹的逼供,未遂后勇敢地拒绝为纳粹演出。得知罗伯特已经回到瑞士,她才强打精神为德军进行最后一场演出时,浓妆面庞隐约露出病容,头部上扬,眼睛微闭,声音有气无力,似是无声的抗议。演出结束时,广播宣布德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屏幕上出现维莉苍白的面部大特写,严肃而阴郁的表情掩藏着复杂的情感,她再也不是不谙政治的天真女性了。钢琴师塔斯纳参加的东线部队听到《莉莉·玛莲》的歌声,误以为是自己人而中埋伏覆没,他中弹后咯咯笑,醒悟那不是自己人,随后离世。他是否想起自己曾经说过不想在战争中丧生,希望“让我们这个不争权夺利的艺术小组一直保留到这可恶的战争结束为止”?他是否自嘲自己试图远离政治的天真幼稚呢?歌曲不能挽回德国纳粹的战争败局,反而加速其覆灭,多行不义必自毙。战后维莉终于摆脱了纳粹的控制,却依然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
三、男性的压迫
《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莉莉·玛莲》的两位女主人公都受到战争和社会不公的重创,却都没有屈服,而是坚强地面对。造成她们悲剧的直接因素是她们的丈夫和男友的欺骗、背叛和抛弃。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性别间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最初的诸多对立中的一种。“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奴役同时发生的。”[7]13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不忠不孝,抛妻弃子,由积极抗日的勇士沦落为投靠资本家的寄生虫。他抗战只是一时热情而已,在遭受挫折后即丧失了继续斗争的勇气,怯懦地投靠了王丽珍。在订婚之初,仰望明月,张忠良对素芬说:“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他与素芬话别时承诺:“每当月圆的时候,我一定想念你们。”为了这个虚伪的承诺,素芬耗尽身心精力,养老携幼,盼望丈夫回家。在她抱着熟睡的儿子望月思夫时,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几乎毁掉她的家,而此时丈夫正与王丽珍偷情。张忠良屈从于王丽珍的威势,明知母亲和妻儿可能还活着,却根本不去寻找,其自私和懦弱无以复加。正是丈夫的抛弃使在抗战中坚韧的素芬变得绝望。
《莉莉·玛莲》的男主人公也是负心人。有评论家认为:“维莉的爱情是断送于纳粹战争的;同时,它又成为祭奠纳粹复亡的祭品,敲响了历史的丧钟。”[6]确实,正是德国纳粹发动的战争才使得罗伯特的父亲拆散这对恋人。但是,战争结束后,维莉对男友痴情未改;罗伯特明知维莉还活着却没有去找她,而是与世交之女结婚,显然为了事业成功和虚荣抛弃了挚爱,这也是自私、软弱的表现。不过,在战争期间,罗伯特毕竟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维莉;当维莉为救罗伯特的性命偷送胶卷给犹太组织而被捕后,罗伯特担心她遭遇不测,勇敢地跑到电台,用话筒向德国士兵呼告维莉的生命危在旦夕。后来为了避免军心动摇,纳粹头目才保留维莉的性命以胁迫她继续唱歌鼓舞士气。虽然罗伯特能够为爱人付出,良心未泯,但是他的最终背叛使维莉的爱情梦想幻灭,前途未卜。
两部中外电影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男性与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不过却迥然不同,很多思想家对此各有论述。例如,尼采在其《快乐的科学》中指出,男性和女性在爱情方面都有偏见,不存在平等权利,因为他们有不同观点。女性对待爱情是全身心的、毫无保留的“完全奉献”,无条件的爱情类似于信仰;而男性想要的正是从女性那里得到这种爱。如果男性像女性那样“完全奉献”,那他就不是男性[8]318-319。在忠诚的问题上,女性的忠诚包含在爱之中,而男性的忠诚在爱之后,可能是由于感激、特殊品味或者选择的姻亲等[8]320。尼采的观点得到上述两部影片的印证:女主人公的奉献和忠贞,男主人公的占有欲和背叛。那么,为什么男性与女性对待爱情的观点不同?尼采认为:“女性无条件地放弃自己权利的激情恰恰预设着在另一方没有同等的怜悯,没有同等的放弃权利的意志;因为如果双方都由于爱的驱使放弃自己,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得到什么;也许是空荡荡的空间?”[8]319尼采的思路是预设男性与女性之间是矛盾的、对立的,类似零和博弈的观点,而不是合作共赢。他进一步批评这种现象:女性付出,男性索取。这种“自然的对立”是“无情的、糟糕的、难以捉摸的、不道德的”[8]319。尼采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归于两者之间的自然差异。另外,既然尼采说女性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就说明女性本应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如前所述,他认为女性与男性在爱情方面没有平等权利。这既说明女性没有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和能力,也凸显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受男性压迫的现实。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不同意尼采的观点,她认为男女对待爱情的差异不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差异不是天生的,而是其处境不同所致。男性是有勇气掌握世界并行动的主体,而女性缺乏主体性,不能在行动中实现自我[9]608-609。而且,这是由于在历史上女性一直不被承认为完整的人,不被视为主体,而是被视为客体和他者。“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女人。”[9]273也就是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男性压迫女性的产物。然而,也不能说所有的男性都是压迫女性的。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的弟弟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忠诚勇敢,专情孝顺;《莉莉·玛莲》中的钢琴师塔斯纳一直向维莉付出真挚的友情,试图保护她。
《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莉莉·玛莲》的女主人公都对爱情忠贞不渝,遭到爱人抛弃后都非常悲愤,而结局有所不同。素芬见到丈夫在婆婆的斥责声中依然不肯离开王丽珍,于是悲痛欲绝地留下遗书后投江自尽。长江滚滚东流的画面配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字幕和高亢悲怆的音乐,充满愤怒的控诉。维莉满怀期望地来到剧场后门看着罗伯特指挥交响乐,却遇到他的妻子;这时,维莉面无表情,不露声色,只是眨了一下眼睛,与以前的情绪外露判若两人。她没有质问罗伯特,而是拎起箱子,昂首阔步地走出剧场,远离波光粼粼的水面,音乐节奏鲜明而抒情,没有表明维莉的前途。两位女主人公的爱情都以悲剧结尾,造成这种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展现的抗战后的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素芬家极度贫困,她整日艰苦劳作也挣不了几个钱,还要养活儿子和婆婆,生活负担沉重,寻找丈夫张忠良成为支撑她的精神支柱,因此她在得知丈夫抛弃家庭后,万念俱灰,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莉莉·玛莲》没有展现德国的战后状况,也没有表现维莉的经济情况。不过,维莉毕竟当歌手有一技之长,而且没有家庭负担,在经济方面尚有度日的希望。这证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而且充分表现了已婚女性受到更加深重的压迫。
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来看,素芬和维莉都受到性别歧视和压迫。素芬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数千年的各种封建教条和制度使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男性,“三从四德”的教条严格要求女性的德性;男尊女卑的双重标准,使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庸,严重践踏了女性的尊严,压制了女性的独立人格。素芬在战争和困顿中独自承担养家的重担,她坚忍不拔、敬老爱幼,品德高尚。她在精神上、感情上和物质上都热切盼望丈夫归来。在影片结尾,她得知丈夫变心遗弃自己,因此走向绝路,这是无奈的选择。婆婆感叹“要是死了倒好了”,反映了对生活的绝望。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文学剧本的结尾改编了,素芬并没有死,而是与婆婆和儿子投奔了小叔子忠民[10]40。因为抗战胜利后,张忠民已经成家立业,愿意接纳母亲和素芬母子。不过,原版影片中的结尾更加震撼人心。素芬被丈夫抛弃,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感到无颜见人,也无法名正言顺地接受丈夫弟弟的接济。由于丈夫的自私软弱和王丽珍的要挟逼迫,贤惠善良的素芬悲愤自尽。这种极端的悲剧,充分表现了女性对阶级压迫和负心人的控诉和反抗,警醒世人。正如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所说,悲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能够让人们意识到生存中的不正义、压迫和欺骗等问题,激起人们找到解决痛苦的办法,而不是“痴心妄想、零碎的改良主义、感伤的人文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万能药”[11]12。
同样,维莉与热恋的男友在即将结婚时因为二战爆发而分离,战后遭到男友的抛弃,也反映了德国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歧视。《莉莉·玛莲》与法斯宾德的其他影片《维洛尼卡·福斯的欲望》《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劳拉》等一样,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在婚姻、爱情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劣势地位和悲剧命运,表达了对女性的关切和同情。法斯宾德反对媒体把这些冠以“妇女影片”的提法,而是认为所有影片都是关于社会的,以妇女为主人公则能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12]。法斯宾德自幼父母离异,跟随从事翻译工作的母亲长大,切身体会到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和工作的艰辛。他自述关注女性命运的原因是:“存在于妇女当中的社会矛盾是更为紧张的,这是因为,妇女一方面是受压迫的,然而,另一方面……她们又会把这种压迫作为一种恐怖手段加以使用。因此她们是社会中更加引人注目的人物,而她们中的矛盾也是更为明显的。”[12]63
从历史方面来看,德国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也比较悠久。从中世纪早期到18世纪,日耳曼法律就把女性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例如《萨利克法》规定女性在财产和继承等方面的权利都处于劣势。德国学者施泰恩豪尔(M. T. Steinhauer)认为,在德国父权制的性别概念影响深远。至少从18世纪以来,女性的主要角色是生孩子并需要男性保护;19世纪20年代,妇女被赋予“爱情的代理人”的角色;19世纪末,妇女获得了“有尊严的地位”,即“男性的城市、妇女的家庭”[13]39;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女性解放运动兴起,到魏玛共和国时期,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逐步获得了平等权利。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宣称女性的世界在于她的丈夫、家庭、孩子和房子[14]94,女性沦为延续德意志民族的工具,也是政治、经济工具。
《莉莉·玛莲》反映了维莉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纳粹控制,也受到男友家庭的控制。然而,维莉没有结婚,有比较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她对男友始终如一的爱,大多出于感情上的渴望而不是心理上的依赖,她的坚强性格使她不因为其他人的追求和纳粹军官的胁迫而在感情上屈服。维莉直率地表达对男友的激情,同时她自己承认这是“愚蠢的感情”;她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充满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纳粹的厌恶。她面临困境时能够比较理性地选择,特别是最后她看到男友已经另娶时,比较冷静、果断地割断旧情,这只有理性地洞悉人性才能做到。
四、结语
《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莉莉·玛莲》这两部现实主义佳作充分揭示了战争、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残酷性,谴责了侵略者和压迫者的狂妄、贪婪和残忍,歌颂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是不正义造成的,不正义的战争、不正义的阶级压迫、不正义的性别压迫、不正义的男性的背叛和抛弃。这种悲剧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悲剧,即“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双方处于矛盾对立,要陷入罪过和不正义之中了”[15]286-287。两位女主人公是无辜的、正义的,坚贞、坚强而勇敢,却遭到压迫、迫害、背叛和毁灭,这种违背天道的不正义现象强化了悲剧效果。维莉前途不明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悬念和想像的空间,也暗示了编导对战后德国女性命运的不确定性。素芬自尽的结局,是对于女性深受压迫之境遇的强烈控诉,艺术效果更加令人震撼。两部影片揭示,男尊女卑一直是世界性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女性主义运动任重而道远,男女权利要平等,正义需要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