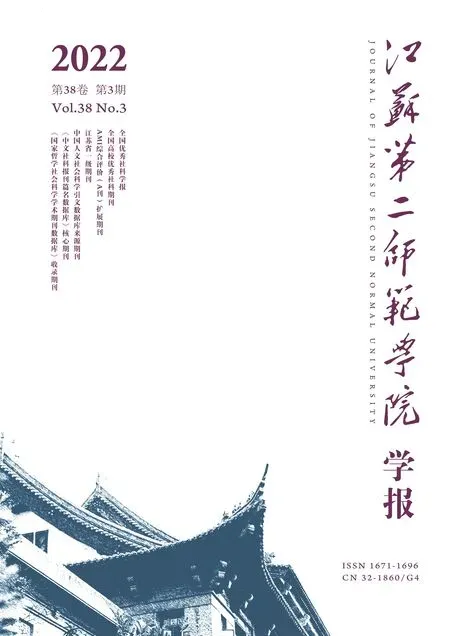语言活动和词的用法: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疏论
2022-03-17张吉廷朱进东
张吉廷 朱进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6)
在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目的、意义、真理性做诠释时,西方学界维特根斯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激烈的争论。首先,这种争论体现在维氏前期《逻辑哲学论》与其后期《哲学研究》的关系上。“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对维氏做出崭新的解读,“他们始终认为,维氏的主要目的——用他本人在描述其后期哲学特征时所使用的一个词说——是治疗……维氏不是渴望提出形而上学理论,而倒是渴望帮助我们摆脱在做哲学时所纠缠于的混乱”[1]1。换言之,新维特根斯坦学派哲学家,皆将维氏理解为规避提出某种“实证的”形而上学计划,进而将维氏理解为倡导作为“治疗”形式的哲学。有的西方学者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普罗普斯(Ian Proops)教授却对这种新的解读深不以为然,21世纪伊始他认为“这些新颖的解读无需当作一回事,因为维氏后期的许多自我批评不能被解读为针对与《逻辑哲学论》无关的内容”[2]。其次,要看到这样的争论几乎贯穿于维氏哲学阐释之始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二波”维氏哲学阐释期间就已出现了这样的争论,包括安斯康姆、斯梯尼、波尔等维特根斯坦学者对维氏的阐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波”维氏哲学思想阐释过程中涌现出的新维氏学者(例如卡维尔、皮彻、克里普克、罗蒂等维氏评论家)大体上认为《逻辑哲学论》预示着维氏后期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著作。再次,在维氏哲学思想中,“规则”没有被置于核心地位。不过,当代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克里普克(Saul Kripke)却把遵守规则的悖论当作维氏《哲学研究》的中心看待,并坚信该悖论是“哲学迄今所见到的最激进的最原始的怀疑问题”[3]60。与此同时,有些维氏阐释者则认为,哲学只能描述日常语言而不能改变日常语言自身。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得有点因循守旧;如果这样来解释维氏诉诸日常语言的意义,那么看来好像有失偏颇,其实维氏的意思是单凭哲学根本无法改变语言自身。就日常语言的论述来说,维氏的论证是为日常信念辩护,反对与其论证相冲突的哲学见解。因此维氏眼里的哲学与常识之间本质上不存在什么相互冲突的因素,而且只因坚信人类知识是有条件而非绝对的所以才致使人们诉诸日常语言。本文尝试在此争论背景下从语言活动和词的用法角度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理路做出文本诠释意义上的疏论。
一、形而上学:后期语言活动与早期逻辑
讨论逻辑的《逻辑哲学论》和探究语言哲学的《哲学研究》二者既具有难以断裂的深度关联又做不到与形而上学一刀两断。当代哈佛大儒卡维尔曾对维特根斯坦的这两本杰作之间的关系做了卡氏式的别具一格的论述。维氏《哲学研究》所揭橥的是他自己早期思想如何导错了航向。奉献一套崭新思想理念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对《逻辑哲学论》学说的扬弃式的否定而绝非彻底的颠覆。
我们认为,《哲学研究》属后期维特根斯坦或维氏后期代表作亦为其扛鼎之作,它与前期维氏著作《逻辑哲学论》具有一种不应切割且难以断裂的深度关联。后者在内容上牵涉的是逻辑,在这里哲学变成了实行澄清的过程,但我们知道诸多事物的逻辑却因言不达意或言不尽意而无法表达这些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前者在维氏那里具备“风景速写”[4]2画册之特质,其中被了解为一种活动的语言在这种活动中起到了工具的作用或扮演着工具的角色,在这里哲学研究展露为从形形色色方面探究一个相同的问题,这大有哲学上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意味;公正地说,不管是在维氏后期著作《哲学研究》里还是在其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也无论是讨论逻辑还是探究语言哲学,要想完全撇开认识论或形而上学是根本做不到的。对于这种“不应切割的深度关联”,我们尝试做出以下几点阐述:
第一,这里必然牵涉当代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卡维尔(Stanley Cavell)教授的著名论述。20世纪70年代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杰出运用者卡维尔在其《理性的主张》这本著作开篇就发问:“假如,不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开端入手,因为哲学起点的闻名度在开始时和哲学如何收尾不相上下;假如,不从《哲学研究》开篇入手,因为它的开篇不能被混同于它所体露的哲学的开端,因为人们几乎不能提供可以用来理解开篇的术语连同开篇本身;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可,无论如何抛掉开篇不谈,这本著作的撰写方式是与它论述的内容具有内在联系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先理解具有某种方式的作品才能理解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方法);假如,我们不从依赖我们的历史入手,因为几乎能够同时将这本书置于历史和哲学的地位;假如,我们也不依赖从维特根斯坦的过去入手,从此以后我们很可能假定《哲学研究》的写作源于《逻辑哲学论》遭受到的批评,这样的假定与其说是错误的倒不如说是捕风捉影的,这既是因为知道什么构成对《逻辑哲学论》的批评当然意味着知道什么构成《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也是因为现时关键问题不只是明了《哲学研究》的撰写怎么源于《逻辑哲学论》自身遭受到的批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从何入手且怎样走近《哲学研究》这个文本呢?我们应该怎样让这本书教我们走近它或什么的呢?”[5]3
第二,这里的两个发问,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这两本著作之间的深层关联,做出了卡维尔式的别具一格的论述,同时也让人联想到晚年卡氏在哲学回忆录中的一处感悟:“能够使余对先见之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吾人诲人不倦,学而不厌,学然后知不足;他者永远担心天下何人能识君,并老是向吾人倾诉衷肠。这乃是通向解读维氏《哲学研究》开篇的一种路径,也即余这些年以不同方式提出的解读。”[6]122这堪称是卡维尔式的解读,也使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维氏《哲学研究》没有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悉心研读了其中的一百多节。就《哲学研究》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关系而言,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对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持有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得不说的是,后者使维氏跻身20世纪领军哲学家如杜威、海德格尔、罗蒂等人行列,但是此后他所形成的哲学见解与使他享誉世界的见解相去甚远,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他在《哲学研究》中所揭橥的是他早期思想怎样导错了方向。有的西方学者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皮彻(George Pitcher)就持有类似这样的看法[7]。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彻底颠覆了前期哲学思想,换句话说,绝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承继关系即后者实乃纯粹是断裂式的另起炉灶的哲学思想产物。
第三,说《哲学研究》试图提出一套崭新的思想理念,这一说法是符合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实际状况的而绝非是强加给他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哲学研究》呈现出对《逻辑哲学论》学说的否定而绝非彻底的颠覆。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维特根斯坦学术研究中不断谈到,说后期《哲学研究》不代表与早期《逻辑哲学论》一刀两断,而二者曾经被认作是毫无关联的:早期与后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同等重要”[8]68,但是哲学界不少学者持有后一种看法并在维氏本人那里寻章摘句。我们赞成前一种看法,同时认为在《哲学研究》突显的许多理路中,维氏在哲学性质为何这一问题上确实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全新的理念。不得不说,在欧洲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家不是将哲学当作逻辑看待就是当作皇冠科学看待,甚至就连早期维氏也抵挡不住这种看法的极大诱惑。不过,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思考我们使自己陷于困惑状态的缘由何在,结果发现了人的思想中具有一种根本的寻求同一性的天生倾向,发现同一性渴望的在于去弥合甚至忽略相关对象间的差异。我们认为,通过对哲学本性的分析,可了解维氏的方法在于使人打破借以看世界的眼罩之缘由,也在于论述语言使用中和世界中的差异性,这种论述既有别于黑格尔对同中之异的论述又有别于黑氏对异中之同的论述。
二、超越独断论、迈向日常语言与拥有卓殊的“书写”形式
《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独断论藕断丝连或含有浓厚的独断论色彩,但向后期过渡之际已经完全跨越了独断论的藩篱。从逻辑领域迈向日常语言领域从而也就跨出了逻辑范围。“新维特根斯坦主义”哲学家卡维尔对后期维氏风格上变化做了辩护:维氏的特殊“书写”形式将“自白”“对话”揉为一体。哲学上的“治疗”功用体现在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语言的活动中。
首先,作为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杰作《逻辑哲学论》,其中最重要的真知灼见之一是哲学既然不作为一种学说那么哲学就不应该被加以独断论式地看待,而维氏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却坦承其早期哲学含有浓厚的独断论色彩。这就揭橥维氏早期哲学思想不可能与对终极实在的追寻毫无关联,因为形而上学的根本旨趣在于对终极本体的追寻。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那里作为幻象的终极实在就已遭到无情的批判,同时康德对未来形而上学做出了论述;近代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就形而上学的一些问题,譬如第一性质、第二性质、空间与时间、运动与变化、因果关系、自在之物、事物、思想与实在、谬误、自然、恶、身体与灵魂、善、绝对及其现象、终极怀疑等等,做了淋漓尽致的“头脑风暴”式的沉思;胡塞尔、皮尔士、罗素、马利坦、塞拉斯有关形而上学著述是与认识论不可分割的。
与上述这些哲学家与形而上学的牵连一样,要解释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独断论因素不大可能脱开维氏的后期思想。如同任何哲学的建立皆必然植根于一定的基础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逻辑哲学论》这座哲学大厦奠基于的假定,在于逻辑分析之任务实即去寻找特定的基本命题。因此,如果说早期维氏还与独断论藕断丝连余情未了的话,那么从早期维氏向晚期维氏过渡之际已经彻底地超越了独断论而且这种超越或摒弃势必带来一定的后果,换句话说,维氏那向极端的反独断论之过渡必然促使他所关注的焦点,乃是从逻辑领域迈向日常语言领域从而跨出逻辑范围,实际上从强调对“家族相似”“语言游戏”做出界定而变成聚焦对它们做出实证的分析,这在风格上当属从系统全面的哲学写作变为格言警句式的写作风格(其中维氏哲学出场风格因呈现为格言警句而饱受后世许多哲学家的诟病)。
其次,作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或“新维特根斯坦”)巨擘,美国哲学家卡维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后期维氏风格上的变化,表明自己独到的见解或为维氏哲学上的“变法”做出了呕心沥血的令人信服的辩护。卡氏的这种辩护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维氏《哲学研究》乃至维氏整个后期哲学所呈现出的风格令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不已,因为它看来好像算不上哲学的风格(或传统的哲学风格或现代哲学意义上的风格),但是,卡氏旨在表明维氏的这种行文风格对于哲学并非面目全新的而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将“自白”和“对话”这两种风格糅合在一起[9];第二,在卡氏看来,论证的性质促使维氏不得不采用这种风格而非故作标新立异。我们认为,跟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布拉德雷等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无论其前期哲学还是后期哲学都不可能与形而上学完全脱钩,而维氏的《哲学研究》又确实可以归入哲学的哲学和语言哲学之类;形而上学本身却稳坐黑格尔所垂青的那座哲学庙宇,同时绝不会遇到黄昏而始终散射出玄学之芳香。
再次,从风格上观之,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采用的格言警句式的表述方式,完全可以说是奇而不怪新而颇为有道。第一,必须指出的是,维氏的确意识到了自己“力主的研究方式”与“某些人的研究方式格格不入”[10]103,与某些人的研究方式不合轨辙,因为人们适应不了他的方法所要求的而根本上不同于科学上要求的“那种思考方式”,正如格雷林所说的那样,“维氏后期著述风格上不具有系统性但绝不意味着内容上不具有系统性”[11]v-vi。第二,关键在于必须对维氏所说的与他说出所说的之方式做出毫不含糊的区分,因为维氏所言说的东西与他说出所言说的东西之方式这二者之间是不可画等号的。作为一本遗著,维氏《哲学研究》所含有的一些新颖的思想,应当与他《逻辑哲学论》中那些旧思想加以比照而加以理解;他的新洞见可理解为重在揭橥哲学史上哲学的传统思想方式之谬误。第三,维氏《哲学研究》这一著作应该被设想为一部“治疗”式的著作,将哲学本身设想为它应当成为的东西(或设想为“治疗”);在维氏那里,“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4]137。
此外,就哲学具有“治疗”的功能而言,最根本的在于最好把语言视为一种活动,语言活动中“词”是当作工具使用的,而词(不作为事物的标签)的用法是形形色色的,在用词进行“游戏”(即“用词行事”)过程中来理解词,这其实表明可以说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因为,存在着“感觉”一词的“语法”,以及像“痛苦”和“记忆”这些词的语法,它们可被知晓相关“语言游戏”的人加以把握,与此同时,期待、意向、记忆皆由于使用语言而可能变为“生活方式”,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应该说,维氏奇特的、翻来覆去的方法,并没有遮蔽其《哲学研究》这一著作里的理论论点——语言最好应该被理解成是一种活动,其中词是被言说者作为工具来使用的,词的用法是林林总总的和变化无常的,这就使得某些哲学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对语言的误解所造成的。
三、词的用法:“语言游戏”与“意义”
语言是游戏(“语言游戏”或原始语言)和工具之隐喻。“语言游戏”揭橥的是语言实乃人类的植根于社会的“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在于突显语言的述说是一种活动或生活形式的构成部分)。词的用法穿越错综复杂的相似关系的网络。词的意义在于语言中的使用。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的“语境原则”发展出“后弗雷格哲学”时代达米特(Michael Dummett)赋予语境原则。哲学家不应该再将词当作可以用各种方式运用的工具看待,因为它具有鲜活的语境生命而绝非类似商品流通过程中一经铸成的标签式的硬币。
第一,在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时,最应该关注和探讨的是它的内在理路。在维氏眼里,哲学研究不在于追求论题或理论(即不提出理论)亦非要去发现固定不变的意义或对象。“词”是这种对象的永久的标签,因此,要解决“当语言放假时”哲学问题如何发生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乃是通过注意跟手头问题牵涉的语言的用法。拿做诗人与做哲学家相比,诗人之为诗人是刻意为之,而哲学家之为哲学家却是无心插柳。我们认为,在《哲学研究》这本著作里,维氏使用的是语言作为一种游戏和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这两个隐喻(亦即语言是游戏和工具之隐喻)。维氏在对用词来称谓对象的原始语言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主张可以把词的整个过程当作儿童学习母语的种种游戏之一种看待,并且把这些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有时候把原始语言形容为“语言游戏”。这样一来,维氏就把由语言和行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之为“语言游戏”。
第二,引入“语言游戏”这一关键性概念,维特根斯坦为的是论述数不胜数的形形色色的用途、用途的非确定性和用途“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构成《哲学研究》中一条重要的哲学理路,但维氏从未对语言游戏做过明确的界定和诠释,这是奇怪而不争的事实。其一,他反复回到语言游戏这一概念且尝试厘清他关于语言的大体思路。《哲学研究》第二节中论述了原始的语言游戏。在建造语言游戏过程中,建造者及其助手恰恰使用了四个术语——石块、石柱、石板和石梁,被用来说明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部分内容可能是正确的。其二,语言游戏的一些特质可见于维氏列举的若干例子和评注中,同时这些品质构成被用生活形式短语所描述的较为广义上的语境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游戏”的选择奠基于对语言与游戏的全盘类比。其三,这就决定了最初不能对“游戏”做出一锤定音式本质上的界定,所以维氏坦言未提出某种对于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为共同之物。在这里显然是淋漓尽致地宣称从根本上摒弃了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解释”,同时绝不是指向哲学家“醉心于一般”的症候,倒是应当借词的用法穿越“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4]48。因此完全可以说的是“游戏”形成一个家族,而且家族相似可用来展示描述同一概念的不同用法缺乏边界和远非具有确切性。
另一方面,与在近代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和罗素那里语言不是自给自足的抽象系统不同,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说的“语言游戏”恰恰要表述的是语言实乃人类的、植根于社会的实践或“生活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显语言的述说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这就可以用“下命令,服从命令”“报告一个事件”“演戏”“猜谜”“诅咒”等来表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考察语言游戏中发现,“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4]48。这种相似性的特点被他说成是“家族相似”。在各种各样游戏构成了“家族”的同时,表达的各种用途也组成了“家族”。如此而来,就探讨语言本质唯一有意义的方法而言,借助考察语言在各种方式中的使用情况这种做法最为合适。
第三,在词的用法方面,除了“语言游戏”之外,《哲学研究》还有对人们使用的“意义”一词的界定。“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4]31。脱开运用中特定的语言环境,词就会变成标本式的毫无生命力的标签。首先,在这里人们使用的“意义”一词可界定为“词的意义”即为在语言中而非游离于语言之外的使用。这句话成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口号,从而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就成了对整个“哲学研究”的理解或做哲学过程的理解,“这个口号出现在对专名的探讨中,强调吾人无法根据一个名称的实指定义(the ostensive definability of a name)来断定这个名称的意义是它的承担者。其次,虽然它的意义可做实指解释,但它的意义仍然是它的使用,因为解释一个名称的意义乃是赋予它正确使用的规则。意义是否被吾人理解,这个问题的标准是后续的正确使用”[4]99。我们认为,在西方语言哲学史上,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弗雷格就在《算术的基础》中就提出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语境原则”,暗示仅仅在句子语境中词语才表示特定的意思而在句子语境之外语词无异于硬币式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后弗雷格哲学”时代英国当代哲学家达米特赋予语境原则标志着哲学的基础性转换(亦即“语言学转向”)的主要意义。最后,在弗雷格那里“语言转向”意味着若要分析思想的结构,那么唯一且必须做的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语言是我们领会思想的主要手段、甚至成了唯一奏效的实用手段,而后期维氏尝试用“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来俘获语境所拥有的敏感性。
第四,坚持“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这就要求哲学家不复将词当作对象的名称看待,也就是说,不再将词当作可以用各种方式运用的工具看待,这并不比要求哲学家习惯于以符号(指称的方法)分析语言更容易。我们认为,在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比喻为游戏时其在于突显语言表达构成“生活形式”的内容;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这一观点直接反对的是,认为语词的意义蕴于说话者心中或私人的感觉。然而,关于感觉的言谈不是无意义的,因为“感觉”一词不可能成为只对言说者有意义的一种私人语言的成分;《哲学研究》中论述的很多东西之所以有些哲学家完全无法接受,主要是因为这些哲学家形成了使语言出毛病的坏习惯。因此开明的“哲学家处理问题就犹如治病一般”[4]137。这一哲学治疗后来成了新维特根斯坦派学者如卡维尔、普特南、麦克道威尔等人的主旨话题。
四、遵守规则的悖论与“逮蝇瓶中的苍蝇”
在赋予词意义时应该以对用途的描述替代阐释性概括。遵守规则悖论使得维特根斯坦具有潜在的无法过滤掉的怀疑论色彩。维氏后期哲学里带有一种神秘主义即某种哲学上的神秘境界。哲学对一切既不做说明亦不做推论。这种反理论的立场绝非颠覆了早期有关哲学的论述,因为《哲学研究》所揭橥的是哲学具有非独断性意义上的治疗的性质。找不到一种哲学方法而确实又有诸多不同的“治疗方法”。在辨析语言虚妄权力的同时,哲学家揭橥了无意义的哲学论证之陷阱,从而突显哲学的目的在于指出“逮蝇瓶中的苍蝇”出离的方向。
其一,上文已经考察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语言规则和“家族相似”与意义的用法方面的理路,我们现在再来梳理对规则的遵守和哲学的蕴意方面的理路。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这一基本陈述成为后期维氏思想最为典型的视角变化之基础,这就是从作为表象的意义概念到一种看似用作哲学研究的关键观点之变化。传统的意义理论专涉某种与命题无关的、赋予命题以意义之物。“某物”常常不是被置于某个客观的空间就是被置于心灵中作为精神表象。必须看到的是,在《哲学研究》之前,维氏就已经明确揭橥,我们如果指称任何作为象征生命的东西,那么就必须说它是具有用途的;而《哲学研究》中表明,哲学家在研究“意义”时必须“看看”词被赋予的各种不同用途,因此这个新的视角截然不同于“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4]47这也就意味着不要煞费苦心地冥思玄想而必须直面具体事件。因此,在赋予词意义过程中但凡阐释性概括皆应被对用途的描述取而代之,这恰恰构成了维氏后期哲学的主旋律。
其二,遵守规则是《哲学研究》中特别加以强调的内容。它成了何者应用于词语全部用法问题探讨的又一核心观点。在这一问题方面维特根斯坦显然超越了以往哲学的独断论立场。“现在,我们让这学生从1 000以后接下去写一个(比如+2)的数列。——而他写下1 000,1 004,1 008,1 012。”[4]112在这个受到纠正的学生回答道,但是我要以同样方式继续做下去时,我们在做什么且这样做又意味着什么呢?维氏对现时这一问题做了这样的揭橥:我们怎么学习规则?怎样遵守规则?它们在社会和公共场合被教之于人、被强使人们遵守吗?《哲学研究》中这样论述道:“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于规则。回答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被搞得符合于规则,那么一切事物也就都能被搞得与规则相冲突。因而在这里既没有什么符合也没有冲突。”[4]121这里就悖论而言,引来后人大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阐释。在对此做出怀疑论式诠释的某些学者眼里,这个悖论竭力鼓吹的是一种怀疑论式的悖论而且解决办法也是怀疑论式的。
我们认为,公允地说,在遵守规则悖论这个问题上还看不出维特根斯坦带有明显的怀疑论色彩,更重要的是,要从其整个前后期哲学贯通来看待这个问题,诚然他的后期哲学中潜在的怀疑论色彩是谁也过滤不掉的,不止于此,维氏后期哲学中还带有一种神秘主义,换句话说,他达到了某种哲学上的神秘境界,如现代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芬德莱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的那样:“这种神秘主义至今依然无人提及但却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存在。”[12]68诚然,维氏的意义哲学不可能使他去过多地谈论神秘主义,但不应将他理解成是把形而上学家赶回柏拉图洞穴的人,同时也不应把维氏理解成科学主义巨人和自然的语言行为的仲裁者。但美国后分析哲学家卡维尔的浪漫的怀疑论可以追溯到维氏这一时期的怀疑论。
其三,哲学对一切不做说明同时亦不作推论。大凡哲学家都依据自己的哲学对哲学意蕴做出一番独具匠心的诠释。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认为,哲学世界是神生活的世界、真正神秘的世界,同时作为真正完善的人,癫狂的哲学家因通灵而向往神明的世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不是一门生产科学,人们研究哲学缘起于惊诧,哲学智慧不是实用智慧,是非凡的、深奥的和神圣的但却是无用的;在西塞罗眼里,哲学扮演生命的引路人、宇宙的探险家、罪恶的驱逐者的角色,而且赐予人类和平的生活和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照黑格尔说,哲学实为思想对哲学所处时代的领悟;尼采主张,真正的哲学在于把握推理的限度。与西方哲学史上这些哲学家对哲学的看法不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对哲学的性质做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颖独特的描述。如在《逻辑哲学论》中一样,维氏依旧坚持认为哲学家没有或不应当提供什么理论之类的东西。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呢?“哲学只是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既不做说明也不做推论。——因为一切都一览无余,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说明”[4]76。我们认为,这种反理论立场是与早期维氏思想一脉相承的而绝非颠覆了早期有关哲学的论述,公正地说却和他早期思想又是具有显而易见的区分。原因在于,《哲学研究》所揭橥的是哲学具有治疗的性质,而非具有独断论意义上的性质,搜集提示物,确切点说,为特定目的搜集提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哲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不同于柏拉图认识论上的回忆说,维特根斯坦在其他地方讲过,研究哲学归根结底就是回忆,而且人们提醒自己事实上是在以这种方式使用词语。
由于某些回忆和一系列事例,各种不同的问题才能够得以顺利地彻底解决。必须指出的是,《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一直坚信,“解决哲学上的困难乃是消解哲学以往发现的全部有问题的话语领域”[8]63。哲学上这个话语领域既是极其抽象的也是纯然思辨的,同时消解现有哲学问题的进路绝非是清一色而却是有较大差异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研究》中找不到一种哲学方法,确实其中却又存在着诸多方法(也即不同的“治疗方法”)。通过分析语言虚妄的权力,哲学家揭橥无意义的哲学论证的陷阱,以前被视为哲学问题的东西,现在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解决,这只不过表示哲学上的疑问“应当完全消失”,这里的“应当”类似于“批判哲学”中的伦理意义上的“应当”。所以说,哲学问题所拥有的形式乃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4]75。如此而来,哲学的目的旨在“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飞出去的途径”[4]154-155。这可以说实即哲学家在哲学(在做哲学或从事哲学活动)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