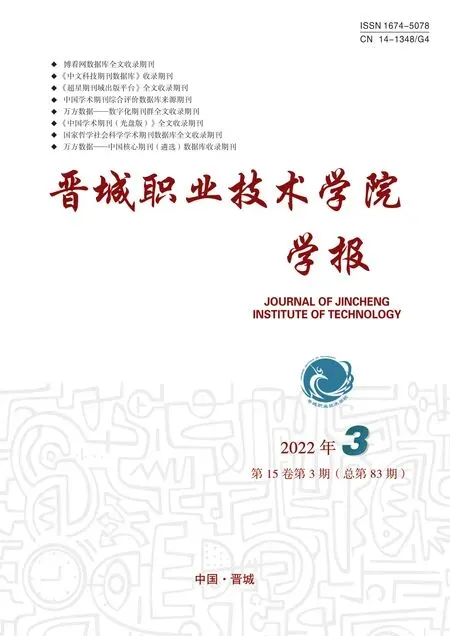《瓦尔登湖》中文译本物质文化传译比较研究
2022-03-17张心瑜
张心瑜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福州 350007)
一、前言
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9)1854年所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作者对人生真谛和大自然的精彩诠释,在全球的不同文化中呈现出深刻的启迪意义。一百多年来该书已经有150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四十几种语言(白阳明,2012)。《瓦尔登湖》的中译本自1949年首次出版,到2014年有37种中译本问世(林丽,2014)。目前,仍有新译本出版。不同译本的翻译,各有特色。通过比较三个中译本的翻译特色,目的是探讨影响英汉文化传译效果的决定因素和方法策略的有效性。
本文研究依据的英文版本为梭罗1854年所著的Walden,为了引文的方便,本文所使用的页码采用外文出版社2015出版的英文本。本文借于进行比较分析的三个中文译本分别是:1949年徐迟译《瓦尔登湖》(外文出版社2015年版),简称徐译;许崇信、林本椿1996年合译《瓦尔登湖》(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简称许林译;王义国译《瓦尔登湖》(2011年2月,北京燕山出版社),简称王译。
按照文化的表现形式,可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生产工具和设施、经济生活和日用品以及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条件。”(孙蕾,2014:64)物质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要用到的各种度量衡单位体系,旧时中国所采用的市制单位寸、尺、丈、里,英美国家所采用的英制单位吋、呎、码、哩,以及现在通行的国际单位公分、公尺、公里,就是物质文化差异的体现。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必然涉及两种文化的差异。
170多年前,梭罗在新英格兰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地体验了一次简约生活,并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与远近邻居们的友善往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细心观察,使全书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内涵。下面通过7个例句,来分析三个译本在物质文化传译上的特点。
二、例句比较
【例1】第9章The Ponds和第16章The Pond in Winter中的“Pond”的翻译。
先看三个译本对这两章标题的翻译。徐译和许林译都意译为“湖”“冬天的湖”,王译直译为“池塘”“冬天的池塘”。从英汉词汇的字面意义上来说,“Pond”是“池塘”,“Lake”是“湖”。所以,王译把“Pond”翻译成“池塘”,似乎更准确。但是在中文中,“池塘”往往用来描述比较小的水体,而“湖”则可大可小,比较灵活。如果细读两个章节,会发现梭罗对“Walden”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面积(大约373亩)、水深(最深处102英尺)、水质、水色、水底、水位的高低涨落、水中的动植物、环水岸上的地貌景色、远近其它的湖泊等等。根据这些描绘,这一方水与中文字义上的“池塘”相距甚远,而中文的“湖”更能反映出这一方水的全貌和本质。看三个中译本对“Pond”一词的翻译。徐译和许林译相同,行文中与章节标题的译法保持一致,都意译为“湖”;王译则比较混乱,时而与章节标题一致,译为“池塘”,时而又译为“湖”,这种情况出现在同一段落特指同一个对象的情况下,给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不该有的文化困扰,弄不清作者写的究竟是同一个Walden,还是别的什么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中的理解和品味。
【例2】度量衡单位“rod”
与例1相关的另一个文化传译上的问题是度量衡单位“rod”。为了更清晰地呈现Walden的面貌,梭罗还根据自己的测量,按照十杆对一英寸的比例画出了Walden的地图。笔者在查阅一些英文版的Walden时,大都可以看见这张图。可惜的是翻遍了三个中译本,只有许林译本收录并翻译了瓦尔登湖平面图(2011:205)。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其它两个译本在文化传译上的缺失。
在许林译本中看到的那张“瓦尔登湖平面图”上有这样的信息:
比例:1:1920,或40杆:1英寸
面积:61英亩103杆
最宽处:175.5杆
对照英文原图的信息是:
Scale:1/1920,or 40 rods to an inch
Area:61 acres 103 rods
Greatest Length:175½rods
这里有一个目标语读者陌生的度量衡单位“rod”。其实浏览全书可知,梭罗在书中多处使用了这个度量衡单位。它可用来表示长度和面积。
表示长度的,除了地图上标注“最宽处:175.5杆”外,又如:
My house was on the side of a hill,…and half a dozen rods from the pond.(2015:114)
徐译: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离开湖边六杆之远。(2015:106)
许林译:我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腰上,……距离湖边有六杆远。(2011:81)
王译:我的房子是建在山坡上,……距离池塘有六杆②远。(②杆(rod),英国长度单位,一杆等于五又二分之一码。六杆等于三十三码。)(2011:93)
表示面积的,除了地图上标注“面积:61英亩103杆”外,又如:
He would need to cultivate only a few rods of ground.(2015:57)
徐译: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③的地就够了;(③一平方杆等于30.25平方码。)(2015:49)
许林译:那么,他只须种几平方杆③的土地就够了。(③一平方杆约等于25.3平方米。——编注)(2011:38)
王译:那么,他就只须耕种几个平方杆①的土地。(①平方杆(rod),面积单位,等于三十点二五平方码。)(2011:45)
评析:此例可见,对“rod”这个陌生的度量衡单位三个译本都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进行了文化传译,不同的是在传译的内容上又有些差别。徐译和王译用“码”来解释“杆”,或者用“平方码”来解释“平方杆”,这对目标语读者来说还是有隔雾看花的感觉;相比之下许林译用“平方米”来解释“平方杆”就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习惯,相关的物质文化信息的传递也更清晰,最易为目标语读者接受。
【例3】Idoubt if Flying Childers ever carried a peck of corn to mill.(2015:54)
徐译:我怀疑飞童①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①英国一匹著名的赛马。)(2015:47)
许林译:我看飞童②未必曾把大量的玉米带到磨坊去。(②Flying Childers,18世纪著名的英国赛马)(2011:36)
王译:我怀疑,飞马奇尔德斯⑤是不是曾经把一配克的谷粒送到磨房里去。(⑤飞马奇尔德斯(Flying Childers),是一种英国纯血马,比赛用马。)(2011:42)
评析:这句话中有两个带有文化信息的词,一是“Flying Childers”,另一个是“peck”。不能确定徐译和许林译为什么将“Flying Childers”译为“飞童”,王译用直译加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飞马奇尔德斯”,并加注说明这是一种英国纯血的比赛用马,不仅最符合原文语境的意思,传达的文化信息也最完整。再看“a peck of corn”,徐译为“一粒谷子”,许林译为“大量的玉米”,两个译本都用意译,传递的信息与原文都有距离。王译直译为“一配克的谷粒”,但没有加注说明一配克的分量究竟是多少。三个译本都没有对“peck”这一计量词做任何说明,所以才会有“一粒谷子”和“大量的玉米”这样相距甚远的表述。
【例4】and on my shelf a little rice,a jug of molasses,and of rye and Indian meal a peck each.(2015:244)
徐译:在我的架上,还有一点儿米,一缸糖浆,还有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各一配克②。(②在美国,一配克合8.809升)(2015:227)
许林译:在我的架子上有点白米,一大壶糖蜜,还有黑麦和玉米粉各一配克②。(②peck,英制干量单位,约合2加仑或9公升。——编者注)(2011:173)
王译:在我的架子上有一点大米,一罐子糖浆,还有一配克①黑麦和一配克玉米粉。(①配克(peck),水果谷物等的计量单位,一配克等于八夸脱或者二加仑。)(2011:202)
评析:这个例子在计量词翻译的角度上与前一例子相关。“Peck”一词上例中已出现过了,三个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在此处才对它加了注释,很显然是因为这个语境对计量词信息的准确性需求提升了,译者不能再像前例中那样做主观的猜测,而是必须要有客观准确的表述才能传达原意,故三个译本都用了注释法来处理。比较起来,徐译和许林译的注释比较方便目标语读者,因为这个读者群对“升”和“公升”是有概念的,具有可比性。王注用“夸脱”和“加仑”这样英制的表达,可比性会打折扣。
【例5】On the one side is the palace,on the other are the almshouse and“silent poor.”The myriads who built the pyramids to be the tombs of the Pharaohs were fed on garlic,and it may be were not decently buried themselves.The mason who finishes the cornice of the palace returns at night perchance to a hut not so good as a wigwam.(2015:36)
徐译: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筑造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要像像样样地埋葬都办不到。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入晚回家的石工,大约是回到一个比尖屋还不如的草棚里。(2015:30)
许林译: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就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①。千千万万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人,吃的是大蒜头,死的时候很可能都没有像样埋葬。做完了皇宫飞檐的石工,夜晚可能回到一间比棚屋还不如的小屋子里去过夜。(①对自己的贫困忍气吞声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被送进贫民院。18世纪时康科德筹集了一笔基金来帮助他们。)(2011:24)
王译: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①。那些建造法老陵墓金字塔的千千万万的工匠,他们是以大蒜当饭,而且可能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体面的埋葬。为宫殿造出飞檐的石匠,也许在晚上返回的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茅舍。(①康科德用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二年的遗赠款项建立了“沉默的穷人基金会”,该基金由第一教区教堂牧师和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支付。)(2011:27)
评析:这段话三个译本都采用了直译,其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文化信息:“silent poor”“The myriads were fed on garlic”和“wigwam”。对“silent poor”,许林译和王译都加了注,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那些穷人为何会保持沉默。关于工匠们吃大蒜的事据说在金字塔上有记载,这些大蒜主要是用于医疗而不是充饥,故徐译和许林译尚可接受,但王译“以大蒜当饭”之说似不可取。“wigwam”是这个例子讨论的重点,因为这个词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三个译本都没有译出“wigwams”是特指印第安人棚屋、尖屋,丢失了作者原文中在“wigwams”与“hut”(简陋的小屋)之间进行对比的文化内涵。
【例6】I thought often and seriously of picking huckleberries;that surely I could do.(2015:71)
徐译:我常常严肃地想到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做到。(2015:63)
许林译:我时常认真地想去采摘黑浆果,这我肯定能干得了。(2011:49)
王译:我经常认真地想到,还不如去采摘黑果①;我毫无疑问能够做得到。(①黑果,即黑果木(huckleberry)所结的浆果。)(2011:56)
评析:本文从这个例子出发,探讨三个译本对“huckleberries”一词以及相关的一些植物名称的翻译。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评判翻译结果的正确与否,而是着眼于探讨在翻译过程中应该保持植物名称的一致性与可读性问题。这个例子里“huckleberries”一词,徐译用了笼统的说法“浆果”;许林译强调了浆果的颜色特征,译为“黑浆果”,同样是比较笼统的说法;王译给出了这一植物的名字“黑果木”,并加注做了说明,信息比前两个译本具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huckleberry”在全书多次出现,而分别细看三个译本,比如:徐译本在此处把“huckleberry”译为“浆果”,而在后文中又多次将“huckleberry”改译为“越橘”(2015:108、161)。例如在163页“huckleberry”和“blueberries”同 时 出 现 时,“huckleberry”被译成了“越橘”,而“blueberries”则被译成了前文已经用来翻译“huckleberry”的“浆果”。在许林译本中,后面几处再出现“huckleberry”时,一次译为“黑果”(2011:82)、一次译为“越橘”(2011:124)、还有一次译为“黑越橘”(2011:126),而“blueberries”则被译成“蓝莓”(2011:126)。王译本中前后几次对“huckleberry”的翻译都保持一致译为“黑果”,是三个译本中文化信息传译得最明晰的。可是,如果观察王译本对“blueberry”一词的翻译,同样也可以发现译名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当“blueberry”出现在第93页时,王译本将其译为“乌饭树”;随后在第145页,王译本将huckleberries译为“黑果”,将blueberries译为“蓝莓”。总之,从三个译本的比较来看,这种在同一个译本中对同一植物翻译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出现,这是文化传译不准确的表现。
【例7】The most aldermanic…the next in seniority and girth…the master of ceremonies…the least distended,leakiest,and flabbiest…the patriarch…(2015:127)
徐译:最高头儿的青蛙…另一只青蛙,官阶稍低,凸起肚子…司酒令的青蛙…最没喝饱的、漏水最多的和肚子最瘪的青蛙…可敬的老青蛙…(2015:118)
许林译:那个最高级的青蛙委员…有一只资格和肚皮均数第二的青蛙…司仪的青蛙长官…那膨胀最小,漏水最多和肚皮最松的青蛙…青蛙长老…(2011:90)
王译:那只级别最高的牛蛙…那只级别次高,腰围次大的牛蛙…司仪…那只肚子最不膨胀,最不漏水最肌肉松驰的牛蛙…那位家长…(2011:104-105)
评析:在这一大段写环湖众蛙和鸣的文字中,笔者选出了这5组描写不同青蛙特点的词来作比较,似可从一斑窥全貌,看出三个译本采用直译和归译的一些特点。对第1只青蛙,三个译本都着眼在它的最高级别上,不同的是许林译还强化了这只蛙“委员”的身份,最契合“aldermanic”一词的原意,也最有西方文化的色彩。对第2只青蛙,三个译本都抓住它级别和腰围排列第二的特点,许林译和王译用了直译,唯有徐译用“官阶”这样富有目标语文化色彩的词来给青蛙排座次,别具特色。对第3只负有司仪职责的青蛙,许林译和王译分别直译为“司仪的青蛙长官”和“司仪”,而徐译冠以“司酒令的青蛙”,让目标语读者很快就能对自己熟悉的酒文化产生联想。对第4组青蛙三个译本都用了直译法,译文上差别不大,表述了它们可提升的肚皮空间。对最后那只具有“the patriarch”身份的青蛙,三个译本翻译各有特色。徐译着眼于目标语文化敬老的特色,将其译为“可敬的老青蛙”;许林译取其“元老”之意,译为“青蛙长老”;王译取其“家长”之意,译为“那位家长”。综合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在三个译本中徐译本归化的色彩最浓;王译坚守直译策略,许林译介于直译与归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三、结语
本文比较研究的三个中译本产生于不同年代,四位译者都称得上资深译家,都较好地完成了《瓦尔登湖》作品的翻译。但三个中译本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信息丢失或误解、误译现象。如例3三个译本都没有对“peck”这一计量词做任何说明,所以才会有“一粒谷子”和“大量的玉米”这样相距甚远的表述。例4“peck”的翻译,王注用“夸脱”和“加仑”这样英制的表达,可比性会打折扣。例5,三个译本都没有译出“wigwams”是特指印第安人棚屋、尖屋,丢失了作者原文中在“wigwams”与“hut”(简陋的小屋)之间进行对比的文化内涵。例6,对“huckleberries”一词以及相关的一些植物名称的翻译,在同一个译本中对同一植物翻译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出现,这是文化传译不准确的表现。
在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上,直译、意译,必要时加注释,依然是最主要的翻译方法。在直译和意译方面,如例1对“Pond”一词的翻译。徐译和许林译相同,都意译为“湖”;王译则直译为“池塘”,时而又意译为“湖”,给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不该有的文化困扰。例2对度量衡单位“rod”的翻译,三个译本都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进行了文化传译,不同的是,徐译和王译用“码”来解释“杆”,或者用“平方码”来解释“平方杆”,这不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而许林译用“平方米”来解释“平方杆”更易为目标语读者接受。例7可以看出在三个译本中徐译本归译的色彩最浓;王译坚守直译策略,许林译介于直译与归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译者不可能始终只用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翻译中的直译、意译与归译可互为补充,唯有将其巧妙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文化传译效果。
通过本文的研究,说明英汉文化传译中存在的文化信息丢失或误解、误译现象主要是和译者对文化因素的理解有关。这是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从理解到表达的过程”(杨士焯,2011:9)。译者要想让译文成功转化,传达文化,感知是首要的环节。同一原文,因不同译者的感知不同,对文化因素的理解不同,产生的译文也不同。“译者要对原文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有准确的判断、否则就会造成翻译错误。”(杨士焯,2012:42)译者应提高对英汉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感知、理解方面,才能灵活处理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达到文化传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