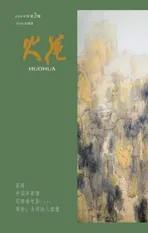穰草有情
2022-03-17王垄
王垄
儿时的秋天,当金黄的稻谷被乡亲们用镰刀一颗一把地收割干净,稻田里又显露出泥土亲切而酥软的本色,大地之上弥漫着一股迷人的清香。随着成捆成捆的稻把被人手挑肩扛运到打谷场上,乡亲们又抢抓晴好天气夜以继日地将稻谷脱粒、扬净、晒干,直至颗粒归仓。接下来的主角,该轮到穰草粉墨登场了。
穰草为何物?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也许另有多少人已猜到,穰草是里下河地区老家的人们对稻草的别称,“穰”这个字不知有多少人认不得、不会写。小时候,我替担任生产队小队长的父亲排工、记账、记工分时,遇到“穰草”的“穰”字,不晓得怎么写,抓耳挠腮大半天,最后也只得用“狼”字代替。好温暖的草被我弄得兽性十足,也算是冤枉穰草了。字典上的解释是:穰ráng,稻麦的秆,泛指黍稷稻麦等植物的杆茎,如“穰草、穰子”等。在我的故乡,麦杆(音读gai)就是麦杆,穰草则专指脱粒之后晒干的稻草。直至今天,像我八十五岁的母亲那样上了岁数的老人还仍然把稻草叫作“穰草”,说成稻草的很少很少。
记忆中,穰草是乡下人的宝贝,是世上不容轻视的有温度、有感情的草。新收的稻谷经过水牛拉着石磙一遍遍来回辗压,到最后与稻谷彻底分离时已成为乡亲们口中的“熟草”,其时它们与“生草”已有了许多的变化,那就是穰草的前身。再在秋冬太阳下暴晒几日,其间需要人工用木叉定时地翻晒,直到完全去除草中水分,草色由青黄转为金黄,便可用草葽(yao)子(一种用穰草搓或绕成的用来捆扎的粗绳)包扎成捆了。也有直接在场头田边一层层地推成小山包似的草堆(文绉绉的说法叫“草垛”,但我们那儿只叫“草堆”),乡下的孩子于是就又有了“躲星蒙蒙(即捉迷藏)”、斗鸡(另一种乡土游戏)、“打仗”等等的好去处。有时候,我和调皮的几个小伙伴爬上不高不矮的草堆顶上,什么也不做,只躺在草香四溢的草堆上,看天空、数星星,那些往事足够刻骨铭心。
那时的乡村,没有煤、电,也没有液化气、天然气,一日三餐,大锅做饭,烧的全是柴草,所以穰草和麦杆什么的,是不能随意糟蹋、浪费的,否则会被大人骂成“败家子”。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有几个草堆,大人心里才踏实。穰草经精挑细选,手工删(土话读shuan音)去旁枝岔叶,就成了齐展展的“齐头草”。那些日子,乡下到处可见晒“齐头草”的,一把把,扎成稻草人或坟滩顶的形式,也是一种特别的风景。乡亲们在屋檐下、锅屋里仔细地“收藏”着这些草们,可随时用来搓绳、打草鞋、盖屋顶等等。即使是比这些还要普通十倍的草,邻居之间相互“救急”,借一捆都是要还的,更不要说借十斤百斤千斤了。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物里就发现了一张庄上某读过些书的人借父亲稻草1145斤的欠条,应该是随着日子好转,一个忘记还、一个忘记要了。
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分穰草是我难以忘记的事情。每到分草时分,场头就人多嘈杂,顿时热闹起来。各家各户按人头或者按劳力,论斤论两,分多分少也会急得面红耳赤,我甚至还见过一两回因分草不公大打出手的场面。各家上秤称好分得的穰草堆在一边,由自家两个人一人一根“草杠”(顶端削尖的长树棍子)插在穰草底部,然后就像抬担架似地把穰草抬走,如同得胜还朝的将军得意洋洋。
说穰草有情更多的是表现在当年“挺尸的榻上”(对睡觉和床的一种粗俗说法)。像我这般年纪的人如果当年没睡过用穰草铺的床铺、没枕过用穰草揣紧的枕头,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乡下人。穰草色如黄金,柔软舒适,保温耐寒,而且终年有股奇特的草香,又不大容易生虫子,确实是农民眼中的好货,传说还被某皇帝册封过哩。穰草救命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儿时,庄上有一小子闯了天大的祸,吓得寒冬腊月躲到穰草堆里两三天,硬是没被冻伤冻死,真是穰草“创造”的奇迹了。老家还有一个传统的习俗,老人死后孝子贤孙要披麻戴孝,其中亲生的孝男孝女要在腰间系草葽子,那是穰草与人的另一种情分了。
儿时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睡在满是穰草的味道的板床上,听着席子底下发出沙沙的响声,常常能做出香甜的美梦。即使白天冒雪前往学校,也有父母用穰草、芦花、麻绳等等编成的“毛窝子”(从前的一种草鞋,或许是世上最古老的保暖鞋),纵然滴水成冰,靠这御寒“神器”,冬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如今,短短的几十年过去,穰草成了无人待见的废物。乡亲们早已用上了现代化炊具、厨具,以柴草烧大锅的寥寥无几。被大型收割机光顾过的稻田,遍地撒满了稻草,如何处理竟成伤脑筋的事。每到秋收秋种时节,乡村的高音喇叭及巡回宣传车上便整天叫喊着“严禁秸杆焚烧”之类的通告,随意“放火”烧穰草已是违规违法的行为了。好在聪明的家乡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相关企业,对包括穰草在内的秸杆进行综合开发和科学利用,终于使人见人厌的穰草们变废为宝有了较好的结局。但与穰草有关的回忆,以及对乡村沧海桑田的感慨,却时常浮现在脑海、生动于内心,久久挥之不去。
郑渡老街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叫郑渡,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柳堡乡政府的所在地,后来因撤乡并镇慢慢湮没在岁月流转之中。如今,郑渡还在,但那条古典的老街,却消失殆尽,只有无数干净、温暖的镜头留在记忆深处,让我及少数带有怀旧毛病的人独自咀嚼、回味那古朴、纯真的过往,仿佛有一张黑白胶片,在郑渡老街的唱机上旋转,值得怀念的时光便一一重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穷且缓慢的时代,如果采用倒叙的手法,我们可以看见长满青苔的童年,在以青砖黛瓦作为外衣内饰的老街小巷里穿行。其实用现在的眼光丈量,那条东西走向的老街最多不过千米,但在儿时的眼中却如天上的街市。最东端临河处是供销社的码头,最西端则是粮站,当年的繁华、热闹尽在这狭长有限的老街上演。“老街虽小,五脏俱全”,从东到西,肉案子、老澡堂、裁缝铺、烧饼店等等,应有尽有,就连为死人“张罗”寿衣寿烛的门面也赫然在一旁,乡野村童即使再野,也轻易不敢朝它随意张望。
记忆中,老街南北两边的居民点里,排列着一条条狭窄、幽深的小巷,最窄处只容一人单行通过。小巷里有着凹凸不平的砖路、石子路,四周布满土墙、砖墙。这里的街坊邻里大多姓郑,其他杂姓寥寥无几。倘若叙起家谱来,几乎都有共同的郑氏祖先,在一个门头甚至“五服”之内的更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为了芝麻大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姓之间大打出手、最终落得老死不相往来的也不鲜见。
大人的世界,孩子们永远不懂,也从来不管那些鸡零狗碎。小伙伴们相互串门,或者走街串巷,亲如一家。大家尽兴地玩着抓瓦子儿、跳橡皮筋、格房子、捉迷藏、斗鸡等等游戏。老街上传来的喧闹,似乎与孩子们无关,只有玩到肚皮响如鼓时,小巷里家家户户争相发出的锅碗瓢盆之声,才会引起饥肠辘辘的小子们的注意。老街西北角有一家面食店,那里的麻花子能让人馋得流口水。偶尔,我们也会从家里的米缸里偷点米藏在书包里,等放学路过这家面食店时用米换些麻花子吃。解过馋之后,便在小巷里打纸角、砸钱溜子,有时也去尹瘸子家捣桌棋……要是被大人知道了,少不得“享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最喜欢的是逛供销社,里面不但有花花绿绿的布匹等商品吸引眼球,还有烟酒糖醋等混合的气味让人百闻不厌。那时,乡下还没有书店,但供销社里有两三节书柜,专卖小人书、作文书,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著。那里便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我平生所拥有的第一套“四大名著”就是用年终可怜兮兮的奖学金在郑渡供销社书柜买得的,至今还没有舍得扔掉。当年,郑渡也没有电影院,但供销社门口的老街上经常放露天电影。每次有电影的当晚,老街上就像过年似的,早早就有人家炒好瓜子、摆好板凳、抢好位置了,四乡八邻的人们也会赶过来凑热闹,老街见证了那个特殊年月的喧嚣和温暖。
老街西首有一小邮局,门口摆放着大大的邮筒,穿着绿色工作服、骑着绿色脚踏车、驮着绿色邮布包的“送信的”每天穿梭在老街上。邮局大厅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读书模样的人,面前摆着一块小牌子“代写书信”。那时替目不识丁的乡下人代写家信、拟发电报等是种职业,但收费也极其低廉。其时,我已开始向报刊杂志投稿,常常把写好在方格稿纸上的习作灌进信封里,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塞到邮筒里,企盼着有哪位好心的编辑能打开我的信封看稿、审稿并使之变成铅字。尽管一次又一次寄出去的“作品”都如泥牛入海,毫无音信,但老街却真真切切地记录了我最初的文学梦想,至今想起仍是刻骨铭心。
我长大上学之后便离开了郑渡老街,后来的郑渡老街也逐年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当年的小屁孩都一个个地老了,当年的老街却再也不见零星的踪影。原来的供销社地基上建起了一座复兴庵,庙门前一副对联是“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也不知面目全非的老街上究竟有几人懂得其中的含义。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城镇化节奏的步伐,习惯了抖音与麻将之声不绝于耳的生活。偶尔返乡陪同风烛残年的母亲去郑渡购物,逛逛从前的老街,自然会念叨起旧时的光影。木心先生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此闲适、恬淡、纯粹的日子已经不会再有了,郑渡老街的诗意被我夹在一本黑白相册里、写在无人欣赏的诗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