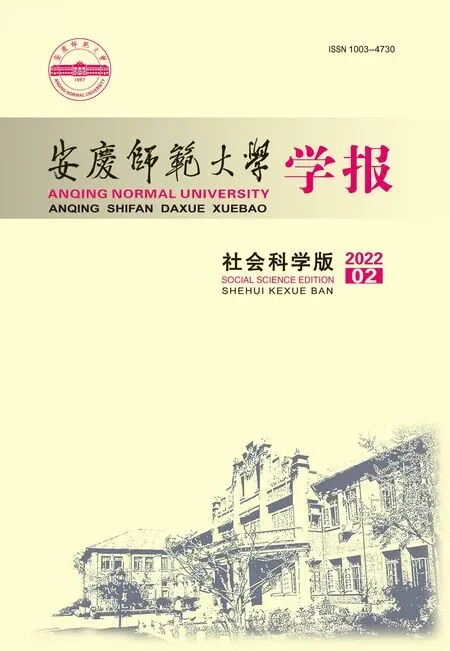“十召坚辞一羽毛”:方以智“十辞疏”考论
2022-03-16郑晨晨
郑晨晨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面对易代之际的乱世纷争,在以身殉国未果的情况下,他毅然逃禅,成为明遗民中的代表人物。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方以智的生平事迹一直备受关注,但学界所论多是关于他的逃禅和死节,其南明永历年间长达四年之久的辞官行为,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实际上,方以智的辞官发生在亡国和逃禅之间,是其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其自身,乃至整个永历朝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容忽视①亡国作为最惨烈的时代背景,深刻影响着方以智其后的举动,自然也包括辞官行为,而逃禅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看作是方以智辞官选择的接续。若能清楚揭示出方以智辞官的缘由,那么诸多与此有关的行为也将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其时,南明朝廷偏居一隅,政权更替不断,内忧外患不绝。当权者们却深陷权力的争斗,无意为复国而战。南明的形势岌岌可危,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危难之际,永历帝数次以内阁大学士之职征召方以智,方以智却坚辞任命,于辗转流离中留下了扣人心弦的“十辞疏”②关于“十辞疏”,学界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仅陈璐的硕士论文《方以智散文研究》(闽南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90-95页)中有所论及,作者虽对方以智辞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并未展开深入探究。。在这十封辞疏中,方以智对辞官一事作了详尽的解释,其中不仅涉及到其本人四年间的遭际,对南明的时局也多有论及。因此,我们得以返回现场,对方以智的心路历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历史线索,展开更为深入的探析。
一、“十辞疏”的篇目界定
“十辞疏”是永历元年(1647)至永历四年(1650)间,方以智为辞永历帝内阁之召所作的十篇文章。当时,南明永历帝初立,方以智代言颁布,后任宫詹。因与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坤不和,放舟而去。岂料,元年二月初五,永历帝复以东阁大学士之任召之,方以智力辞不就,故作“十辞疏”。其所作诸篇虽名为“十辞疏”,其中明确题为辞疏的,却仅有《四辞请罪疏》《六辞入直疏》《七辞疏》《八辞疏》《九辞疏》《十辞疏》六篇。经笔者推论,余下四篇应为《答吴年伯书》《夫夷山寄诸朝贵书》《夫夷山再辞疏》和《请修史疏》。
首先,从时间上看。《四辞请罪疏》和《六辞入直疏》的创作时间均十分明确,分别作于戊子(1648)八月和己丑(1649)九月。据此,前三封辞疏必然作于永历二年(1648)八月之前。《四辞请罪疏》中又提到“臣自元年三月再疏陈辞”[1]588,说明上一封辞疏应当作于永历元年三月,意即前三封辞疏均作于永历元年,且永历帝初次下诏是在元年二月,如此便进一步将范围缩小到永历元年二月至三月间。符合这一条件的有《答吴年伯书》(作于二月)、《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作于三月)。五辞疏则应作于永历二年八月至永历三年(1649)九月之间。符合这一条件的有《请修史疏》(作于永历二年十二月)和《寄朝中诸公书》(作于永历三年春)。其次,就内容而言。在明确题为辞疏的六篇中,《四辞请罪疏》衔接了前三封辞疏与之后的数篇辞疏,内容显得尤为重要。疏中,方以智首先详细描写了元年三月至今的经历,来解释何以对永历帝之召未有应答。并随即就此自陈其罪:
一年以来,臣凡八奉温纶,三蒙特使,而臣曾不能一有应答,此则臣之罪也!权奸乱政,臣每畏忌其锋,不能抗疏劾争,此则臣之罪也。丑■凭陵,臣仅万苦伏匿,自保短发,不能起义婴城,与萧旷等骂贼而死,此则臣之罪也[1]590。
永历元年至二年间,永历帝数次专派特使,以内阁之职召方以智入朝。方以智本人亦在《九辞疏》中写道:“从来朝廷召用新卜,不过降麻,敦起耆旧老成,方遣专使。”[1]598永历帝的厚遇由此可见,但方以智始终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君有诏而臣不应,这在当时堪称逆罪。因此,方以智必然要对辞官之事有所交代,这也是他会以较大篇幅记录行程的原因。只是,此处所列的后两条却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权奸当朝,方以智以未能弹劾力争为己罪;贼军频至,他又以未能誓死与之抗争为己罪。既是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愧疚,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则更应入朝为官、施展抱负。然而,方以智似乎并没有发愤图强的打算,反倒以此“三罪”为辞,试图婉拒永历帝的征召。可见,不论内中有何曲折,方以智的最终目的都是在于辞官。
其实,在辞疏的开头,方以智就已明确提出“乞赐处分事”[1]588,文末又再次“伏乞明赐处分,以肃纲纪”[1]590,足以看出他的决心。至于辞官的原因,从文中来看,应是对自己的“才之不堪”[1]590有所顾虑。且疏中有“阁臣”明旨,说明永历帝征召的职位便是内阁大学士。也就是说,《四辞请罪疏》是永历二年八月方以智为推辞内阁之任所作的辞疏,辞官的原因是自觉才能不堪。
此后的几封辞疏中,方以智均表达了不愿出任内阁之职的想法。《六辞入直疏》中明确写道:“伏乞皇上收回阁衔,免其入直。”[1]594《七辞疏》亦称:“实无分毫之功、尺寸之才,何敢叨冒宰相,以误国欺君?”[1]595《八辞疏》以为:“疏散之才,实不足以济国匡时。”[1]597《九辞疏》则认为:“臣之不可为宰相,非独臣自知之审也,人皆知之。”[1]598《十辞疏》坚称:“才卑庸劣,叨留史官,已为过分,何敢冒忝揆地,误国苟荣?”[1]600方以智固辞的态度十分明确。由此可见,“十辞疏”的主旨便是固辞内阁大学士之职,且这一主旨在十封辞疏中贯穿始终。
既然要达到辞官的目的,那么方以智所作辞疏中必然有明确推辞的言语,且相邻辞疏之间应有一定的连续性。《答吴年伯书》开篇即提到:“不谓复滥及此,捧纶读谕,病人惊惧失魄矣。”[1]511此当是方以智首次奉诏。《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中称“得吴年伯书,始知不免”[1]512,并以“三不能”“三可笑”“三不便”为由推辞。以此推测,吴炳的来信即是就内阁之召规劝方以智,故而才有后文的“求以原官”[1]513,可惜此文今已不见。另外,《十辞疏》写道:“臣第三辞疏,引郑綮之辞。”[1]599《夫夷山再辞疏》中恰有“唐郑綮之歇后之诮”[1]588云云,且辞疏中亦有“若非常之任,则臣万万不敢冒受,以误国家”[1]588的说法。因此,《答吴年伯书》《夫夷山寄诸朝贵书》《夫夷山再辞疏》三篇应属辞疏无疑。
至于《请修史疏》和《寄朝中诸公书》,前者明显是为辞官而作,后者则仅是就时政发表看法、提出建议。《请修史疏》的开头,方以智就誊抄永历帝的诏书,以示对圣恩的感激。虽有表达出为史官的意愿,但他的最终目的仍是推辞阁职。正如文中所述:“倘蒙天恩,罢其入职,但守翰院,老为史官。”[1]591也就是说,史官之职只是方以智的以退为进。此外,《六辞入直疏》中也提到了《史学自当尽职》一疏[1]592,即《请修史疏》,表明两封辞疏是前后接续,并有所关联的。综合来看,五辞疏当是《请修史疏》。
综上,笔者以为,就现存材料来看,方以智的“十辞疏”应是《答吴年伯书》《夫夷山寄诸朝贵书》《夫夷山再辞疏》《四辞请罪疏》《请修史疏》《六辞入直疏》《七辞疏》《八辞疏》《九辞疏》《十辞疏》这十篇文章。在这十封辞疏中,方以智明确表达了不愿出仕内阁之职的意愿,并罗列了各种理由来说明辞官的合理性。在南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情形下,方以智的济世之志本可有机会得以实践,他却坚定地数辞征召,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二、“十辞疏”中的辞官缘由
“十辞疏”中,方以智坚定地表明了不愿出任阁职的态度,但毕竟是呈给永历帝的辞疏,应当要有合理的解释。因此,在十封辞疏中,方以智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给出了辞官的几个理由。
(一)身患痼疾之限
方以智在“十辞疏”中反复强调了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劣。《答吴年伯书》中,他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成病人,称“捧纶读谕,病人惊惧失魄矣”[1]511。此外,他还自陈病史:“自木石海滨,冤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即发。”[1]511-512不仅如此,已然危重的病情尚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近日呕血之后,益觉虚仆,目昏气逆,头大如箕,顾影残生,无复人理。”[1]512《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中,他又将病情列为难当重任的“一不能”,写道:“病且一年,今桂林复发之后,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见,加以气逆,一有所思,则晕大如斗,何以胜劳乎?一不能也。”[1]513次月,方以智作《夫夷山再辞疏》,更是自称“年来忧愤,遂得痼疾,人且怜之为废人矣”[1]588。《四辞请罪疏》中也不乏对身体状况的描写,如“冒病投小艇”[1]588“孤身强病”“稿身骨立”[1]589,都在无意间透露了积病未愈的情况。《请修史疏》亦称“疾病连年,虑入骨髓,近者粗能拜起,而腠理已残”[1]591,且特意强调“此诏使臣之所亲见也”[1]591。《六辞入直疏》则进一步说明了“积病以闲可养,狂直以冷可免”[1]593的动机。《九辞疏》也提到“病骨支离,毫无资藉”[1]599。《十辞疏》中,方以智则再次于请罪后表明自己已是“木石残喘”,不仅“旧疾时发”,且“膏肓之症,增发无次”[1]600。并第一次明确辩解,“非直以病为辞”[1]600。显然,方以智的病贯穿“十辞疏”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时年方以智36 岁,在他早期和同期的作品中均有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据笔者统计,此前,方以智所患的疾病主要包括消渴、痈疽、水肿、眼疾等①方以智的诗文中多有关于所患疾病直接的记载。消渴病:《病中作万索诗书此》有“消渴**行”(《方以智全书:第九册》,黄山书社,2018年版,第108页);《又用前韵》有“醉饱反令消渴甚”(同上,第137页);《秦淮漫兴十首·其七》有“消渴伤心学酒徒”(同上,第198页)。痈疽:《怀龚孝升蕲令·其三》有“中年恐病疽”(同上,第93页);《又与农父、克咸夜谈作》有“腹心此日患痈疽”(同上,第164页)。水肿:《闻事有感》有“腰肢患疾偏生肿,手足皆疲更剥肤”(同上,第138页)。眼疾:《过梧州卡》有“病眼耐摩挲”(《方以智全书:第十册》,黄山书社,2018 年版,第257 页);《病目》有“欲除文字障,左目竟无光”(同上);《书周思皇纸》有“止匡庐,养翳目”(同上,第29页)。按,笔者以为,方以智所患的主要疾病是消渴,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糖尿病。。这些疾病深深困扰着方以智,在他的诗中时常能见到诸如“今岁妨多病”(《乙亥元日侍大母仲姑坐志感》)[1]83、“寒暑常有疾”(《自简少年所作率尔放歌》)[1]48、“一病尝旬月”(《出入愁十首·其十》)[1]95的记载。疾病对方以智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他的结局都曾被认为是“疽发背而死”。
“十辞疏”中,方以智所提到的疾病主要包括虚劳和心悸②虚劳:《答吴年伯书》载有“近日呕血之后,益觉虚仆,目昏气逆,头大如箕,顾影残生,无复人理。”心悸:《夫夷山寄诸朝贵书》载有“即得怔忡惊悸、呕血头晕之症。”虚劳是现代医学的慢性消耗性和功能衰退性疾病,心悸则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心律失常。。同一时期所作的《九龙盆饭僧题辞》中,也有“理疴莲潭刹中,日与芐苓伍”[1]514之句,芐即地黄,苓即茯苓,二者很可能是方以智用以调治身体的药物。其永历三年所作的《祭姚默先文》中,亦有“入山病矣”[1]553的记载。此外,他还在此时期所作的数篇文章中自称“病夫”。不难想见,疾病确实对方以智造成了较大的困扰。而且吴炳和方以智原本都是追随永历帝的,后因方以智“仓促载病”[1]605,才追驾不及,这也就意味着疾病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行程。因此,“十辞疏”中所描述的病情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症状是否像方以智所陈述的那般严重,却要另当别论了。
辞官期间,方以智几经辗转,四处逃亡,如果他的身体状况确如描述的那般恶劣,恐怕很难承受长途奔劳。且从方以智之后的行踪中也不难看出,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一直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即使身患多种疾病,他依然笔耕不辍,并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斗争。可见,痼疾缠身固然对方以智的抉择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不是其辞官的决定性因素。乱世之时,士人们常以疾病为喻,表达对家国天下的忧患之情。方以智很有可能也只是以夸大的疾病症状,来表明其忧国日久、心系天下的情怀。
(二)性情狂直之虑
病情之外,方以智也多次论及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在《答吴年伯书》中,他自称“贱性狂直,外放内狭,与人龃龉,动而得祸”[1]512。《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中他则将“贱性狂直”列为“二不能”,并补充以“见人之不善,则若不能容。今日之势,能一刻与人处乎”[1]513。此外,“三不便”也是“贱性外和内方”[1]513。性情方面,方以智还始终以“狂”自认①“狂生”称谓在方以智早年的诗作中也经常出现,但当时所谓的“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倒不如说是由现实遭遇而产生的一种宣泄行为。与年少时的慷慨悲歌不同,此时,方以智再次以“狂”自认,面临的境遇比数年前更加严峻。乱世中,死生只在一瞬间,如果连自身都难以保全,更遑论为国效力了。因此,在宣泄之外,方以智的这种行为可能也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夫夷山再辞疏》称:“臣秉性疏直,动即多忤,半生消肮脏于诗酒,人目之为狂生。”[1]588《九辞疏》亦有:“臣不惟半世疏狂,无益世事,兼且天性直率,动与物忤,觏闵受忌,无祸不历,以言仕宦,竟属废人。”[1]598《十辞疏》也称:“臣性疏易,少颇不羁。”[1]599
不难看出,性情狂直也是方以智辞官的原因之一。他在早年即意识到:“智性疏散,不知事事,言语过失,多不能免。”(《膝寓信笔》)[2]方以智自知性情疏散,很容易有所过失而得罪于人。当前的局势之危急,更让他很难不有所顾忌。显然,性情狂直也是方以智的托辞,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避祸。至于何以需要避祸,细读之下,便可在自称“狂直”之余窥见祸事的源头,即与朝臣的政见不合。《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中的“一不便”和“二不便”正展现了这种政见不合:
弟议废三衙门,以六曹带之,分班直中书,又欲废巡方、废监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愚议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几空,得无怪乎?二不便也[1]513。
议废之事不可行,议行之事不可用,方以智为官的意愿难免会有所消减。况且,这两条仅是针对朝廷的行政制度而言,便已无法实行,那么,在根本性问题上的分歧之大就更加可以想见了。乱世之中本就难以自保,若再与当权者有所抵牾,自身的安全将更加难以得到保障。更何况,方以智之所以辞去宫詹之职,正是因为王坤的弄权。
此外,方以智的被举荐亦不排除与党争有所关联。虽无确切史料记载,但由吴炳之寄书可知,他在此事中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吴炳是由瞿式耜推荐入阁,且方以智与作为父执的瞿式耜往来密切,瞿式耜亦有规劝方以智的举动,或可推断三人间存在着某种更为隐秘的联系。瞿式耜《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中曾称:
上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今须博学词臣,大开经筵,终日讲学究,而内去其口衔无宪、擅作威福者,毋使炀灶;再得一二有担当力量阁臣,每事主持;不为群奸所煽,将来犹可想望太平[3]258。
在瞿式耜看来,南明太平中兴的关键之一就是为永历帝寻觅良师。此前他对方以智的称呼便是“词林方以智”,可能正是将辅佐永历帝的希望寄托在了方以智的身上,毕竟方以智在崇祯朝就曾担任过定王讲官。而且,瞿式耜对当时的内阁构成颇为不满,其《戊子九月又书寄》中称:“朝中宰相则江西王化澄、浙江严起恒、吾乡朱天麟。朱天麟吾所荐者,而不合时,合时者惟严一人,以善媚人逢时也。”[3]266严起恒与当时的锦衣卫文安侯马吉翔勾结,相为表里,几乎垄断了军国大事的决定权。方以智对此事也是了然于心,因此才会自称已“局外久矣”,似是有意地与南明朝廷脱离,并试图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脱身。
不仅如此,入阁后的方以智还会成为清廷的重点关注对象,甚至牵连其家人、朋友,给他们带去巨大的灾难。明遗民若被清廷追捕,往往牵连甚广。方以智的好友陈子龙便身遭此祸,清廷对涉嫌窝藏陈子龙者大肆追捕,受牵连者多达五十余人。方以智的《灵前告哀文》亦证明了这一点,文中称:“家乡传闻,遂令大人有子相南海之嫌,迫令索归,受尽委迮,洗橐幸免。”[4]35这也就意味着,仅是征召之旨已经给方家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方氏家族历来以孝著称,方以智本就因不能侍奉老父膝下而心怀愧疚,自称“为子者竟未能尽一日菽水之职”[4]34,必然不愿再因入阁而牵连老父②“十辞疏”以外,方以智也曾透露出辞官的原因,即为白发老父故。他在《辛卯梧州自祭文》(《方以智全书:第十册》,第4页)中称:“流离岭表,十召坚隐,不肯一日班行,为白发也。”《象环寤记》(《方以智全书:第一册》,第393页)亦称:“然中丞公白发在堂,眦为之枯,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正以此故。”他的好友钱澄之也在《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田间文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79页)中写道:“屡诏不起,无他,为有老亲在故乡也。”忠臣与孝子的冲突古已有之,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也确实因担心他的安危,多次劝其归隐山林。另据《祭直之弟文》(《方以智全书:第十册》,第9页)记载,流亡期间,家人在与方以智的通信中“独嘉”其之不仕,以为“将谓择祸,犹可免累”。可见,家人对方以智的辞官是知情且十分支持的。这应当与方孔炤晚明时期的遭遇有一定的关系。。
总结而论,方以智自认性情狂直,故与朝局格格不入。此种情况下,不仅无法为国效力,甚至难以保全自身。他在辞疏中就曾提到,“今且出而死”[1]512“今出则速死”[1]513。意即借性情狂直之由,行全身远害之实。方以智虽不惧为国献身,却并不期望以此种方式遭祸。因此,更准确地说,他是看清了南明朝廷的腐败和政治的昏暗,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更不愿为党锢之争作出无谓的牺牲①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以为,方以智“虽然祟尚东林精神、积极主盟复社,但他思想上却认为党争是为了各自的私利”。宋豪飞《明末桐城方以智与阮大铖两大家族交往考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第78页)也认为,方以智与阮大铖的矛盾“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阉党势力与复社清流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党争延续和矛盾的逐步激化的反映”。。因而将过失揽到自己身上,以性情狂直之虑为辞。
(三)才能不堪之忧
“十辞疏”中,方以智还反复提到自己的才能不堪。他在《夫夷山再辞疏》中称“马齿未及四十,历官不满两年”[1]588“不敢以后进浅俸,逾越老成”[1]588,故无法承担“中兴恢复之相”[1]588的重任。《四辞请罪疏》中写道:“至于臣才之不堪,则臣前三疏,哀辞恳切,已渎圣听矣。”[1]590《七辞疏》以为“无分毫之功、尺寸之才”[1]595。《八辞疏》则自称“不足以济国匡时”[1]597。《九辞疏》指出:“臣之不可为宰相,非独臣自知之审也,人皆知之。”[1]598《十辞疏》亦称:“本为才卑庸劣,叨留史官,已为过分,何敢冒忝揆地,误国苟荣?”[1]600
可以看出,才能不堪之忧也是方以智辞官的重要原因。在方以智看来,为相之人必须声望极高,能使天下信服。“朝廷用一人,必先养其资望,足以服天下;练其才具,足以理庶务”(《夫夷山再辞疏》)[1]588;“朝廷用一相,必其心有以自信,又必养其望,使天下皆信,然后参赞佐理,内外咸服”(《九辞疏》)[1]598。粗略来看,方以智所虑确是事实。相较而言,他年纪尚轻,为官时间尚短,并不是宰相的最佳人选。而据《小腼纪年》记载:“明征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前大学士王锡衮入阁,道阻不至,乃以前朝翰林学士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5]似有退而求其次之嫌。况且,在前辈重臣面前,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方以智都不可能坦然受命。
不过,永历帝的数次下诏必然是有其考虑的,正如诏书中所称:“卿天人实学,忠孝世传;鼎铉弘谟,人伦师表。……实望卿居端揆之任,理机务之繁,树表于朝廷,则四方豪俊,知所归依;发策于疆场,则远迩群英,共夺挞伐。”[1]595显然,永历帝十分看重方以智,尤其是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据《明季南略》记载,当时南明群臣粉饰太平,如醉如梦,“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三人”[6]421,方以智便是其中之一。且直到《青原志略》中,尚有人认为其“当见宰相身,可使邦国活”[7]。因此,方以智的才能显然是得到时人认可的。若非如此,吴炳也不会致书方以智,力劝其出山辅政。此外,瞿式耜也有《庚寅八月,方密之相国四十初度,敬赋二律申颂,促其入朝以慰圣眷》诗,称“为君置酒兼成颂,须及銮舆早出关”“为语谢公高卧久,承恩四载急从王”[3]232。钱澄之亦以“兴朝大政需公出,早办收京并马归”(《昭江寿曼公四十》)[8]相劝。余如刘湘客、丁时魁、金堡等,均曾力劝方以智入朝。他们的敦促,应当都是出于对方以智的认可。
同时,方以智对自己的能力也是有信心的。他的诗中就曾有“生小逢乱离,长大学军务”[1]46之说,《方以智先生年谱》也称其“专心于致用之学,并学习兵事”[9]63-64。身处“天下多事时”[1]52,方以智密切关注时局,常针对重大事件拟策。因建议始终未被采纳,他不禁发出“我独困蓬蔚,被褐行且迟”(《吴门遇卧子作兼寄舒章》)[1]52、“被褐困草莽,所望无一遂”(《舟次三山,阻风不进,欲投梁父,遂徒步至芜阴,夜雨雪。翌日,冒寒至其设,见其儿女想与,感慨赋此三章》)[1]54的感慨。甚至在写就《夫夷山再辞疏》后,他还呈上过《刍荛妄言》,条分缕析,积极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由此可见,方以智并无才能不堪的担忧,反而是多次献策不被采纳,让他在焦虑之余,渐生隐退之心。
因此,当南明王朝出现中兴转机之时,在“弹冠者遍地……一时人情咸以出仕为荣,不仕为辱”[6]250的情况下,方以智坚隐不出,并再上《四辞请罪疏》。所虑之事仍是:奸臣当道,却无力抗争;国难深重,却不能为国献身。尽管如此,他还是以“才之不堪”为由,婉拒了永历帝的再次征召。不可否认,在动荡的时局面前,方以智或许确实有过才能不堪、难以胜任的担忧,但他的济世之心可昭日月,面对残破的南明王朝不可能无动于衷。据此推测,方以智反复强调自身的才能不堪,应当都只是谦辞而已。并且,在自谦之外很难不感受到他的无奈和失望。即使是在危急的局势下,才能不堪也尚可补救,而南明王朝日益显现的颓势已然无法挽回。
(四)不入班行之誓
方以智的“自矢不加官”之说也多次出现在“十辞疏”中。《答吴年伯书》中称“未尝一日列班行”,因“向在端州会议,原自矢不加官”[1]512。《夫夷山寄诸朝贵书》也提到,“当端州会议,自矢不加官”,因此“自圣人登极以来,未尝一日立朝,一事与闻”[1]513。《夫夷山再辞疏》亦称:“一则自矢不加官。”[1]587同一时期所作《赠诏使》诗中,也有“辞官因血誓,忧国仗天心”[4]222之句。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更是反复强调“始终未尝一日立班行”(《与程金一》)[1]526、“智未尝一日立班行”(《寄张尔公书》)[1]530、“自登极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与金道隐给谏》)[1]551。
据此可知,方以智似乎曾有过“不入班行”的誓言,只是未见相关资料。但结合上下文不难发现,除了反复说明“自矢不加官”,方以智还一直在强调一个时间节点,即“端州会议”时。《九辞疏》中亦论及了这一问题:“即自皇上监国时,臣议开创之政,一切与人不合,得罪首辅,从此暌违。”[1]598也就是说,方以智的不入班行是以端州为始的。那么端州所议究竟是何政策,才会导致方以智“自矢不加官”呢?这从他的《刍荛妄言》中可以见出端倪。《刍荛妄言》第一条就是关于制度的更改:“端州之始议曰:‘以行在为大营盘,天子如总督,群臣如偏裨,不设百官,不用部覆,君臣同心,文武戮力,鱼水之深,义犹朋友。’”[1]601这里所说的始议,应当是指永历帝登基时与群臣议定的行政制度。其主旨是不设置官职,减少繁杂的程序,君臣同心,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复兴明朝基业。
“本龙来自糖人国!”休息足够,糖龙的身体也恢复到原来的硬度,它坐起来昂着脑袋,龙须也显得格外飘逸。糖龙因为由糖制成,遇水遇热身体便会融化,一疲劳身体就会变软。不过,这糖龙的性格倒是像龙一样高傲呢。
如此,前文所议“二不便”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它们针对的其实是永历帝登基之初所设立的制度。因为种种原因,这种制度并未得以实行。方以智的不入班行,也不是真的拒不为官,而是对“不设百官”这一政策的坚守,因此,他不仅在“十辞疏”中,也在写给朋友的信件中,频频强调不入班行。端州所议还提到要“文武戮力”,方以智就曾致信时任督师的何腾蛟说:“为今之势,各督各镇,戮力同心,天子为神祖之胤,中原有不归命者乎?”(《寄阁部云从何公》)[1]524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武力为先的时代背景下,南明朝廷多由武将拥立、操纵。“自弘光朝廷以来虽然任命了阁部、总督、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大抵仅拥虚名,实权分别掌握在盘踞各地的军阀手里。”[10]623-624军阀们则“因袭了过去朝廷上党争故套,一切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害为转移,国家大局被置于脑后”[10]401,永历朝更是如此①详情参见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永历朝廷的内部党争”一章。。永历帝不仅放任武将的跋扈,还试图通过任命官职来笼络人心。
由此,我们得以追溯到方以智辞官的源头。面对复杂多变的时局,方以智始终坚守初心。但是,他的进言并未被永历帝采纳,且又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进言未被采纳意味着他的理念没有得到认可,得罪权臣则意味着他的理念在未来也不太可能付诸实践。方叔文就曾针对这一点发表看法:“公非偷安忘事也明矣。徒因开创建议时,即与首辅相忤,且佥任盈廷,魁柄陵替,一二正人君子,几无立足之地,不惟恢复无望,即欲少申正气,暂守偏隅,亦不可得,故公十疏哀辞,岂得以哉?”[9]141方以智的无奈被充分地解读出来。因此,不入班行之誓归根到底也是方以智的托辞,他是想借此来提醒永历帝,同时表明与当事的不合,以及远离朝堂的愿望。
至此,方以智的辞官疑云得以揭晓,十辞阁职无疑是其人生的重大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更可谓影响深远。综合来看,身患痼疾确实限制了方以智的部分行动,性情狂直也着实容易招致祸端,才能不堪或许确是他的担忧之处,但其辞官的最主要原因应是碍于不入班行之誓。而在不入班行的背后,则隐含着方以智对永历朝廷的心灰意冷。甚至可以说,方以智的这种失望是从崇祯朝就开始累积的。初入朝堂,方以智便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冲突;亡国后,他更是不得不直面信念的崩塌。“十辞疏”中亦存在着由矛盾到无奈,再由无奈到失望的态度转变。方以智一度积极救国,忍死以苦守志节,只是在认清现实后,他才最终对南明朝廷彻底失望。
此后,方以智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出任内阁之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朝局。南明阁臣已然权力不足,无法真正地参与国家政治,发挥应有的上传下达作用②顾诚《南明史》(同上,第602页)中对瞿式耜的慷慨就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可以转移的时候不肯转移,宁可束手待毙”,原因之一就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瞿式耜本人亦在家书中写道:“只是目前局面,凡勋镇之强梁跋扈者,则奉之惟恐不及,而留守、阁臣与地方抚、按,直视为可有可无。”(《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瞿式耜当时已身处内阁,可以说是永历朝的政治中心,但他仍然无力改变南明的局势,足以看出阁臣之职已今非昔比。。由此亦可见出,方以智作“十辞疏”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辞官,更意在表达对南明政局的不满和怒其不争的无奈。从半壁江山到残疆剩土,南明王朝败给了清军,更加败给了内耗。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方以智才失望地走上了另一条反清复明的道路。其后的逃禅虽是无奈之举,却也从侧面说明,方以智已不再寄希望于南明朝廷,而是试图以民间的抗争力量实践复国大业。凭借着自己的号召力,方以智尝试唤醒遗民们对故国的情感,戮力同心,共图恢复大计。反观南明朝廷,则依旧沉浸在内部斗争中,渐失民心。终于,在1650 年底,桂林被攻破,永历帝再次踏上逃亡之路,永历朝廷已然形同瓦解。
三、“十辞疏”在遗民研究中的价值
“十辞疏”作于南明永历元年(1647)至永历四年(1650),此时南明王朝经历了三个统治政权,仍在苦苦支撑。放眼而观,遗民群体无疑是这一时代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作为遗民代表人物,方以智的经历和创作鲜明地反应出这一时期遗民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为遗民群体及其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就“十辞疏”而言,它不仅展现出遗民生存状况的恶劣,而且凸显出遗民心理状态的复杂,最重要的是,还呈现出遗民文学的真性情。
(一)展现遗民生存困境
从“十辞疏”中不难看出,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方以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遭受着沉重的折磨。
此外,方以智还面临着心理上的折磨。身处恶劣的环境,在辗转流离、为国忧思的同时,他还遭遇着道德伦理层面的苛责。因为拒绝入仕南明,他已然引起不少非议,此后的逃禅则更有甚之。全祖望在为《周囊云文集》所作的序中就曾写道:“方阁学以智,熊给事开元,皆逃禅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为君子所讥。”[11]1211虽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些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尚有迹可循。其《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有云:“公(黄宗羲)弟宗会,晚年亦好佛,公为之反复言其不可。盖公于异端之学,虽其有托而逃者,尤不肯少宽焉。”[11]219黄宗羲对“有托而逃”者严苛的道德审视,可见一斑。其《亭林先生神道表》记载:“方大学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书招先生为助,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11]231顾炎武亦将逃之世外视为最下之选择。
可见,即使是在遗民间,也横亘着巨大的道德鸿沟,亦足以见出遗民们所处境地的艰难。“在这种责以死节方是完人的极端化伦理氛围中,易代士人——尤其是声高誉隆者——难免会陷入生隐与死殉二难抉择的政治伦理困境,遗民群体选择了生隐或斗争,这并不能消弥殉节者所带给他们的政治伦理焦虑。”[12]这就意味着声名越大的遗民,所受的世俗之累也越重。方以智即深为声名所累,这一点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了他的多病上。
虽是以病为辞,但方以智的病是真实存在的,且这些疾病均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①前文已论及方以智所患疾病,主要包括消渴、虚劳和心悸。消渴可能的病因应是情志失调和先天不足。这在方以智的六叔方文的《疽叹》(《方嵞山诗集》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88页)一诗中可以得到部分的验证。诗中细致地描写了两年内两次病疽的经过,并分析得出了病因病机:“二疽但属厥阴经,肝火郁抑气血停。内淫发于怀抱间,坐卧行立各不宁”。明确了“肝火郁抑”是导致两次病疽的原因,肝火郁抑即属于情志失调的表现。考虑到方文和方以智的叔侄关系,尚不排除遗传,即先天不足的可能性。虚劳则常由先天不足、情绪失调及久病失养、病后失治等引起,故消渴很有可能进展为虚劳,且情绪失调会导致病情加重。心悸病情较轻者为惊悸,病情较重者为怔忡。大凡惊悸发病,多与情志有关;怔忡则多由久病体虚所致,亦与情志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所患疾病的发生、发展大多与情志失调有关。在描述病情时,他也将病因归结为“年来忧愤”[1]511“冤愤入骨”[1]511,虽然只是简单地提及,其背后的含义却颇值得深究。此外,方以智的病疽①潘务正《“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文史哲》,2016年第6期,第141页)中指出,“明清之际‘疽发背而死’是载集中遗民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死亡方式,与屈原自沉汨罗江、文天祥英勇就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疽发背传达了遗民的心曲,体现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和忧患意识。以及症状上的呕血和头晕等,均极具冲击性,亦蕴含着强烈的情绪情感色彩,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对黑暗现实活生生的、最惨烈的反抗。遗民们的生存困境亦由此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揭示遗民心理冲突
“十辞疏”同样揭示出遗民们最激烈的心理冲突。他们既对南明王朝保持绝对的忠诚,又因朝政的腐败而对其失望至极。
方以智对南明王朝即怀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自幼受到忠孝思想的影响,对皇室正统忠心耿耿。马其昶《方密之先生传》有云:“自先生曾祖明善为纯儒。其后廷尉、中丞,笃守前矩。”[13]方氏家族世受国恩,与大明王朝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且方以智“因午会之说而对时代充满乐观”[14],亦对抱负的实现充满希望。崇祯甲申年(1644),方以智就曾上《请缨疏》,谓“誓暴此骨,愿就河北行伍,父子枕戈,以报国恩事”[1]376。可以看出,方以智起初是热心用世的,其从政的意愿强烈,十分渴望能有一番作为。
另一方面,方以智对南明朝廷是失望的。出于士的责任感,他一直关心时局、针砭时弊,积极为朝政、军事出谋划策。然而,令其大失所望的是,南明朝廷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至永历朝,“阉人用事,内批、廷杖等旧习,寖寖复行之”[15],已然看不到恢复政治清明的希望。统治阶级最在意的始终是权力的争斗,权臣秉政,忠良下野,内忧外患也阻挡不住他们的自相残杀。“大厦忽如此,一木何以支!”[4]235赵园即认为:“明清之际的遗民如方以智、熊开元,各有其复杂的世俗经历,其逃禅固然因抵抗的失败,也应缘于对政治的深刻失望。”[16]正是对方以智心态确当的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的辞官长达四年之久,也就意味着永历帝求贤四年。其中或有战时通讯不便的因素影响,但永历帝的诚意和决心仍可见一斑。受此殊荣,本应感激涕零,并以实际行动回报②钱澄之在《昭江寿曼公四十》(《藏山阁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09页)中即写道:“主恩十召君应起,莫恋沧江负白麻”。,方以智却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永历帝的征召。其实,方以智也不是没有矛盾和纠结过。他曾问语钱澄之说:“吾归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亲,其缁乎?”(《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17]流离岭表之时,他亦“长期徘徊在事君与事亲、出仕与隐遁之间”[18]。虽然南明朝廷混乱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方以智入世从政的积极性,他却并未完全置身事外,“十辞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为此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永历帝的内阁之召,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方以智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解决南明王朝所面临困境的办法③彼时,方以智的好友陈子龙、孙临皆曾以文人之身领军,意图举兵恢复。对于他们的从戎,方以智应当是十分羡慕的。他在《哭陈卧子》(《方以智全书:第十册》,第200页)诗序中即写道:“闻卧子死难,得死所矣。”且方以智一直都有从军的志向,或许在他看来,相较于入朝为官,这种在战场上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暴力手段成效更加明显。。如果不对朝中的诸多问题加以重视和解决,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扭转颓势和败局的,南明朝廷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兴。方以智之所以在“十辞疏”中将心力交瘁的状态展现出来,不仅是为了表达不满和怨愤,还期望能以此达到劝谏的效果。换言之,他是通过“书写不幸与痛苦来发挥干预政治、批判社会现实的作用”[19]。借此,历史的细节在文学作品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看似私人化的情绪情感,其实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得失,像这样因为党争、私怨而被诬陷、排挤的,又岂止方以智一人!《又寄尔公书》中,他就曾感慨道:“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尽杀天下善人名士,何独于智?”[1]529在政治分歧所造就的乱局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永历帝原本期望方以智能够成为入世为政的典范,他的推辞却把自己推到了对立面,反而成为辞官的典范。因此,即使言辞再委婉,方以智本人也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出于挽救南明的目的,却做出了辞官的举动,两相违背之下,方以智的心路历程必然是不平静,甚至波澜起伏的。明亡以后,这种矛盾性导致遗民心理一直处于拉锯状态。因此,每个遗民的选择都难免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鉴于此,遗民作为群体的复杂性尚能加以探讨,但从个体角度出发则很难加以诠释。方以智的“十辞疏”恰好为此提供了个案,他将自己在面对出处问题时的矛盾和纠结展现出来,使后人得以窥见遗民心理的细微之处,对遗民心理的理解更加深刻,这十封辞疏也因此呈现出重大的现实价值。
(三)抒发遗民真性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十辞疏”中呈现出了遗民文学中的真性情。方以智虽数次以身患痼疾、性情狂直、才能不堪、不入班行等理由推辞,且流露出难掩的怨愤之情,可这十封辞疏读来却让人感受到难得的真诚。由此,亦可以见出其以真为美的审美追求。
性情之说由来已久,在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李瑄以为,“明遗民真正将‘性情’作为论诗的根本立足点,它决定了作诗的宗旨、诗歌的命题立意和评价标准”[20]482。潘承玉亦认为,“南明遗民诗人普遍强调诗歌抒写真性情”[21]。他们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南明诗歌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明遗民群体中,有些人持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有些则强调发愤以抒情,但他们都十分看重性情背后的真,强调抒写真性情,即以“真”为美。“真正的性情,负载着诗人的理性深度与感性热情,显示出生命的力度”[20]485,于明遗民来说尤其如是。
这一点在文章中亦有所体现,“十辞疏”便是其中的典型。这十封辞疏不仅凝聚着方以智明亡以来真实的生命体验,亦蕴含着其真实的情感抒发。魏藻德曾谓方以智“伤父功之不成”[1]365所作的《激楚》,仍是“发情止义,而体归于不怨矣”[1]366。到了“十辞疏”中,他的怨也算是有所显露。疏中所述看似是为避免被卷入政治漩涡而论,却也难免蕴含着一丝怨愤的意味。永历二年中元节,方以智曾作《屈子论》凭吊屈原,通篇所论固然皆是先贤之事、生死之论,可“孤臣孽子,何代无之”[1]534的感慨,还是瞬间将人拉回同为乱世的当下,也就很难不将二人联系起来,忠臣的无奈和失望因此实现了互通。司马迁以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22]方以智亦当如是。
但是,流亡的困顿、疾病的困扰和被污蔑的困境都没有能够阻止方以智,他将忧国的情怀和忧愤的情感诉诸文字之间,试图通过文学书写达到干预现实政治的目的。其中的担忧是真,怨愤亦是真,“十辞疏”也因此显得愈发真诚。易代之际,时局混乱,人心动荡。方以智于此时坚辞永历帝征召,此种决定不可谓不艰难,他本人却指出:“士不幸生乱世,既已幸全于当时,而犹不得全于后世之说。”[1]429对于舆论,方以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抉择都是出于本心,而不是为了一时的褒誉或身后之名。因此,以“易代”为契机,他对明王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省。他的《满江红》写道:“烂破乾坤,知消受、新诗不起。正热闹,黄金世界,红妆傀儡。”[4]305《满庭芳》亦有“锦绣园林,芙蓉筵席,从来狼藉东风”[4]305之句。词中不仅揭露了南明王朝的腐朽破败,还对朝廷一直以来的粉饰太平予以抨击。即便是在中兴有望之际,表面上的太平也根本无法掩盖南明深层的危机。
这一时期,方以智的创作多是感于时事而作。他将对社会和政治的悲愤情绪爆发于文学创作之中,并为诸多遗民作传。正如他本人所说,“性情之发,发于不及知”(《周远害诗引》)[4]72。“十辞疏”因是呈给永历帝的疏奏,其中忌讳颇多,言辞也应当尽量委婉,但方以智并未磨灭真实的性情。“闻足以戒,激怒亦中和也;孤孽哀鸣,怨兴亦温厚也”(《正叶序》)[4]5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方以智以为怨怒亦中和、亦温厚,纵然发不及知,却也着意为之。因此,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信念的坍塌与维护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冲突”[23],方以智却也达成了创作实践与“以和为美”审美追求的高度一致。
早年,陈子龙曾因方以智的诗歌过于悲凉,劝诫以“悲歌已甚,不祥”[1]410。方以智回应称:“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然非无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1]312然而,在国变之后,连陈子龙也“不再斤斤于风貌是否合乎汉魏盛唐,诗学重心转为强调诗的情感宣泄与道德规范功能”[20]472。这种转变既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时局的需要。同方以智一样,遗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相连,不论是内心的矛盾挣扎,抑或是怨愤不满,均可诉诸文学创作。
文学是遗民群体抒发的重要手段,他们期望通过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加以干预,继而实现经世的理想。文学也是他们的情感寄托,用以表白忠节,发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反思。因此,解读“十辞疏”,必将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南明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明确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过禾黍之悲,遗民文人笔下的情感抒发已然变得越发丰富、真实,他们诗文创作中所流露出的情感,一改晚明文学的颓废、矫情,形成了南明遗民文学“真性情”的品质,也因此呈现出独特的真实、真切的文学价值。
四、余 论
南明永历朝,方以智的数次上辞疏并不是个例。瞿式耜亦有《力辞勋爵疏》《辞督师敕命疏》和《坚辞勋封疏》。当时,瞿式耜已身任东阁大学士,永历帝进之以临桂世伯,武英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他亦坚辞不就。永历四年,瞿式耜再上《引咎乞罢疏》,自列七罪,以病请辞①参见《瞿式耜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以上诸篇皆收入《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理想的高昂和行动的无力,往往使得南明遗民们始终身处矛盾状态。瞿式耜就曾在家书中表明:“与之同流合污既不能,终日争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犹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戊子九月又书寄》)[3]265这与方以智“不入班行”的顾虑亦有着相通之处。针对这一现象,或可继续展开群体性的研究,充分挖掘遗民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此外,“十辞疏”中的疾病书写也需要予以充分关注。以病为辞在辞官中本是最常见的现象,方以智的书写却明显展现出其本人对医学的熟识。乱世与疾病有着天然的联系,不仅因为乱世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因为古人习惯于以疾病来比喻国家和社会的弊病。方以智身处乱世,他的创作中会出现大量的医学元素自然可以理解。只是,这固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与方氏家族及其本人医学储备的关联则更加紧密。同时,作为一名思想家,方以智十分重视融会贯通,他的文学与医学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碰撞。因此,关注到其文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方以智其人及其文学理论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