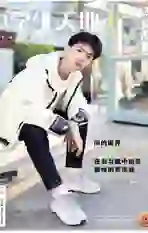承载着须弥的芥子
2022-03-14金博涵
金博涵
诗,生于人却不囿于人,只是以人这一客体承载起情、理乃至宇宙。诗意便生发于此:正如仰望天空的蝼蚁,所见是无限地晕染苍穹的蓝,天所感则是蝼蚁面对无穷的勇气与诗情。
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豪咏,看似在理性和知性的观察下都是谬误。从理性上,他走向了一种二律背反:无论“得”或“不得”这千万间广厦,他都不可能大庇天下寒士;从知性上,我们看到这潦倒的诗圣孤独而无助,这空口白话易说,却难有实现之可能。但在经验知识对其做出彻底批驳后,一个先验的、纯粹的声音却坚定地告诉我:“这是一种真真切切的诗意,是诗圣在大地上栖居半生所发出的金鸣。”
没错,这是无法实现的梦,是被第欧根尼之流嗤笑的挣扎,是芥子在茫茫天地之间绝望的呼号,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它本身的诗意,以及它对中国“士”这一阶层做出的综合判断。在盛唐的幻象破碎于“三吏三别”的惨凄之际,在步中武象的宫廷音乐被节度使僭用之时,在龙旌落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之日,杜拾遗颠沛流离,家徒四壁,痛彻心扉。但他仍不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愿去寻一块“适得我所”的乐土,而是以渺小的生命走上了看一切、写一切、感一切的内圣外不王的道路。于是诗史的意境在一粒芥子上须臾间展开,终于承载起一朝代的悲哀、一民族的无奈和一须弥的咏叹。生命的质量亦只能用一“圣”字衡量。
我最是赞赏这种容纳式的“大庇天下”的人生态度,并认为其代表了诗意在人间的最高境界。杜甫的“广厦”虽只是他这先验主体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咏叹中流淌出的诗意,那种于世内却整个包容了世,于人间却深愿带来神言的大容纳、大宽广,实在使诗歌在艺术上臻于极致。这种艺术于个人,可以冶性情、立圣心,并由内而外地生发出对社会的责任感;于世界,可以促和善,减自私的不良风气,进而构筑人人和而不同的高度文明境界;于诗美,可以增进厚重感,又在与世界的共鸣中奏出一种正道上的风雅。于是诗的美感得到擴延,小小的芥子也得以跨越分析判断的界线,走进大美的范畴。
生命立此种诗意于大地上,更是一种生存上的正确之态度。尼采式的生命可以成为天才却仅限于度己,只因其过分强调“我”而缺了一份包容;斯宾诺莎式的哲学可以玄微之至却不能将人性圈进几何法演绎中。而遵循“大庇天下”之言,不仅度己于兮山之上,亦可度人至幸福彼岸,自我便从独断论的梦境中惊醒,开始探求永恒的“道”与“义”。在论证杜甫的生存态度正确后,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广厦”梦的生存方式是充盈着诗意的。当精神世界的广厦建成,人生见生人如知己,见仇敌如旧友,一切都容纳在小而又小的人的心灵中,散发出充塞于宇内的青光,这种人生,难道不正是活成了诗的样子?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事实上,开颜的难道不是那位执笔写下此语的圣人?他的泪痕弯过双颊,弯成嘴角的一抹笑意。他欢颜了,他知道了,我亦知晓了这一句已永恒地落在青史之上,并成为古往今来多少芥子去扛起须弥的勇气与诗意。
指导老师 尹柱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