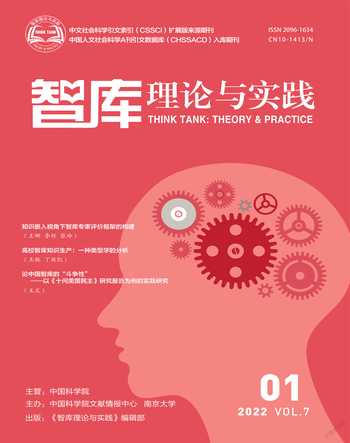专家的决策影响力:评价体系、现实状态与优化路径
2022-03-14费久浩
费久浩

摘要:[目的/意义]专家是现代国家政策过程中一类规模庞大且显示度极高的政策行动者,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和决策咨询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聚焦于专家决策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建构、现实状态描述和优化路径提炼,对这一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知识推进和累积效用。[方法/过程]本文借鉴并整合已有研究文献,从广度、深度和实度三个层面构建一个专家决策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此定性地评估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这一典型案例中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水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专家决策影响力的优化路径。[结果/结论]定性地看,在政府非常设决策咨询机构这一效度范围内,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总体上处于中等偏弱的水平,可以从决策咨询工作职业化、政策思想市场开放性、政学两界交流常态化等角度出发优化专家的决策影响力。
关键词:专家 决策影响力 評价体系 现实状态 优化路径
分类号:C932.4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2.01.03
1 引言
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面临的政策议题愈发复杂和多样,对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需求大量增加,并进而使得作为后者载体的专家①成为现代国家政策过程中的建言者和智囊团,广泛见诸不同的政策领域,逐渐成为一类规模庞大且可见度极高的政策行动者。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决策体制改革以科学化和民主化为目标,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要求不断提高决策网络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而其中的一个具体抓手就是建立决策咨询机构。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由此不断地被引入政策过程,成为我国各级各类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非官方政策参与主体。专家的政策参与实践引起了相关研究者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兴趣,而专家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构成了该领域的重要议题。目前,研究者围绕这一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差序格局和圈层结构特性的类型学研究路径,即以某个较小领域内的影响力为核心,逐渐向外水纹般扩展,进而从对象、范围等视角呈现专家影响力的不同层次。例如,朱旭峰较早以距离决策中心远近为标准提出了决策影响力(核心)、精英影响力(中心)和大众影响力(边缘)的三分框架[1];胡鞍钢则将智库专家的影响力类型分为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2];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其系列年度报告中,将智库专家的影响力细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②——后两者在对专家影响力的研究上具有同样明显的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的特性。
显然,在不同的专家影响力形态中,决策影响力处于核心地位,其他影响力均要服从和服务于决策影响力的实现,并以转化为决策影响力为最终目标。正是在此意义上,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Abelson)指出“对他们(指智库专家)来说,与其费工夫去登早报的版面,不如加强与关键决策者的联系”[3]。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主要聚焦专家的决策影响力。不同于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分别涉及专家与同行、专家与公众(媒体)、专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专家的决策影响力主要涉及政策过程中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指专家以其智力成果和思想产品为核心资源,通过特定的渠道和途径作用于政策决策者,并使其优先议题、方案选择等发生改变或优化的能力。基于对该领域目前研究的判断,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应如何观测或评价专家作为一类政策行动者的决策影响力?政策过程中专家的决策影响力实际上处于何种水平?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优化专家的决策影响力?为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学界已有研究构建一个专家决策影响力的评价体系,然后将其运用到现实层面,即以此为框架定性地分析一个典型案例中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水平,最后尝试针对上述典型案例所反映的现状,提出具有一般性的专家决策影响力优化路径。
2 专家的决策影响力:评价体系的建构
2.1 主要研究成果综述
评价专家的影响力有着特殊的困难,而决策影响力的评价尤其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经验资料和证据的难以获得。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认为,评价智库专家影响力最有效的指标无疑是“实际的政策采纳、变化、实施”,但此类“因果性的研究(案例研究)和数据却非常难以获得”,故研究者不得不“依赖捕风捉影的事件、决策者的证言和旁证来替代直接的铁证”[4]。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基于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实证研究表明决策咨询活动通常具有隐蔽性,其过程“不显山露水”“记录其活动的文件少得可怜,我们也很难了解或评价他们对政策决策的影响”[5]。或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有些研究者笼统地将专家的决策影响力转化为以下表述,即由于专家的参与而使政策发生了某种变化——变化越大,则决策影响力越大;反之,则越小。迪恩·斯库勒(Dean Schooler)认为,如果专家带来了新的政策方案或使原有政策发生了改变,那么其对政策就有影响力[6]。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指出,判断专家咨询是否成功的一个简单法则就是,看其能否促进政府机构在“态度、视角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发生某种改变[7]。瓦尔达(Varda)则认为,判断专家影响力的方式非常简单,即如果政府官员在写作政策备忘录时,手头上正好拿着专家的研究报告,并引用了其观点和分析,那么就有影响力,否则就没有影响力[8]。
显然,迪恩·斯库勒和布鲁斯·史密斯的评价方法很难操作化,因为两者均未提供确定专家参与和政策变化间因果关系的具体程式以及呈现政策变化幅度的观测指标;而瓦尔达的观测方法则过于单一,遗漏了很多显而易见的影响力因素。因此,有些研究者不再纠结于专家参与和政策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很难确定),而是从专家行为、成果产出等更具公开度和可量化的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例如,唐纳德·埃布尔森认为智库专家对决策者的影响力可以转化为以下观测点:在政府部门担任内阁、内阁下级机构、普通官员等职务;在总统选举期间加入政策工作小组和过渡团队,以及之后加入总统顾问委员会;保持与参众两院的联系;邀请当选的决策者参加智库的内部会议、研讨会和专题讨论;允许政府官员在智库里有限期地任职;邀请前政府官员到智库任职;为决策者准备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3]。而在詹姆斯·麦甘的研究中,智库专家的影响力指标则同时涵盖因果关系、专家行动及其产出两个层面。其中,前者包括被决策者采纳建议的重要性,对政党、候选人、政权接收小组的顾问作用,成功挑战华府官僚机构和民选官员的传统做法与标准运作程序;而后者则包括所获奖励,学术期刊、媒体对智库出版成果的引用,电子论坛与网站优势[4]。
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智库专家的影响力做了更为细致、深入且更具本土色彩的研究,典型表现就是对专家的影响力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并分别构建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朱旭峰较早将智库专家的影响力分为上文所提的三类[1],并将每类的来源均分为“思想”和“人”两个方面,进而将其细化为“文字”和“活动”,具体到决策影响力,“文字”包括研究报告、政策咨询研究项目、定期内参,而“活动”则包括听证会、派驻专家、政策咨询会、政府讲座,最后两者分别被操作化为“研究报告获得领导批示”和“接受政府邀请参加决策咨询会”[8],由此领导批示和与会数量成为专家决策影响力的直接量化指标。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是另一典型,在其自2014年起每年发布的中国智库年度报告中,决策影响力同样居于智库专家诸多影响力类型中的核心,在對决策影响力评估体系的建构上,该中心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目前已基本趋于稳定,包括领导批示(每年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领导批示的件数)、建言采纳(每年获得国家或地方政协、人大及国家部委议案采纳的件数)、规划起草(每年组织或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发展规划研究、起草与评估的件数)、咨询活动(每年参加国家级或省部级政策咨询会、听证会的人次数)等四项指标。
2.2 基于已有研究的建构:一个梯度递进的分析框架
多数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并未对政策过程中专家的影响力进行细分探索,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为细化和深入,其基本思路是从中心向外围扩散,将专家影响力分为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公众)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并分别构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这种追求“覆盖面”的研究取向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开疆拓土”和“锚定边界”贡献重大,但本文未再从横向上“往外画圈”,而是选择一点“往深处挖”,即选择其中一种类型的影响力做集中深入研究。考虑到决策影响力在诸多类型影响力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将围绕其进行分析探讨,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下文将首先基于既有文献和经验资料提出一个带有“梯度递进”色彩的评价体系,即按照广度、深度和实度③的递进顺序,层层深入地考察专家的决策影响力。
其一,在决策影响力的广度层面,本文具体分解为“专家参与的比例”和“参与活动的频次”两个观测点。其主要表征专家群体发挥决策影响力的可能性和潜在机会,这意味着只有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实际参与率,才有可能谈得上决策影响力的实际发挥。其中,“专家参与的比例”主要从“人”的角度考察当专家经过筛选和审核获得政府咨询顾问的身份,从而得以直接介入政策过程的机会和渠道之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愿意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和渠道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参与活动的频次”则从“活动”(即专家的各种参与形式,如承担咨询课题、提交内参报告、参加咨询座谈会等)的角度来展示专家政策参与的实际情形,主要反映那些真实开启了政策参与的“机会之窗”的专家实际运用这些机会的频次如何。
其二,在决策影响力的深度层面,本文细化为“影响议程设置的能力”和“影响政策方案的能力”两个观测点。其中,议程设置是政策循环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9],反映了政策过程的基本权力类型[10]。在政策参与实践中,“影响议程设置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专家能否影响参与领域或主题的确定,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做“命题作文”;“影响政策方案的能力”则是指专家在决定政策选项和行动方案上的作用水平,尽管这被认为是最能发挥专家知识优势的环节(因为其主要涉及“怎么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知识运用过程,而专家恰恰是专业知识的承载者),但其强度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值得强调的是,选择上述两个政策环节具有比较扎实的文献基础。罗伯特·达尔等很早就将影响力分为影响他人接受有效选项、影响他人设定议事日程、影响结构和影响意识四个层次[11]。其中,前两者显然对应此处的影响政策方案和影响议程设置④。此外,约翰·金登[12]、朱旭峰[13]等在研究专业共同体的作用时,同样都聚焦于“议程设定”和“方案选择”两个阶段,这也加强了本文选取此两项作为指标的信心。
其三,在决策影响力的实度层面,鉴于“领导批示”在中国政治体制运作和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将其作为专家决策影响力实度的观测点。这同样得到诸多研究者的认可。例如,朱旭峰发现领导对内部研究报告的“批示”在决策中占独特地位,并认为内部研究报告获得“领导批示”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形成政策的标志[8]。孟庆国等[14]也注意到“批示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影响力巨大,政府部门和智库都高度重视领导批示,并以获得高层领导批示数量作为自己机构影响力的衡量标志”。不过,近来也有研究者认为“批示是否真的实现了对决策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15],并且影响力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形式”“A对于一个结果的影响力在量上应该相当于由A的欲望所导致的结果(B的反应)的量”[11]。鉴于此,本文认为不仅要观测“领导批示”在量上的表现,还要进一步考察批示与政策选择的因果关系,由此“领导批示”就细化为“领导批示的数量和比例”和“批示的实质性作用”两个具体观测点。
决策影响力的广度层面主要反映专家发挥决策影响力的潜在“可能”空间,而深度层面和实度层面则代表着专家施加决策影响力的“现实”机会。综合以上分析,可构建一个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专家决策影响力评价体系(见表1)。
3 专家的决策影响力:现实状态的描述
本文接下来将以上述评价体系为分析框架,借助一个典型案例定性地呈现专家决策影响力的现实状态。G市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较早地推进了行政决策体制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各级各类的专家库作为决策咨询机构和专家参与平台。目前,G市共有市一级专家库3个,各委办局自行设立的专家库(委员会)63个,入库专家总人次达14,000余人。在G市诸多专家库中,成立于2005年、前身为决策咨询顾问团的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市一级)发展比较规范、制度化程度较高,故本文以此作为典型案例检验和呈现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水平⑤。由于该专家库历史较长,产生的资料非常庞杂并且受篇幅所限,本文从其政策参与的系列活动中挖掘典型素材,以反映其在决策影响力不同观测点上的表现,其涉及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数据(如专家库的参与率、各类参与形式的频次)、核心环节(如专家库的产生流程、决策咨询课题的确定、领导批示)和重点领域(如五年规划编制中的专家参与),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专家参与及其决策影响力的基本图景。
在正式分析专家的决策影响力之前,有必要简要论述本文所选案例的典型性,这是由于其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首先是整体案例的典型性。从宏观上看,像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这种由各级党委或政府发起成立的非常设专家咨询机构(亦常被称为顾问团、委员会之类),是改革开放以来专家政策参与中一类普遍的组织媒介和制度平台;从微观上看,实地调研表明G市决策咨询专家库在产生方式、参与渠道、管理机制及各方对专家决策影响力的预期等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政府非常设专家咨询机构这一广泛范围内具有较好的可外推性,而能否将其扩展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新型智库之中,则有待做进一步验证,本文不进行讨论。其次,所选素材的典型性亦值得关注。如前所述,考虑资料体量和篇幅限制之间的矛盾,本文选取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政策参与过程中的具体素材(亦可被称为子案例)展开论述。由于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政策参与的程式化和同质化程度较高,因此,这些素材亦具有较好的典型性。例如,不同届别专家库的产生流程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只需呈现其中一届即可;由于制度化水平较高且不同届别专家库在成员上重复度较高,因此不同届别专家的参与率亦是类似的,等等。
3.1 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广度层面
3.1.1 专家参与的比例 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的产生通常需经过请示领导、名额分配、初选名单和请求批复等若干环节,可谓层层把关。但专家经过筛选成功入库,只意味着其得到了介入政策过程并直接影响决策者的机会,而实际上是否会充分利用此种机会是另一个问题,专家参与的比例则是重要的观察视角。此处以具有代表性的第二届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的实际参与情况来说明该问题。该届专家库共117人,分11个功能组别,主要参与方式为承担课题研究、提交内参报告和参加咨询座谈会。资料显示,在为期五年的聘期内,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或方式组合参与政策的专家共54人,占比约为46.2%,不到总数的一半;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不同功能组别的参与情况差异较大,但参与率超过50%的只有开放与合作、资源与环境保护及体制机制改革3个小组,其他多数小组的多数专家均处于“休眠”状态,在聘期内并未以任何形式提供决策咨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咨询专家变成了简单挂名,甚至成为荣誉性的头衔,因此,也就无所谓决策影响力的发挥。
3.1.2 参与活动的频次 以上从“人”(即专家)的视角呈现了实际的政策参与比例,如果从“活动”视角来看,在那些有实际参与行为的专家中,其在各种参与形式上的表现如何?就承担咨询课题而言,G市2007—2019年通过决策咨询专家库委托给专家的课题分别为15个、21个、12个、8个、9个、7个、9个、10个、5个、8个、10个、10个、9个。除极少数课题由两个专家各自同时承担外,其他均为一个课题由一个专家承担,这就意味着只有少数专家才有机会承担决策咨询课题,进而产生政策话语权。就提交咨询报告而言,专门刊登专家政策建议的《决策与咨询》2009—2017年的发行期数(通常1篇报告为1期)分别为每年16期、20期、11期、22期、10期、23期、22期、7期和15期⑥,相对于动辄百人左右的专家库规模而言,其产量偏低,而如果对照G市另一本由政府工作人员自身供稿的内参报告《G府调研》的发稿量⑦,上述数量显得更少。就参与咨询座谈会而言,以市长召集的为例,多则每年2次,少则没有,每次受邀参与的专家为10人左右,因此,绝大多数专家并无与决策者开展直接互动的机会。
3.2 专家决策影响力的深度层面
3.2.1 影响议程设置的能力 承担咨询课题是专家政策参与并形成决策影响力的重要形式,而咨询课题的确定过程最能反映专家究竟是可以自主(或参与)确定研究议题,还是只能被动地做“命题作文”。G市决策咨询课题的确定通常经由以下程序:首先,是选题征集,专家库管理机构G市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向市政府组成部门发布课题征集函,后者结合自身实际和重点工作推荐选题;其次,为初步筛选,专家库管理机构依据相关标准逐一分析推荐上来的选题,形成一个初选名单;再次,为政府研究室领导票选,每位领导从初选名单中勾选特定数量的课题,并经过会议议决;最后,为市长批示,得到同意的课题数量和名单正式对外公布,并动员专家承担研究任务。对政府咨询课题产生过程的详细描述显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科层权力主导的过程。其中,政府各部门集思广益,政府研究室主导推进,决策者(市长)拥有最终决定权,而专家是缺席的、不在场的,其并不享有设定研究议题的权力,只是回答政府和决策者提出的问题⑧。
3.2.2 影响政策方案的能力 五年规划在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其制定过程对吸纳专家参与有着制度性要求和规范化程序,能够较好地体现专家在政策方案选择中的影响力水平。在G市,为切实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2015年11月—2016年1月,政府研究室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依托专家库的相关功能组别组织了一系列的专家座谈会,座谈会通常由市委市政府的正副秘书长主持,市发改委作为规划编制的具体负责部门指派专人出席,与座谈内容相关的工作部门则需派专人参加会议以记录专家建言,可谓高度重视。该系列座谈会面向专家库全体专家,对于因故无法出席的专家,则开通书面建言通道,最终,专家为G市“十三五”规划编制提出了大量建议和意见,并形成《G市“十三五”规划建议专家系列座谈会专家发言要点汇编》和《G市“十三五”规划建议专家系列座谈会专家书面意见汇编》,共计十余万字,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自贸区、科技管理体制创新、“一带一路”、國家创新中心城市、碳排放权等内容,一定程度上优化并具体化了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内容。
3.3 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实度层面
3.3.1 领导批示的数量和比例 在G市专家主要的政策参与媒介中,刊登在《决策与咨询》上的内参报告和以《市长专报》形式提交的课题研究成果均以书面材料呈现,故存在领导批示的可能性。由于领导批示具有相当机密性,无法直接获得整体数据,但亦可从不同年份的工作总结、专家提交的述职报告等内容中梳理出一些可用数据;尽管可能并不系统,但仍可借此管窥其中的草灰蛇线。其中,2014—2017年G市领导(市委常委、副市长)对《决策与咨询》的批示数量和比例如下:2014年编印23期,获得市长批示1次,副市长批示1次,批示率为8.7%;2015年编印22期,获得市委书记批示1次,市长批示1次,批示率为9.1%;2016年编印7期,无批示,批示率为0%;2017年编印15期,获得市委书记批示1次,市长批示1次,批示率为13.3%。而《市长专报》的批示情况与《决策与咨询》差异不大,例如,2017年刊印7期,仅获副市长批示1次,批示率为14.3%。对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研究成果批示情况的考察表明,无论领导批示的数量还是比例都处于较低水平⑨。
3.3.2 批示的实质性作用 其主要是指领导批示与政策选择的因果关系。对所得领导批示文本内容的分析表明,批示在内容强度上存在极大差异,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仅仅是“圈阅”,即领导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阅读日期,代表“已阅”或“知道了”⑩,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不是批示⑪,很难由此认定其与政策选择之间有何关系。第二种主要是领导提请相关部门或负责人参阅专家研究成果,而并未明确要求采取具体行动,通常含有“参考”“研处”“阅研”“参阅”“思考”“研究”等字眼,语气较为温和,表述多较笼统,且带有商请而并无命令的意思,因此,相关部门在处理过程中有较大弹性,其与政策选择的关系亦充满不确定性。第三种则是责成相关部门对照专家建议跟进相关工作并形成解決方案,有时还附带具体的时间限制和操作性要求⑫。考虑到政府科层体系中命令服从关系的强制性,本文可以认为具备此种强度和明晰度的批示就“意味着‘采纳’‘处理’‘执行’等政策行为的发生”[8],并可以认为其代表着决策影响力的实现。
3.4 专家决策影响力的整体评价
上文以一个具有梯度递进色彩的专家决策影响力评价体系为框架,分析了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这一典型案例中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在决策影响力的广度层面,入库专家的政策参与率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积极性和能动性偏低,而对那些有实际参与行为的专家而言,各类参与的频次亦并不高,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发挥。在决策影响力的深度层面,专家在议程设置阶段属于零参与和零影响,并无设置议题类型或定义议题轻重缓急的能力;在方案规划与设计阶段则能起到较大作用,专家可以凭借专业知识和第三方角色协助政府优化行动规划、凝聚行动共识。在决策影响力的实度层面,决策者对专家研究成果的批示量通常很少,比例也很低;而领导批示与政策选择间的因果关系则需视情况而定,在批示内容强度和清晰度最好的情况下,获得领导批示的专家建议的确很有可能转化为政策选项。总体而言,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专家群体作为一类政策行动者的决策影响力处于中等偏弱的水平,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4 专家的决策影响力:优化路径的提炼
总体而言,寻求决策影响力的最大化是包括专家在内的所有政策行动者的基本动机和诉求,而上述案例研究表明专家的决策影响力处于中等偏弱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探讨专家决策影响力的优化路径进而促使专家在高可见度之外实现高影响力是一个紧迫且重要的议题。下文将针对上述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尝试提出优化专家决策影响力的可行路径。
4.1 实现决策咨询工作的职业化
针对专家参与比例和活动频次较低所反映出来的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全面实现决策咨询工作的职业化。从激励的角度来看,专家参与的整体效能和决策影响力之所以偏弱,是由于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影响决策者并取得决策影响力,属于典型的“弱激励”。因此,必须提高专家政策参与的激励水平,发展职业化的新型智库组织。目前我国的许多智库或各类专家委员会(如本文中案例)大多数是高校教授兼职,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其并不需要赖此为生,从事政策研究只是副业,没有“必须做好”的紧迫性。故当务之急是要发展职业化、市场化的新型智库组织,让智库从业人员(如政策分析师)成为一种区别于高校教师或纯学术研究者的职业。
由此而来的是,这一职业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和业绩成果评价体系。目前,我国的决策咨询专家主要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但后者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审标准与职业智库并不兼容,“学术论文”和“咨询报告”在其职业发展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对称,这使得以高校教师或学术研究者为主业的咨询专家更多地仍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而并无动机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研究和咨询专家的角色上,只是将其作为一种锦上添花的荣誉头衔。因此,必须要将智库从业人员与高校教师或学术研究者分离,使之职业化的同时,为这一职业设计不同于纯粹学术研究的评级体系和激励机制,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使之不仅“可以”而且“愿意”积极为自己的思想产品寻求市场和买家。
4.2 促进政策思想市场的开放性
针对专家在议程设置环节中的“零参与”问题,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是促进政策思想市场的开放性。科斯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16],具体到专家参与和决策咨询领域,就是政策思想市场的开放度和多元性不够。通常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由党政体制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但这一状况其实并不是必然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即仍然可以在党政体制的整体框架内提高政策思想市场的开放度。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我国思想界(包括政策思想界)的活跃及其与政府频繁而密切的互动说明了这种状态是可遇且可求的。
因此,首先要确立政策思想市场供给方(即智库专家)的主体地位,改变那种为既定方针做解释和宣传、为领导意图做注脚和论证的情形,提高政策过程中智库专家群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确立其在思想市场中的市场主体地位,正如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强化企业和企业家在商品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一样,与此对应的是,要确保政策思想市场的多元和竞争特性,在决策研究领域“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17],不同的专家或智库组织可以就特定时期政府的优先议题开展公开理性的政策辩论,可以自由地“兜售”或传播自己的政策理念和思想主张,而行政官僚和决策者则主要起最终的“把关人”作用。
4.3 寻求政学两界交流的常态化
为进一步提高专家改进政策选项的能力以及决策者对专家研究成果的批示水平,一个可行的突破口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政策研究虽然不同于纯学术或纯理论研究,但其仍然属于“研究”而不是“实践”的范畴,这就使得智库专家在行动逻辑和思维方式上势必与注重“经验理性”和“行为知识”的决策者产生冲突,经典的“两个群体理论”(The Two-Communities Theory)[18]呈现的是专家与决策者的这种紧张。然而,这也并非完全不能解决,“旋转门”机制就是很好的方案,可以建设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以实现政学两界的良性、常态互动,双向打通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角色壁垒,促进双方对彼此的“圈子”更加深入的理解,从而增强智库专家政策建议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可接受性。
目前,我国的“旋转门”机制尚不健全,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这种机制是单向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退休官员进入智库担任分析师或领导职务较为常见,而且很受欢迎;但咨询专家或政策分析师进入政府内部深度了解决策“黑箱”则非常少见。未来,需要下大力气双向打通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角色壁垒,建立起对双方都可称之为“引进来、走出去”的沟通互动机制:一方面,针对咨询专家进入政府的机会较少的现实,要特别推行智库人才到党政机关挂职锻炼、到基层和一线单位蹲点调研制度,让其身份在决策者、执行者和研究者之间常态化切换,提升决策咨询和综合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官员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机制,目前主要是退休官员进入智库的情形较多,未来也应探索建立在职青壮年且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短期专门政策研究的通道。
5 结语
本文借鉴并整合了目前关于智库专家决策影响力评价的已有成果,建构了一套带有梯度递进色彩的专家决策影响力评价体系,以此为框架分析了G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这一典型经验案例中专家的决策影响力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专家决策影响力完善路径。本文对于深化智库专家决策影响力这一核心议题具有明显的知识推进和累积效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这为今后进一步拓展该研究议题提供了思路。
其一,专家决策影响力在不同政府层次(如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政策领域(如民生政策、科技政策或外交政策等)、政府部门(如发改部门、民政部门或监管部门等)是否呈现不同的状态?这显然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并未做具体分析。
其二,不同研究领域(如工程科学、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等)、不同身份背景(如作为前政府官员的专家或来自知名高校的专家等)、不同个性特点的专家在决策影响力上有何差异及其发生机制是什么?这同样不是一套评价体系所能覆盖的,需要另做分析。
其三,正如詹姆斯·麦甘和希拉·贾萨诺夫等所注意到的,专家与决策者的互动通常可见度极低,因此,本文只能通过决策者的讲话稿、批示件以及对专家和专家库管理者的访谈去管窥专家决策影响力的线索,虽然已属不易,但仍存在资料效度和信度的问题。
其四,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效性止于广泛存在的政府非常设专家咨询机构,但当前我国专业化和职业化新型智库发展势头同样迅猛,虽然两者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运作方式、激励机制、资源禀赋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后者的决策影响力水平需要另行研究。
参考文獻:
[1] 朱旭峰, 苏钰. 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18(12): 4-5, 21-26.
[2] 胡鞍钢.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3, 34(5): 1-4.
[3] ABELSON D E. A capitol idea: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M].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7-148.
[4] 詹姆斯·麦甘. 美国智库与政策建议: 学者、咨询顾问与倡导者[M]. 肖宏宇, 李楠,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62.
[5] 希拉·贾萨诺夫. 第五部门: 当科学顾问成为政策制定者[M]. 陈光,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
[6] SCHOOLER D. Science, scientists, and public polic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32.
[7] 布鲁斯·史密斯. 科学顾问: 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M]. 温珂, 李乐旋, 周华东, 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7-8.
[8] 朱旭峰. 中国思想库: 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105.
[9] 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 公共政策研究: 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 庞诗,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79.
[10] 羅伯特·海涅曼, 威廉·布卢姆, 史蒂文·彼得森, 等. 政策分析师的世界: 理性、价值观念和政治[M]. 李玲玲,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2.
[11] 罗伯特·达尔, 布鲁斯·斯泰恩布里克纳. 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版)[M]. 吴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9-63.
[12] 约翰·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2版)[M]. 丁煌, 方兴,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13-204.
[13] 朱旭峰. 中国社会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1, 26(2): 1-27, 243.
[14] 孟庆国, 陈思丞. 中国政治运行中的批示: 定义、性质与制度约束[J]. 政治学研究, 2016, 32(5): 70-82, 126-127.
[15] 朱旭峰. 智库影响力测量的多维性[N]. 学习时报, 2017-04-10(006).
[16] 科斯. 中国改革: 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发展[J]. 学术界, 2012, 27(2): 242-244.
[17] 万里.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 中国软科学, 1986, 1(2): 1-9.
[18] CAPLAN N. The two-communities theory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79, 22(3): 459-470.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Evaluation System,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xpert Database of Policy-Making Consultation of G Municipal Government
Fei Jiu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angdong Research Center for NP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xperts are a kind of large scale and highly visible policy actors in the policy process of modern state, the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ink tank and policy-making consultation, a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system, descripting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extracting optimization path of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which has obvious knowledge advancement and cumulative utility to this research area. [Method/process] By referring to and integrating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from breadth, depth and reality, and then uses it to evaluate qualitatively the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in the typical case of G city’s policy-making consultation experts databas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especially optimization path for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Result/conclusion] Qualitatively, withi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s’ non-permanent policy-making advisory bodies, the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is generally at a medium or weak level, and it can be optim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 openness of policy thought market and norm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exper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evaluation system realistic situation optimization path
收稿日期:2021-09-15 修回日期:2021-11-02
3548501908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