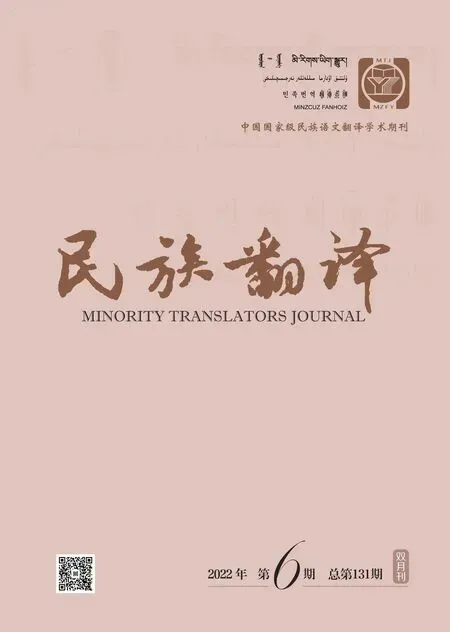“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1951—2021)*
2022-03-13姜燕
姜 燕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构建是当前翻译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为翻译学术话语的建构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确定“中国翻译研究”的命题之后,学者们又针对“中国特色翻译学”还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中国学派”还是“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涉及话语理论到学科体系,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逐级建构奠定了基础。本文在梳理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并思考路径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提升策略。
一、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概念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认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要把握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1]。从董秋斯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到董宗杰、桂乾元、谭载喜、张柏然等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以及后来刘宓庆、潘文国、王克非、傅敬民、刘金龙等针对翻译学中“中国特色”的概念,从历时与共时、民族性与文化性、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等角度展开了一系列探讨。由此,“中国特色翻译”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水到渠成之势。
中国特色翻译研究首先是基于对中国翻译话语的讨论。张佩瑶将翻译话语阐释为“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和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2]。耿强将“翻译话语”定义为“翻译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有关翻译的陈述。它的外延足够宽泛,可以涵盖形形色色的有关翻译的论述,且和福柯的话语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突出了话语并非发生在真空中的事实,这可以很好地揭示翻译与意识形态、政治、诗学、经济等外部话语系统的关联”[3],因而当下对中国译学的讨论,更多使用翻译话语的概念代替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就是源于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思想的表述,以中国人的观点与理念形成的一套能够阐释中国文化特色与传统,满足中外互译的标准并能指导中外互译实践的方法、理论规范与话语体系。它是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能够与世界话语进行“双向”交流的动态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精神实质是其形而上的哲学范式,以及在这种哲学范式观照下翻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西方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都具备典型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特征,但依然能被不同国度的学者理解并接受。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同出此理,从哲学思想层面考察,它具备国别性和民族性特征,即中国特色;从方法论考察,它具备哲学思辨性、路径引导性和实践操作性特征;从应用性层面考察,它具备指导一切翻译实践研究的特征。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患得患失于是否会因“中国”的民族性而丢失了世界性,或因“特色”性而排斥了“普适性”,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时代召唤下,“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更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从翻译的视角构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现实价值,并将其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可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丰富世界翻译话语体系。
二、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研究现状
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研究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51年董秋斯提出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方略为标志,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是时代与世界发展的必然。董秋斯指出:正如一切科学理论,翻译理论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建设一方面要符合普遍的科学法则,另一方面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4]。但是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思考只能说是萌芽了,或是处于感性思考阶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与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已成为翻译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学者们围绕中国翻译研究有无特色,特色是什么,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如何构建,发展趋势如何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思考与论争。罗新璋、董宗杰、桂乾元、谭载喜都对建立中国翻译学提出富有见地的见解。罗新璋在《翻译论集》中首次提出了“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体系,将其核心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5]。后来,张柏然、刘宓庆、孙致礼、许渊冲、潘文国等人从不同的视角阐释、论证并倡导“中国特色翻译学”。这一时期是对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理性思辨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研究已经步入科学发展阶段。面对“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时代之需[6],如何准确全面地对外译介代表中国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作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以及建构的方法和路径问题成为该阶段的主要议题。体现为一系列发轫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翻译研究的本土叙事与本位观照的翻译理论的提出。如,张佩瑶的“推手论”、刘宓庆的“师墨说”、许渊冲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吴志杰的“和合翻译学”、刘满芸的“共生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杨枫的“知识翻译学”、任东风的“国家翻译学”和傅敬民的“中国特色应用翻译学”,等等。这些代表中国特色的翻译论述,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翻译学者们的学术话语,而且加强了他们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逐渐轮廓清晰、发展壮大。
三、“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在21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阶段里,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及实践的研究视野更高远、方法更多元、领域更宽广。既着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化话语价值,又兼具国际视野,综合利用现代的跨学科、多模态、数字化等多元化的研究手段,呈现出本土化与中西融合并重的研究路径。
(一)本土化路径
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路径,主要发轫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概念的话语生产与实践,具有原创性、人文性和哲学性的特点,引发了翻译学界的关注与思考,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与拓展空间。从话语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传统翻译话语”与“现代翻译话语”两种形式,体现既注重继承历史,又注重现实关照的特点。
1.传统翻译话语
传统翻译话语源于中国哲学及传统文论话语,主要是以传统文论关键词进行话语生产与创新。体现出箴言式、寓言式的话语特征。如“玄(学)”“文章(学)”“和合(学)”“易(学)”,等等。辜正坤从哲学层面探讨和研究翻译理论与翻译文化相关问题的方法论,建构了“玄翻译学”及其理论体系、理论模式[7],具有开拓意义。玄翻译学可分为“元翻译学”和“泛翻译学”,对应翻译研究的本体理论和非本体理论。具有代表性的“玄翻译学”话语还有“元泛论”“阴阳论”“心物一体论”“五相论”等。潘文国从我国传统的文章学角度出发,以“文章之学”为基础,将“信达雅”与“义体气”结合构建“文章学翻译学”理论体系[8]。再者,继张立文提出“和合学”、郑海凌提出“和谐说”之后,吴志杰基于“和合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注重和谐与多元,关注过程与创生,提倡一种追求伦理与审美的理想生存模式”[9],撷取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诚”“心”“神”“适”五个关键词,对应翻译本体、翻译伦理、翻译认识论、翻译审美和翻译文化生态问题,建构了“和合翻译学”,将翻译与传统文化有效“和合”。最后,陈东成依据易理哲学提出“大易翻译学”,以“文化交易”“太和”“求同存异”“阴化、阳化”“与时偕行”等中国传统话语讨论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境界、翻译的总原则、翻译的策略以及复译的必要性等问题[10]。陈大亮依托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境界观,基于译者应具备的觉解、学养、悟性境界与翻译作品所应反映的精神内涵与审美特质构建翻译境界论,指出翻译境界具有主体性、层次性与超越性[11]。正如杨镇源所言:“境界作为较高维度的存在,却总是能够涵摄知识,为知识的发展创新带来根本性的动力。相应地,如果停留于知识的积累而忽视境界的升华,一个学科则必然会面临发展的瓶颈”[12]。翻译境界论超越了知识、语言与文化,提升了人们对翻译理论、行为及其实践的整体认识,体现出传统文论的“境界观”。
2.现代翻译话语
现代翻译话语是指以现代的汉语表达方式,从现代学科发展、社会发展的视角讨论翻译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对人(译者)以及人(译者)与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等翻译外的世界)的宏观观照。如,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系列理论体现出对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论及翻译思想的继承、变通与创新,也体现了文学翻译话语的原创性与系统性的中国特色。“这些理论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概括的内容上都表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13]。黄忠廉在分析了产生于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西方文学翻译的全译观之后,指出“变译”是相对于“全译”的新范畴,并提出了变译理论[14]。从变译的系统与体系、变译的手段与方法、变译的过程与机制等十八个方面架构变译基本理论;又结合读者、译者、客体三个方面建构变译主客体论。既关注人(翻译主体),也关注人与世界(翻译客体)的相处之道(变译),从理论到方法系统建构了“变译理论”,是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探索与创新。周领顺从译者行为的视角出发,将“翻译外”与“翻译内”、翻译的文本与人本相结合,提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除了译者主体性行为之外,也关注制约译者选择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外部因素,进而探讨翻译的“社会性”和“社会化”、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等问题,架构了“求真—务实”的译者评价模式,是具有原创性和本土性的中国翻译话语。任东升进一步提出“国家翻译实践”,是指国家作为翻译主体的实践活动或国家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的实践活动[15]。他指出,国家翻译实践关乎国家语言安全、国家话语传播、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等重大议题,因而要遵循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化、国家翻译实践理论化、国家翻译学科化“三步走”的战略来构建国家翻译学研究体系[16]。近两年来,国家翻译学从宏观的体系建构到微观的理论支撑、实施机制等方面不断地深化、细化,对于促进国家文化传播能力、增强国家话语解释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西融合路径
中国译学发展至今的无数史实证明,如果只是陶醉于传统话语的自说自话就无法突破止步不前的研究瓶颈。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无法孤立存在,中国特色翻译话语通过域外研究手段“借船出海”,使我国译学得以传播与发展的融合路径是时下中国翻译研究的大势所趋。诚如方梦之所言,“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我国译学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融合,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17]。中西融合路径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种形式。
1.中国思想结合西方研究范式创新翻译话语
胡庚申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借助生态整体主义和“适应/选择”论,围绕文本生态、翻译生态、翻译群落生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提出“生态翻译学”的概念[18]。事实上,季羡林也曾提到“翻译生态平衡”的问题,指出要防止只翻译英美作品的“偏食”现象,重视研究和翻译东方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要加强对翻译文本选择的统一,“择优翻译,协调介绍”[19]。生态翻译学将中国“和谐统一”的生态观与西方的生态进化论结合,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彰显了中国文化中“生命”与“和谐”的哲学思想。同样,刘满芸借用由生物生存方式发展而来的“共生”自然哲学,即将“同质相合、异质共生”的中国哲学与“生物共生学”的西学概念相结合,提出“共生翻译学”,讨论翻译的主体共生关系、客体共生关系、翻译伦理与规约的共生关系,将翻译的一众因素都囊括在一个共生环境之中,构成完整的翻译生态体系[20]。又如,王寅将中国的“体用”哲学与西方认知语言学范式结合,强调翻译的本体性,即中国文化中的“体用”关系,也强调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认知加工的体认过程,即翻译主体的认知活动、认知能力与认知效果等的重要性;杨枫结合西学有关知识的本质、地方性知识等概念[21],基于“道生名器”的中国哲学思想,提出“以知识、语言和译者三个内在要素,真、善、美三个科学方法,文化、社会与政治三个历史维度为‘名器’”的知识翻译学[22],强调知识之于翻译的理论性与方法性,同时也强调翻译的知识属性以及翻译行为的实践特质,跳脱出文化、语言,乃至学科范式的桎梏,从更高层面上认识知识以及知识翻译行为对一切学科的基础性作用,将翻译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2.中国国情与特色背景下对西学翻译研究的话语创新
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学。霍姆斯最初划分的应用翻译研究是与纯翻译研究平行的研究,大致分为译者培训、翻译工具与翻译批评三部分内容。西方学者杰里米·蒙代(Jeremy Munday)在此基础上对应用翻译的概念有一定的扩展。我国以方梦之、黄忠廉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研究应用翻译本体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应用翻译的策略和实践等问题,对应用翻译学做出了更全面、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论述与研究,是指向翻译理论的研究。傅敬民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应用翻译研究”,指出中国应用翻译研究在符号、资源、主体、问题以及价值五个方面所独具的特色。“中国特色应用翻译学”是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与中国人文特色,在西学概念基础上大力发展与完善的翻译话语创新的典型范例。国内的此类研究还有很多,如,译介学、翻译伦理学、跨文化阐释、文化翻译学、建构主义翻译学、社会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译者行动网络研究,等等。这些富有创见的新论以中国传统哲学为认识论基础,“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结合本国国情,探索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科的构建与完善”[23],在不同维度上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推动了中国译论的发展与成长。
四、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发展路径的思考
“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号角吹响至今70载,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各具特色。我们发现在上述两种建构路径中,仍有许多有待书写的领域和需要细描的空间。本土路径中借鉴传统文论的翻译话语创新,体现了中国翻译话语言简意赅、意会胜于言传、内涵多于明示的文化特色,而这一特色也在翻译话语传播、阐释以及接受上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如何向世界传播“玄”“和合”“易”的内涵及外延,外国受众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并接受等问题。现代翻译话语涉及中国当下的国情与人文特色,对外传播与阐释时,能否引起受众的兴趣与共鸣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西融合路径下,中国思想结合西方研究范式创新翻译话语中,一些话语与西方话语有相似之处,需要厘清概念,突显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与特色背景下对西学翻译研究的话语创新则更要体现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与研究,是否具有中西融通性,是否推动了世界翻译研究,或者能否被西学所借鉴。针对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建构中的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如下提升策略。
(一)本土化路径
本土化路径借用我国传统哲学与文论,如“文与质”“变与化”“太极”“和合”等概念提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无论是“推手论”“大易翻译学”还是“共生翻译”,都体现出翻译话语是由话语生产到话语实践的理论创新过程。对于翻译话语生产,我们还需考虑如下问题:
1.话语分类的明晰性
中国传统翻译话语包罗万象,涉及古典哲学、古典美学、宗教、古典文论等。话语生产过程中需要依据关键词进行分类,并结合具体语境,向外精准传播与译介,以防落入“以讹传讹”的尴尬境地。比如,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中分为以“神思、赋、比、兴”等关键词为代表的创作论;以“气、神、境、观、象、文、趣”等为代表的美学论;以“体、意境、文质、情采、形神、势”等为代表的文学批评论。以这些关键词衍生了诸如“文章学翻译学”(关键词为“义”“体”“气”)、“境界说”(关键词为“境”)等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可以参考这些话语分类,有目标、有导向地进行翻译话语生产与创新。
2.话语设置的阐释性
确定翻译话语的分类及翻译话语生产范围之后,需要对相关的话语概念、关键词进行背景铺陈与介绍。因为中国译学话语的创新与对外传播最终还要落实在受众的接受上,如何能让受众理解并接受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因而,以中国故事的方式介绍中国翻译话语的“前世”,受众才能理解它的“今生”,盼知它的“来世”。只要话语设置足够吸引人,把握正确导向,符合受众期待,其传播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3.话语目标的导向性
翻译话语生产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才能达到“以中释西”“东学西渐”的效果。需要用浅显易懂、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翻译话语的交流目的,否则会使人如坠云雾之中,产生抵触情绪,达不到传播效果。无论是中国话语还是西方话语,翻译的最初与最终目标都是沟通与交流,实现建构人类文化共同体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梦想。
(二)中西融合路径
“跨学科研究是促进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24]10。该路径下的研究通常是中西概念结合,在中国国情或者中国翻译实践基础上对西方话语进行创新研究。需要注重以下三个环节。
1.厘清概念
对于重合的翻译话语概念,要发掘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与西方翻译话语的不同之处,彰显中国研究的独特视角。比如,中国的“体认翻译学”与西方的“认知翻译学”有何区别,中国特色体现在何处,能否阐释西方翻译实践。又比如,中国的生态翻译理论与西方所说的“生态”有什么共性与差异性,两种“生态”概念的区别是什么,何以产生等问题。同理,还有翻译伦理学、社会翻译学、译者行动网络研究等都需要厘清概念,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解决翻译问题。
2.融汇中西
融汇中西的实质还是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国际化的问题。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既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进行文化身份建构,又需为世界所接受,与世界沟通交流。“充分学习西方的分析能力,不忘发挥本土的综合能力!……赋传统译论以科学形态,炼当下实践以理论范畴。”[24]8因而我们要致力于解决如何真正达到中西方翻译思想互参互证、共同构建翻译话语概念、翻译研究路径与翻译研究方法的问题。既能借古参今,也能以中释西;既有形而上的理论关照,也有形而下的实践策略;既有诗学的话语表述,也有科学的研究手段;既搭建翻译话语体系的结构框架,也充实以血脉肌理。如此,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就会丰满厚实,茁壮成长。
3.人文性与科学性统一
如前所述,中西融合路径是将中国的哲学与人文传统与西方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探索。若是一味强调翻译话语的模式化、标准化,容易滋生翻译研究的简单化、机械化倾向;而一味追求翻译话语的人文特性,又易导致翻译研究的重复性、经验性和片面性问题。因而需要将人文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与统一,使二者相得益彰,使中西融合路径切实地促进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建构。
五、结语
王东风说:“中国国运兴衰的曲线与翻译事业兴衰的曲线若即若离,大体一致”[25]。面对中国已“从一个理论消费的国家转向一个理论出产的国家”[26],且“国家翻译实践”与“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有利形势,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繁荣昌盛乃大势所趋。同时,在建构与发展我国翻译话语体系的浩大工程中,如何在翻译话语生产、翻译话语实践中正确地设置译题,合理地加以阐释,融汇中西,最终被目标受众有效地接受,实现国际化是广大翻译研究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正如黄忠廉所说:“国际化,不只是引介西方的译学成果,将中国译学思想从特殊总结为一般,初创理论,试创学科,才是真正的国际化”[27],这也是我们翻译学人谨以自勉,共同奋斗的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研究”(19XWW002)、2022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翻译话语关键词与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建构研究”(CYB22257)、2022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翻译话语的建构路径与发展模式研究(1951—2021)”(2022A-09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