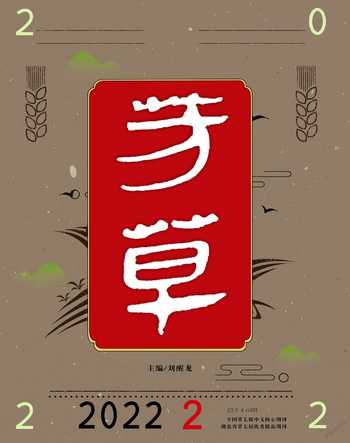“人类世”意识、图腾隐喻与文学的她性表达(评论)
2022-03-11金肽频

金肽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曾参加《诗刊》社第十七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有《圣莲》《花瓣上的触觉》《金肽频诗选》《鲸脊与刀锋》《夜修辞》,主编《海子纪念文集》《安庆新文化百年》等丛书。
海男长诗与“人类世”大意识
“一个人可以有一场图腾吗?”海男最新创作的长诗《图腾物语》,用隐喻和隐秘的语言完成了回答。每当看见它,海男的心情就会更加忧伤,有一股黑丝色的云烟,从她暗恋过的旧事物中升腾而起。这是旷日持久的图腾,充满了“人类世”思想意识的谜底,在等待探寻者。
与海男过往的长诗《穿越西南联大挽歌》《边疆》《涅槃》《海拔》《夜间诗》相比,这首《图腾物语》在原有叙事基础上,海男从她一如既往富有天赋的语言里不停跃出,铺展开一场图腾隐喻下的“人类世”色域叙事,整首长诗洋溢着“人类世”的大意识。这种“大意识”犹如海男词语的根须,来自于自然与命运,却激扬了作为女诗人的七彩内心。高原上的色域故事在历经诗人多重时间性的错位重置后,已成为诗人身体、灵魂与诗歌行为的血脉饱满的塑造。
海男诗歌在“人类世”视域下,彰显着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她作为人类,不仅仅作为个人,在关注着时间中的某个答案。这是她对大自然(她的出生地云南)的洗礼与膜拜,她站在原色的故乡地理,用自己高海拔的图腾想象,不仅对过去的文化,而且也将所有现实生活的种种风景都不能取消地置于一个现时的坡度。这条时间的溪流中,一些身影往上游动,一些身影往下流走,花园、废墟、牧场,隐含了秘密的时间、剪刀的哲学,此刻都变成了时间的缤纷意象,幻化为一条魔法之路。这是海男独特的精神牵引术,让多少秘密在灵魂躯体外漂泊。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海男的诗,总是一股通往超人类的姿态。艺术试图借以超越人类界限的途径千差万别,但海男的途径只有一条,在《图腾物语》这首长诗中,借助意象的千万条途径,抵达诗歌的终极意义。正如阿多诺那句:“唯有通过对它的非人性,艺术才忠实于人性。”海男的诗歌中,这种从“非人性”到“人性”的意义与重心的转变非常清晰,她在诗中写道:“云端上的客栈,完全使用岩石铸造/男人或女人在不同时间上完了最后一级台阶/秋色沿台阶漫游,形同一个旅人”,海男盡力让这种“铸造”的体验上升到“人类世”的维度,形成属于人类整体的“大诗”。骆一禾在评价海子的长诗《太阳·七部书》时,就曾指出,《七部书》的想象空间十分浩大,东至太平洋沿岸,西至两河流域,分别以敦煌和金字塔为两极中心,构建了恢宏的史诗图景。真正的长诗,从来都不属于某一个人,属于人类的共有命运。海男长诗《图腾物语》仿佛给人一种唯有挣脱了地球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的视角空间,展现出“超人类”的想象力。因此,这是基于主题、人类及其凝视的非人类超经验诗歌创作。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但精神将蒙绕着灰土”,海男的诗歌精神蒙绕着记忆的灰烬,猛烈地燃烧着自己的语言,在夜晚降临之后,她就将光亮转换为阴影,在光与影处在永恒的交错波动之中,构造出了一种宁静神秘、壮观辽阔的大诗氛围。
在《图腾物语》中,人不是独一无二的概念。人,可以是“模拟着花冠”的女人,可以是“这一生不可能错过火车站”的你,可以是“抖落了旅游鞋的沙石”的我。我们必须以图腾背景下的“人”为起点,万物必须指向他。然而,当海男的诗意一次次撞开人类自我参照体系时,“我愿意撤离到时间的另一边/面对那黝黯的光轮/我愿意成为你其中的一部分”,她的语言重现葱茏的现代性,开始引领我们实现这种可能——这是更为深远的可能,将我们引到一种超越人类记忆限制的地界。
海男对一些诗歌意象幻化处理后,成为图腾的基本塑形。尤其自始至终贯穿全诗的黑色基调的意象群。当人们真切地视“记忆黑色”为“人类黑色”的时候——不是作为一种有趣的表现颜色,而是作为诗学意义上的底色——人们在凝视中突然发现了新的内容,遽然陷入无限之中。现在,我们面对海男诗中关于“黑色”的叙事,有了一种不淡定的感觉:“踏着黑暗的辙色,我是我自己的幻影/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在地上飘忽”,“哪一种生活是我们的地狱?我已走出了黑暗/红色的裙裾裹紧了并非蒙难的身体”,“每当看见它,心情会更加忧伤/黑色像是一种从暗恋中升起的图腾”,“历史并不是空洞的,许多人在黑暗中来往/并非都是幽灵显现的梦,更多的是光圈”,“漂泊的足迹被土或雨覆盖后再无历史可言/有红色的太阳,必须有黑色的夜幕/在橄榄枝上有通往另一个星球的路线”。至此,人们终于理解,海男诗歌中的“黑色”底色,是她通往另一个星球的心灵路线图。这种“黑色”本身是有发音功能的,海男从语言无限多的可能的发音中选择它的重要发音。在诗人的眼中,黑色最为纯粹,在黑色的色彩里可以创造诗歌。大自然、缤纷往事以及个人的忧伤,经过了猛烈的燃烧,其灰烬已化为了诗歌的黑色元素,成为诗中时隐时现、人类相对意义上的“黑色”。
“人类世”源于地质学的概念,在进入人文领域以后,它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强烈反差。地球进入“人类世”的特征,与诗歌进入“人类世”的方式、感知和改写是一致的。现代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已将人类带入“人类世”时代。作为文学和诗歌,我们也应看到充盈着生态学意味的“全球化”,人类需要修补地球破碎的“精神圈”。这是诗人面临“人类世”的神圣使命。海男《图腾物语》的诞生,使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的人们,看到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可能在人文领域爆发,科技本身正在超越任何的意义话语,因而,海男将思考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破损的“精神圈”,希望用自己的“图腾”意识来深度塑造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来看《图腾物语》中指向“人类世”的有关片段:
锈迹小心翼翼的,尝试着如鲜血梅花/一朵朵的绽放,这是试探期,色彩艳丽的/物种们,总能屏住呼吸,勾引人类的知觉。
伟大的暗夜是一个巨空的秘密/是一个个出没于梦游状态中的逃离/蚊子出入夏夜的房间,偏喜欢吮吸肉体的甜蜜/而蝙蝠侠离人类的屋宇有足够多的距离/踏着黑暗的辙色,我是我自己的幻影/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在地上飘忽/是的,一个不可能触抚的时代。
门或墙垒屋檐,来自文明最初的前夜/在文明的前夜,人类在石洞中生活/避开了野兽和战乱。我想象不出我的前世/而当我熟练的移步于门外的辗转旅路/前世就像水一样清澈见底。
牛羊奶被手挤出,人类的胃啊/所有食物所到之处,均是生命的原力/羊群们穿过了陡峭的山脉走向/这是人类学家走过的地方/凡是人或物所在途经处,总有痕迹/…就像研究经纬度上飘落的云絮之谜。
万物万灵都在劳作/脚踝摩擦着野外向前伸展的荆棘/溪水突破了自己的禁锢最终跃出了峡谷/除了圆舞曲,手拉手扭动肢体/忘却死亡和痛苦,人类最高的境界/在于我们用身体尝试着各种深度的体验。
在这些诗句片段里,海男的“图腾意识”已然成为一个为“没有历史”的人们书写没有时间的历史的总和性方案,体现着现时深度。当人类社会经历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之后,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需要重新从诗歌的叙事开始。这和人类文明最初发端于原始诗歌是同样的原理。海男的长诗《图腾物语》通过现时深度的叙事方式,导向诗歌意义的终极。将自身作为一种“经过”、一种“故事”、一种“言说”,作为奉献给这个世界正在召唤的生命图景。海男隐喻性地描述着我们从何而来,又往何而去,以及与人类共同生存的核心话题。其诗歌本身已无可避免地成为同时代文化的物质元素的某种文本容器或镜像,然后又呈现了价值、立场、情感、心理等深层的文化意识。海男的诗歌语言与身体意识之间,具有一种血肉同构关系。这在海男“人类世”大意识的有机融贯之后,人们从她对于文化的深描中已可看到关于未来的想象,一种现时性的“深度现实”在诗中有效地创建起来。
图腾隐喻下的万物心灵与个性思考
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创造沉默,而不是声响或喧嚣。海男长诗《图腾物语》一开始,就用一种“窸窣声”创造出诗歌的沉默。《图腾物语》共有二十八首短诗构成,每首既可独立成诗,又融贯一体。时间与记忆是同生的。第一首《窸窣声穿过的花园面积》,海男让诗中女人穿上了“带有草本植物痕迹的衣裙”,镶嵌着时间的“柔软的花片”,但女人穿过的是“花园面积”,而不是“花园”。“花园”具体可感、可触,而“花园面积”就是一个引领人的想象无限延伸的愿望,隐含有人类栖居的第三种意义:“人类每天面对时空/不知不觉中就会将看不见的沙粒咽进去/是的,应该有可食的沙粒就像有可食的花朵和荆棘”。这句海男的诗,我们也可以像含着可食的沙粒一样来反复咀嚼它。
海男没有对诗歌意象进行原始性开发,及时抛却了传统意义,进而在时间中重构了人类的物化记憶,结构性地嵌入隐喻。并在诗歌的主体要素之间,依照波普尔所说“具体情势上的逻辑”,摆脱时间上的“过去”(仅属理论上的)。海男将一切确切的个人意识事件,解构为“文化花园”,亦即“文化灵魂”,它们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它们和人类劳动也不关联(这是诗人的一种普遍现象)。海男以文化单元的形式捕捉到了“窗户”“栅栏”“仓房”“村寨”“城池”“古堡”“草帽”这些有着灵魂信息的物事,打磨为和诗人、和他者紧密关联的意象,诗人生命的另一种人间再现。这些物事(标志、示意、符号)都有着自己谜一般的人类学叙事。海男诱导人们进入了布洛赫般的隐喻性梦幻,然后与她本人一同操持着一面面镜子(镜像),让它产生奇迹的力量,使其生活的原本目标消失——进而借助对家园(高原)文化的精神分析,犹如魔术师或穿插表演者,最后完成了图腾意象的解码与重构。在这首诗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尽管离梳妆镜很近,但似乎它已成为“文化花园”的某一种藩篱,“铁栅栏”是边界维持体系的象征,参与了海男图腾的初始构建。
长诗《图腾物语》的骨骼架构是由一部分主要短诗来实现的。《窸窣声穿过的花园面积》《箱子论》《我当然见证过云梯上的房子》《落日下出现了一片废墟和城池》《暴风雨之后的相遇》《关于魔法之路的幻想》《那使我忧郁的正是我的灵魂伴侣》《在每一个人的领地上都有光巡视》《有多少秘密在灵魂躯体外漂泊》《在幕后咖啡色的古城堡里》《一个人的图腾》《狂飙和孤独游走于时间尽头》,这些短诗是海男创建精神图腾的节点,但不是全部。读海男的长诗,感觉诗意会在无意识中突然地蹦跳出来,刹那间渗透到你的思想和情绪里。然后,她用极富撞击力的语言,带你迈入无人之境,看她过往的往事,如何从神坛上滚落。在这时,海男的魂灵一次又一次地跃出了语言,与读者窃窃私语。
无疑,海男是掌握着“时间语法”的诗人。她在写给“人类世”的话语中,发现着可能的诗意。在语义层面上,海男的很多语言充满了迷惑性,用多种或另一面的方式表示“时间”的概念化和现时性(如系列、持续性、间隔、轮回、起源以及发展)。海男诗歌的每一个意象,没有清晰的时间标志(如时间、时间段、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暗示),但她却用个性的刻刀将现时化功能从其所使用的情境中提炼出来。“时间”距离的效应有可能会体现在,比如,表面上看起来纯粹却具有诗意内涵的时间术语里,或者“激发的诗意”所产生的时间内涵。“石灰岩”“山寨”“发髻”“绳索”“古陶”这些作为进化论话语下的技术性术语,表示人类发展系列中的一个片段。本身就携带有伦理、美学及社会的内涵。“激发的诗意”累积起来,导致一种语义功能,它清楚地表达了人们与海男图腾的现时性距离。我们在这些词语的尽头,时常看到海男跃动的身姿,她是敢于从词语的尽头跃下去的女性,尽管下面已没有河流与泥土。只有被她移植过的时间花园。她捞取了一些诗的敏感的意象,担负起心灵建设的任务。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海男在诗中穿着“带有草本植物痕迹的衣裙”出发了,她拎着一只“箱子”。这只箱子装填着她的哲学奥秘和未来诗学的诗歌:“拎起箱子的欲望,箱子的历史总是伴随人的命运在辗转。”海男作为当下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总希望有一只“箱子”伴随她人生之旅。因为这些“试图像钢铁般坚硬,却免不了要生锈”的男人,不属于海男的世界。她只愿人世间有一只一尘不染的“箱子”,让她在人生旅途中产生片刻的兴奋,像造物主一样对她有温度、有耐心、有张力,遇到了风,她也不会脱落:“手指被沁湿了。人,有时候,就想在看不清楚的/想不清楚的,没有答案的时间中/让模糊蒙蔽着双眼,直到我们转眼间醒来。”这时的“箱子”嚯的一声,立即升腾为诗歌中的“图腾意识”。诗评家霍俊明在海男另一首长诗《夜间诗》评论里,也反复提及海男的箱子:“箱子(手提箱)在海男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经验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比如她的小说、散文、自传和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皮箱,比如诗歌《火车站的手提箱》)——移动、迁徙、漂泊、出走、游离、漫游、未定、不安。”诚然,这只“箱子”装满了海男秘可示人的图腾,以及海男独立旅程中的个人自传。
生于“七彩云南”的海男,她内心的色彩比高原上植物色彩更为丰富、纯净、辽阔。这是她心中不灭的色彩。《图腾物语》中就有“铁锈色”的栅栏、“黑色的巨蜂”“偏蓝色调的生活方向”“黑的”山岳、“红的”土地、“蓝的”水、“白的”云朵、“有黑有白”的羊群、“碧绿的”泉水、“紫色的”云雀、“褐色的”绿荫地、“碧蓝色的”澜沧江,这些色彩仿如哲学的“笺注”,更似一部丰富的《色彩学》。诗人有关云雀的描写,足可创建一本深藏玄机的《色彩学》了。海男认为这些色彩在隐喻中“仿佛也有了翅膀,往返于天空与人世间/我的图腾,就是我的礼赞”。
海男用色彩创造诗歌的能力,可与梵·高用色彩创造油画的能力相媲美。当然了,海男也热爱油画,而且在色彩的深度表现上,她打通了油画与诗歌之间的关节,让二者互为因果。海男用语言画画。《图腾物语》的主题意义就在于,世界与精神的那种交互影响。海男诗歌为我们描绘的图腾景象,又不可描绘,是一种无以言说的忧伤、孤独、行走和仰望,万物的终结和极致。图腾进入一个人的心灵,就成为一个人的某种传说,撞击着读者,回应着读者。她借用非艺术的超诗歌体验,展开对宗教价值的寻求,她用自己的双眼与自身的情感进入到人、物或自然的神秘的过程之中。她写“云梯上的房子”,不是进入,而是“见证”;她写“锁骨下的旅途”,不重于行走,而是一场“沐浴”;她写“牧场”,不在于“穿过”的感受,而是“对人与物留下痕迹的密码有兴趣”;她“使用剪刀”,看见了哲学,聆听到音律;她看到“云雀又来到了庭院”,爆发了一场关于色彩学的思考;她描寫“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情绪”,不是迷乱、惶恐、惊异,而是“蓝光闪烁,是幻想推动着身体/红光弥漫,是理念中飘过了烟火”;她猜想着“咖啡色的古城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真实的地址里有创世主的原形符号”。海男在诗中叙说的“埋葬”,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就好像秋天的树叶落下来那样的简单——只是挖一小块地,立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梵·高)尽管与梵·高同时代的尼采早已宣布“上帝死了”,但海男依然用自己的诗歌经验在观察世界,对宗教真理充满激情的渴求,“每个活跃的语词,都是一条命/每个妇女都因柔软的月光而信奉水的宗教”。将图腾视为一种纯洁的宗教,这是海男《图腾物语》带给我们的又一启发。
地理标识、灵魂诗学与她性表述
图腾是时间中的一种符号,它存活于话语中。由指示物、参照物和对应物构成。海男的这“一场图腾”是诗人用“时间”创造出来的精神客体。“实证主义幻觉”认为这是一种天真的现实主义,似乎缺少了依据,但历史文本的词汇和短语真正代表了世界的客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诗歌的精神客体,我们从过去海男的诗中就能发现,记忆、过去、幻想和现时环境,在诗中相互缠绕。带有黑夜色彩的,都是海男的身体“自传”,这是对海男诗歌的一种误读,其实,这种黑夜的“色彩自传”是她性的。“她性”的表述与“他者”的存在相对应,属于孪生姊妹。“她性”表述一旦成为诗歌中的经验过后,已不同于诗人本身。它是诗人的另一个精神客体。在海男的诗歌中,我们应该对海男的黑夜传、身体传……等进行“反身性”思考。我不赞成对海男诗歌是“身体诗学”的评价,而应定位于“灵魂诗学”。因为海男作为诗歌中精神客体是反射到读者身上的思考,不是海男的某一“传记”才有的存在。海男写诗的“反身性”能力,能够让读者看到“他者”的存在。有时,为了充分地知道彼此的现在,我们必须分享彼此的过去。如果我们的时间经验是非反身的,非直接的,那么,在个体交流层面上,除了彼此肤浅的认识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
因此,我主张倡导一种反身性立场,而不是反省性立场来面对海男的诗歌。在《图腾物语》的章节《羊群们为什么需要牧场》里我们看到,诗歌特定的主体是隐匿的、含而不露的,例如“地图上的”的小蜘蛛、照相机、测量绳、刺猬、野兽、“有黑有白”的羊群,这些诗歌的特定意象主体,并没有主动出场,就将“羊群”是人类生命体系的一个过程讲明白了,尤其强调“羊群们穿过了陡峭的山脉走向/这是人类学家走过的地方”,诗意一下子无限拓展开来。当我们用“不可感知”来感知海男诗中的她性叙事时,她的“反身性”表述,需要我们回头看看,让我们的经验回到我们身边,比如记忆、流浪和成长。然后和海男的经验产生碰撞与交融,在图腾隐喻下呼吸到诗歌的芳香、哲理的味道。
G·西美尔曾经有言,现代人只是沉溺在路途之中,由自己临时搭建的那座“桥”上。“桥”上有富足豪华的现代风景,有快感和娱乐,但缺乏的就是质朴的诗意与自由的憧憬。海男的《图腾物语》,既是站在高处的“图腾”,也是埋于深层的“图腾”,它为徘徊在“桥”上的现代人,指向他们回溯人性的源头,眺望人生的前程。实现人类有机的完整、完善、完美的生存,这是海男真诚而善良的愿望,是她的诗写给每一个人的理由。海男在诗中伸展的愿望,依旧是海德格尔的那一种:“在真正欢乐而健朗的人类作品成长的地方,人一定能够从故乡大地的深处伸展到天穹。天穹在这里意味着:高空的自由空气,精神的敞开领域。”在自己灵魂的故乡,海男以“天穹”的方式向众人敞开了有关图腾的神话故事。
海男的诗歌包括《图腾物语》,均具有明显的高原地理标识。海男持续以神话般的结构分析来对照空间分布变异的背景,她意识到,单纯的客观描述对于文化特征的地理分布的“历史”重构而言可能是一种破坏。如果一个诗人从表面上使用了过硬的关于巨蜂或羚羊的生态学描写,终极指向有关巨蜂或羚羊的结构分析及其关联性,便是对历史地理学的一无所知。海男故意在结构的、生态的与历史的论点之间制作许多矛盾,因为她喜欢这样跳跃式的矛盾。《图腾物语》通过在诗歌意象的源头与变异、中心与边缘、纯净模式与混合变异、质性的显示与物性的感知,将人作为孤立物所处的位置归因于有意识的行动和历史性事件(如借用、迁徙或传播),进而在无意识中生发出强大的诗意法则。列维·施特劳斯就说过:“如果人们对语言学的主题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刻,就更容易信服……一个让我们思考更多的真理,即人们建立起来的先于事物而存在的相互之间的联系……事物的本身以及决定了他们的事物。”海男本人也用诗的语言道出这层意义:“我渺茫的身体里装满了词语的黯淡和光亮/哪一种生活是我们的地狱?我已走出了黑暗/红色的裙裾裹紧了并非蒙难的身体”,释放出灵魂诗学的高原色彩。
海男的诗歌不仅属于地理概念的云南,云之南,这是人类的故乡。诗人可以眺望到的地方,都是人类的故乡。
故而,在人类学中有两个宏大、对立的概念:自我与他者。“他者”语言的性格释放、故事讲述,就成为“他性”的叙事特征。海男是中国女性主义代表诗人之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不再把性别关系看作是男性对女性欲望和权力的凝视,而是尊重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将女性“他者”放置在与男性主体等同的地位。这是海男的亲口访谈。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她性”与“他性”的关联以及性别叙事区别,这是人类的女性主义声音在诗歌语言中的回响,也是一种必然。
诗人海男在《图腾物语》整体叙事上,保持了“她性”的风采。这是人类学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的现时性距离。诗中没有置入预期的审美逻辑,以及作品主客体的亲密关系。这不是抽象的考虑,而是一种奇怪的命运。海男诗歌意象指涉的世界关系与内生性的世界有着某种转换。诗歌的力量置身于这种张力之间。叙事进程中的内在性,这是更高的真实之路。这有发生于海男身上的可能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海男诗歌有着宗教直觉、神秘哲学卡巴拉以及类似的神秘主义追问。许多严肃的思考在于方法转向。不是从表面上将个人转为主张交互主观性、仪式和制度,而是它被假设为一个纯粹的通道,通过它,图腾与象征才能进入“她性”的叙事当中。阅读者的目光与诗人的意象,同时绑定在结构主义的根上,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诗歌空间。《图腾物语》有两条关键词的回环,形成了开放性的逻辑理路:穿过——见证——隐藏——归宿;沐浴——覆盖——聆听——撤离。海男诗歌意象具有开放性和机遇。一个意象的出现,并非某一“主题”的逻辑发展,而是如喷泉一般思想情感的喷涌,将读者引入到自身的节奏。随着一扇大门的开启,你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宛如音乐元素的涌流。一种不熟悉的呼吸声,只能在诗中慢慢感知。人类是属于自然的,但不与自然同质。海男的诗句给人以富有启发的方式,撞开人类那有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感知之門。她的诗歌没有沉湎于“空”的苍白之感,或者一种所谓被要求的“自我的消除”的思索之中。海男认为体验与存在的连通性是一件极为身体的事情,丝毫没有必要把感官经验置于诗里。即使有人通过冥思获得了关于连通性的观点(这本身涉及深度身体性的事情),它的效果在于打开锈色的栅栏、“人类的胃”、欲望的“箱子”、模拟的“花冠”以及“时间外面的事件”。事实上,我们由这种经验所穿透、改变、激活或唤醒。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之物。倘若对海男在《图腾物语》中将读者与“她性”连通的经验视为对我们的真正自我的唤醒,那么在我看来,它必须包括我们的整个存在,即我们的身体存在与我们的精神存在。在关涉“人类世”的隐形语境中,海男始终保持了一位冥想者的姿态。
切斯瓦夫·米沃什有《诗的见证》:“我一代人都失去了。还有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民族。/但这一切都在稍后。与此同时,在窗里,一只燕子/表演它的瞬间仪式。”海男《图腾物语》告诉了我们,这些失去的“一代人”“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民族”如何在自己的图腾想象中赎回,并且赋予它以鲜活、纯净的生命力,让每个人的精神图腾永久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诗句,均引自海男诗文)
(责任编辑:王倩茜)
3787501908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