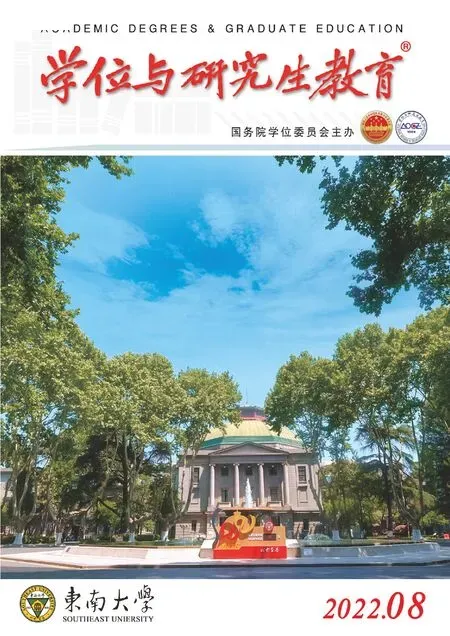知识社会发展中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动因、举措与成效
2022-03-03郑高明刘宝存蔡瑜琢
郑高明 刘宝存 蔡瑜琢
知识社会发展中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动因、举措与成效
郑高明 刘宝存 蔡瑜琢
基于文献梳理和政策文本分析,探究了2011—2021年间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动因、举措与成效。2011年以来,在国内需求和国际影响等动因驱动下,芬兰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博士生院、推动在地国际化、提升博士生就业技能、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缩短博士生毕业年限等,以加强博士生管理,提升博士生教育与知识社会需求的衔接。芬兰的博士生教育改革是欧洲博士生教育改革的缩影,也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扩散。
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知识生产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社会的发展对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社会”这一概念来源于社会学,最早于1966年由美国学者莱恩(Lane R. E.)提出,描绘了当时人们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美好愿景:即科学与理性将逐渐融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一种社会共识[1]。发展至今,“知识社会”也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一种共识,它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知识、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不同文化及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不同组织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社会中的工业生产和人类活动的重要特征”[2]。在人类发展知识社会的过程中,博士生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科发展的后备人才,还要培养知识社会中各个行业的知识工作者,发展满足知识社会需求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这给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培养满足知识社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是21世纪以来芬兰博士生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议题。面对挑战,芬兰自2011年开始进行新一轮博士生教育改革。
一、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过程和动因
(一)改革历程
1947年起,芬兰将研究生教育明确划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从而奠定了芬兰现代博士生教育的开始。同年,芬兰科学院成立,宏观调控芬兰的科学与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包括博士生教育[3]。基于前人文献分析,本文将现代芬兰博士生教育发展定义为三个阶段:芬兰传统博士生教育阶段(1947—1994年)、芬兰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阶段(1994—2010年)、芬兰大学博士生院阶段(2011年至今)[3-4]。
1.芬兰传统博士生教育阶段
芬兰传统博士生教育基于德国洪堡模式建立,具有三大特点:①以培养学术接班人为导向。在芬兰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中,导师通过指导博士生完成某个学科的研究来培养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实现该学科学术职业的延续[3]。博士学位论文是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②以教授为主导。传统模式中,芬兰博士生导师在录取和培养博士生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3]。③以学生为中心。芬兰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尊重博士生个体发展,所以不设置培养时间限制,也不设入学年龄门槛限制[3]。尽管芬兰博士生教育随着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但“洪堡”模式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芬兰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苏联解体,芬兰进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这促使芬兰重新调整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教育发展政策,开始向知识经济转型。知识经济是知识社会所衍伸出来的概念,强调知识的经济效应[2]。人类经济活动向知识经济转型对高等教育发展有两大重要启示:第一,教育和培训能够提升个体的认知能力和生产力;第二,基于知识的生产力的增加会给个体带来经济收入,这些经济收入的获得也会成为衡量个人资本的重要指标[5]。因此,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芬兰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机会来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增加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发展信息通讯和电子技术等经济发展亟需的学科,这为芬兰博士生教育发展提供了资源和机遇[6]。这一时期,欧洲的高等教育也开始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强调培养效率和社会问责。这些内、外部因素冲击了芬兰博士生培养的传统模式,促使芬兰对博士生教育进行改革,其中一个主要措施是实施博士生培养项目制。
2.芬兰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阶段
1994年开始,芬兰借鉴了一些国际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尝试通过实行项目制博士生培养,进行博士生教育改革。项目制博士生培养是通过新成立的“研究生院”来组织实施的。芬兰的这些“研究生院”和美国高校的研究生院不同,前者是基于国家需求所开设的跨校和跨学科的联合博士生学位项目。因此,这一阶段的芬兰博士生教育被称为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阶段[4]。芬兰政府希望通过推行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来加强国内高校合作,加强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网络建设。实践中,芬兰大学可以基于不同的研究主题向芬兰教育部申请建立该主题的“研究生院”——跨校、跨学科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获批的项目由芬兰教育部提供经费,用于支付博士生的工资和从事博士研究的相关费用。
这一时期实施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在芬兰政府宣布结束国家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改革的次年(2012年),芬兰共有112个国家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共招收了约1600名带薪博士生;而同一时期,芬兰大学有约4800人接受传统博士生教育[7],可见这一阶段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仍是主流。换句话说,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作为芬兰政府专项经费支持的机制,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芬兰大学博士生的管理结构。同时,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在实施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因此,芬兰科学院于2008年授权以奥卢大学海奇•鲁斯考合(Heikki Ruskoaho)教授为首的专家工作组对芬兰博士生教育的整体发展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设计新的改革方案。
3.芬兰大学博士生院阶段
2011年,鲁斯考合专家工作组代表芬兰科学院发表了题为《提升芬兰博士生教育的质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关于芬兰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建议》的调研报告(简称“《鲁斯考合报告》”),围绕大学定位、博士生管理、质量保障、财政安排等方面对芬兰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提出了12条具体建议[8]。同年,芬兰政府宣布停止接受新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的申请,之前已审批的项目运作至2015年全部结束。这意味着芬兰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至此画上句号,芬兰博士生教育进入第三阶段:芬兰大学博士生院阶段。
(二)改革动因
1.满足国内知识社会发展需求
芬兰需要改革博士生教育以满足芬兰知识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第一,提升博士生教育和社会需求的相关性。2010年,芬兰教育部曾预测,如果芬兰大学继续以过去十年的培养效率(每年1600名博士毕业生)培养博士,随着学术职位的填满,至21世纪20年代,芬兰博士生教育将面临博士毕业生的生产过剩、失业率上升、人才流失的问题[9]。芬兰科学院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调查几乎同时指出,芬兰大学对博士生的职业规划仍然以学术职业为 主[10]。这就意味着,芬兰大学需要尽快转变观念,加强博士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培养博士生在知识社会的可迁移就业能力。第二,构建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文化(quality culture)。质量文化是指在一种全民为质量负责的组织文化,它强调加强质量管理的过程管理,保障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实现其职能,实现过程中的“零瑕疵”。这既需要芬兰大学对博士生教育发展有更明确的统筹规划和更系统化的组织管理,也需要建立更规范的质量保障机制,最终实现博士生教育质量的社会问责制。
2.提升芬兰国际竞争力
2009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给芬兰经济带来了冲击,芬兰经历了经济衰退、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深度重组和传统工业的转型。在此背景下,要维持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博士生教育需要营造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吸引高水平的国际学者和学生[11]。然而,2009年OECD的调查报告显示,芬兰是发达国家中少见的人才流失(net brain drain)的国家[12]。该调查报告显示,芬兰每年向其他OECD国家提供了大量人才,流失比例达到6.8%。大部分来芬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国际人才是为了继续接受教育,而不是工作移民,而这里面只有48%的人有意愿在毕业后留在芬兰工作[13]。这些都与芬兰高等教育体系的在地国际化程度较低密切相关。芬兰缺乏有效的支持国际人才融入社会的机制,大大降低了国际毕业生的留芬意愿[11]。因此,芬兰教育部在2016年发布的《芬兰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2017—2025)》明确指出,“芬兰应该吸引和鼓励在芬兰的国际学生继续博士阶段学习,将其所学服务于芬兰社会发展。要实现这点,芬兰政府、高校和企业都应当积极改善其对国际学生的态度和环境支持”[13]。
3.解决博士生联合项目制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芬兰科学院2006年和2011年对芬兰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调研报告,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的推进已遇到了瓶颈,也亟需改革[7]。在宏观层面,随着立项数量逐渐增加,芬兰并没有采取有效的项目管理措施,导致了项目的质量参差不齐、运作模式不清晰、重复立项、经费分散而未能有效利用等问题[10]。只有少数的规模较大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建立了质量保障机制(如清晰的项目指南、质量跟踪调研),并为博士生提供了足够的课程资源等。在微观层面,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未能改善芬兰传统博士生教育的弊端。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制阶段的芬兰博士生导师指导仍然存在导师数量不够、导师职权不清晰、导师指导不足、指导质量缺乏监督等问题[7]。除了导师指导的问题,联合培养项目制改革之前存在的其他问题,如培养年限长、学生辍学率高、国际化程度低等,也未能有效改善[7]。这个阶段,芬兰大学对博士生国际化的理解也局限在多派学生去参加国际会议,限制了芬兰博士生教育的国际化发展[10]。
4.参与欧洲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
芬兰博士生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欧洲诸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2003年,欧盟部长会议将博士生教育改革纳入“博洛尼亚进程”的议程,并拨款给欧洲大学联盟(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EUA)用于对欧洲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调研。这也确立了EUA在欧洲博士生教育改革中的话语权。2005年和2010年,基于两轮调研结果,EUA发布了《萨尔斯堡建议》和《萨尔斯堡建议II》,提出博士生教育的成功与否,主要由其所在的科研环境所决定[14]。因此,EUA提出欧洲大学应该开展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通过大学参与来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实现博士生教育的质量保障。在具体改革措施方面,EUA提倡效仿部分国家(如丹麦、荷兰、德国)试行的博士生院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芬兰探索国家联合博士生培养项目制的同时期,丹麦和荷兰的高校率先尝试成立了博士生院[15],德国研究协会也成立了一批“研究生院”(graduiertenkolleges),后来逐渐演变成博士生院(graduiertetnschelen)[16]。博士生院是设置在大学内部的支撑博士生培养的管理组织,旨在在导师指导之外,为博士生教育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营造跨学科的科研环境[15]。博洛尼亚进程推进中,EUA通过发布相关改革建议、定期组织论坛和会议、每3~5年进行改革现状调研,总结和推广改革中欧洲各个大学的有效举措(good practices)等措施,来推进欧洲境内的博士生教育改革。如2005年,基于2004—2005年关于EUA成员大学的博士生教育开展现状调查,EUA在萨尔斯堡会议上发布了《为了欧洲知识社会发展的博士生项目:欧洲大学联盟博士生项目调研报告》,从组织结构、经费支持、质量保障、创新举措、联合培养等方面总结了调研中发现的来自22个不同欧洲国家的48个大学的一些好的博士生教育举措,并以具体实例说明,向所有欧洲大学进行推广[17]。芬兰自1995年加入欧盟以来,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建设和“博洛尼亚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因此,芬兰大学也积极参与到欧洲博士生结构化改革中,成为此次欧洲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二、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在上述动因的驱动下,芬兰大学博士生院阶段的改革诉求是在原有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加强芬兰大学在博士生教育中的参与和管理,对博士生教育的质量进行监督,为博士生职业发展提供支持,最终实现博士生教育学术质量和社会相关性的双提升。从2011年起,参照芬兰科学院的《鲁斯考合报告》,芬兰的博士生教育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通过大学内部建立博士生院,加强博士生管理
《鲁斯考合报告》提出“大学应该主动承担博士生培养和发展的总责任”,加强大学在博士生教育方面的战略规划和管理,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在大学内部成立博士生院[8]。芬兰科学院建议芬兰大学建立“(学校)博士生院—博士生项目—导师指导”的三级博士生教育管理机制。
第一步,建立博士生项目和博士生院,并确定其与学院的关系。在学校层面,或者学科大类层面,建立博士生院。各个学院可以向博士生院申请设立博士生项目,博士生项目可以是单一学院、单一学科的,也可以是跨学科的项目。学院层面所设立的博士生项目,由所在的学院负责具体运作和管理。博士生院通过在博士生招生过程和选拔标准、导师指导实践的范畴、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措施、学生反馈和及时纠错机制等方面提出一定的规范(纲要),实现对校内博士生项目的统筹规划[18]。
第二步,确立导师、学生、博士生项目的关系。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下,博士生只需要向导师或者导师所在学院申请入学,由导师和学院决定录取与否。此次改革要求博士生在申请入学时,向具体的博士生项目申请,同时要确认个人意向的导师。如此一来,博士生在入学后,在博士生项目内接受导师的指导,通过与项目建立联系,博士生也与博士生院建立了联系。
第三步,明确博士生院的职能。芬兰大学通常在所发布的博士生教育纲要中,明确博士生院的职能,包括:制定博士生发展纲要、规范博士生教育的过程、开设公共课程、组织博士生集体活动等。通过博士生教育纲要,芬兰大学也明确了学生、导师、学院和博士生院在博士生管理中角色,逐渐形成了校内博士生管理的组织结构。
(二)提升博士生的就业能力,增强博士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
为了应对就业市场的需求,《鲁斯考合报告》提出,在培养目标方面,提升博士生就业能力应该是芬兰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芬兰博士生培养应该既包括科研训练、通识课程,也包含博士生通用技能的培训[8]。在此目标指导下,芬兰大学从提供通用技能培训和加强校企联系两个维度,积极建立博士生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衔接。
一方面,芬兰大学相继开设了通用技能课程。内容包括项目管理、学术伦理、研究方法、学术期刊论文写作、学术报告、科研经费申请、求职等,提升博士生自身的就业能力。有的芬兰大学(如图尔库大学)还为博士生提供职业规划指导,定期分析芬兰博士生就业市场形势变化,帮助博士毕业生了解就业市场的需求。
另一方面,芬兰大学加强了与企业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博士生在学术和非学术行业间的流动。如开设校企联合博士生培养项目,实行校企双导师指导模式,鼓励博士生到企业研发部门实习和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开展校企交流活动。同时,芬兰大学鼓励博士毕业生到企业就业。在这方面,芬兰最有影响力的举措为2015年开始的“企业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 Docs in Companies,PoDoCo)项目”。PoDoCo项目是由芬兰的大学、基金会、企业联合发起的实现博士毕业生与企业匹配和对接的项目,其目的是通过利用芬兰社会资源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推动博士毕业生在企业就业,促进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18]。截至2020年,已有11家基金会加入了PoDoCo项目,组成了PoDoCo的基金会。具体实践方面,博士毕业生通过PoDoCo项目平台搜索和联系与自己研究相匹配的公司,然后与该公司一起向PoDoCo项目组提交博士后课题申请。PoDoCo项目组管理层和基金会代表对申请课题进行会审和筛选。最终,各个基金会将对其选择的课题提供经费资助,支持课题负责人到所选择的公司中完成课题;该公司则负责提供完成博士后课题所需要的场所、设备,并承诺在该课题完成后,雇佣该名博士。
(三)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完善博士生教育的社会问责机制
为了满足社会问责需求,《鲁斯考合报告》对芬兰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做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大学博士生院要明确博士生录取的标准和程序、导师指导的范围、博士生教育质量监督和评估的标准。大学还应该设置学生反馈渠道、错误修正机制。”同时,《鲁斯考合报告》还强调博士学位论文是评价博士生最终学术成果的重要指标,大学是其质量保障的负责单位[10]。
在《鲁斯考合报告》的指导下,芬兰大学在维持以同行评议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依据的同时,采取了适当的管理措施来满足知识社会的问责需求。具体如下:
首先,在芬兰大学内设立了博士生反馈渠道和纠错机制。如图尔库大学的博士生院为解决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专门出台了指南,将矛盾分为学术伦理、行为不当和其他冲突等三类,并对每一类矛盾的反馈渠道和解决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允许博士生更换导师。
其次,芬兰不同大学的博士生院各自发布了博士生教育发展纲要。通过制定纲要,芬兰大学为博士生教育构建了质量管理的过程,并明确过程中各个环节(如录取、导师指导和学位论文等)的衔接和质量要求。
第三,进行校内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估,以质量评估促进质量提升。例如,于韦斯屈莱大学在2016年结合院系自评和跨院交流对校内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了评估,总结好的实践经验,向全校进行推广。2018年,该校邀请了外国专家对校内科研环境建设情况(含博士生教育)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改善大学的科研支持服务,包括对博士生和导师科研的支持。
最后,开展博士生导师指导培训。例如,坦佩雷大学每学期为博士生导师定期开设培训课程,培训的内容包括学术指导的责任和过程、与学生互动的方式和技巧、不同指导模式(单一导师制或者联合导师制)等。每次培训参与人数限定在20人以内,进行小班培训,确保了培训的质量。
(四)缩短培养年限,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2009年,芬兰颁布了新《大学法》,规定芬兰大学具有终止博士生学习资格的权力。2011年,《鲁斯考合报告》提出“一个博士生全职完成学位的年限为四年,非全日制的博士生的年限可以适当延长,但总有效学习时间不该超过四年”[8],这为芬兰大学明确博士生学习年限和提升博士生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依据。
在《鲁斯考合报告》的建议下,芬兰政府通过芬兰大学核心经费资助政策对高校提供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支持。芬兰大学核心经费资助政策是芬兰教育部基于芬兰大学的规模和绩效,为大学提供经费,支持芬兰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日常运作的重要财务政策。芬兰政府所提供的核心经费也是芬兰大学运作的主要经费来源。其中,在芬兰大学核心经费资助政策的财政投入计算公式中,(预期)博士毕业生人数被作为经费计算的重要绩效指标之一。将大学核心经费与毕业生人数直接挂钩,使得芬兰大学在提高博士生毕业率方面有了更多动力。
在法规政策和财政刺激的支持下,大部分芬兰大学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举措,鼓励博士生按期毕业,提升培养效率:①明确学习年限为四年。大部分芬兰大学明确将“为期四年的有效学习年限”写入了各个大学博士生院的博士生教育指南中,对博士生学习年限提出了清晰的要求。②跟进学生进展。除了年限要求,部分大学还要求博士生和导师共同制定相应的学习和科研计划,博士生需要经常向导师汇报进度,更新计划的完成情况。这与传统芬兰博士生教育中的“放养”模式存在明显不同。③设立博士生分流和退出机制。通过博士生自我汇报和导师跟进,识别学习不活跃的博士生,调整他们的学习资格为“休学状态”。博士生如果长期不活跃,将有可能被取消学习资格。④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经费支持。例如,坦佩雷市政府、坦佩雷大学为博士研究后期的博士生设立了学位论文完成奖学金(3~6个月)和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金,鼓励他们积极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和答辩。
(五)推进在地国际化,提升博士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芬兰博士生教育国际化,提升芬兰的国际竞争力。根据芬兰科学院的《2012年芬兰科研现状报告》的建议,芬兰的国际毕业生应达到该年度博士毕业生总数的20%[1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芬兰大学在继续支持博士生国际流动的基础上,加强了博士生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建设。主要举措有四个方面:
第一,为博士生开设了更多的英文课程。芬兰大学博士生院所提供的通用技能课程,大部分为英文授课。英文课程不仅提高了博士生的英语水平,也促进了本地博士生和国际博士生的课堂融合,营造了更为国际化和具有包容性的校内支持环境。
第二,协助博士新生适应当地的新生活。例如,东芬兰大学博士生院专门为国际博士生发布了《国际博士生生活指南》,成立了博士生协会,通过老生带新生的传帮带形式,统一提供入学初期的融入支持服务。坦佩雷大学和坦佩雷市政府联合开设了“国际人才人生导师”项目,为国际博士生匹配在坦佩雷工作的优秀人才为人生导师,引导他们尽快适应在坦佩雷的生活。
第三,组织校内国际经验分享活动。大部分芬兰大学的博士生院会定期为博士生组织分享活动,介绍国际访学、国际论坛、国际项目的机会和经验,提升博士生的国际跨文化素养。除了加强在地国际化的发展,芬兰大学仍坚持原有的鼓励博士生国际流动的措施,为博士生提供国际差旅费,支持博士生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如国际夏(冬)令营、国际学术论坛、国际学术交流和访问、国际科研项目等。
第四,支持芬兰博士生毕业后的国际学术流动。2010年开始,芬兰多个社会基金会联合推出了“国际博士后研究奖学金(Post Doc-Pooli)”项目平台,支持优秀的芬兰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后到世界各地进行博士后研究,向世界推广芬兰的科研成果。截至2021年,该奖学金共资助了约700名博士毕业生到国际各地进行博士后课题研究[20]。
三、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的特征、成效和不足
(一)改革特征
欧洲各国的博士生教育改革作为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研究区的重要环节而备受重视,也同时受到欧盟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相关政策和财政调控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相同的价值观[21]。同时,在EUA的推动下,欧洲各国各个高校在相互效仿和影响中推进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改革具有一定趋同性。因此,芬兰的博士生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二十年来欧洲博士生教育在全球知识社会发展中的改革特征:
第一,改革具备自下而上的特征。欧洲大学联盟发布的《萨尔斯堡建议》、《萨尔斯堡建议II》和芬兰的《鲁斯考合报告》都是由政府委托专家组就博士生教育的现状评估作出的发展建言,给大学提供了改革建议。不仅仅是芬兰,法国的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也充分体现了《萨尔斯堡建议》的基本原则,如法国博士生院的创立、博士生可迁移职业技能的培训的开展等[21]。但是这类报告,它们本身并没有强制的政策约束力。如何进行改革,取决于每所大学,实践中也是由各个大学自下而上、相互效仿、结合本土需求实现改革,所以体现了欧洲博士生教育规范性制度化发展的趋势。
第二,通过立法或者修订法案来推进改革。比如说,芬兰通过颁布和施行新《大学法》,从大学管理体制、学校领导结构、财政和国际学生管理等方面,赋予了大学改革的自主权,包括聘用、管理、开除博士生的权利。类似地,德国在2002年修改了高等教育法,支持德国高校缩短毕业年限、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和效率、增强课程国际化等[22]。法国在2007年推出了《大学自主与问责发法》,扩大法国大学校长的权力范围,支持了法国的博士生教育结构化改革[21]。
第三,改革体现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在博士生教育层面的不断扩散。芬兰高校建立博士生院,在校内为博士生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不断完善的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过程,提升博士生培养效率。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在芬兰大学内部构建“全民为质量负责”的质量文化,加强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管理体现了新公共管理主义在博士生教育中的渗透。根据EUA最新的调研报告,截至2021年,62%的被调研的欧洲高校已经建立了博士生院,这说明了芬兰高校不是特例,借鉴新公共管理主义来实现博士生教育管理已经逐渐被大多数欧洲高校所接受[23]。
与此同时,芬兰的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也有其特色。其一,给予大学高度自主权和充分信任。通过发布的新《大学法》,芬兰政府赋予了芬兰大学更多办学自主权(包括博士生办学),这成为芬兰各个高校能够自主开展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法理基础。整个改革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芬兰政府对其教育体系的信任,由大学自主摸索改革路径和实践,政府仅通过调研建议、财政刺激来宏观调控改革方向。其二,创新文化融入实践。强调创新、敢为人先是芬兰教育的一大特色,也在此次改革中有所体现。如PoDoCo项目最早来源于坦佩雷大学Yrjö Neuvo教授的创新教育课程“Bit Bang”和他在创新领域的研究积累。其三,基于科研成果开展实践。此次芬兰博士生教育改革延续了芬兰教育中强调科研精神的特色。除了以上提到的PoDoCo项目是基于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所产生之外,芬兰高校的其他改革措施也有所体现。如于韦斯屈莱大学通过校内定期开展博士生教育质量调研来调整博士生院的定位、职责范围、发展需求等,并邀请国际同行来参与调研,提升调研结果的科学性。
(二)改革成效和不足
经过十年的努力,芬兰博士生教育在组织管理、质量提升、国际生数量增长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首先,截至2021年芬兰13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0所大学成立了博士生院,并构建了“博士生院—博士生项目—博士生指导”的三级管理机制。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芬兰传统博士生教育松散的组织结构,提高了芬兰大学内部校级层面对博士生教育的参与度,为加强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提供了组织支撑。其次,在质量方面,所培养的博士生与社会需求的关联度更高,博士生在非学术行业的就业能力也得到了一定提升。2011年以来,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对博士需求的逐渐饱和,芬兰博士毕业一年后的失业率曾一度持续攀高,2016年时高达8.1%,但在2017年开始下降(6.8%),于2018年时降低到3.6%[24]。这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芬兰博士毕业生开始在非学术行业,如工业界和商界工作有关。再者,2010—2019年,芬兰在读国际博士生人数从2094人增长至4002人[25],国际博士毕业生人数也从201人增加至444人[26],国际博士生人数占博士生总人数的比例从13%增长至26%[27],实现并突破了原来芬兰科学院设定的20%的比例目标。
尽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学院在改革中的参与度相对较弱。由于博士生的三级管理机制是由校内博士生院推动,许多改革举措也停留在了校级层面,院系层面的管理人员和博士生导师并没有全部参与改革。不少学院和导师对博士生院的角色、定位以及改革措施并不了解。例如,于韦斯屈莱大学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估报告(2016年)显示,许多被访的在校师生表示不清楚博士生院是什么,从未参与博士生院相关的任何活动[28]。
其二,改革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在此次改革中,芬兰政府虽然将责任下放到大学,但是并没有专门为大学提供相应的改革经费支持。近几年来,随着芬兰政府对芬兰大学核心经费拨款的整体削减,芬兰大学所能获得的博士生教育经费支持也整体减少,导致了芬兰大学不得不减少了带薪博士生职位。芬兰研究者工会的调查报告指出,2017年,可以持续四年获得经费支持的芬兰博士生占整个群体不足25%;对于有四年持续经费支持的博士生,只有60%能够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业;而其他没有四年持续经费的博士生70%以上无法按时毕业[29]。同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在芬兰一名博士生平均需要6.3年完成博士学位。可见,虽然芬兰政府和大学在提升博士生教育培养效率的改革目标方面形成了共识,但是在实施中,博士生教育经费削减的问题让这个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其三,芬兰的博士生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局限性和不确定性。2017年,OECD关于芬兰的科研创新体系调查报告显示,芬兰大学的国际科研合作仍然比较局限,合作者主要来自其他北欧国家,国际合作网络不够广泛,国际影响力不足[30]。在实践中,芬兰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也停留在芬兰政府和芬兰大学校级博士生院层面。
[1] LANE R E.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6, 31: 649-662.
[2] VALIMAA J, HOFFMAN D. Knowledge society discourse and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2008, 56: 265-285.
[3] LAIHO I. Mestareiden opissa Tutkijakoulutus Suomessa sotien jälkeen[D]. Turku: Turku University, 1997.
[4] KIVISTO J, PEKKOLA E, SIEKKINEN T. Latest reforms in Finnish doctoral education in light of recent European developments[J].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7, 7(3): 291-308.
[5] MARGINSON S.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Australiad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AHOLA S. Doctoral education in Finland: between traditionalism and modernity[M]//The doctorate worldwide. Berkshire England and New York: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cGraw-Hill, 2007: 29-39.
[7] KAMULA R, LAINE K, KLOVE B. Systematic doctoral education in Finland since 1995[C]//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ld regions development, 2013: 75-86.
[8] Academy of Finland. Tavoitteeksi laadukas, läpinäkyvä ja ennakoitava tohtorikoulutus[R]. Helsinki: Academy of Finland, 2011.
[9]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inland). Tohtoritarve 2020-luvulla: ennakointia tohtorien työmarkkinoiden ja tutkintotarpeiden pitkän aikavälin kehityksestä[R]. Helsinki: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Finland, 2010.
[10] NIEMI H, ALTTOLA H, HARMAAKORPI V, et al. Tohtorikoulutuksen rakenteet muutoksessa: tohtorikoulutuksen kansallinen seuranta-arviointi[R]. Tampere: Academy of Finland, 2011.
[11] PUUSTINEN-HOPPER K. Mobile minds: survey of foreign PhD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 Finland[R]. Helsinki: Academy of Finland, 2005.
[12] OECD. OECD reviews of tertiary education: Finland 2009[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9.
[13]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inland). Better together for a better world: policies to promote internalisation in 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7–2025[R]. Helsinki: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6.
[14]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Salzburg II recommendations: European universities’ achievements since 2005 in implementing the Salzburg Principle [R]. Salz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10.
[15] BYRNE J, JORGENSEN T, LOUKKOLA T. Quality assurance in doctoral education: results of the ARDE project[R]. Brussel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12.
[16] 朱佳妮, 朱军文, 刘莉. 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师徒制”与结构化的比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3(11): 64-69.
[17] 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Doctoral programmes for the European knowledge society: report on the EUA doctoral programmes project 2004-2005[R]. Brussels: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2005.
[18] PODOCO. Post docs in companies[EB/OL]. [2020-11-19]. https://www.podoco.fi/.
[19] AITTOLA H. Doctoral education reform in Finland—— institutionalized and individualized doctoral studies within European framework[J]. 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7(7): 309-321.
[20] Saatioiden Post Doc-Pooli. The principles of the Säätiöiden post doc -pooli[EB/OL]. [2018-05-24]. https: //postdocpooli. fi/background/.
[21] 卞翠. 法国博士学位制度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5): 90-95.
[22] 王文礼. 当前德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措施及其启示[J]. 现代教育科学, 2015(6): 162-166.
[23] HASGALL A, SAENEN B, BORRELL-DAMIAN L. Doctoral education in Europe today: approache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R]. Geneva, 2022.
[24] Statistics Finland. Main type of activity of completers of qualifications one year after graduation 2007-2018[EB/OL]. [2020-04-07]. http://pxnet2.stat.fi/PXWeb/pxweb/en/StatFin/ StatFin__kou__sijk/statfin_sijk_pxt_111l.px/table/tableViewLayout1/?loadedQueryId=6e169a26-3e50-48fb-af7f-2276e14369e5&timeType=from&timeValue=2007.
[25] Vipunen. Korkeakoulujen ulkomaalaiset opiskelijat[EB/OL]. [2021-05-19]. https://vipunen.fi/fi-fi/_layouts/15/xlviewer.asp x?id=/fi-fi/Raportit/Korkeakoulutuksen%20ulkomaalaiset%20opiskelijat-%20n%C3%A4k%C3%B6kulma%20vuosi.xlsb.
[26] Vipunen. Ulkomaalaisten korkeakouluopiskelijoiden suorittamat tutkinnot[EB/OL]. [2021-05-19]. https://vipunen. fi/fi-fi/_layouts/15/xlviewer.aspx?id=/fi-fi/Raportit/Ulkomaalaisten%20korkeakouluopiskelijoiden%20suorittamat%20tutkinnot%20-%20n%C3%A4k%C3%B6kulma%20vuosi.xlsb.
[27] Vipunen. Yliopistoissa suoritetut tutkinnot[EB/OL]. [2021-05-19]. https://vipunen.fi/fi-fi/_layouts/15/xlviewer. aspx?id=/fi-fi/Raportit/Yliopistokoulutuksen%20tutkinnot-n%C3%A4k%C3%B6kulma-vuosi.xlsb.
[28] LYYTINEN A, PITKANEN K, TASKINEN T.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research evaluation report 2018[R]. Jyväskylä: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2019.
[29] FUURT. Survey for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in Finland by the Finnish Un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2017)——an English Summary[R]. Helsinki: The Finnish Union of University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FUURT), 2018.
[30] OECD.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Finland 2017[R]. Paris: OECD Library, 2017.
10.16750/j.adge.2022.08.012
郑高明,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上海 200092;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中芬教育研究中心中国方主任,北京 100875;蔡瑜琢(通讯作者),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与商科学院副教授,中芬教育研究中心芬兰方主任,坦佩雷 33014。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上海实践的中欧博士生联合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编号:C2022241)
(责任编辑 黄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