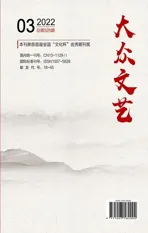老庄“道”“物”关系浅析*
2022-03-03段海庚
段海庚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人在天地万物中总体上扮演着被动适应者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万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技进步表明人正对“物”进行更深层次的利用,而诸如资环环境、科技伦理等问题却彰示着人与“物”之间愈益深化的矛盾。无疑,人类需要对万物有一个全面、深刻而切实的理解。“道”的提出便是老子反观天地万物的成果,对老庄“道”“物”关系思想的梳理,或可为理解“物”提供有益的思考。
对于老子“道”“物”关系的解读,生成关系是主流,历来研究多以“始” “母”“生”等概念来阐述这一关系,如王弼:“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为其母也”。而在生成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又阐发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如李锦全、曹智频认为“道”由万物混杂组合而成,二者间是相因相存的关系。此外,也有对老子“道”“物”关系的系统梳理,如陈鼓应总结的:本原、本体与现象、形上与形下、一与多以及隐含的体用关系,林光华总结的:道生物、道成物、道统物、道通物等。关于庄子,研究者大多认可其“道”“物”关系是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如冯禹指出庄子继老子之后,给了“物”以明确的定义,而“道”“物”关系是“物物者”与“物”的关系。在肯认对老子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强调庄子思想蕴含着的生存论关怀,如邓联合认为庄子在老子“道”论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以“体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体系。
一、“母”与“宗”
老子所强调的“道”,是他提出的“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的哲学范畴,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而关于“物”,在《老子》中主要指形下的、纷繁复杂、形态万千的事物,亦即“万物”之“物”。当我们总观《老子》文本,“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两方面概之:一者,道生成天地万物,而后化之育之,为万物之母;再者,“道”乃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遵循,是为万物之宗。
1、“道”:万物之母
《老子》有言“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老子•一》),“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五十二》)。显然,“始”与“母”是同一的,都指“道”。而所谓“母”,不过比喻“道”作为万物的生成根源,同时又覆养万物的功能。这一概括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其一,道生万物;其二,道成万物。
道生万物,可谓历来学者注老最为普遍认可的观点之一,毕竟《老子》中不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这样直白的章句。这些无不表明,道是生成万物的根源,万物由道而演化而来。关于“道”生万物这一过程,老子将之描述为一个“恍惚”的状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
不过,道之于物,不仅仅是“生”而已。《老子》第五十一章言:“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老子•五十一》),这些范畴都体现了道的“成物”之能。所谓“道成物”,指的是在万物长成的过程中,道使万物各得其性,成为自身。王弼将长、育、亭、毒、养、覆释为“谓成其实,各得其庇荫,不伤其体矣”,这显然是道演化出万物之后,万物的变化、发展过程。道赋予了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法则,万物只需顺之变化发展,便能各得其性,成其自身。
显然,道之于万物,“生”与“成”相辅相成,道生物的过程就确立了“物”的本性和法则,而物之“成”则是道生物赋予潜能的充分发挥。
2.“道”:万物之宗
“道”的生物过程规定了物的运转法则。这一生成论上的法则赋予,反映在存在论视域下,就体现为“道”之于万物的宰制之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便可以将“道”称之为万物之宗,它是万物运动变化所效法、遵循的对象。
道为万物之宗,首先体现在万物对“道”的效法上。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王弼注:“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可见,天地万物以道为运动变化所依循的根源法则,才能充分实现自身本性。而“道”所效法的“自然”,并非“道”之外的某个存在,而是“道”“自己如此”的本然之性 。
然而,虽然道作为万物的根源法则,具有统御万物之能,但老子认为这并不是“道”对万物的主动宰制。“道”性自然、无为,对于万物,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 第五十一章)。物并不是被动地承受者,其发展变化,都是自主自为的过程,甚至对道的顺从,也是万物自为的选择,对于这一过程,老子称之为“自化”。
二、齐通万物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物”关系思想的基本思想:“道”是万物生成基础的“物之所由”(《庄子•渔父》),同时也是主宰万物运转的“物物者”。不过,庄子更多的是借助“道”以齐通万物,正如他所说的古之道术,“齐万物以为首”(《庄子•天下》)。
1.“道”:遍在万物
在庄子的思想中,“道”并不高高在上,始终超越万物,而是普遍地内在于万物之中,正如他借老子之口所言:“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
于小处,道在蝼蚁屎溺。《庄子•知北游》东郭子与庄子的对话中,东郭子问:“所谓道,恶乎在?”庄子依次回答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以这些愈益卑贱的物来强调道的无所不在,大如泰山、小如秋毫、寿如彭祖、夭如殇子……道公正无私,无一不在。于大处,天地阴阳无不道。《知北游》篇言:“天地者,形之大着也;阴阳者,气之大着也;道者为之公”,显然道也存在于天地阴阳之中。
道既在万物之中,那么二者如何相融呢?庄子提出了“物物者与物无际”(《庄子•知北游》)的命题。“物物者”便是“道”。庄子在与东郭子的对话中说道:“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庄子•知北游》)。主宰万物的“道”内在于万物之中,与物交融没有边界,物本身是有边界的,那是不同的物之间的界限。大道存在于万物之中,似乎随着物之边界而有了边界,但实际上,因为“道”本身的无限性,因此是没有边界的,谓之“不际之际、际之不际”。
2.“道”:超越万物
“道”普遍地内在于万物之中,但“道”之于物,却也不止于此。能“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说明 “道”对万物还具有某种超越性。
物与物之间,由于自然性分总有所不同,或白或黑、或坚或脆……庄子肯认事物之间这种固有的差别,“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但他又认为这些差别是出于认识的立场的不同,正如北海若告诉河伯:“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庄子•秋水》)。正是出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才有了诸子百家的彼此是非之争,他们在“物论”上的是非之争,实际上出自认识的局限性对“道”的遮蔽,“道隐于小成,言隐于浮华”(《庄子•齐物论》)。
无疑,万物各有立场,因而就有了彼此是非等差别性的观点。而“道”能超越这种差别,“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齐物论》),能让彼此、是非、美丑等相对概念不再相互对立,而只是环之一节。此时再看具体事物,“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当然,并非说以道观之万物就完全相同,而是“道”能客观、平等地对待天地万物,无有任何的成见偏私。
这样超越彼此是非的“道”,实际上已非老子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形上之“道”了,它俨然已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是庄子境界之“道”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境界之“道”无疑是形上之“道”在心灵的落实,它的超越性也源于形上之“道”本身的无限性。正是形上之“道”浑然一体、无成无毁、无生无灭,境界之“道”才能做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庄子•天下》)。
一方面,万物无论大小善恶美丑,都如一地内含大道,因而千差万别的事物本质上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当认识主体摒弃成见,便能照见作为一个整体的天地万物,不同事物都只是其中一环,因此认识主体对待万物也应当平等如一。庄子正是从“道”之于物的普遍内在和超越性来说明万物的齐通特征,以此强调万物的平等性。
三、由“道-物”而“心-物”
老子的“道”,万物由之而生、恃之以成,并遵循于道的规制。庄子将老子的“道”作了内在化与境界化两个方向的深化发展:其一,将形上之道内化于万物之中,成了物内蕴的生命力,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其二,总结了“道”对人类社会的指引之能,以境界之“道”概之,进而将“道”“物”关系引入了“心-物”的领域。
1.化“道”入“物”
老子“道”与“物”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对立性,这包括形上与形下、生成与被生成、主宰与被宰制等多方面的对立。而在这一对立当中,“物”的存在被“道”遮蔽了。一方面,老子言“物”是为了论“道”,甚至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物”的定义;另一方面,老子的“物”缺乏生命力和自主性,“万物”终须在由“道”而生的机械的存有原则中生育亭毒。反映到老子的政治思想上,就显示出了对百姓的忽视,“愚民”“小国寡民”等理念,对百姓的真正诉求显然是缺乏关怀的。
庄子似乎看到了这一矛盾,因而力图将“道”化入物中。这一过程,他主要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强调道与物的共在共存:他发挥了老子“大道氾兮”的思想,认为“道”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天地阴阳蝼蚁屎溺无有遗漏。第二步,说明“道”与“物”的无际融合:以“物物者与物无际”(《庄子•知北游》)的命题,说明“道”不仅存在于“物”之中,而且与“物”完全相融,毫无界限。
正因为“道”在“物”中,所以“道”对万物发展变化的支配性已经内化为万物本身的内在本性和生命力,从而实现了万物真正的“自化”,庄子也借此实现了“道”的有序性与“物”的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的融合。在这样的“道”“物”关系之下万物的发展便有了无限的可能,而这样的发展与事物自身本性的发挥又是完全统一的。
2.由“道”而“心”
“道”乃万物之宗,于人亦如是。老子将顺道而为的人称之为“有道者”。庄子则进一步将这种顺道而为的理念凝练为一种精神境界——“道”,这一境界之人,其所行所为无不顺道,即顺遂于万物的自然本性,进而能遨游于无穷的境界而无所待。因为无所待,他们的立场无有局限,因而认识超乎彼此是非的界限,甚至“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
庄子对“物”的态度,通过道的内在化与超越性而达到一种公正无私的境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便是这一开阔而宏大的平等理念的彰显。然而平等待“物”却不意味着积极求“物”。在庄子眼中,一切“物”皆是“外物”,而趋求外物会不断损耗生命的自然本性,正如《骈拇》章所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庄子•骈拇》)。他消解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物”的对立,却将这种对立转移到了境界之“道”与“外物”的对立,或者说 “心”与“物”的对立之上。
此外,庄子还认为人对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无能为力的,“死生、存亡……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人只有在于物境接触时只客观反映而不带成心,让这些变化不侵入心灵,不扰乱本性,才能与万物同游于和,心情安适顺畅。这种方法,庄子称之为“游心”。“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世间》),能在天下万物之间、世间不得已之间游心,他认为这便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四、老庄“道”“物”关系启示
老子与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普适性,也存在着或源于他们个人、学派乃至时代的局限性。在认识论层面,老庄的“道-物”认知模式让人得以从整体上把握天地万物,却也因“道”的存在而对“物”有所遮蔽;在方法论层面,老庄“道”“物”关系思想发展出了顺道而为的智慧,同时又不免消极倾向的“无为”思维。唯有秉持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观点理念,面向时代,去粗取精,才能让他们的思想具备与时俱进的生命力,而我们也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当今时代,资源环境、科技伦理、个体的非全面发展等问题困扰着人类。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问题都和人类与“物”的关系相关。应对这些问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面对是前提,“顺道而为”是应对问题的基本原则,而对于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于这些“不得已”之间“乘物游心”或许不失为一种积极而洒脱的应对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