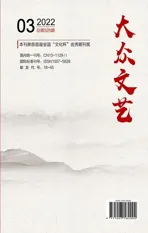研判翻译与互文性的关系
——由《魔侠传》的回译引发的思考
2022-03-03谭登华
谭登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72)
一、《魔侠传》与《堂吉诃德》
林纾、陈家麟将《堂吉诃德》引入中国时,大刀阔斧地修改塞万提斯的原文,仅翻译了两部中的第一部,还赋予其一个中式书名——《魔侠传》。相比“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魔侠传”显得简练而陌生,暗含着经过变译、改译的译本与塞翁原作几乎判若两书的隐喻。当阿莉西亚•雷林克将《魔侠传》回译至西语,她尊重林纾译作,保留了很多新情节,没有为了回归《堂吉诃德》而修删。比如主人公在中译本里名为吉萨达,西语译本以Quisada对应之。
这场跨越百年的翻译接力将翻译、互文性两个概念拉入研究视域。此前国内无学者把回译(traducción inversa)这一特殊翻译现象和互文性相提并论,而主要探讨如何借助互文性开展翻译研究,印证互文性理论的可操作性。堂吉诃德的中国化与魔侠的西化让“信”的翻译、“不信”的翻译、回译并入同一神奇的翻译历程;要阐明翻译与互文性,将翻译的下属概念“回译”纳入研究无疑有启发价值。
二、翻译中的回译
回译,从字面意思上考察,是将已译入其他语言的文本再译成原语文本。王正良的《回译研究》给出了定义:“回译……是将他人的译语文本再翻译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四个要素:译语文本、他人、再翻译、回归原语文本的过程”。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释“traducción inversa”为“反译”:“译者从母语向外语译的一种翻译”。查找文献、语料库可知,多数语境里“traducción inversa”是用B语言翻译A语言文本,个别学者以之指回译;故而,反译不是回译的同义词,回译和西语的“traducción inversa”也不能等而视之,此处按下不表。
如把译出、译入看作两个过程,不考虑涉及多少语种的转译,那么经历两次翻转后,文本的细枝末节必然有变。本雅明在《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中认为,高级语言是其他语言的翻译,翻译让不完全的语言变完全,不完善的渐完善,“是通过一系列持续的变形而达成的由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普遍意义的“翻译”是本雅明所理解的广义的“翻译”的组成部分;回译作为一种反复的过渡,乃翻译的复数,具有持续的优化力量。
本雅明对翻译的认识离不开其纯语言构想。犹太教传统影响下,他将语言分为神、人和物的语言,神语作为精神沟通媒介,有道成肉身的创造力。作为命名者的人讲着纯语言,而自然物之传播依赖于语言,问题最终还是指向人。至高的语言传达精神实质;如果回译后的《魔侠传》未能接近“纯语言”,无法把作品的精神实质传给读者,那在本雅明看来,这根本不构成翻译行为,如此一来,翻译岂不是陷入自我定位的矛盾?
《中国译学大辞典》载有杨自俭对翻译的定义:“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定义针对普遍意义的翻译,而译者是变量,把译文引向无法预测的方向;联系林纾的译法,翻译发挥透明的中介功能之余保留了一定主动性,否则只能算一种特殊的修辞,或符号系统的机械转化。该定义说明:意义可以推衍至本雅明强调的精神本质,而翻译是意义的跨境运载工具,在语际摆渡;语言本身无内容,是透明介质,唯有其传播的精神才可被言说。综合这些观点,翻译的定位不再游移不定,回译的学术身份也被厘清。尽管“回译”这个能指只对应最后一次由译出语输出到译入语的逆转,一次尘埃落定的文本回归,但在回译发生前,数轮翻译曾连番上演,意义在语际置换、更替,文本可能经历过无数次勒菲弗尔意义上的折射。写作《魔侠传》的过程中,陈家麟据《堂吉诃德》英译本进行口头转述,林纾复将之转写为文言译本,后一个过程也是有阐释特征的语内翻译。
把翻译过程推至无限,回译便扩张成场域,代表文本间的关系。这种直接性关系有时十分密切,以至读者会视一部名著及其译本为同一部书。如《堂吉诃德》原著、杨绛和董燕生的译本,统称《堂吉诃德》,一个默认的名字囊括多个对象。此既是话语上的选择,也是语言上的强迫。翻译是能动的参与者,在意义的传递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原著、译著的同一性是虚假的、隐藏的,被译者的无形之笔遮掩。当回译作为一种行为、活动、事件成为不同语言领域内的文本间的纽带,当原著经多次翻译重回原始语域,当数量庞大的译者群体与原作者同时面对文本,以至于其主体性可以忽略不计,写作者的概念整合进时代精神和意识形态,而精神和意识又在文本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洗涤、净化,另一概念也呼之欲出,即与翻译保持着学术亲缘的互文性。
三、互文性的提出与发展
茱莉娅•克里斯特瓦通过《词语、对话和小说》介绍了巴赫金分析文本的对话性理论,为了代之以她提出的互文性。互文性强调文本间互相补充、指涉的作用,即“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所以,凡为文本,必是互文本,作为来自其他文本的“马赛克图案”而被生产。正如克里斯特瓦的理论灵感来源——巴赫金所强调的,所有文本皆有文本间的对话性,不可完全孤立地将作品与其他作品割裂开,它们处于一种互问互答的喧哗中。一组业已完成甚至尚待写作的文本构成一个网络,文本凭借相互关系而存在,某一文本同时是其他文本的换位。文本是吸收和转换文本的唯一场所,无论主体意识参与与否。作者在这后结构主义的网络中缺席,绝对的个人原创力退场。
互文性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带动下不断发展,今已不能单纯用克里斯特瓦的框架来限定其内涵,秦海鹰在《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中总结出两条进路:
一个方向是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另一个方向是诗学和修辞学;前一个方向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而模糊的解释,把它变为一个批判武器……后一个方向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越来越精密的界定,使它成为一个可操作的描述工具
随着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已将翻译研究同互文性联系在一起了”。可以发现,自互文性被提出,到批评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进行梳理、总结的70年代,再到各理论相互交叉,强调跨学科研究的当下,“互文性”罕少作为专属于符号批判理论的概念进入学术论坛。《魔侠传》被译回西语这一特殊翻译事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有必要以回译代替翻译,拉开互文性研究的新序幕。
四、翻译与互文性
回译至原语的文本相比其他译本更能体现出与初始文本间的互文性;互文性这个普遍存在的场于此处给出了能量极值——相同的语言赋予互文本的比较研究更宽松的准入规则。被林纾汉化的魔侠不再是堂吉诃德的镜中影,受儒释道影响的奎沙达内心笃定,博学多识,勇于捍卫尊严;林纾未翻译序言和第二部,文本结构改弦更张,只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作者、读者的运思方式都随之变化。《魔侠传》在林纾的操纵下非复是《堂吉诃德》这张地毯的背面,直至雷林克完成回译,堂吉诃德与奎沙达、Quijote与Quisada,他们在同一水平面上远离翻译的一极,走向互文的一极,但实际上是在翻译、互文的双重场域向上奋力攀升。
堂吉诃德不是奎沙达的主人,桑丘也不是山差邦的主人,正如互文本没有主人,在移植过程中斩断了来路,于新文本中发挥作用。先锋批评与文学史批评的迥异之处在于,前者不致力于探究文本起源和去向,互文性的场中无法考察“引言”出自哪里,影响施往何方。罗兰•巴特提出“每个文本都依存于互文状态,互文……不应与文本的某种本源相混淆,试图找到一个作品的‘来源’‘影响物’也就落入了起源关系之神话的案臼”。同样,部分文本借助翻译关系而依存于其他文本,第一种情况是不考虑回译,循译介方向溯源而上,标记出文本语际传递的路径,须有较强可行性,方能䌷绎出传播途径;第二种情况,若涉及大量译作,对应各样语言,多位译者改译、操控,回译到原始语种的文本必会脱离表面从属关系,与原作割袍断义,在这方面,回译与互文再次不谋而合:回译的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秦海鹰总结的作为描述工具的互文性和作为批判工具的互文性这两种学理内涵。
然而,联系文本间性讨论翻译时,研究者很难将译者主体性搁浅。有很多未标出的引用,因为互文联系对于读者而言是隐在的,不能就互文做定量分析,海量的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甚至令作者对这些微妙的引用毫不知情。与之相反,译者常是显在的,一个译本对应一个译者,读者阅读作品前已有了译者、文本必会发生视域融合的前理解,默认译者对原作施加了个人影响;也罕有翻译研究者采用与互文相类的场域观点看待翻译,往往不把译文看作由文本拼贴而成,它就是从那个确凿无疑的原文处被搬运过来,否则译文便不够“信”。此非翻译本身局限,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当研究话语指向一个文本时,其译者就站立一旁,构成不容忽视的维度,宣示对文本的生成负责。
翻译和互文通常涉及跨语言的情况,且因为文化的隔膜,往往不为异文化体系的他者所知,便成了语际转替中的超语言参数和诠释障碍。讽刺的是,翻译本是解决这些阅读问题的工具,但无法实现绝对透明,自身竟构成问题。读者不能透过模糊的窗看清另一面窗。只译了一部的《魔侠传》,多少中国人能通过它认识到《堂吉诃德》的价值所在?塞万提斯通过人物性格、对白、写作手法揭露的时代精神尽数被林纾以中式思维代替,可谓是归化翻译的典型。别有暗喻的巧合是,未译的第二部上升到讽刺现实、考验理想高度的文旨顶峰,《堂吉诃德》第一部中,现实的真实、合理与堂吉诃德的幻想、荒唐形成对比;第二部中现实的虚假、荒诞与堂吉诃德的真诚、热忱构成反差。《魔侠传》回到自己百年前错失的家乡,但家乡已物是人非,因为魔侠本就不是堂吉诃德,《魔侠传》与《堂吉诃德》是诞生于两种异质性文化的两部书。不过,曲折的传译、改译、回译过程赋予作品别样魅力,带来重审翻译与互文性的契机。
进行回译与互文性的对照研究,以期发现文本在扩散、流动、换位中的秘密,结果回译、互文性陷入相同困境,所以须引入第三个参照来觅得突破口,即用写作这个概念统筹翻译和互文:翻译是一种写作,或者勒菲弗尔意义上的“重写”或“改写”,通过翻译总有新文本被生产出来;写作也是重写,是对其他文本的引用,不存在悬浮于真空中的文本,一切写作都如马赛克拼贴、镶嵌在一起。这样,翻译的场和互文性的场被写作的场涵摄,在写作的领域内,作者和语言轮番上场,个体性和社会性都不甘缺席。林纾创作了《魔侠传》,这部书也由《堂吉诃德》改译而来,二者构成互文本;雷林克翻译《魔侠传》,也完成了一种写作,一种文本的生成,Historia del Caballero Encantado与《魔侠传》《堂吉诃德》也构成互文本。
托多罗夫总结过,书写提供的是“不可还原的多样性”“无限分延的视角”,但是当多样和分延成为默认事实,翻译和互文性这种带有明显重复、近似特性的“异类”让自信不拾人牙慧的书写陷入沉默。文学的本质问题变得日趋复杂的背后,是文本间同性相斥、诸多概念纠缠;我们不再斩钉截铁地为文本、概念划定阈限,像归置图书一般分门别类、互不干涉地摆放,文本和概念都破碎了、混杂了。不妨引用“写作”这本书吧,它总有足够的包容性来构建这座不再对翻译和互文强行归类的图书馆。总体而言,上述的多样性抑或单一性都不算是威胁意识的风险,看待问题的狭隘视角远比它危险得多。
总结
前人多从翻译实践角度研讨翻译与互文性的关系,认为互文性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可以更好地发挥译者的主体地位。互文性彻底工具化后,只能指导两种层面的翻译实践:一是微观层面的判断、反思和调整,发觉词句或段落的表达方式与其他文本有关,从而有意增强翻译的意义关联性;二是宏观层面的文体结构、意识形态、创作手法等,译者在捕捉到文本间性的基础上推动译本向互文本靠拢。之前的研究成果都不能否认:互文性和翻译不是只具单一方面的纯净物,而是复杂的混合物。要全面地看待翻译与互文性之关系,必须反抗拘泥于翻译实操的惯性,从现实的翻译现象寻求理论灵感,研究才能既及物又及理。
恰恰因为互文性将单向度的话语流动变成多向度的场域,对作品、话语的研究势必面临模糊性,而在翻译中虽难免存在删改、替换等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形,但假如两个文本彼此没有互鉴互照的作用,那也不构成翻译,所以译本与原作间的关联逐渐脱离掌控,双重模糊让精准的新批评式的研究变得扑朔迷离。话语、主体模糊了身份,不再独立,转换过程以文本为始端亦以之为结果,历时粘连成共时,共时延展为历时。
把翻译和互文并置讨论,译者有必要像作者一样,隐没在互文或翻译的场域当中?某些情况下,这种运思方式有其裨益。翻译场和互文场都可以试图消除创作者维度,通过克服主体性推动文本自由嬉戏,但在理论的历时性发展中这观点难免暂告失败,文本不可能永远任意浮动,居无定所;两个场在回译这一概念范围里实现最大交叉,场强达到峰值,文本间的亲缘关系紧密到让人怀疑回译后的译文与原文是否存在差异;当翻译和互文性归入写作,二者的模糊性被文本生成(创作)的奥妙掩盖——拿起笔开始写作,笔端流露之物既可能是某文本的译本,也可能是某文本的互文本,但能或不能鉴别出其性质、定位、归属又如何呢?
莫里斯•布朗肖说:“一种合适的翻译研究将揭示一种抵达本真思想的方法。因为这样的翻译会揭示表达带给思想的那种为语言所固有的变化……通过陈词滥调的使用,思想将恢复纯粹……处于在言语的亲密当中。只有陈词滥调能够把思想从反思的畸变中拯救出来。”。语言在发展、变化中存在,无论多么新颖、独特的表达都终将与其他表达建立互文关系、翻译关系乃至回译关系,但这不是缺憾,反而是拯救思想的良机,试设想翻译作品极大丰富的那天,原文、译文一并成为陈言,我们会对互文性与翻译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Traducción que se hace del idioma del traductor a un idioma extranjero.
②Translation is removal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hrough a continuum of transformations.Translation passes through continua of transformation,not abstract areas of identity and simil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