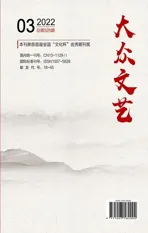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流浪地球》:中国科幻元年的类型开拓与女性的缺席
2022-03-03陈琳
陈 琳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 030000)
2019年的春节,《流浪地球》一经上映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成为票房黑马,将《流浪地球》放置在中国科幻电影坐标中,无疑这是一个令人雀跃的起点,被誉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狂欢之后,更应该注意到影片对女性话语的压制。《流浪地球》所展现的中国式科幻电影范式建构和有效的价值表达值得总结,也需要正视影片中笼罩着一层性别的阴影,打破科幻片中男权话语的虚妄,为中国科幻电影打开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
一、审美文化的表达:科幻电影的中国底色
一直以来,科幻电影的长期缺席,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隐痛。中国第一部有据可循的科幻电影是出现于1938年的《六十年后上海滩》。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小太阳》、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1年根据科幻小说《王府怪影》改编的《潜影》、1991年的《隐身博士》以及之后诸如《霹雳贝贝》等儿童科幻片、21世纪以来质量堪忧的科幻电影创作等,这些科幻电影零星地散落在中国电影的序列中,难成体系。因此《流浪地球》在中国电影史上尤为可贵,学者戴锦华因其在2019年上映,称该年份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流浪地球》改编自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科幻文学作品,讲述人类为应对太阳极速老化的危机,开始“流浪地球”的计划即倾尽全球之力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从此人类开始了带着地球长达2500年的流浪。中国航天员刘培强肩负起领航员的重任,他与儿子刘启以及其他救援队在地球遭遇木星引发全球发动机停摆时,奋不顾身拯救地球。影片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以中国本土科幻小说为框架,以恢宏瑰丽的想象和酷炫的视觉奇观带给人们迥异于好莱坞科的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审美体验,这也正是《流浪地球》成为票房黑马的原因所在,影片的类型创作加上中国元素,带给观众未曾有过的审美愉悦。
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流浪地球》展现了末日背景下的中国景观,带有一种强烈的中国式价值表达和在国家崛起的背景下的大国当担。首先,影片视觉上的呈现是熟悉的中国符号,再也不是好莱坞科幻大片中的中国,如《2021》里的影像,一个模糊的、意义不明的可有可无的存在。《流浪地球》开头的地下城旋即展现一幅熟悉的春节图景:春晚的配乐、舞龙舞狮的传统艺术的展现、搓麻将的过节传统。另外,楼宇间横架着的晾衣栏杆、扫码支付的未来变形、红底白色的积极向上的横幅、20世纪的“工装制服”的改造,地下城展现了一幅既年代感与未来感兼具的“诺亚方舟”。地表上的冰封世界里,央视的“大裤衩”与上海东方明珠取代了经典好莱坞影片《后天》中的自由女神像,北京、济宁、济南、杭州、上海等地名一一展现,兰州拉面的招牌在冰雪中隐约可见,一种文化认同感油然而生。其次,以几千年来根植于血液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故土情怀和儒家文化的浸染下的家国情怀,扩宽了影片的精神向度,也使得“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故事逻辑,贯穿于电影中“回家”这一主线索以及父辈对子一辈的牺牲更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影片“流浪地球”计划所带有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愚公移山精神、外公韩子昂救下无数人在水中托着的人类稚子韩朵朵所展现的仁义,刘培强的俄罗斯同事以自我的牺牲换取空间站的控制权所展现出来的肝胆相照、刘培强与刘启一起拯救地球是“上阵父子兵”的谚语映照以及刘培强甘愿牺牲的济世情怀等等,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像化的传达。最后,影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以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集体主义下的救世情怀的表达,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精神和文化内核。影片将好莱坞科幻片中自诩为救世主的美国搁置,统领世界的是各国一起组建的“联合政府”侧面体现了对西方国际强权的不满。故事以亚洲为主的救援队为主要描述对象,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与地缘政治的考量,重新调整和改写好莱坞科幻电影美学,从而建构起科幻电影的中华民族想象。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世界各国集体付出行动,影片中的中国人更是为了地球勇于牺牲,使得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格局中更能显示出大国智慧与人类气度。影片不再是拥有超能力的孤胆英雄拯救世界,而是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对未来抱有期望,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集合集体之力,对地球进行“最后一分钟营救”,这也是对中国民族向来笃信的“人定胜天”审美心理的契合。
当然,影片文本仍然有许多瑕疵。或是因为叙事篇幅的局限,对人物背景描述的不足,导致人物动作逻辑的断裂。另外,地下城空间有限,因抽签而被“抛弃”的一半地球居民何去何从,影片未对此进行交代,由此产生的叙事空白割裂了影片的价值观,电影本意立足于以人为本的角度,但为了拯救全体人类带着地球流浪却因救援资源不足任由另外一半的地球居民在灾难中无辜丧生,这与电影的整体立意相悖。
二、“在场的缺席”:《流浪地球》中的女性形象
在欣喜于影片成就的同时,更应关注其不足。影片中对女性的遮蔽,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科幻电影作为舶来品,源起于西方。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剧作难以摆脱男性主义的窠臼,复制了西方电影中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与性别身份的贬低。
影片当中的女性角色屈指可数。刘启母亲是个全程静态的角色,或是在全家福中展现幸福的微笑或是在病床上形容枯槁地躺着,影片将其与刘启的亲子时光全然省略,刘启对母亲的眷恋以及对父亲放弃救治濒临死亡的母亲由此得积攒的怨恨也就无从谈起,尚且需要观众的自行补足。
韩朵朵作为主要的女性角色,故事或许想呈现见证多次英勇无畏的牺牲后明白责任与担当、一个主体意识的自我成长和担任众人救赎重生希望的人类稚子,然而编剧对其刻画有失水准,一个前期叛逆、闯祸、令人反感的稚弱女童,后期在历险中始终处于被拯救者的形象。在最后请求各国支援的广播中,只能哭哭啼啼的传达自己的无助、却无法准确传递具体的救援方案,“他们都在拯救地球而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在一番毫无意义的“演讲”后,各国队员竟然纷纷调转车头,返回苏拉威西,一起推动撞针,拯救地球。这一角色展现出的功能除了加诸其上的“希望”的意涵外,更多的是衬托拯救地球的男性英雄的无私奉献与崇高伟大。
周倩作为救援队唯一的女队员以及全片唯一的“女英雄”,在影片前期是默默无闻、服从队长王磊指挥的背景板与工具人。令人咋舌的是在“火石”所剩无几的情况下,为了阻止队员再牺牲,突然用枪将其毁灭想以此唤醒队长的理智,事实上,这一看似颇具有推动叙事的举动,也只是为了塑造救援队长王磊的悲悯即对杭州地下城全员覆灭的悲伤。另外,周倩在最后救援任务中,只是承担着照顾韩朵朵,试着向其他救援队发布求助消息的任务,而这一任务的主要实施者是韩朵朵(人类稚子/希望之花)。在地震中,周倩用身体护住韩多多和与李一一(男性英雄),展现出一种母性的力量。这仿佛是谢晋镜头中的女主人公再现,唤回队长/成为一些男性的精神港湾,“更重要的是,女人不能因为弱小而无所作为,也不能超出男人自尊心的承受力而有所作为。他们应该按照男性社会的需要来实现自我,柔而不弱,曲而不折、顽强生存,九死不悔。”
诚然,影片中以朵朵和周倩为主要女性角色,已经跳脱男性凝视的视角,使其承担一定的叙事重量,在影片的片段里成为推动叙事的驱动力。但仍然无法否认《流浪地球》中对女性主体构建的缺失以及忽视女性的经验即对女性的适当描述难以掩盖事实上女性话语、女性立场、女性困境的缺失。显然,《流浪地球》中性别角色的二元对立,遵循的仍旧是传统两性的性别认知:男性为冒险、智慧、勇于牺牲的统治者与领导者,女性则是慈祥、善良、柔弱、母性的服从者。影片默认了男性英雄与女性弱者的形象,强调了现代社会中男权的价值以及强化了女性观众对既定男性形象的想象和对男性秩序的认同。
影片在上映后获得诸多美誉,甚少有人提出批评,惘论揭露影片对女性身份的偏见与刻板了。如果从对建设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意义出发,认真指出影片的某些缺陷更有利于这一电影类型的质量提升以及发展的可持续,从而为中国电影工业的类型化生产提供品质保证。
三、想象与超越:中国科幻电影与女性主义
市场期待什么内容的科幻电影?或者说,除却技术层面上的不足,中国科幻电影在内容创作层面还缺少什么?从上述对《流浪地球》的文本缺陷的分析中,或许可以为之后中国科幻电影寻求一个可能的创作思路。
在想象力消费的时代,中国科幻电影应该如何寻找超越的突破口?科幻电影属于一个历史范畴,显现了一个时代基于现世又超于现世的想象与情感。好莱坞科幻电影向来以想象力丰富奇诡为重要制胜之道。从《2001:太空漫游》的伟大幻想到《2012》的末日灾难,《黑客帝国》的数字想象与《阿凡达》的外星殖民奇观还有《星际穿越》《地心引力》等等,这些影片通过调动非凡想象力,组织独特艺术语言,展现丰富与多元的科幻类型与叙事范本。我们背靠5000年的历史文明,拥有着神魔诡异的《封神演绎》,更有奇思异想地《西游记》,以及《列子》《水经注》《考工记》等古籍甚至记载着不少关于古代科技发明的幻想故事。站在中国丰饶的文化土壤上,电影创作者应该借助想象力的天梯,去创建属于中国的科幻殿堂。另外,影片也应跳出西方的“普世价值”融入中国本土的科幻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符合中国人民的审美范式,构建起中国的科幻审美系统,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展现别样的民族气派。
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女性书写已经朝着颠覆与超越的姿态进发,糅合各种特质展现出鲜活复杂的女性形象,突破了既往类型化、刻板化的女性形象。《神奇女侠》《惊奇队长》《复仇者联盟》系列中,拯救世界的女英雄和女救世主。例如《湮灭》中的创造的精通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写)女性形象尤为值得一提,《湮灭》由女性主导叙事,展现了女性的力量,以一种较为客观中性的立场深入把握女性的内心体验。这些都体现出女性主体性所能具有的生动复杂意涵。而我国科幻电影的创作在塑造女性角色方面仍任重道远。如若中国科幻电影在起步之时,能够超越与批判长期以来的父权制文化,大胆冲破传统性别规范的牢笼,突破男权社会规范的底线,对女性自身主体性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实现对身体——主体的话语的自我掌控,并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充分思考中国本土女性的生存环境与现实困境,找到一条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且具有创新点的发展之路,那将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都流露出对技术主义的反思,呈现出对技术/人文二元对立的思考,在探讨科技伦理中,对生命的本质和人类的终极问题进行追问,从而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好莱坞科幻片中往往能生发出康德意义上的崇高的美学意味——在绝对大、无形式(数学上的崇高)、兼具威力和威胁力(力学上的崇高)的对象面前,我们产生了恐惧,但又因而生发出作为主体的理性精神,这才是对人性尊严的肯定”。中国科幻电影更多呈现的是“科技乐观主义”,一种为我所用的美好希冀。那么,依托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深厚的文化,在《流浪地球》将中国传统儒家美学的意蕴融入电影创作的同时,或许更可以回望过去,思考未来,对观众发出关于科技与人性的深刻诘问,使得影片的价值处于一种更为深远的阶段,在最后回落至中国文化中。
罗伯特•考克尔在《电影、形式与文化》指出:科幻电影有自我翻新的能力,可以渗透着文化关切或包裹着政治含义。科幻片向预言展开并且预言随时可变。与别的类型电影一样,无论叙事被设定为在什么事件发生,科幻电影是关于当下的。科幻的终极旨趣并不仅仅在于建构一种叙事的趣味性,其重要内涵也在于投射某种现实的焦虑,对现实政治展开严肃思考。也就是说,科幻电影实质上是以想象力为桥梁横跨人类的现实经验一集对未来的设想以此探讨人类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科幻电影可以回首过去、照亮现实同时又指向未来。基于此,科幻电影里的世界能重构人类的历史、文化、性别阶级,故而在其叙事空间中也就具备了探讨现实议题的巨大潜能。因此中国科幻电影的文本创作路径应该:立足传统、观照现实、关怀女性,在这个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
结语
正是《流浪地球》在中国电影史中里程碑式的存在,所以爱之深,责之切,意识到影片文本里多重文化标识意义的同时也应指出其中的不足。影片开启了中国式科幻片的新时代,在对未来世界进行想象与描绘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女性形象创作经验的匮乏与失真。因此我们仍需要在影像中建立更加自由平等的性别秩序和性别规范,从而推动现实世界的男女平等,消除两性歧视。此外,影片创作过程中所遭遇的中国电影科技层面的技术困境,也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关于电影体制建设的反思,加强电影工业建设,培养院校人才,提供更多的创作资源也是科幻电影发展的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科幻片既有凌驾于具体历史的抽象,又拥有非凡的视觉奇观以及恢宏的叙事,可以消弭特定历史和政治的影像禁忌,可以讲科幻片作为一种通用的电影范式,为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提供一条通途。但,中国科幻电影注定是漫漫长路,因此,作为中国电影人切忌急功近利仅为谋取利润,或者好高骛远地设定遥不可及的目标,脚踏实地才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