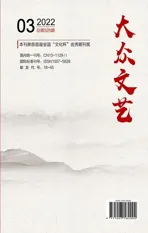观念性为核心的当代写实绘画于中国发展研究
2022-03-03马传铎于胜男
马传铎 于胜男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00 )
一、以东西方艺术家为例的当代写实绘画差异特征
当代写实绘画作为全球性的艺术思潮于20世纪的艺术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东方、欧洲、和北美地区的艺术家都对其当代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现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应。美国作为二十世纪后现代乃至当代艺术的中心,于世纪末出现了如查克•克洛斯,或是马库斯•哈维、奥德丽•弗拉克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写实主义艺术家。他们的写实绘画多表现为巨幅的人物肖像,使用到的材料也更加的综合与现代化。在查克•克洛斯的巨幅作品《自画像》中使用了一种“指印”的方式以造型关系的手段在事先打好的网格中填满了颜色,以“素描关系”达到了写实;马库斯•哈维高达四米的巨幅肖像《迈拉》也采用了异曲同工的指印手法来达到一种超写实关系的效果,他们的绘画更加不携带一丝感情的温度:幻灯片、喷绘笔,投射在巨幅画布上面的人、物或街景被完完全全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将画面制作了出来,以此传达纯粹的图像性信息。
在西方写实绘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沉迷超技术,对客观事物做全因素再现之时,中国的艺术家则是将视角聚焦于对写实观念与精神性的表达上,冷军与石冲都可以说是同时期中国当代写实绘画中的领军人物,二人都将全球性的当代写实绘画注入了个人化、民族化的精神内涵使得其走向本土化,同时两人的作品面貌又有所区分开来。从技术层面来讲二人仍在忠实的遵循着我们最熟知的绘图过程与方式,对客观事物,或是摹本进行传统的绘画式的再现客观事物的一切;从精神层面来讲,无论绘画的中心是人物还是经过一系列处理过的客体静物,都是在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生命与环境的关系,或是批判性质的人文关怀。
以冷军的《蒙娜丽莎——关于微笑的设计》一画为例,作者没有高科技的加持,没有网格填色式的制作方法,东方与西方创作过程和材料方法上的差异实际上则是东方以一种登峰造极的超技术,运用传统古典的方式对西方具象写实主义一次早有预谋的“误读”和猛攻,表达典雅的审美取向追求,到达一种至高的精神世界。而在“误读”背后的猛攻,是中国式的当代写实对当代环境下对自身的理解与即刻的需要做出的“断章取义”式的切割,是在社会政治大环境发生巨剧变,大量前卫、新奇、潮流的外界信息涌入的自身环境下以写实绘画作为了语言手段,以此传达与号召社会时代对人文精神、对传统信念的坚守、古典艺术和谐的理想追求。
从结果来看,中国与西方当代写实油画从写实语言的表现手法、作品的结果面貌上是存在一定重合相似的,但本土化下的当代写实坚持以传统写实的手段进行传达写实这一当代特征,传达观念与精神性在这一点上以冷军与石冲为例的艺术家是与西方,特别是同时期的美国具象写实绘画存在着技法、观念等层面上的极大偏差;在冷军与石冲的具象写实绘画中具象写实仅仅是作为了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二、中国当代写实绘画艺术家个案研究
冷军与石冲两位艺术家于1963年同年出生,并学习成长在湖北武汉,同为科班出身,有着相似成长环境经历的两人在同时代一并踏上了后现代绘画的道路投入了传统油画的具象写实表达中。尽管有着相互交集交叉的题材作品,尽管两人都是善于使用具象写实的手段,在表现手法上也是非常的相似,但纵观两人最终的艺术作品面貌却也存在着差别——冷军极负盛名的具象写实绘画强调对客观物象极致的写实,石冲图式中经过一系列处理过的静物与裸露的人体则蕴含着似乎更加浓烈的隐喻。
在对比研究冷军与石冲这两位画家时,难免需要将这两位艺术家放到时代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世界背景里,中国的艺术语境奋力摆脱着以往的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历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85思潮等一系列的艺术现象后,九十年代的中国艺术愈发的走向艺术自觉,身处全球化的潮流中逐渐与世界接轨——西方哲学的涌入,前卫观念的影响,艺术市场的萌芽,物质文化环境的改变,使得这时期的艺术家吸收和借鉴着外来的形式由此诠释和解释着当下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这时的美术不可避免的转向了一种前卫对抗传统,先锋对抗保守,多语言多格局多形式的态势。而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的全部总和,艺术作品的面貌即是当下全部文化的真实再现,艺术的窗口真实反映出了社会精神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丰富的多元化。冷军与石冲,以他们各自对待现实与当下的态度既是表现亦是再现,促使他们走上了各自不同,又与西方写实绘画区分开来的道路。在冷军的作品中我们惊叹其丝毫毕现客体事物的超技术能力,在石冲的艺术作品中我们重新审视到了当代艺术绘画中引入观念的重要性,在创作前期的素材准备时事先制作好一系列的架下物,再对摹本翻制描绘,将观念由架下由转移回到了架上绘画中,写实绘画的语言的转换给国内架上绘画向观念的转化指向了一条新路和方向。如果说冷军让观者认识到了当代写实绘画的超技术超巅峰与超极限的迷恋,那么石冲就是通过当代写实绘画的外壳注重到了观念性的表达。
(一)题材的选择和摹本的使用
冷军与石冲二人在绘画题材的选择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互交叉的合集,无论是人物肖像,还是经过拼贴、焊接、综合材料等一系列方式重构而成的现成物,二人在对客观物象的选择和处理上都有着高度的重合,即介质中转的手法——“摹本的摹本”的方式进行一种“异性绘画”。在第九届全国美展荣获金奖的《五角星》一作中,冷军开创性的将金属物挤压变形切割拼贴,将其制作成了充满政治寓意的五角星图案并用采用写实的手法将其再现了出来;在另一幅《世纪风景》中同样采用了制作现成物的方法,将工业垃圾的废弃物,生锈了的金属片与铁线焊接制同样作成了实际的现成物,使其组成了一副荒凉又残破的世界地图,再对这件充满隐喻的摹本进行细致入微的写生创作。
石冲在其早期的作品《被晒干的鱼》中选用了现实中的实体鱼作为材料,经过风干熏烤解剖涂抹,鲜活真实的物体不再被单纯点对点的媒介转化,而是先以更加前卫的观念作为主导方式转变成了装置,再由装置再次经过摄影的处理,再由照片搬上了架上绘画。这种方式从“结果”来看似乎极度烦琐且毫无意义,但如果将创作的全部“过程”解构来看,每一步烦琐的转换过程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材质转换的陌生感,作品制作过程中的复杂性,使得石冲的作品已经不能单纯以具象写实的框架进行定义,在超写实的背后包裹着的是装置、行为、观念、技巧等一系列融合混杂在一起的带有严苛理念的综合绘画;在石冲的另一幅写实油画作品《今日景观》中,将女人体、装有水的巨大玻璃牢笼,黑白海报和日常生活中我们熟知的物品材料组合而成,这样一副画面使我们不难联想到达明•赫斯特以及其惯用的“浸泡”式的装置艺术,从二人对客观物象制作的艺术摹本可以看出冷军与石冲二人均善于通过“摹本的摹本”以当代具象写实绘画的手法传达一定的观念性。
(二)表现技法的差异
冷军与石冲在创作中最为显而易见的差异展现在了其表现手法的表达方式上,冷军最为惯用的写实手法是现实真实的客体物象做全因素的再现表达做极端的具象写实,利用模特或者道具做参考进行最为直接最为客观的反映。从技术层面来讲这种具象写实并不单纯是作为摄影的全部反映,我们在冷军的作品中常常可以发现到一系列强化过了的色彩、结构、形式,冷军当代具象写实的背后实则是在以最传统,最直接的方式挑战和超越摄影的技术,以流露他古典式的、学院式的理想:即对客观物象全方位全因素再现,和对人自身本身价值的关注。
石冲对于语言的诉说上来讲又是中国式的含蓄委婉,在这一点上从他的近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水、蒸气、氛围、塑料、玻璃质感将肉体的真实若即若离的分隔开来,清晰又模糊,直白的话题以语言的技巧魅力娓娓道来,又留给观看者开放式的想象余地,将三维空间降维处理虽然放眼世界现当代艺术来讲并不是一件多么新奇的手段,但二维化了的,抽象化了的,甚至有些“冲撞”“冒失”“妖魔”化了的图像信息的确是对以往经典艺术的挑战与大胆进步。石冲用具象的手段将图式符号化的处理巧妙的结合却又保留着强烈的绘画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认识到一件事实,具象写实仅仅是画家的技术手段,裸女形象也同样是手段,“具象写实”与“人体”从文学上来讲似乎与经典传统密不可分,而隐藏在手段的背后的内容更值得观看者去深思,冷军的极端写实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石冲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写实,便越是拉远了这种距离,用具象追求抽象,在朦胧之中绽放诗意。如果说冷军的写实绘画传达的是运用超技术对于古典精神的号召,那么石冲的绘画则是借助了当代写实这一手法传达了图示信息中更为深刻、隐喻成分更为浓烈的精神反思。
(三)精神性与隐喻
毫无疑问的是,冷军的具象写实绘画是非常传统且严肃的,青少年时期展现出来的敏锐观察力,学习模仿能力,以及对细节刻画的狂热等无疑推动了冷军走向具象写实的道路,走向敬畏传统,走向神圣的道路,从《蒙娜丽莎——关于微笑的设计》到《肖像之相》系列,再到《圣贤书》无不透露出他对传统人文和理性的坚守,这是一种对人类崇高精神文明的传承守望——画中皆选取了女性作为整个画面叙述的主体,从着装到神情再到姿态与道具,甚至连手部动作的摆放都在向着过去的大师致敬,冷军笔下的女性形象与神韵祥和沉静,甚至与文艺复兴中的圣母如出一辙。三角形式的稳定构图,精湛的油画技法,光线的处理方式都遵循着西方经典绘画的一切构成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号召着此时此刻,当下的观众以及艺术家们回归经典与传统,回到人类文明乃至道德最崇高的顶点,以传统学院式的叙述方式坚守阵地以对抗着新潮美术中各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内在因素。同时,极端写实的手段也是大众流行趋势下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模仿现实,再现真实,力图拉近作品与物象的距离,即使是《关于网的设计》《文物-新产品设计》《世纪风景之二》《五角星》等变体的工业金属材料所传达的观念也并不显得晦涩,用具象的描绘追求具象的造型表达肯定的理念,传达写实性这一当代性观念,便是冷军写实绘画中暗喻的全部艺术精神。
相对于冷军而言,石冲没有选择像冷军一样选择单纯对图像信息做最直接的转化,没有选择客观物象“安宁和谐永恒静止”中的状态,而是将其放在了一种“动态冲突”中,使其处在了赤裸着的,不稳定的,不安全又生理不适的状态中,如果说冷军的绘画是“精神古典式”的,那么石冲则更贴近“精神巴洛克式”的。在石冲的绘画中对于“赤裸感”的表达几乎贯穿了他至今全部的艺术作品之中,其对于鱼、对于人、对于物、对于人体本身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残酷的,血淋淋的扒下鱼,或人的外衣、皮囊展示给观者来看,这种“赤裸感”在其作品《被晒干的鱼》中表现为被解剖的鱼,在《欣慰中的年轻人》中表现为被扒了皮的鹌鹑与剥光衣服的人,在《红墙述事》中是由无数残肢断臂构成半浮雕式的巨大景观,石冲一视同仁将画面中出现的全部物象都当作了某种“赤裸的物”看待,这身体是一个物化的身体,借此隐喻和探索人体、生命的意义;在石冲的笔下,超技术的具象写实绘画是为了服务于观念的,这也主要得益于石冲“观念先行”的艺术理念,在从“观念——架下——架上”针对一件作品采用复合语言的表达,而不仅限于架上的具象写实。
(四)身体符号的价值
人体作为西方传统艺术的语境中有着极其敏感的符号意义,人体符号所传达出的人文精神就如同绵羊与十字架传达出的宗教气息一样强烈。在欧洲传统文化中,人体的出现始终都代表着一种古典式的英雄与崇高,人的价值随着人文思潮被发掘,被确立,人的血肉与自然的对抗,与外物的激烈冲突时刻都彰显着人的高贵精神与伟大;而进入了工业文明人体的意义便不完全与自信、优雅、美丽,强大对等,白人殖民主义的遮羞布被扯下暴露出的更多是肮脏、亵玩、情色、肉体的不完美却丝毫毕现血淋淋的真实;而如今裸露的人体在石冲笔下的意义在如今的时代则变得更加意味悠长,他不再与古典的政治或者道德相关,不再是洛可可式的甜腻,也不是高更笔下原始粗犷的真实肉体,也不是席勒的病态情色,石冲则是选用了更加粗暴,更加直白、更加坦率明了的方式——袒露的性特征,窥探式的独特视角,将女性扭捏却健康饱满的身体作为绘画的题材,直接又大胆,普遍又典型的人体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关注。
从更加隐喻和象征的角度来看,身体的符号在当代语境的艺术创作中反映出来的价值则更加的敏感:美国抽象表现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日本艺术家小野洋子、塞尔维亚出生的女性艺术家玛丽亚•阿布拉莫维奇,均使用着身体作为艺术的媒介,用行为或装置来揭示千百年间被隐匿着的,尚未摆放在公众视野中的侵犯、暴虐的行为,用血肉之躯来对抗社会制度下的压抑,传达暴力强权下对人自身的伤害,这样的人体是几十年甚至百年里性压抑下的触底反弹和释放,是从肉身的主观偏见到客观正视;石冲从最早的鱼系列,到《行走的人》中由石膏制成的破碎男人体、《舞台》中由钢线缠绕的女人体、《某年某月某日的肖像》中涂满卸妆油的截取女人体躯干,被缠绕全身的铁线用对肉体的束缚和控制来表达反束缚与反控制,暗示了生命本源在外部的压力下、人的本体处于未知环境下的不安和危机与冰冷残酷的悲剧性以及当下人们所处困境的反映,是属于当代社会环境变革下对于人本身价值与生命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