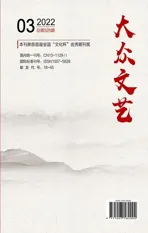由圣像破坏运动浅谈马列维奇与至上主义
2022-03-03罗聪
罗 聪
(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从理论上说,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形象的。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得以用图像、用线条或者色彩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可以被人直接所感的视觉形象,即便其指向的精神内涵或许仍旧抽象且难以被人把握。本文通过探讨圣像破坏运动中争论的焦点,即上帝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圣像是否能够代指上帝这一问题,引申到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作品上,探讨其如何用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至上主义的精神内涵。
一、圣像破坏运动
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圣像”一词有着多层含义,既可以指二维的画像,也可以指各种材质的浮雕塑像,但不变的是表现题材及内容均围绕着宗教展开:耶稣基督、圣母及圣徒、圣经故事及宗教历史事件。这一明确的限制,使得圣像较纯粹的绘画艺术而言,更多地被视为基督教的圣物。圣像艺术曾因这种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达到过繁荣,后也因这种密切一度沦为政治与历史活动的牺牲品。围绕圣像展开的圣像破坏运动,除开其政治因素,便是因为基督教圣像自诞生伊始就伴随着一个矛盾——上帝形象是否具有可表征性,是否可用圣像这一可见形式来表征其形象。
基督教从犹太教演变而来,在犹太教传统中,上帝形象的不可见性是被反复强调的,其形象不可诉诸视觉,不可为人的肉眼所见,因此犹太教虽有神龛却没有神像。早期基督教也继承了犹太教这一思想,但随着基督教教义和圣典的形成,基督教与犹太教有了根本的分歧。如马丁•杰伊所指出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差异,归根结底便是基督教确信神化身为了人形。上帝形象的肉身化,即所谓“道成肉身”,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上帝让玛利亚以处子之身由圣灵感孕,并诞下了耶稣。耶稣就像是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他以各种可被世人所见的行为,如他的诞生、他所行的神迹、他的牺牲以及复活等等,以“可见性”传递着上帝“不可见”形象的神秘,并实现着上帝在人世间的荣耀。由此,以耶稣形象为题材的圣像,便也受到了圣像支持者们与信徒们的虔诚敬拜。
拜占庭帝国曾有两次关于圣像的争端和针对圣像的大规模破坏。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从制度上揭开了反圣像崇拜的序幕,他于公元726和730年颁布了第一部反对使用和崇拜圣像的法令,下令将皇宫大门三角墙上的基督像毁掉,用十字架取代。在其强硬措施下,大量的主教、神职人员以及信徒遭受流放、刑罚甚至被处死。君士坦丁五世时期,对圣像的破坏运动达到了巅峰,绘画圣像被视作不虔诚和亵渎的,因为它试图再现基督、圣徒和圣母玛利亚。对图像的崇拜也被认定来自撒旦。圣像几乎被完全摧毁,僧侣们受到暴力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画圣像而被截去双手或烧死。
公元787年,在女皇伊琳娜于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大公会议中,圣像崇拜得以恢复。会中重申了上帝在他的本性中是不可被代表的,但通过圣像,人们记住了它所描绘的原型。尼西亚会议同时指出,圣像应该被“尊敬”,而不是被“崇拜”。
就这样,伴随着教会势力的削弱,圣像破坏运动直到公元843年才真正宣告结束。这一持续了百年的争论最终以圣像崇拜者的胜利画下了句点,但由圣像争论的核心矛盾,即上帝的可表征性问题所引发的讨论却并未结束,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图像的思考,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图像文化及艺术发展。
二、神圣的“可见”
关于上帝到底是否有形象,根据《旧约》的记载,上帝形象是不可能诉诸视觉可见的,不仅是因为上帝并不具备肉身化的维度,人的视觉也无法承载上帝的光辉。然而上帝却又有着耶稣这一道成肉身的形象,这就引起了是否能够用可见的形象来代指上帝这一争论。
对于圣像反对者而言,圣像崇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最为有力的论据是《圣经》中上帝对摩西说的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他们坚持上帝是不可能被诉诸形象的,其不可见的本质无法被可见之物传达,甚至这种人为之物——圣像的存在也是对上帝的亵渎行为。
而圣像崇拜者的观点往往与神秘主义神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象征论的话语模式中,上帝是无形的、充盈的、超宇宙的,圣像则是通往感知并接近上帝至纯至善至美之光的桥梁。圣像崇拜者们常把圣像称为“无字之书”,认为其起到像经文一样的作用。圣像也更有利于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尤其是对于目不识丁的信徒而言,相比于文字书写的抽象的教义,圣像可见、可触摸,更为直观也更易于理解。而在这些观点中,早在圣像破坏运动新生之时,君士坦丁堡的德国牧首就曾留下过一些珍贵的书信(715-730),信中清晰地阐述了他支持圣像的论据:
“我们允许制作用蜡和颜色涂抹的圣像,不是为了歪曲神圣崇拜的完美。因为,对于无形的神性,我们既不制作圣像,也不制作复制品或任何形象。然而,现在,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已经恩赐地决定成为人。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圣像中描绘了他的人类特征,因为他是按照肉体而不是按照他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神性出现的[……]。”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像崇拜者的一种基督论观点,实际上已经为圣像所蕴藏的矛盾找到了一种可解释的、微妙的、细腻的平衡。大马士革的约翰在《圣经三论》中对此有更为清晰的阐述,他认为画像并不等同于原型,它只是原型外观的一个复制品,因为它与原型并非完全相同。耶稣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正是不可见的上帝在人世间的活的、真实可信的形象。画像是可见事物,但它象征的却是不可为人所见,也无法显现的事物:画像对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加以呈现,以此加强我们并不充分的推测与想象。通过画像,我们认识并见到了之前无法想象,也无法得见的事物。在此意义上,画像实际上是使得无形之物在我们面前有了形式。
可以说,上帝化身耶稣来到人世间,显示出其与教徒们相同的血肉之躯,在变得可触及的同时,他的肉身也指向了上帝不可言喻的、无法计量的、不可理解的绝对精神。用马西莫•卡拉伯尼的话说,耶稣其实就是上帝的第一个复制品,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比作“父”与“子”,上帝的“不可见性”确实可以在可见的范围内被“重复”,被“复制”,但仅限于“子”,而非上帝这一原型。这里实际引出了摹本和原型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摹本是无法代替原型存在的,但摹本却可以使得原型的部分表象被有意义地表达出来,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人们通向原型本身。
圣像破坏运动所引发的这一问题,一直以来也为艺术研究领域所面临着,讨论着。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性质生产的创造物,其内容本质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内涵。精神本没有形态,无法把握,但具体的文字、语言、色彩、线条等形式因素却具有可以被感官感觉到的特性。这实际也是将“不可见”喻于“可见”之中。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与普及逐渐替代绘画的功能性与实用主义,艺术也被推动着走向更深层次的思想表达。这种富含隐喻性的关系同样地体现在了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作品里,且表达得更为极致。
三、马列维奇与《征服太阳》
卡西米尔•塞维利诺维奇•马列维奇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前卫艺术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在他生存的时代,俄国经历着十月革命,整个西方世界从社会结构、艺术创作、哲学理念也都正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彼时,在俄国两位大收藏家希楚金和莫洛索夫的购藏下,新印象派、野兽派及立体派这些艺术时代最前沿的作品得以在俄国定期展出,这些作品对马列维奇的创作影响极深。到了1907年,马列维奇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莫斯科艺术家协会的联展目录中,他也由此接触到了当时俄国的一众前卫艺术家,包括康定斯基。但是没过多久,马列维奇就成了他们之中冲在最前列的人。
1907年至1908年,马列维奇的作品《基督的寿衣》明显受到了象征派的影响。到了1910至1911年,他的作品又出现了野兽派的色彩。他于1910年创作的《浴者》,人物巨大的手脚则给人以原始绘画的联想。在他对于风格的不断大胆尝试过程中,他持续地探究着几何结构,并在1912年至1914年期间创作了大量对造型进行几何分析的作品,朝向立体主义迈进。其中《磨刀匠》这一作品,在展出时被标上了“立体未来派写实主义”。马列维奇不断地将从前卫艺术中汲取到的养分与自己的风格结合起来,做了众多的尝试。1912至1913年是马列维奇的绘画风格明显转变的时期,而他1913年的歌剧作品《征服太阳》则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征服太阳》是一出未来派主题的荒诞剧,就其主题而言实际上已经蕴含着至上主义的思想。为何马列维奇要征服太阳?在这一作品中,其实存在着对于过去的、古老保守主义的否定,其打破过去的目的并非为了寻找新的东西,而正是对于可见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的一种否定与颠覆。现实的物象世界正是因为有了太阳,有了光才得以为我们所见,因而马列维奇在其思想中所指的征服太阳,实际上代表着征服真实,并寻求超越物象世界的存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征服太阳》设计草稿中的黑色方形,马列维奇明白这个黑色方形具有某种意义,即便他实际上是1915年才领悟了黑方,他仍然将他的至上主义诞生放在1913年,其实也正寓意着对于伟大艺术家而言,并不存在需要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排列其时间。1915年,马列维奇创作了他的至上主义代表作《白底上的黑色方块》。他说,“我将形式归零,将自己从学院派的泥沼中打捞了出来。”
四、黑方、白上白与其至上的艺术世界
立体主义分解了物体,抛开了客体性;未来主义在具象形貌的基础上,以动态来分解物体;立体未来派则是在正方形之上堆积物品而无法彻底消解,三者从理念上都并未能超越具象本身。而马列维奇称自己是从虚无中创作,是非物体的创作,在这一意义上,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是具有革命性的,其对于具象的超越是彻底的。他的至上主义代表作品《白底上的黑色方块》,绝非对于一个完美的正方形的描绘,譬如其画面中方形左侧的角实际上要略高出一些,使得它并不是由完全的直角构成的。这也说明了马列维奇所使用的方形并非一个简单的、数学上的正方形,而正是他称为“零造型”的存在,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全新的、超越的存在。
这样一个充满意义的造型,并非一个符号、一个象征,马列维奇坚持它并不象征任何事物。在他的至上主义中,黑方是纯粹的绘画,是全新的、未来的语言,这一语言也是为了表述未来而存在的。它被定义为至高无上的、纯粹的艺术感觉,代表着超越物象本身,用感官直接感知对象。对此马列维奇表示,“方的平面标志着至上主义的开始,它是一个新色彩的现实主义,一个无物象的创造……所谓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的纯粹感觉至高无上的意思。”
这也使我们理解了黑方的主题——超越客观世界的视觉表象,追求纯粹的、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可以从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宣言》中看到他对此的理解,他将至上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绘画现实主义,认为自然创造的形态实际是艺术家们的镣铐。在他眼中,自然主义画家,即竭尽全力重现自然创造形态的画家,与原始人无异,仅仅只是技艺高超的再现艺术,并不能催生艺术的新形式。但与此同时,马列维奇的思想核心并不悲观,通过“征服太阳”,通过“零造型”,他找到了一个令他能够从传统的、具象的、学院派的绘画枷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在马列维奇看来,创作仅存在于绘画本身,其所包含的造型并非借鉴于自然与客观物象世界,而是来源于绘画的质与量。马列维奇还将时空概念放入了他的作品中,在展出时,他的作品可以有多种悬挂方式,几何形脱离了地球引力,上下左右的概念被消解了。
关于马列维奇至上主义作品的哲学含义,与老子的“道”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如他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所引用的,奥斯本斯基介绍《老子》的话:“道是一个无角的巨大方形,伟大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伟大的形象是没有造型的。”这便是老子的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很多人对马列维奇的艺术理论感到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其作品绝非浪漫主义,而更接近于哲学,如他之后推出的《黑色圆形》,是黑方以其中心点为圆心旋转而来的,《黑十字》则是将黑方一分两半再十字交叉,二者实际都是黑方的一种动态表达。1918年,马列维奇又接连创作了一系列绘制于白色背景之上的白色作品,其中的代表就是《至上主义构成:白上白》。他称白上白并非许多人认为的虚无主义,而是代表了绘画的最高喜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冲破蓝色局限的乌黑而进入白色…在我面前是畅通无阻的白色太空,是没有终极的世界。”
马列维奇以绘画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这一思想某种意义上同圣像与上帝的关系有着共通之处,即将“不可见”喻于“可见”之中。圣像实际上是通过其具有意义的可见表达通向上帝的不可见本身,正如马列维奇所使用的黑色方形并非一个数学上的方,而是通向他所追求的艺术世界的至高理念。而在其后期的新至上主义作品中,他所创造的无脸无臂的人物,似乎更加富于这种象征的意义。在他《农夫的头像》这一作品中,人物形象甚至给人以宗教的联想。通过圣像与上帝这一模型来理解马列维奇与至上主义,更能体会到其作品中的形象并非随意而作,其艺术理念也并非玄虚而不可捉摸的,而他关于艺术至高、极致、纯粹的追求,对于艺术颠覆性的思考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达达主义、极简主义艺术等多种新艺术运动。
结语
马列维奇所推动的这一艺术革命,其中对于具象绘画的观点或许过于激进,但在艺术形式及哲学意义上,他的追寻是极致的,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艺术要表达的是什么?如何用可见的形象艺术去诠释阐述纯粹的抽象概念与精神内涵?面对这些问题,马列维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终其一生追求着至高无上的艺术世界,绘于画布上的神秘方形,如同于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中寻求到的可见之物,蕴藏着马列维奇关于艺术的理解,它是通向非具象艺术乌托邦的窗口,也即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形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