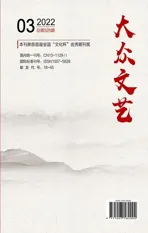论北宋院体花鸟画变革中“韵”范畴的移植*
2022-03-03黄文丽
吴 俊 黄文丽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38)
一、北宋初期院体花鸟画的承袭
北宋雍熙元年时设置的翰林图画院在继承和发展了五代后蜀、南唐画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身的机构组织和教育体系,至熙宁年间受官学运动影响,其制度和人才选拔才基本趋于成熟。因此在画院创建之初,最早的一批画家来自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如后蜀善画花竹翎毛的黄筌与其弟黄惟亮、其子黄居宝、黄居寀,及夏侯延祐等,工画佛道人物的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父子三人,王道真、石恪、孟显,及兼擅人物、花鸟的赵长元、袁仁厚等人;南唐的则有擅长花鸟的徐崇嗣、解处中,以及工画人物的厉昭庆、顾德谦等。
在花鸟画方面,由于黄氏父子选材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作品精细工整、造型逼真、色彩富丽,能尽显皇家之气派,加上积攒多年的声誉和威望,所以整个宋初院体花鸟画创作都以“黄家富贵”为标准,画家们恪守黄氏的格法不敢逾越,拘泥于题材、形制、技法上的套式不加以创新突破,导致花鸟画长达八十余年的发展停滞。虽然期间有真宗时期的赵昌取法徐崇嗣,设色明润,笔迹柔美,较黄氏画风更富有生意,有仁宗时期的易元吉另辟蹊径,专攻獐、猿、鹿等题材,清新淡雅,灵动野趣,极尽对象的情态特征,但是未能改变院体画的风貌。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他们缺失了对“韵”这一范畴的把握与开拓,从而无法把托物言志和崇尚简淡的形式进行完美的统一。如欧阳修在《归田录》里批评赵昌说:“笔法软劣,殊无古人格致”,汤垕也在《画鉴》中对其表达了遗憾:“惟以傅染为工,求其骨法气韵稍劣。”他们并未能够真正地撼动画院黄氏体制的统治地位。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北宋画院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创建初期、神宗时期及徽宗时期,也都是把神宗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作品视为院体风格变革的滥觞,例如郭熙《早春图》之于山水画,崔白《双喜图》之于花鸟画。在现有研究中对于变革的因素分析,一部分是关注画家为了打破因循守旧的萎靡之风,主动地在创作思想和审美取向上发生改变;一部分是把研究视角集中社会、政治、制度的剧烈变化;还有一部分是从士大夫参与的角度出发,认为他们所倡导的文人画影响了宫廷绘画的发展进程。而上述的研究都往往忽略了绘画的本体语言的变革,即“韵”的审美范畴的转移对绘画题材、形制、技法及意蕴的影响。
二、北宋“韵”的审美范畴
“韵”本是与听觉相关的乐的美学特性,引申到诗语中之“韵”,体现的是“诗”与“歌”的密切关系。最早对“韵”作出解释的是三国时训诂学汇编《广雅》,释“韵”为“和”,表明和谐的乐音即为“韵”,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韵”的范畴逐渐迁延到评价人格之美、书画之美、诗文之美。如南梁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曰:“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就是从诗文的押韵出发进行延伸,而东晋陶潜《归园田居》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南梁江淹的《知己赋》写:“每齐韵而等迳,辄同怀而共术”,其中的韵则是指向了人的情态、情趣,“韵”范畴也由此进入了人物品藻的领域,在《晋书》《宋书》《南史》以及《世说新语》里也多次出现了以“韵”论人的记载,形成了诸如“神韵”“高韵”“雅韵”“风韵”等词眼。南齐谢赫六法论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气韵生动”,则开始了“韵”从人物品藻向人物画的转移,要求画中人物的风采、神态及肢体以整体浑融的艺术效果进行裁夺。从谢赫《古画品录》里评论戴逵的画“情韵连绵,风趣巧拔”、陆绥的画“体韵遒举,风采飘然”中看“韵”,仍然没有脱离对人物风度、体态、情趣的品评范畴。
随着艺术自觉意识的强化和对作品意境探索的深入,唐宋文人意识到仅仅从创作者的主与客、心与物的关系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从观赏与创作相应和的角度去探索,唐末已经开始了作与观、生成与反响结合起来,如司空图提出“韵味说”,将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景外之景的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北宋则继续发展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主要体现在对“韵”范畴的论述,其审美范畴和诗学内涵得到真正的成熟和完善。
北宋文人“言韵”“尚韵”蔚然成风,遍及文艺各个领域,同时十分热衷于投入到绘画品评甚至是创作里,其中以苏轼、黄庭坚为首,他们通过“韵”来评艺的高低,表现为对于作品和人格的双向关注,且赋予“韵”以“雅”的美学趣味。如苏轼认为“韵”的主要属性是“萧散简远”,以求作品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在《凤翔八观之三•王维吴道子画》中评论二人:“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吴道子的绘画虽然游刃有余、运斤成风,但却太过豪放、流于刻露,不如王维的画得之于象外而更有韵味。黄庭坚也提出“凡书画当观韵”,认为书画、诗词都要以韵胜,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凌左义在《黄庭坚“韵”说初探》一文中认为黄庭坚所言“韵”有四层内涵:超尘出俗的风神、作品的余味、生动传神以及结构的和谐之美。跟随黄庭坚学习诗词的范温,是苏门关于“韵”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在《潜溪诗眼》里认为绘画出现“韵”的范畴较诗词更早,却流于表面不及诗词那样兼容并包,他给韵下了一个定义:“有余意之谓韵”,也就是指要使作品的意蕴和技巧必须含而不露、化巧为拙,甚至也指出创作者本身的灵犀妙悟也是“韵”的一部分。钱钟书在《管锥篇》中就认为自范温起,“韵”作为一个审美本体已明确不等同于“潇洒”“不俗”的概念了,在绘画的范畴里也与谢赫六法论中的“气韵生动”分离开来,因此钱钟书直接指出:“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
反观整个北宋的画论与画学思想中关于“韵”的论述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宋初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提出鉴赏绘画要领会“六要”之中的“气韵兼力”,可以看作是谢赫“气韵生动”的补充,他评范宽“求其气韵,出于物表”,评赵邈卓“气韵、形似俱备”,仍然是从神采、风度出发,而郭若虚再《图画见闻志》中提出的“气韵非师”把气韵认为是画家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法学习和传授的天赋,已然把“韵”跟画家本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韩拙作为宣和画院待诏,又与文人画家王诜往来密切,常共同评鉴古今书画,他所著的《山水纯全集》可以说是杂糅了文人审美思想和院体格法的画论,从笔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于“韵”的视觉形式:“纯质而清淡”“僻浅而古拙”“野逸而生动”“幽旷而深远”“真率而闲雅”等,虽然这些画论中的“韵”没有被当时的评论家用很准确的语言进行描述,但从熙宁至宣和这五十多年间画院创作的花鸟画的变革中,能看到“韵”范畴从诗词到绘画的移植。
三、北宋院体花鸟画中的枯淡之韵
虚融淡泊的心境和澄澈宁静的观照方式,是北宋中期士大夫们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的构成基础,也是他们诗词创作时平和婉顺、优游不迫的直接因素,梅尧臣、欧阳修以“平淡”论诗,苏轼崇尚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以及黄庭坚在其诗词和书画的中追求平淡闲远的韵味,都可视为北宋文人群体对枯淡自然美认知的代表,他们的诗词大多兴平而曲长,少激荡之情而多摇曳不尽之意。北宋诗词创作者们以一种文人视角的审美观念,把文学里倡导的老、真、闲、余转化为了绘画中的枯、简、淡、远,直接影响到院体花鸟画的创作趋势,在北宋中后期时完成了由富贵艳丽转向枯淡自然的嬗变。
如神宗元丰年间的画院待诏崔白,历来都被视为北宋院体花鸟画创新变革的主将,现有的研究往往着眼于他把“徐黄异体”兼容并收的创新贡献,但更为重要的是,崔白是同时期的文人们关于“韵”的理论在绘画中进行阐释的践行者,使得这种院体新风能一直影响延续至今。如他所作《寒雀图》描绘寒冬之际,数只麻雀在古木上憩息安眠的场景,画中麻雀自右往左的动静分布,与苍劲的树枝形成了气脉呼应,造型落墨为格,略施赭色,下笔勾、皴、点、染一气呵成,浑穆恬澹的古木与骨轻灵秀的麻雀共同营造了枯寒野逸的韵味。这种枯淡自然的风格在崔白的其他作品中也十分突出,枯枝、残叶、野凫、芦雁等寻常生命景象相映成趣,下笔用墨也是不拘于工细精整,以至于灵活疏放。苏轼认为在文艺作品中要做到枯淡就必须要经过“气象峥嵘,彩色绚烂”的阶段,也就是技艺高度成熟的过程,然后再由雕琢到自然,化工巧为拙朴,崔白正是在熟练掌握院体法度的基础上发挥写生的精神,逐渐隐藏甚至去掉作品中华丽的修饰、绚丽的色彩等痕迹,反而显得老练雄健,实现了对自然天真的回归,黄庭坚称赞他“盗造物机,巧夺天工”,也是指他将丰腴的技艺蕴藏于作品中而不露工巧的痕迹。因此,师法崔白的吴元瑜、赵佶等人对于院体花鸟的探索方面,与苏、黄等词人所推崇的诗词韵味一样,在外呈枯淡与内质膏腴的层面上,力求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形成枯淡自然艺术风格的过程,也即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过程。
崔白之弟崔慤官至左班殿直,与其兄一样也是神宗朝中极富变革精神的画家,《宣和画谱》卷十八载:“至如翰林图画院中较艺优劣,必以黄筌父子之笔法为程序,自慤及其兄白之出,而画格乃变。”崔慤极善于在画中表现秋冬季节的山林野逸,禽鸟的神态往往和荒郊的环境相映成趣,他传世的《杞实鹌鹑图》绘有一只鹌鹑立于一株枸杞旁,俯身对一只蝼蛄虎视眈眈,虽然画作尺幅较小、空间有限,但仍然能以疏简枯淡的笔墨留出悠远的想象空间,尤其是他用不作勾勒的没骨点染法,将鹌鹑的机警锐利表现得极为准确而生动,他笔下的芦汀苇岸,风鸳雪雁,在摒弃工巧修饰、追求枯淡自然的方面较之崔白显得更为彻底。
崔氏兄弟无论是从题材的攫取还是技法的铺陈上,都打破了北宋初期画院对黄荃父子的推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枯淡之韵引入画中,深刻地影响到神宗时期同时代画家的创作倾向,为徽宗时期院体花鸟画提供了借鉴的范例,并导致北宋后期乃至南宋的绘画品评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宣和画谱》卷七就夸赞内臣杨日言作画“荒远萧散,气韵髙迈”,卷十四评价宗室赵令松“工画花竹,无俗韵。以水墨作花果为难工,而令松独于此不凡。”卷十七评价宗室赵宗汉的《八雁图》,气韵萧散,有江湖荒远之趣。可见萧散、简远、疏淡已经成了这一时期关于花鸟画中韵味的最高评价。《宣和画谱》还批评了道士牛戬因画作“工巧有馀,而殊乏髙韵”,所以不得附名记录于画谱当中,可见单纯的工细精巧、绚丽修饰已不是宣和时期院体花鸟画所提倡的风格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淡质朴的题材和形式下,寄寓奇趣和丰腴深厚的诗意。
四、北宋院体花鸟画中的余意之韵
范温与王定观关于画中之韵的辩论一文被钱钟书先生发掘并研究后,使当今学者们重新审视文人群体关于“韵”范畴的定义和延伸,也让北宋后期宣和画院的创作风格发生又一次变革的理论基础显得清晰起来。陈良运先生在《论“韵”的美学内涵》一文中通过分析北宋范温与王定观辩说的专论,总结出韵的内涵是“生于有余而成于和”,是两种美感形态的互生、融合、转换。因此“韵”不等同于含蓄美,含蓄是“有余意”中的较直接和表层化的审美内涵;“韵”又不仅指诗的某种具体的美,它应具备诗歌审美的本体意义,是个多向度、包容较大的审美范畴。北宋士大夫们偏向“韵”的诗词主张,符合他们偏向内省的文化特征,使得北宋中后期在品评绘画时也开始倾向于委婉的意境进而影响到院体花鸟的创作变革,从而给欣赏者留出想象、酝酿、揣度的空白。
宋徽宗赵佶自身极富文化修养,年轻时就与文人交游甚多,诗词、书画皆十分精通,他主导下的画院在制度保障和画学教育方面的改革更为猛烈,把神宗以来画院的变革成果继续进行探索和完善,宣和体画风得以形成。徐建融先生在《宋代名画藻鉴》中认为赵佶倡导的院体花鸟画纤巧工致、典雅绮丽的新风貌可以概括为三点:即生活的真实性、诗意的含蓄性和法度的严谨性,即是指出赵佶在继承宫廷绘画一贯的造型严谨、设色富丽的同时,强调用有余意的诗意来拓展画境。从赵佶本人的作品中就可以窥见一二:如他在大观年间所作的《腊梅双禽图》《桃鸠图》在设色上都呈现出清雅秀丽的视觉效果,墨色、赭色都是淡淡渲开,营造层次氛围,对于石绿、白粉这种覆盖性较强的颜色,采用轻薄、反复、多遍的方式,使色彩之间形成层层相透的含蓄表现,这种墨与色和谐地相融为一体的花鸟画,已经基本摆脱了宋初时那种单纯、艳丽、明亮的色彩的铺陈直述,变为了复杂、细腻、含蓄的婉转起兴。
对于这一时期的画家群体而言,赵佶一方面给予了较为优厚的待遇,提高了创作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画家在创作的各个阶段均严格以自己的审美理念进行规划,阮璞先生就在《画学续证》中明确指出赵佶对文人士大夫绘画思想的接纳和挪用:“徽宗之艺术见解,实受苏轼残膏剩馥之沾溉非浅,而经徽宗改进之画院评艺标准,实与苏轼所揭集之文人画宗旨”,而直接代表其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里主张的“笔韵高简为工”,更是把“韵”这一审美范畴与院体画的技巧法度融合在了一起。同时,赵佶设立的画学十分注重培养人才的文学修养,其中对绘画融入诗韵的引导尤为关键,《画继》中记载了不少以诗题取士的案例,如“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等,还有“因试‘蝴蝶梦中家万里’题,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这种能将原本诗意引申,在画面中做出超拔的巧妙构思,事实上就是发挥了诗词的余意之韵,将文字转化为视觉再延伸到想象的过程,以描绘画外之意的空间取胜。
综上所言可以看出,花鸟画自神宗时期的变革以来,在造型上形神兼备,设色上含蓄细腻,既达到了院体精工尽美的要求,又能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宣和画院致力于绘画的文学化、诗意化,把余意之韵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南渡之后的南宋院体花鸟画,则把这种余意用精巧的扇面形制、简约的笔墨设色以及疏旷的留白呈现出来,是对“韵”这一范畴最为直接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