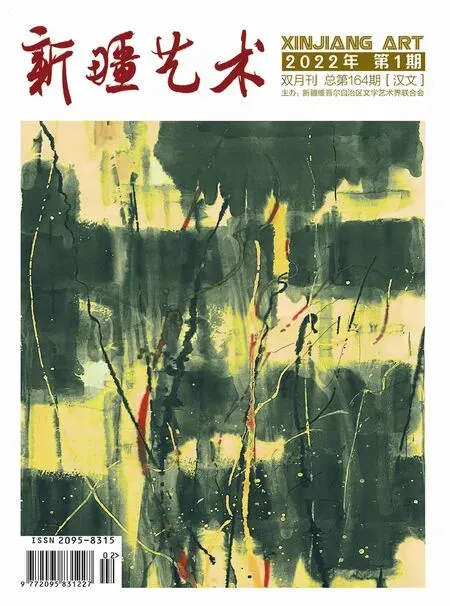《野葫芦引》的“时空体”形式
2022-03-03□何英
□ 何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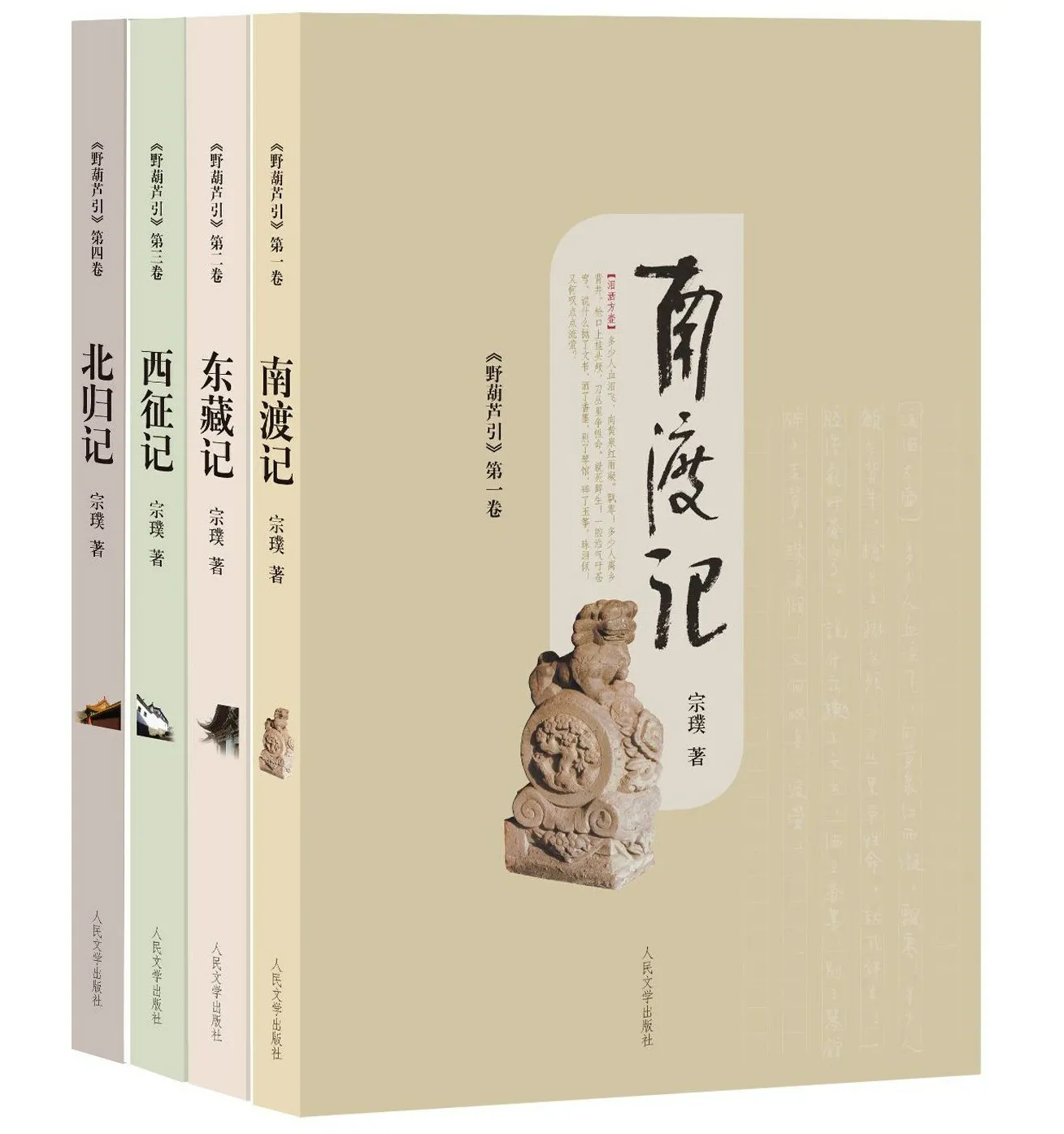
宗璞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在考察当代作家宗璞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形式时,会发现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关系,显得尤为突出。对《野葫芦引》而言,时间性本来就是第一义的。因为这是一部介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编年体小说。但这个编年体的叙事,却极大地依赖于小说的空间表现。“野葫芦”即是空间的象征,它象征着作者“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的空间意识。而小说中最大的物理空间就是“双城鸿雪”中的“双城”。《野葫芦引》“四记”以离开北平到昆明为开始,以重归北平为结束,在空间上划了一个圆,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但时间已经过去了8 年。加上《北归记》中的4 年,这个时空不可分割的叙事联合体,把小说各个部分紧密地组织在一起,产生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和情感价值。“时空体”本身即可看作是“人生之路”的转喻,“好像时间流入了空间并在空间里慢慢流淌”。还有一些空间,比如校园、战场、方壶、腊梅林等等,也都在小说中与时间一起,构成了小说时空体的具体表现。

云南西南联大旧址老照片
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时空体”概念,有助于我们阐释《野葫芦引》“四记”中时间与空间结合的叙事结构。巴赫金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借用了一个时空(chronotope)概念,用以阐明小说世界的结构方式:“为了揭示文学中作为艺术表达形式的时空关系的内在联系,我们提出chronotope(本义即“时空”)这个概念……其要旨在于,它表达了时空的不可分割性……可以说,时间能变浓,能长出肌肉,能在艺术上看得见;同样,空间也是有负载的,能回应时间、情节和历史的律动。这两个轴心的交叉和指示词的融合便是艺术上的时空体的特点。”巴赫金更多地是在小说体裁的意义上阐发“时空体”概念,在本文中,我们取这个概念的“时空的不可分割性”意义,也即正因为“时空不可分割”的叙事进程构成了《野葫芦引》“四记”的小说结构方式。
《野葫芦引》“四记”的时间线索非常清晰,从1937 年7 月7 日起,到1949 年春天。其间的时间走向无疑是线性的,作者甚至多处标明了那些“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的具体日期。这里的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体现为一种真实时间,也即传记时间,与巴赫金所谓传奇小说的“传奇时间”相对,是一种世俗生活时间,也即日常生活里那循环往复的时间。与达维德·方丹描述《包法利夫人》的时空,也非常相似:“是一种有厚度有粘性的时间,在空间中匍匐前行”。《野葫芦引》“四记”中时间的稳定性,益发促进了小说对空间的依赖。
双城,是小说中最大的两个空间。1937 年7月7 日卢沟桥的炮声,使小说的主人公们以及他们的家族发生了从北平到昆明的南渡事件。之后的空间表现遍布《野葫芦引》的叙事。在本文中,由于小说中的时间具有稳定性,着重以空间分析为主,阐述在叙事结构中,空间如何负载了情节,回应时间、情节和历史的律动,与时间构成不可分割的叙事进程,并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叙事的形态。
空间在小说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它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点。其二,它还可以作为背景。以《南渡记》中的“方壶”为例,它既是一个结构,一个行动的地点,还是一个空间背景。它是孟家人在北平校园的居所。对孟樾来说,这里是他在学校乃至社会上的地位的象征,也是他的形象得以塑造的场所。方壶,相传是东海三仙山之一。历代帝王为了接近神仙,在园林里挖池筑岛,模拟海上仙山的形象。乾隆将传说中东海的龙宫移植到圆明园,取名方壶胜境,被誉为圆明园最美的景观。方壶,也是紫砂壶的一种器型。在《野葫芦引》中,校长秦巽衡住的是“圆甑”。甑,是中国古代的蒸食用具。可见圆甑、方壶都是根据建筑的形状而命名。方壶与圆甑平行出现。足见在叙述者笔下,孟弗之在明仑大学的地位和影响。方壶的另一个寓意,与历代文人隐居时自号的居室名有关。如宋代诗人汪莘,自号方壶居士。以上种种透露出来的微妙象征及联想,都为这个人物形象附着上了作者欲附之上的信息。
在《北归记》中,秦巽衡校长最终离开明仑去台湾之前,还与孟樾就方壶、圆甑有过几句对话。“巽衡说:‘这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过没有?’弗之道:‘大概是说住在里面的不过是——’巽衡抬手插话道:‘不过是酒囊饭袋之人。’两人大笑。”这彼此会意的大笑,既有无用书生面对政治历史风云的无奈,更有对此身份的自矜与自怜。
《南渡记》中,孟弗之是和庄卣辰一起最先出场的。一般而言,小说中最先出场的人物即是主人公。接着作者就写到方壶,书房是一个更小的空间,属于孟弗之一个人。这个空间是他形象塑造的重要场所。这种描写寓所的手法,使人联想到《红楼梦》贾母带刘姥姥参观大观园一节,金陵诸钗们的住所被曹雪芹一一写来。这历来被认为是借寓所写主人性格命运的经典笔法。事实上,住所在揭示主人的性格、爱好及性情方面,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对秦可卿卧房的描写,就将其人物性格及最后的命运揭示得淋漓尽致。黛玉、宝钗等的居所也无不浸透主人的性格情性。宗璞是熟读《红楼梦》的,小学时就和兄弟们在上学的路上对回目。《红楼梦》等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作为潜在的文化底蕴,对《野葫芦引》的写作构成一定影响:“进入弗之的书房。书房在孟家是禁地,孩子们是不准进的。书桌更是连碧初也不能动的。书房中有一副对联,是从泰山石峪拓下来的,这几个字是‘无人我相,见天地心’。台灯的灯身镌满五千字的道德经。接着他开始写他的著作《中国史探》”。文人知识分子的形象,往往借助于楹联来双关表意。这副对联,便是作者理想化地塑造人物的手段。“无人我相”,出自《金刚经》,原句为: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对联的重点在下一句:见天地心。天地心,就是天道。这副对联,意即看破表象,感受到天地至理的意思。令人联想到冯友兰的“人生四重境界”中的最后一重,也就是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这正是作者寄寓在这个人物身上的境界写照。
从书房的摆设,尤其是对联的寓意,叙述者的目的是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可触。背景本身可以展现故事,是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几件道具往往就可以省去作家几页篇幅的人物描写。可使人物行动更加令人信服,使虚构故事增添真实的色彩。在这里,时间让位于空间,空间产生了叙述,并在人物塑造、主题思想方面发生着作用。
宗璞这样描写吕碧初的卧室:“是方壶中最舒适的一间房,她在这里度过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十多年来弗之的学问事业年年精进,嵋和小娃都在这里出生;……室中件件家具都是她精选心爱的……”对孟嵋和孟合己来说,方壶是他们的乐园世界。这里是家,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是有安全感的生活。而当这一切失去后,孩子们的天堂失去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也随之消失了。小说正是从这个“失去”的陡转开始写起。方壶是叙事的起点,也是终点,只不过经过了时间的空间毕竟不同了。失去了方壶,孟家人随大学南迁。目的地是云南昆明。在那里,孟家人找到了藏在腊梅林中的家。
腊梅林,是一个新的承载着孟家人情感与寄托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爹爹拿一本书坐在腊梅林下读书”。到孟家来的访客,都先穿过腊梅林,客者闻着花香而来,主人听得梅林路上或喧哗或轻悄的脚步声。这个腊梅林的空间,在叙述者的叙述中,使读者仿佛领受了三种感觉:视觉、听觉和嗅觉。腊梅林的形状、颜色,通过嵋的视角表现;客者或家人穿过腊梅林总会有各种声音可以辨识;一家人在腊梅盛开的季节,嗅着花香生活。在这个新的空间里,家的认同感达成,家人们感觉到安全和温馨。这个腊梅林,更是一个语义上的象征,凌冬开放的腊梅花,象征着抗战中不屈的民族精神。所以,当腊梅林被炸,作者忍不住借碧初的口吻写下了《炸不倒的腊梅林》,这一插入式抒情文章的写法,在四记中都有表现。例如《南渡记》中,就有历来被认为是孟樾的心灵独白的《野葫芦的心》。
先是方壶、接着是腊梅林,这两个孟家人的居所,都因日本的入侵而失去、毁掉了。通过这两个空间的情节,叙述者叙述了一个中国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另一方面,从方壶到腊梅林,是从一个空间到了另一个空间,小说也便在叙事结构上进入到新阶段。这正是空间在小说结构上的表现,使得故事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地拓展。在空间拓展的同时,一系列的对照也由此展开。小说开篇的北平,是孩子们眼里的天堂,日本人占领后就成了一个亡国奴的牢笼。人们怀着解脱的心情逃离出来,逃到云南,在云南怀念着北平。在这里他们又有了一个腊梅林的家,可以替代方壶安放一家人的身心。但好景不长,腊梅林也被日军战机炸掉了。孟家人从尊贵的教授人家,到与猪同住。“它们散发的特有气味和不停的哼哼声透过地板缝飘上来弥漫全屋”;“最可怕的是坑里还养着猪,它们哼哼着到木板下来接取新鲜食物,还特别欺生,遇见人来,似有咬上来的架势。所以城里人来用这坑时,大都手持木棒,生怕被咬上一口。”空间的变化,体现出一系列的对比。如顺心—不顺心、幸运—不幸、熟悉—生疏、安全—不安全等等,这些心理上的转变,是通过空间的对比表现的。
在《南渡记》中,整个第六章都在写南渡的旅途。旅行总是一个好情节,因为它形象地表达了小说要求的距离感。这个距离,即是一个空间。在“船”这个空间里,之芹死在了船上。这件事对嵋的震撼和打击,使她从幸福的方壶脱离出来,见到了世界残酷的一面。在嵋这里,空间的划分,是以内部与外部为基础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形成一种对照、对立的关系。海上航行中“船”这个外部空间,充满了不测的危险。当然,外部空间也意味着“自由”,所以嵋和一班孩子会在船上欢呼。联系整个旅途,嵋经历了海上的惊涛骇浪,之芹的死,经历了火车上的抢劫,丢掉了自己精心收拾的小箱子。那里面藏着无因送给她的萤火虫手镯,预示着两人的爱情没有结果。在嵋的视点下,离开方壶的空间,就离开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外面是与之对立的一个也许自由,但充满危险的空间。在叙述者潜在的心理结构中,这正是以方壶为代表的校园空间与外部空间的某种对照。而对这一空间的穿越,最终到达行动的目的地的过程中,几个主要人物都有了一种变化,或增长了见识,或历炼了心性。
碧初的慈母形象也是在这个外部空间里,进一步塑造出来的。她温和而坚韧,有涵养有风度。带着一班家眷南下,从一个北平的教授太太历练成经风雨、临大事的女性。她的形象自然地与金士珍形成对比:
碧初回头,立刻转身扶住之芹:李大姑娘,你怎么了?之芹摇摇头。金士珍也来扶住,说:就你事儿多!玳拉说她大概要晕倒,几个人连扶带抱,让她进房睡下,只见她脸色惨白,直出虚汗。金士珍慌了,不知怎么好。碧、玳二人商量,先让她抿些糖水,又找出多种维他命捣碎灌服了,过一会儿,她脸色回复过来,渐渐好了。之芹的脸色渐好,土珍的脸色就不大好看,若是在家,就要发作埋怨,说女儿照应不好自己,怎么帮着照顾弟、妹和家?岂非大大的失职!……这时金士珍已吃完饭,用餐厅的小毛巾擦着嘴走进来,大惊小怪地说:孟妹妹心眼儿真好,这么招呼之芹,之芹真不争气,上路本来就艰难,还生病!也太娇气了!李姐姐就是有点儿晕船,一会儿就好。嵋辩解地说。士珍撇撇嘴,大有嫌她多管闲事之意。……碧初温和地说:饭都凉了。吃馒头吧。舀了一勺刚添上来的热汤给她。嵋慢慢把馒头泡在汤里,忽然抬头问:“为什么有些人是那样的?”“世界不是方壶,你慢慢就知道。碧初温柔地鼓励地微笑。”
碧初对待孩子倾尽心力,温柔亲切;金士珍却迷信愚昧,对孩子们严厉而冷淡。在后三记中,这种家庭间的对比叙述还将延续。事实上,《野葫芦引》“四记”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发生在家庭这个空间里的。
香粟斜街三号,在《南渡记》中是一个重要的空间。“什刹海旁边香粟斜街三号是一座可以称得上是宅第的房屋。和二号四号并排三座大门,都是深门洞,高房脊,檐上有狮、虎、麒麟等兽,气象威严。原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的产业。”这一段描写的文字,是吕清非社会地位的间接说明。作者对这一空间的偏爱,主要体现在《南渡记》中的重头戏,吕清非老人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他最后拒绝出任伪职殒命于此。这里是以吕清非老人为中心的碧初等的娘家,也是吕清非的形象得以塑造的重要场所。还是瞻台玹、瞻台玮、绛初、赵秀莲、吕贵堂、吕香阁等人在此聚合的空间。四女占蜡、玹子与保罗的故事、汉奸缪东惠的情节,等等,都发生在这个空间。姑表兄妹们在此相聚玩闹,承载着他们的童年记忆。
小说中的校园与外界的空间对立,可以说,时时体现在小说的叙事中。叙述者不但把大部分的笔墨用在了校园事件、情节的叙事中,因为这是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和场景。一旦离开了校园这个空间,可以明显感觉到叙述者的场景叙事变得完全倚靠材料或想象了。这种校园与外界空间的对立还反映在作者的情感、认知中,而这些必定对小说结构产生潜在的影响。
一、小说中空间的主题化表现
在《野葫芦引》的叙事中,空间常被“主题化”,其自身就成了描述的对象本身。“野葫芦”就是一个有关主题的空间。野葫芦里装的是什么,“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这句话是关于整部小说的内容题旨而言的,也是作者的叙事境界的追求。其题旨与“纳须弥于芥子”同义。所谓“芥子纳须弥”“和光与物同”的境界,正是一位惯看历史风云、曾经沧海的老作家的自我期许。“纳须弥于芥子”还对应着小说的空间布局与素材选择。除了《西征记》,小说叙述大多主要盘桓于校园和家庭等静止空间里,所叙之事也被裁剪得较为细碎,几乎完全溶入了细节的描写、叙述里。宗璞将“野葫芦”自谦为“芥子”,里面的内容则为“须弥”。暗含着“器”虽小,包容的却是芸芸大千世界、渺渺宇宙之道。而这一切,都需要读者去仔细辨认、揣摩。须弥山一般庞大丰富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对应着百科全书式写作。而阿恩海姆却认为,此类写作风格是某种“晚期风格”的表现。
在《南渡记》第一章的末尾,叙述者以孟樾的口吻作了一篇《野葫芦的心》的文章,这篇直抒胸臆的文章可谓整部小说的“文眼”,是小说关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的题旨所在。孟樾于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在强敌入侵、国将不国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还对自己一生进行了“预叙”:“我其实是个懦弱的人,从不敢任性,总希望自己有益于家庭、社会,有益于他人。虽然我不一定做到。我永远不能洒脱,所以十分敬佩那坚贞执着的秉性,如那些野葫芦。”如果说,野葫芦具有“坚贞执着的秉性”,那么,这“坚贞执着的秉性”又指向什么呢?这秉性即是知识分子在野却要兼济天下的本质。
这段心曲自述,也在某种意义上引出“葫芦里装宇宙”的“宇宙”。这个“宇宙”既包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人生选择,也包括青年一代的爱情选择,还有他们的童年记忆。“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葫芦”通“糊涂”,这也便是一个世纪老人对历史无法说清道明的复杂意绪吧。这个主题意义上的空间,将会在读者、阐释者的共同参与之下,在这个动态的交流系统中继续探讨葫芦里的“宇宙”。
浦安迪发现中西方文学中有一个共同母题,那就是园林。他认为:《红楼梦》选择园林题旨作为中心,与西方许多寓言巨作以“安乐居所”(locus amoenus)为中心,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园林寓意的要旨,东西方则有所不同。西方注重真假乐园的区别,或者上帝安排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与造物主的天国之间的区别;中国注重宇宙和个人在自成一体的生活背景上融合。这种不同表明,从同一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推演出不同的哲理。方壶、腊梅林、香粟斜街三号等空间,被作者饱含深情地写来,即有这种中国人注重宇宙自然与人合一的哲学背景和文化旨趣。中国传统小说对于空间的经营历来格外重视,空间构成了小说结构的重要一极。而小说中时间、空间、人物、视角、动作等等,往往也是纠合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
二、时空关系与叙事节奏
经过细读,我们发现,不论是方壶还是香粟斜街三号,令人遗憾地是,这两个空间主要是“行为的地点”(the place of action),而不是“行动着的地点”(acting place)。这导致小说的叙事大多数时候呈静态化,靠着空间的来回转换来推进叙事,而动作与情节的因果链叙事,这种增加小说叙事节奏的动态化推进则相对较少。
如果说,方壶与外部世界形成安全与不安全的对照,与遥远的腊梅林构成一种结构上的先后关系,以及幸福与痛苦的对比,那么,香粟斜街三号,就似乎是一个背景式的空间。在这里,空间等同于描写。而描写是插入性质的,也因此是拖慢叙事节奏的。这些空间描述,似乎只为增加现实主义的效果。
在小说里,宗璞这样写道:“玹子住前院西首小跨院,三间小北房,两明一暗,院子没有正经的门,只从廊上的门进去,大家就称之为廊门院,房子全象绛初上房那样装修过,棕色地板绿色纱窗,中西合璧的布置。”类似这样的纯空间描写,在香粟斜街三号发生过多次。直到“最突出的是满屋摆满了洋囡囡,实际也不全是娃娃,而是各种各样的玩偶。”才总算为后来玹子惩罚自己的玩偶来出气的情节,铺垫了一个于叙事有益的描写。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这种描绘,仅仅突出了写实功能。

民国知识分影像
在宗璞的笔下,“一出夹道小门,虽然是红日高照,却有一种阴冷气象,蒿草和玮玮差不多高,几棵柳树歪歪斜斜,两棵槐树上吊着绿莹莹一弯一曲的槐树虫,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中间耸立着一座三开间小楼。楼下是一个高台,为砖石建筑,高台上建起小楼,颇为古色古香。油漆俱已剥落,却还可看出飞檐雕甍的模样。一个槐树虫在绛初面前悬着,玮玮立刻勇敢地向前开路。”这些描写似乎是动态空间了,突出了玮玮的勇敢,但它们更明显的作用也许是拖慢叙事的节奏,因为过多的空间描写使时间次序中断。
在小说的情节叙事里,碧初回方壶帮进步学生焚毁文件,本来是一个较为紧张的情节。但叙述者仍有闲暇写道:“夹道树木已落尽叶子,路面扫得干净,连路边杂草也拔得精光,小溪近岸处结了薄冰。”直到“快步走向厨房小院时,觉得从秦家移来的荷包牡丹,也已经枯萎了。”整整两个自然段的沿路景物。最后要挖文件了,还不忘描写枯萎的荷包牡丹。再一次证明,当空间被广泛描述时,时间次序的中断就不可避免了。
显然,宗璞无意在一个因果叙事链中增添各种悬念、情节、机遇、起伏,她真正的兴趣,可能在于通过回忆的纪实,丝毫不错地或是客观真实地将历史还原呈现出来,在此过程中,达到某种文化史的旨趣。例如“荷包牡丹,也已经枯萎了”这个细节,是对之前碧初从秦家移来荷包牡丹的续写,抒发一种家园破败的情感;于读者来说,以为紧急处理学生掩埋的文件必须雷厉风行,叙述不能拖泥带水。叙述者在此与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交错了。而作者的读者,也许能够理解此处的妙处:中国注重宇宙和个人在自成一体的生活背景上融合。“荷包牡丹”上寄托着孟家人的家园情怀,这个审美的精神需求,也即文化需求,正是作者所代表阶层的习性和品味。相似的例子还有吕清非老人的死,这个悲壮的情节是《南渡记》中最有份量的情节了。但吕老人死后,叙事却陷于入殓、上香、化纸钱,写了一页半。对作者来说,这些死后的礼仪,也即文化上的意义是更需要呈现的内容。
宗璞对描写景物历来深为钟情。她年轻时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之一哈代(另一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就是写风景的大师,对宗璞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哈代小说中的景色、景物描写,每每与他的叙事紧密嵌合在一起,起到了用风景衬托叙事、表达情绪的绝妙作用。宗璞亦对风景非常热爱,自称“改不了山水旧癖、烟霞痼疾”。宗璞后来又对曼斯斐尔德深有研究,而“曼是写景的能手”。她概括曼氏的景有“眼中景,心中景”。早在《红豆》时期,已见宗璞写景的精湛表现。她曾说:“《人间词话》有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不止诗,小说也是如此。”可见,写景对宗璞具有的写作发生学上的意义。她极擅通过景物描写,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达到“天人合一”的叙事境界。
除了景物表现是作者的艺术特色之一,宗璞在小说中还善于制造气氛、烘托情绪。正如她评价曼斯斐尔德的小说:“她不是靠故事,而是靠情绪,情绪造成气氛,透入读者万千毛孔中,所以戴其斯称她的小说为意象文学,而诗,正是意象文学。”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宗璞对小说的诗意追求。这可以用来阐释为什么宗璞写碧初处理学生文件,会有大段的庭院描写。这些描写的本意浸透着作者对方壶的深深眷恋,她通过各种意象,来抒发有家不能回、任凭家园破败的伤感情绪。
宗璞对曼斯斐尔德也是有着客观的评价的,肯定的同时,也认为:一方面表现出细致、抒情的特色以及和诗的血缘关系,一方面也表现了视野狭窄的缺陷。如果没有《西征记》,《野葫芦引》也许也会堕入“视野狭窄”之讥。幸好在《西征记》,宗璞令读者领略到作者写作史诗性大作品的气度与视野。《西征记》虽然有些地方残存“报告”的痕迹,但终于走出了封闭的校园空间,走向了战火纷飞的滇西战场,因而成为内容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记,是四记之“转”,可谓之高音华彩部分。
①“时空体”概念,是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中提出的,原文的概念解释较为分散,故本文采取了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援引。
②[俄]巴赫金著:《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载《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5 页。
③[英]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著:《空间诗学与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载《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 版,第208 页。
④[俄]巴赫金著:《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载《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279 页。
⑤[法]达维德·方丹著:《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 版,第65 页。
⑥[荷兰]米克·巴尔著:《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1 版,第108页。
⑦宗璞:《北归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第1版,第264 页。
⑧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9页。
⑨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142 页。
⑩宗璞:《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2版,第97 页。
⑪ 宗璞:《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2版,第97 页。
⑫ 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213 页。
⑬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31 页。
⑭ 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第1 版,第39 页。
⑮ 艾江涛:《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三联生活周刊2019 年第40 期,第126 页。
⑯[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 版,第163 页。
⑰ 参见[荷兰]米克·巴尔著:《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1 版,第108 页。
⑱ 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52页。
⑲ 宗璞:《南渡记》,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56页。
⑳ 宗璞:《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载《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241 页。
㉑ 宗璞:《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载《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241~242 页。
㉒ 宗璞:《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载《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240~241 页。
㉓ 宗璞:《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载《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24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