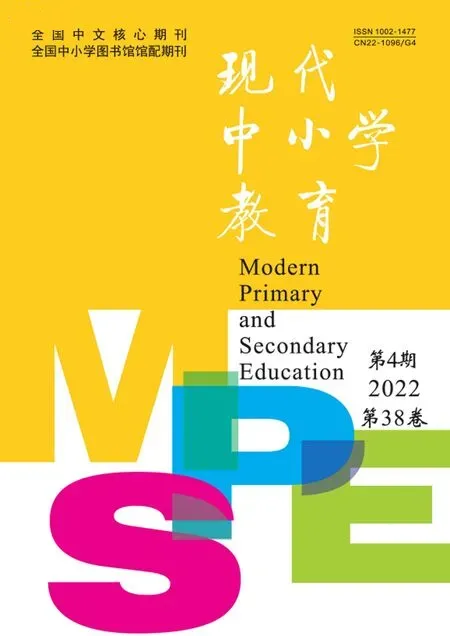美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的标本兼治之道
——以“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为例
2022-03-02陆哲恒
陆哲恒 孙 蓓,2
(1.上海公安学院,上海 200137;2.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校园欺凌(Bullying in Campus)是国内外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校园安全问题,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大众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于欺凌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1]事实上,发生在中小学校园内的欺凌事件对于学校氛围(School Climate)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1908年美国纽约市的中学校长阿瑟·佩里(Arthur Perry)在《城市学校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学校氛围概念,大量国内外研究证实“学校氛围”是影响中小学生个体学习动机、学习成绩、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和情感能力等的核心要素,更与校内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学生辍学率等学校问题行为的发生率息息相关。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系统的校园欺凌防治知识和有效手段干预支持的情况下,教师群体在应对校园欺凌事件时感到无从下手。2020年5月教育部就“十四五”期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的重点工作提出:“需将国家安全、预防校园欺凌等纳入教师校/园长培训。”[2]由此可见,从改善中小学校园的学校氛围和教师视角切入,尝试破解校园欺凌难题是解决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的突破口。
本文以“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为例,探讨在美国东部地区的一所中学,根据循证(Evidence-Based)方式进行的一项“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的校园反欺凌计划(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以下简称PBIS),并对该计划进行分析。“循证的方式”在本文中是指通过对该所中学校园内学生个体行为表现进行全过程评估与监测,将获取数据作为重要客观依据,辅助学校领导及教师们设计和制定校园反欺凌的策略。
一、“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出台背景
1.概念:美国校园反欺凌计划含义和特征
美国中小学一般意义上的“校园反欺凌计划”是指通过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其他教职员工应对欺凌行为的认知水平,使教师们具备应对欺凌行为的知识储备与技能准备的项目。[3]校园欺凌行为背后发生的症结原因大多是基于“欺凌被害者”具备某些个体特殊特征,诸如性取向、性别歧视、身体残疾、肥胖超重、种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等。“校园反欺凌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教师提前识别“校园欺凌事件”的各类角色,在欺凌行为发生前或发生过程中可以成功介入和干预。[4]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当教师们表现出愿意主动使用干预措施来帮助“欺凌受害者”学生时,发生在中小学校园内的欺凌行为会显著减少。[5]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美国中小学的“教师”是一个群体概念,它涵盖了包括学校校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和心理辅导教师以及教学辅助人员(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教育行政管理者、行为学专家、护士和行为咨询顾问)在内的所有教师,这些人员都是参与制定、修改和评估校园反欺凌计划的关键人物。[6]美国法律规定中小学校园反欺凌计划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学校必须制定明确的配套政策和校园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明确校方针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具体处置措施;第二,学校必须注重储存校园监控电子基础数据,确保校方具备公正评估校园欺凌行为性质程度的客观处置证据;第三,学校必须坚持培训所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职员工,确保所有在校教职人员能够在发现或报告校园欺凌事件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2.动因:各类校园欺凌角色饱受欺凌困扰
校园欺凌,意指在中小学校园内的某个学生,带有目的性地、反复多次地对另一名学生实施的攻击性行为[7],这里所指的“攻击性行为”是指在身体、言语、社交或网络上的伤害行为。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2017年度的一份报告声称,美国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学校,大约每天有16万名学生会受到欺凌。校园欺凌对受害者(Victims)、旁观者(Bystanders)以及欺凌者本身(Bullies)都会产生不利影响。[8]美国儿童阶段指从进入幼儿园的学前阶段、小学的初等教育阶段再到涵盖初中和高中的中等教育阶段,在此阶段的美国中小学学校都会实施各类校园反欺凌计划,以期可以降低欺凌发生率和遏制欺凌流行率。
中小学校园内发生的各类欺凌行为对欺凌事件的各类欺凌角色都会造成短期或长期的负面影响。受害者(Victims):短期内会出现经常旷课、情绪焦虑、学习成绩下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自卑、自我效能感低和自杀意念。中小学阶段的“欺凌被害者”相较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受害者遭受的心理痛苦会更加显著,成年后会出现个人成就感水平低、自杀意念强和自杀风险大的严重后果。被欺凌的小学生还会出现倾向于采取暴力攻击行为解决问题,并在中学阶段出现更多不良行为。欺凌者(Bullies):该类学生在青春期吸食毒品的风险会远高于同龄人,在学校阶段的学习成绩往往很不理想,其成年后参与高危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旁观者(Bystanders):中小学校园欺凌情境中还有一类角色极易被忽视,即旁观者。这类学生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由于担心自己目睹并亲历了欺凌事件,很可能会沦为“欺凌者”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必然会出现负面心理情绪。鉴于校园欺凌会对各类角色,“受害者(Victims)”“欺凌者(Bullies)”“旁观者(Bystanders)”产生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和长期影响,因此近年来,在全美范围内掀起了启动“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模型下的校园反欺凌计划(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PBIS)”的教育革新。
3.铺垫:明确教师是反欺凌计划核心要素
PBIS国家中心(PBIS National Center)是1997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获得一笔拨款后筹建的,该中心的成立受益于当时美国政府顺利通过了《障碍者教育法》(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的修正案。自该中心成立和发展至今,PBIS项目已在美国的28个州,为超过16 000多所中小学教师提供了PBIS项目培训服务。
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以下简称PBIS计划)本质上是一种系统化实施预防和干预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模式,它关注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干预方法或实践措施,它强调以循证的方式,通过发展教师的积极行为干预支持策略和系统改变的方法,调整所有校园内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达到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改善学生在校质量的行为干预模式。PBIS计划使用的策略包括制止(Stop)、离开(Walk)和报告(Talk)。看似简单的三个英语单词,实质上内涵丰富,它代表了教师和学生已经形成一种共同语言体系的默契,在应对校园欺凌问题时已能灵活运用一套成熟的适应行为模式。
(1)教师教会学生运用“三步骤模式”,标准化应对校园欺凌。“PBIS计划”发展教师的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主要有三个重要步骤,作者将其概括为“三步骤应对模式”。具体是指制止、离开和报告。“制止”(Stop)是指教师需教会学生在全校范围内灵活运用“制止信号”,当学生遭遇欺凌情境时,会迅速运用口头和肢体语言对欺凌者勇敢地表达出“停止”信号。“离开”(Walk)是指如果该名学生已向“欺凌者”明确发出“停止”信号后,“欺凌者”并未因此停止其伤害行为,那么在此欺凌情境下,教师教给学生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求学生尽快“逃离”现场。如果该名学生在完成了前两个步骤后仍然无法摆脱“欺凌者”对他的持续伤害,那么第三步必须向班主任或其他教师“报告”。教师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地鼓励学生与教师进行沟通,培养学生无畏韧性的个性特征,敢于向教师们报告他们正在经历或亲历目睹的校园欺凌行为。
(2)教师依据学生在校现实表现进行三级分层,分层干预教育问题学生。“PBIS计划”主张学校依据学生遵守美国中学生行为规范和本校校规的实际情况,采用三级分层系统对学生予以区分。约占80%的学生处于第一层,该层级学生遵守规范情况良好,不需要提供其额外支持和干预行为。约占15%的学生处于第二层,该层级学生是已有过参与欺凌经历和存在欺凌他人风险的学生,这部分学生需要提供其如何应对欺凌行为的社会技能和遵守课堂行为规范的要求。约占5%的学生处于第三层,该层级学生包括了需要进行个性化干预的高风险问题行为学生。“PBIS计划”三级分层干预校园欺凌模式已通过美国专家的评估和审查,针对其在中小学校园内的实际应用效果也有了不少实践积累。[9]
4.实施:强调发展教师积极行为支持策略
“PBIS计划”的目标是为全体学生创建安全有效的校园环境,增加学生的在校安全感,教师向学生提供积极有效的行为支持,同时预防校园欺凌等问题行为的蔓延和恶化。Letendre等人发现,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校园欺凌干预计划中需要建立一套共同语言体系[10]。该体系将有助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熟练应用,有助于教师们顺利实施校园反欺凌计划,有助于改变和矫正“欺凌者”的攻击性欺凌行为,有助于师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校园文化。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一所中学内进行的PBIS计划,该所公立中学内的大部分学生是外国移民的孩子,其中76%是拉丁裔或西班牙裔,53.8%的学生是男性。该项研究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人员将符合资格的21名教师(教师组成人员包括课程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预先分成五个焦点小组,其中16名教师为白种人、4名教师为拉丁裔或西班牙裔、1名教师为非洲裔美国混血儿。在性别特征描述方面,15名参与者是女性教师,6名是男性教师。每个焦点小组由3~7名参与者组成,研究人员依次在每个焦点小组进行了大约60~90分钟的互动讨论。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对参与教师们进行了相关“PBIS计划”的培训,以便让教师们充分掌握PBIS计划内容,学会如何通过发展积极行为参与计划。
二、“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实施结果分析
美国以学校为基础制定的校园反欺凌计划,在实际实施结果中毁誉参半。诸如全校欺凌干预模式(Whole-School Models)、课堂与特别学生项目(Classroom or Student-Specific Programs)以及整合了多媒体的干预模式(Multimedia)、父母参与项目(Parental Involvement)、惩戒性干预模式(Disciplinary Measures)和同伴支持项目(Peer Support)的校园反欺凌计划大多被国内外学界公认为是有效的。[11]
1.学校资金不足和社区资源缺乏主要影响教师实施反欺凌计划
中小学学校资源匮乏被学界公认为是影响实施校园反欺凌计划的主要障碍因素,这里的资源不仅包括建设和改善校园环境的资金、设备等硬性条件,还包括学校是否具备改善和应对校园欺凌行为的软实力,诸如教师应对欺凌行为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学校能获得的社区支持及其附加资源、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等。学校所在的社区背景、学生的居住社区环境都会使教师在应对和处置校园欺凌和学生管理上面临巨大挑战。许多美国城市公立中小学因其民族多样性和社区资源的缺乏,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欺凌干预项目。“PBIS计划”则主要依赖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社会互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该类社会互动行为会有助于遏制和防止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个人控制能力差和社会适应能力弱是学生遭受欺凌风险的两大显著相关因素。
2.教师缺乏培训和师生互动不畅直接影响教师实施反欺凌计划
传统上美国公立中小学教师们惯常采用结果性惩罚策略处理校园欺凌行为,这样的做法不仅会给“欺凌者”造成不良行为示范,还会出现欺凌行为被暂时地“人为抑制”,当欺凌行为再次发生时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PBIS计划”将发展教师的“积极互动行为”与“替代性行为”建立直接联系,该计划的假设前提是教师们需介入所有学生的行为规范管理。这里所指的所有学生还包括了“欺凌者”,全体在校学生都可以从教师这里获得积极行为支持和预防校园欺凌的具体做法。“PBIS计划”的实施,其核心要点就是由研究人员指导和培训教师们教会学生在面临校园欺凌行为时可以采用的积极行为,主要概括为三大步骤:制止(Stop)、离开(Walk)和汇报(Talk)。每个步骤的课堂教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能停留在知识传授阶段,教师更应注重让学生不断进行情景模拟演练(Role Play),学生们只有通过重复模仿、练习和强化,才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达成“内化”。
3.家庭隐性文化和家校关系疏离间接影响教师实施反欺凌计划
Swearer,Espelage,Vaillancourt和Hymel断言[12],大多数美国中小学的校园反欺凌计划,包括“PBIS计划”都未能将校内学生的人口统计数据因素考虑在内,例如种族、残障和文化取向等,然而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会对项目实施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儿童和家庭等人口统计因素,包括性别、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对学生参与校园欺凌行为产生影响。“美国PBIS计划”的调研数据显示: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容易受到长期和频繁的校园欺凌,换而言之男生也更有可能成为“欺凌受害者”[13]。与性别因素相关的不同欺凌行为也被工作人员注意到,男生更可能实施身体欺凌(Physical Aggression),而女生则可能偏向利用关系欺凌(Relational Aggression)。少数民族裔人口聚居区域的社区暴力被认为是促发校园欺凌的风险因素之一。[14]此外,移民美国的学生中,社会适应能力差、学业成绩较差以及儿童和父母的原文化适应程度高也被认为是校园欺凌的危险因素。[15]这表明学校和教师们在参与制定和实施校园欺凌干预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学校所在社区环境的真实状况,因为在高暴力社区中,学生很可能会被社会化,其行为表现会将“支持攻击性”行为作为应对欺凌行为的首要解决方式。
4.社会种族偏见和多元文化冲突深远影响教师实施反欺凌计划
“PBIS计划”的实践结果揭示了美国“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y)”子女在中小学校园内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要远高于在当地出生的白人同龄人。[16]在这里提及的“美国少数族裔”是“非白种人”概念,尽管移民后代和美国少数族裔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更高,但本次PBIS计划并未将这类特殊学生的多元文化因素考虑进去。在使用挪威学者奥维斯(Olwus)设计的“奥维斯儿童欺凌问卷”对学生进行调研时,问卷数据结果显示移民后代和美国少数族裔学生未能如实反馈自己遭受欺凌的真实状况。调研结果揭示了美国大部分针对中小学的校园反欺凌计划,运用传统意义上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已无法获得真实的欺凌数据,从而导致大部分干预项目“掩盖”了美国移民后代和少数族裔学生真实安全需求堪忧的境遇。素有“民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其种族偏见和文化冲突问题无形中增加了教师们处置校园欺凌问题的难度。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美国中小学校园反欺凌计划对于教师而言更具挑战性。[17]
三、“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对我国中小校园欺凌防治的启示
1.学校方面提升监控能力,严防欺凌事件发生
学校走廊和操场等教室外面的场所是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干预欺凌行为的最佳机会,大量研究结果证明了加强在课堂之外的非正式教学领域监督可以有效地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和降低被欺凌者的受害风险。[18]提升学校层面监控能力是预防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校园环境有效管理、管理人员专业强化以及高风险学生动态掌握三个方面。第一,校园环境有效管理重点是:校园范围内“欺凌重点区域”的地图绘制与防范提示、“欺凌重点区域”的加强巡查、校园“死角区域”安装监控探头、厕所防虐报警装置等硬件御防设施改善项目。
学校范围内的校园反欺凌计划需有助于建立学校氛围,使每个在校学生都能感到安全,能够发展学业和社交情感技能。了解PBIS计划中起作用的因素,以及如何根据每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地理位置、社区背景、学生及家庭的人口因素、教师的专长与技能等,对反欺凌计划内容进行因地制宜地调整与修改,以期更有效地满足本校学生、教师和家长的独特需求,是每一所中小学校园反欺凌计划的关键环节。
2.课程方面建设教学团队,建立助人校园文化
教师们积极发展“利社会行为”课程,应从努力构筑在校学生的心理环境做起,经由课程教学活动深化学生对欺凌行为的正确认知观,培养学生同理心并在校园日常生活点滴中养成助人习惯。由于校园欺凌事件涉及学生个体与学校环境的交互作用,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学生情感同理心的缺乏以及旁观者多元无知效应是导致校园欺凌事件日益频发和恶化的主要原因。换而言之,冷漠无知的旁观者的心理环境才是校园欺凌事件的最大助推因素。因此,干预校园欺凌的积极做法应从教师积极发展和培养学生的助人文化开始,化解和减少冷漠无知的旁观者,以此来“抵御和抗衡”欺凌者。利社会行为的课程规划和设计应该包含“同理、关怀、合作与救助”四个部分。从同理心出发,积极鼓励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助人行为,抵御欺凌行为,课程目标应侧重建立同理心的态度与行为以及利社会行为的实践。唯有校园中助人文化的正向氛围占据上风,才能使校园欺凌行为没有滋生的土壤,从而真正销声匿迹。
为了使反欺凌计划获得成功,教师们需要通过PBIS计划提供的共享语言体系来解决校园欺凌行为。[19]针对该计划需要修改的地方,例如应在计划中增加某些特殊类型学生的需求,多元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教师们应该通过团队合作高度给予关注。针对部分高风险学生,教师团队可以做出调换班级或另辟教室的方法,促进问题学生发展积极行为的连续性和成功率。欺凌主题课程建设方面,需要充分依托和借助参与合作团队的教师,大家共同反思和讨论以期能够找到更好的积极行为替代解决方案。
3.教师方面完善培训机制,提升教师干预能力
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实践结果显示:影响计划有效实施的最大障碍是教师群体缺乏适当培训。[20]受到欺凌的学生由于感到羞耻、害怕和缺乏信任,抑或害怕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通常不会主动向老师透露自己被欺凌的细节信息。缺乏应对校园欺凌的相关主题培训,教师们无法及时识别出班级中受到欺凌的学生,缺乏可以保护被欺凌学生不再受到欺凌的能力。由此,加强教师培训成为了破解中小学校园欺凌的突破点。
校园反欺凌计划中的教师培训要点是:第一,鼓励教师们“发展积极行为”。教师们需积极转变其过往习惯性地将惩罚作为处置“欺凌者(Bullies)”欺凌行为首要且唯一措施的固有观念,转而采取积极主动向“欺凌者”传递这样的观点:错误的是“欺凌”行为,而非实施行为的“欺凌者”本身。第二,鼓励教师们做出“系统改变”。教师们需向“欺凌者(Bullies)”教授具有与惩罚措施相同功能的替代性行为策略,为问题学生重新设计和改变系统环境因素,如班级环境及文化,使环境对该学生的正向行为发展起到支持作用。与此同时,在培训中教师们需学会向“受害者(Victims)”“欺凌者(Bullies)”“旁观者(Bystanders)”教授具有适应性功能的行为策略。第三,鼓励教师们创新教学方法,“预防和减少欺凌问题行为”,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能够整合干预计划中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精心设计,将校园欺凌主题相关的真实故事投入到课堂讲授中,采用小组情景模拟(Scenario Simulation)和角色扮演(Role Play)的教学形式来丰富欺凌主题课堂学习。诸如“如何应对校园欺凌”和“重新安排学习环境”这两种途径,通过采取三级分层实施课堂教学,增加问题学生个体积极行为,降低欺凌行为的频率或减轻其严重程度。第四,鼓励教师们以“改善学生在校质量”为目标。教师们通过培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可以主动开展教学,为增加在校学生个体的在校满意度和成就感做准备,为学生们充分融入社会打好基础。
4.学生方面加强合作互助,促进形成同辈模式
学生对教师的信息披露不足以及教师对受欺凌学生的认识不足都可能会导致在校内实施反欺凌计划困难重重。那些没有向老师透露被欺凌实情的学生,以及那些由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或因身体障碍无法正常表达真实情况的学生,很大概率上无法从教师方面获得充分的干预和支持。一些学生,如那些频繁出现情绪失控的问题学生,需要额外强化(Reinforcement)来帮助其学习“制止(Stop)、离开(Walk)和报告(Talk)”的三步骤欺凌应对模式。针对校园欺凌中的高风险学生的动态信息掌握首要责任在教师,教师应在班级日常管理中努力营造同理关怀、合作互助的班级风气,让学生在班级环境中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为增进教师辨识高风险学生的能力,同样需要建立班级高风险学生行为数据库,以便教师可以跟踪记录,尽早介入和干预。
学生们可以学着去理解他们的同龄人,帮助某些特别学生获得团队接纳,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和回避。教师可以帮助促进处于青春期的女学生之间形成积极的同伴关系(Peer Relations)[21],授权某些优秀学生承担管理角色,以帮助解决欺凌情况。教师可以建议学校在校内创建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欺凌俱乐部(Bullying Club)”,参与欺凌俱乐部的学生将接受反欺凌计划的培训,并作为“学生专家(Experts)”前往不同年级,演示如何使用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应对欺凌者或帮助其他“欺凌受害者”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这种借鉴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的同辈模式(Peer-Based Model)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园欺凌的共同防治工作中来。
5.家长方面积极参与沟通,建立孩子心理韧性
通过将家长纳入反欺凌计划,可以将学校的反欺凌计划目标扩大到家庭中,从而为学生在学校和社区建立更大的协同性保护区域。对习惯采取“以暴制暴”解决问题的家庭文化以及社区文化的敏感性,教师们可以设计制作一些个性化的资料来解释和宣传校园反欺凌计划。教师们可以使用多媒体网络平台,鼓励父母在家和孩子一起线上参与定期交流。通过在线家校互动平台、电子海报和宣传视频来加强和巩固学生在课堂外的PBIS计划内容,是教师们可以采用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考虑到定期面对面的交流会更好地传递学生在校内的实际情况,教师们与部分问题学生家长的个性化会面可能是确保家长参与的最佳方法。
家庭关系对欺凌情境下的儿童有影响,消极的养育方式,包括虐待和忽视,会增加孩子成为欺凌受害者的风险[22],而家庭支持则能够改善“欺凌受害者”的情绪控制力和心理韧性(Behavioral Resilience)。[23]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认为,家长参与度高是反欺凌的重要关键。在校园反欺凌计划中将家长参与因素考虑在内的计划或项目,在遏制欺凌行为和降低被欺凌风险方面更加有效。此外,父母自我效能感被证实与学生被欺凌和受害程度显著相关[24],让家长参与反欺凌计划,提高他们对校园欺凌行为的认识会产生积极影响。[25]
美国PBIS校园反欺凌计划为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策略,其治标之道为通过系统化改善学校硬环境,将预防校园欺凌纳入教师常规培训项目。[26]其治本之道为鼓励教师不断提升发展积极行为的软实力,不断创新教学能力,改善学生在校质量,从而实现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的目标。未来我国在制定中小学校园反欺凌计划时,需要关注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在任何一项中小学校园反欺凌计划中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