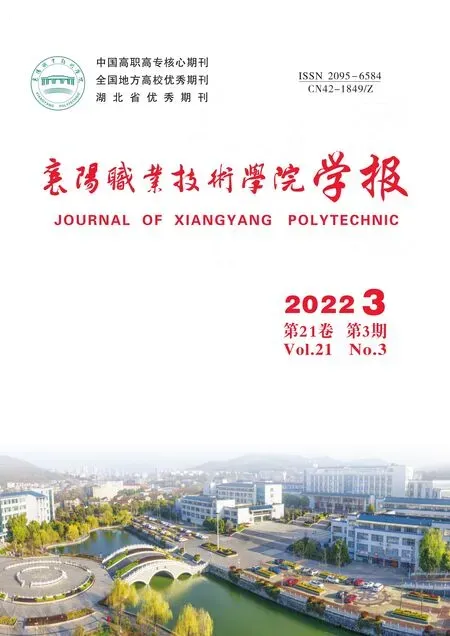对比赏析杨戴与霍克斯《葬花吟》译本
——从“文与质”和“归化与异化”角度
2022-03-01袁在成
袁在成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翻译活动,而《葬花吟》作为女主人公林黛玉所作的一首经典之作,其文学价值至今仍为世人所敬仰,这样一首集大成的诗篇更是为后人所传颂。如今备受瞩目的英译本,包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及大卫·霍克斯的A Story of the Stone。本文分别从“文质之争”及“归化、异化之争”对这两种译本进行对比赏析,探索中诗英译之路。
一、“红学”英译研究现状
早在1830年就出现了《红楼梦》的英译,1830年至1900年是直译时期,1901年至1960年是翻译方式多样化时期,1961年至今是翻译方式高度学术化时期。1830年至1900年期间,总共有四个英译本,分别为:1830年,John Davis译的两首《西江月》,这标志着“红学”英译的开端,极具重要意义;1846年,Robert Thom英译第六回中的一些片段;1868年,英国人Edward Charles Bowra英译了前八回;1892年至1893年,H.Bencraft Joly译成前五十六回,这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译本。1901年至1960年出现四个英译本:1927年王良志的英译本;1929年和1958年王际真的两个英译本;1958年Florence Mchugh和Isabel Mchugh发表的英译本。1961年至今,共出现三个译本:1973年至1980年David Hawke译成前八十回,其女婿John Minford于1982年至1986年补译后四十回,这是第一个《红楼梦》全译本;1978年至1980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全译本陆续出版;1991年,黄新渠的简译本出版。随着科技和时代的进步,“红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研究意义至为深远。
二、“文”与“质”
我国翻译史上历来都有“文质之争”,其间经历了从东汉到北宋的漫长历史时期。[1]“文”即文采,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即实质,是文学作品内容的详实与否;故而言之,“文”与“质”的关系其实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相对应。其二者最早见于《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之后刘勰提出:“以文附质,以质待文”的主张;而胡应麟也在总结了中国从周代至唐代的文学创作史后提出:“文质彬彬,周也。两汉以质胜,六朝以文胜。魏稍文,所以逊两汉也;唐稍质,所以过六朝也。”可见在进行文本翻译时,必须做到文质统一,即:以质为本,以文为附,文质相称,相辅相成。
杨戴与霍克斯在处理《葬花吟》的翻译中,也对“文”或“质”有所偏向。例如:
例1: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杨戴:“By the third month the scented nests are built,but the swallows on the beam are heartless all.”
霍克斯:“This spring the heartless swallow built his nest,beneath the eaves of mud w ith flowers com-pressed.”
一般来看,“三月”即是一年中的第三个月,杨戴按照字面意思译为“by the third month”,是遵从了原文的形式,尚“文”。霍克斯未采取这种译法,意译成“this spring”,既为“三月”,那便早已入春;再者,三月本就是一年中“桃飘”“李飞”的正当时节;还者,在英文文章中,数字一般只是代表了一个虚数,并非实指,相反直接译出原意,可能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文读者而言,更易接受。所以霍克斯“尚质”的译法的确巧妙。
燕子的巢穴一般只是它们产卵和育雏的临时“落脚点”,一旦受到较大干扰,或者有更好的去处,就会放弃已经筑好的巢穴而另择新址。就原文来看,作者其实是借此喻彼,表面是黛玉在叹怜落花的命运,并将这种叹息怨及“梁间燕子”的归去,实则是推己及人,感叹自己凄惨的身世与境地。跳出本诗,放到整个故事情节中,且用谶语来分析,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初定,即“香巢已垒成”,可之后却发生变故,就如同无情的燕子飞走一样,宝玉也离家出走了。杨戴直接不改变原文形式,将“香巢”译为“scented nests”,直译得顺理成章,是为重“文”。原文是“香巢”,霍克斯偏偏意译成了“his nest...with flowers compressed”,既是“香”,那必是花香,因为现在正是桃李纷飞的季节,与原文葬花的大背景相协调,这样也便于不熟悉《红楼梦》的英文读者们理解;霍克斯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所以出此译文,确为精妙,表象是意译,实则是“守质”。而且从感官赏析,杨戴给人以嗅觉感受,而霍克斯则是视觉感受,两种译文各有千秋。
例2: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楼空巢已倾。
杨戴:“Next year,though once again you may peck the buds,from the beam of an empty room your nest will fall.”
霍克斯:“Next year the flowers will bloom as be-fore,but swallow,nest,and Maid will be no more.”[2]
杨戴把“梁间燕子”化成人,译为第二人称似乎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对于“人去楼空巢已倾”,则译成“from the beam of an empty room your nest will fall”,而其实真正的语序应该是:“your nest will fall from the beam of an empty room”,意为“你的巢将会从空房的横梁上坠毁”。仔细推敲,本是“人去楼空”,可杨戴却译成“empty room”(“楼空”),那么“人去”呢?其实,原诗中的这二词即是两个因果词,因为“人去”了,所以“楼”就“空”了,以此看来,译者重在传达原诗大意,是为尚“质”。
霍克斯很注重行文押韵,这一点甚于杨戴,可是明显可以看出,在前半句中,霍克斯只译出“明年花会再发”,而省译了“啄”字,可见是“文”过于“质”。
老子曾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确实有些道理,毕竟将一源语译成目的语时,要考虑到文化因素,而偏偏有些文化信息是无法转换的,因为其中暗含某些文化难点和典故,诗词翻译就更是难了,用严复的话可以概括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个人在读他人的诗时,因为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对于原诗的理解便会不同,读者都是对原作的体会和揣摩,而这种体会和揣摩只是读者自己的感受,身为原作当有另外一种心境;用同种语言表达出的感受尚有不同,更何况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呢?“翻译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3]所以译者的译本都是在向原作无限靠近,而每位译者翻译风格又不尽相同,所以为了尽量向读者表达出原作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又不失“美感”,即“文质相称”,方能“圆满调和”。
三、“归化”与“异化”
作为翻译策略中的一对术语,“归化”与“异化”的定义是由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Venuti,1995:20)中提出的,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4]据韦努蒂所言,“归化”就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即以目标语文化或读者为归宿,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将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用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传递原作的内容,形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实现读者与原作者的直接对话。相对而言,“异化”即“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顾名思义,就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迁就外来语语言文化及表达习惯,使读者和译者尽量向原作靠拢,相应地采用原作的表达方式来传递原文内容,有利于保留异国情调,反映民族文化差异性。下面,笔者将以杨戴和霍克斯的译本为例,分析《葬花吟》中“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具体体现。
例3: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杨戴:“Softly the gossamer floats over spring pa-vilions,gently the willow fluff wafts to the embroi-dered screen.”
霍克斯:“Floss drifts and flutters round the Maid-en’s bower,or softly strikes against her curtained door.”
“游丝”在汉语中指的是“蛛丝”,杨戴采用异化法译成“gossamer”(蛛丝),保留了源语的色彩。蛛丝是多么精细的东西,用“soft”正是巧妙勾勒出它柔软飘荡空中的画面,下句同样把“gently”提至句首,形容柳絮“轻沾绣帘”的情景,对仗工整,且与原文的对偶句式相呼应,再现原文的形美和意美。而霍克斯则归化成“floss”(丝棉,乱丝),明显没有体会到原作的深意。再如“春榭”,原指黛玉的闺房,按字面的意思就是“春天的楼阁”,杨戴同样采用异化法将其译为“spring pavilions”;而霍克斯作为一名西方译者,则归化成“Maiden’s bower”,“榭”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用“bower”虽然不太准确,但能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明显是站在了读者一边。
例4: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杨戴:“Better shroud the fair petals in silk,with clean earth for their outer attire.”
霍克斯:“But better their remains in silk lay,
and bury underneath the wholesome clay.”
“艳骨”一般用来指人,即美人的尸骨,而在此处却是指“残落的花瓣”,所以原作其实是将“残落的花瓣”喻作“美人的尸骨”,是为拟人,又不乏象征的韵味。汉语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所以原作“艳骨”二字用得确实精到。杨戴在处理译文的时候,不译喻体译本体,即为“fair petals”,虽缺少了某种凄凉之意,但也确是得当,更易于读者理解原文深意,因为如果直译为“美人的尸骨”,不仅让没有深悉《红楼梦》的西方读者不知所指,更会丢失原文的意美。霍克斯译成“remains”(遗骸),同样是只译本体,虽未体现出“艳”,失去了几分颜色,但“宁信而不顺”,便于读者接受。所以在此译文的处理上,杨戴和霍克斯都采用了归化的方法。
四、结束语
郭平章在《新译唐诗英韵百首》(2002)的序中谈到:“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诗歌翻译是最难的,这点几乎是译界的一致看法,根本原因在于诗无达诂这一客观事实。”总体看来,杨戴与霍克斯的译文都可圈可点,当然也不乏不足之处。杨戴多直译,旨在能准确传达出原作的深意,而不作过多修饰与改变,在传达原作意思方面比霍译本更贴切,其译文更尚质、重异化;然而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译诗风格,对于本土的中国读者而言容易理解,但西方读者则不然。而霍克斯则以西方读者为归依,多意译、偏文、甚归化,这种求神似的译诗风格确实更符合英诗习惯,易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中国红学专家吴世昌曾说:“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紧扣原文,语言优美生动,体现了他们一贯严谨认真,忠实达旨的译风。”[5]就连杨宪益自己也认为,翻译时不能作出过多解释,译者应该尽量忠实原文的风格,既不要夸张,也不要过分修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写文章了。而戴乃迭却曾谦虚地认为,其二人的译本灵活性和创造性不如霍克斯。笔者以为,在中诗英译时,应“文质结合”“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