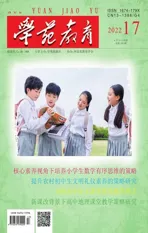常疑生惑,善辨则清
——关于部编版语文必修课本内容的几点思考
2022-03-01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陈常锋丛明娟
山东省垦利第一中学 陈常锋 丛明娟
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我们语文老师不仅要善于读书中质疑,更要善于教书中质疑,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时时怀疑古人古书的习惯,敢于有自己的见解,组织自我思想体系。如此才能增进自己的教业,如此才能培养学生之独立思考意识。笔者教书育人二十多年,用过人教版、鲁教版、苏教版等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有些篇目在细微处有较大不同,给师生造成一些困惑,翻阅相关资料深入思索后,现整理如下。
一、何为“繁霜鬓”
新部编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一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文选取的魏晋唐宋时期的古诗词达八首之多。其中诗圣杜甫的《登高》就以其丰富的意蕴颇耐人寻味。“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一句中“繁霜鬓”一词,课下注释译为“像浓霜一样的鬓发”,窃以为值得商榷。
查阅资料发现:2007 年 3 月第 2 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二单元第5 课“杜甫诗三首”的课下注释,解释为“像厚重白霜似的鬓发”,而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 年12 月第6 版的高中语文必修四课本的课下注释则译为“多”。显然,人教版注释虽表述略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一致;但苏教版则明显不同。
百度百科在《登高》的“注释译文”中,解释“繁霜鬓”为“增多了白发,如鬓边着霜雪”,又解释“繁”为“这里作动词,增多”。
翻阅《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大学教授陶道恕是如此赏析的:“《登高》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此处显然认为“繁”为“多”之义。
《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中“繁”共有五个义项:①多,盛;②繁杂;③茂盛;④繁殖;⑤pó,姓。“繁霜鬓”中的“繁”应取第一个义项“多”,而“霜鬓”为一个表意完整的意象,其意为“白色的鬓发”。这也是有据可依的。譬如说,唐·高适《除夜作》:“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唐·韦应物《答重阳》“坐使惊霜鬓,撩乱已如蓬”;宋·晏几道《浪淘沙》:“霜鬓知他从词曲,几度春风”;宋·苏轼《浣溪沙·赠闾丘朝议时还徐州》:“霜鬓不须催我老,杏花依旧驻君颜”。由此可见,“霜鬓”作为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在历代均被广泛使用。
此外,就表达效果来看,译为“增多了白发”比“浓霜一样的鬓发”也明显要好很多。因为“增多了白发”,不止写出了鬓发斑白,而且突出了“增多”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突出其因“艰难苦恨”而日趋贫病衰老、苦痛难耐的境遇。
当然,“繁霜”一词,确有“浓霜”之义,比如唐代王维《冬夜书怀》中“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宋代黄庭坚《秋怀二首》中“狐裘断缝弃墙角,岂念晏岁多繁霜”,均为“浓霜”之义。然而仔细分析后,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诗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繁霜”为一个表意完整的意象,并且都不与“鬓”连用,与之前笔者罗列的一组诗句有着明显的区别。
综上所述,在杜诗《登高》中,笔者以为“繁”还是译为“多”“增多”为宜。
二、“贤”为何义
新部编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一语文必修上,韩愈的《师说》中“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中的“贤”,课下注释为“超过”,那么“于”自然也就是引出对象的介词,句子则翻译为“因此弟子不一定比不上老师,老师也不一定超过弟子”。在传统教学中,这个句子一直被认为是状语后置句,“于”翻译为介词“比”,而“贤”则译为“贤能”,句子则译为“因此弟子不一定比不上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
比较2007 年3 月第2 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三单元第11课《师说》,发现虽然均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但此次新部编版教材的课下注释是新增的,也就是说这是编者特意做出的一个更正。
那么,这一更正是科学合理的还是多此一举呢?
查阅《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发现“贤”字有四个义项:①有道德有才能的人。②尊重,赏识。③胜过,甚于。④劳苦。显然,课本是选用了第三个义项“胜过”“甚于”,经仔细思考后认为:这次更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科学合理的。
此前传统的解释的确完全可以讲得通,也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但仔细想来,还是译为“超过”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一一道来。
首先,我们来看文章的中心论点。《师说》是一篇典范的议论文,切中时弊,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解决时人不从师学习的社会问题,其中心论点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观点树立了正确的择师标准,厘清了人们的错误认识。很明显,韩愈的出发点在于引导人们从师学习,而从师学习的标准就是“闻道先乎吾”,而非要求人们做“贤士”,因此“贤能”也就不是文章着意探讨的内容。
再者,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文章第三段做结论时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显然,根据作者的分析,“贤”是和“不如”相对应的,译为“超过”更合适;而且,“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都不是在谈论“贤能”与否。因此可以确定,此处“贤”应该译为“超过”。
最后,再来看一下其他文献。《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中有言,“老臣窃以为媪之爱长安君贤于燕后”,此处,“贤”即为“胜过,超过”之意。而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在名篇《伤仲永》中,也有“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的句子,意为“他天生聪明,远胜过一般有才能的人”,“贤”也译为“胜过、超过”。
由此可见,“贤”在此处译为“超过”是非常科学合理的,也就是说此次新部编版必修教材所做出的修正是非常及时准确的,纠正了一线教学的乱象,也给了语文教师课堂教学以科学指引。
三、“书”“疏”之辨
新部编教材高一语文必修下册选用了《谏逐客书》《与妻书》《答司马谏议书》和《谏太宗十思疏》四篇文言文,这四篇文章的文体是否相同呢?因课本注释中并未涉及,不少师生对此心生疑惑,以致影响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就写作对象而言:《谏逐客书》是写给秦王嬴政的,《与妻书》是写给妻子的,《答司马谏议书》是写给同僚的,而《谏太宗十思疏》则是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据此,这四篇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帝王的,一类是写给亲人朋友的。由此可见,这四篇文章文体并不相同。其中《与妻书》和《答司马谏议书》非常明确,文体均为书信体,其中《答司马谏议书》的“答……书”,稍为特殊,是一封回信。而有辨识难度的则是写给帝王的两篇文章的文体。笔者仔细查阅资料后,有以下发现。
1.同源不同名。
被誉为“千古第一奇文”的《谏逐客书》,让秦王嬴政读罢惊叹,立即撤销逐客令。既是写给帝王,那就应该是“奏疏”,为何用“书”呢?
查阅《古代汉语词典》,“书”:文体名。内容、体裁不一。“疏”:一种文体,臣子给皇帝的奏议。据此注释,仍然无法明确区分。
“书”出现最早,适用范围最广,功能也最为强大。战国以前臣下奏谏陈词,向君主进呈书面意见,都统称为“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乐毅的《报燕惠王书》、范雎的《献秦昭王书》、苏秦的《说秦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举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有这样一段话,“(齐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其中就有“上书”这样的说法。
《史记》当中也有很多相关的记载。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
又如《范雎蔡泽列传》中:“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再如《春申君列传》中:“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显然,这几处均为臣下向君主进呈书面的意见,上书进言陈事。事实上,“书”并非奏疏的专称。先秦时期,“书”是书信、意见书的总称。古代“言笔未分”之时,不分君臣,互相来往都用书,只不过,当往来的对象是君王时,人们习惯认为其等同于后世的奏疏,此类用法与课本中的《谏逐客书》一致。
那么,“书”何时意为书信呢?此处仍以《史记》为例加以说明。
《商君列传》中:“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此处是说,两军对峙之时,卫鞅送信给魏将公子卬。
又比如《刺客列传》中:“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这里是说代王赵嘉写信给燕王姬喜。
再比如《魏公子列传》中:“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此处是说,赵国平原君夫人多次送信回魏国求救。
很明显,这三处选文中的“书”皆指代书信,可公可私,与课本中的《答司马谏议书》和《与妻书》用法一致。
2.规范后分化。
那么,“书”与“疏”又是何时分化的呢?
秦统一六国后,改“书”为“奏”,但因为离古代还不太远,所以仍然有人用“书”。
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为“公车”。汉制规定,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如《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中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说东方朔到公车府给皇帝上书,共用了三千个木简。可见,汉代依然有“上书”的说法。
随着汉制的规范,这类文字被分为四个小类,即章、奏、表、议。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里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很明显,已经细化了此类文章的功能。
疏,指分条陈述;作为一种文体,它是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述自己对某事的意见的一种文件,也称“奏疏”或“奏议”。
依然以《史记》为例来说明,《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此处,已经改用“上疏”。
汉代名臣贾谊就有多篇谏疏流传于世。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文帝五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和贾谊同为汉代文景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的晁错,则著有《论贵粟疏》。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更是奏疏中的经典之作。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对此魏征极为忧虑,他清醒地洞察到繁荣昌盛后隐藏的危机,“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
由此看来,“书”在先秦已经出现并广泛使用,而“疏”则是在汉代以后才开始使用。《谏逐客书》和《谏太宗十思疏》名异而实同,均为臣子向帝王上书言事,只是由于不同年代称谓有所不同。
3.仍然在使用。
当然,“书”也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如西汉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狱中上书自明》),用铮铮铁骨和不卑不亢的高尚气节证明自己的侠骨和节操,体现出邹阳正直的品格,也透露出人言可畏的道理。
再有近代著名的梁有为《公车上书》、康有为的《上今上皇帝书》,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由此可见,“书”亦有公私之分,除作为上书的公文外,就是私人往来的信件,如课本选编的《答司马谏议书》和《与妻书》。
综上所述,“书”与“疏”既有重合又有区分,具体应视文章写作目的、写作对象和写作内容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