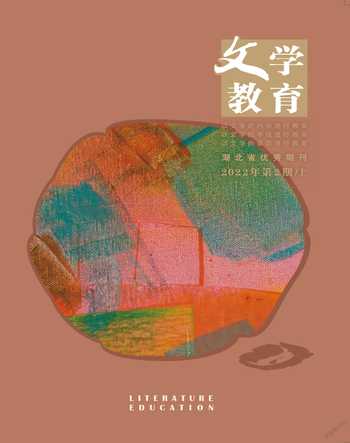概念隐喻视角下狄金森死亡诗歌研究
2022-03-01汪虹
汪虹
内容摘要:狄金森“死亡”诗歌里存在大量新奇隐喻,让人感到突兀难解,从概念隐喻视角解读狄金森“死亡”诗歌,能从认知层面揭示狄金森“死亡”诗歌所蕴含的各种隐喻之迷,从而更好地体验其诗歌的魅力。
关键词:概念隐喻 狄金森 死亡诗歌
1980年,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他们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里首次提出术语——“概念隐喻”。他们认为隐喻并非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修辞手法,隐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以“争论”和“争论是战争”为例,论证了语言表达中的隐喻其实是来自于人的概念体系中的隐喻。在英语表达里,与“争论是战争”相似的概念隐喻和其语言表现形式比比皆是,为更好地进行研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将它们分成三类:结构性隐喻、方位性隐喻和本体性隐喻。其中,结构性隐喻是构造语言表达形式的基础。
“死亡”是狄金森诗歌创作的主要主题,狄金森在其“死亡”诗歌里运用了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在丰富了诗歌的内涵、让读者领略了耳目一新的“死亡”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新奇隐喻的含混难解。基于此,将概念隐喻理论引入狄金森“死亡”诗歌的研究,能让读者深层次解析诗歌里各种含混难解的隐喻,从认知层面赏析各新奇隐喻的独特魅力。
一.“死亡”:一朵雏菊
一朵雏菊今天/已经从田野里消失——/许多浅口便鞋踮起脚尖/向着天堂走去——║在红殷殷的泡沫里/渗出白天退着的潮汐——/开花——轻跳——漂流——/你可跟上帝在一起?[1]
“死亡”往往令人心生畏惧,但狄金森笔下的“死亡”却让人有着不一样的感受。“诗人从雏菊的凋谢联想到朝着天堂迈进的人的脚步,再由退潮般的夕阳西下联想到生命或自然从荣到枯必经的三个阶段”[2]。很明显,此诗歌并不仅仅只是一首描写雏菊生长周期的诗,读者在赏析诗歌时,会将雏菊的一生和人的一生进行相似性比较。那么,这么一首描写雏菊生长周期的诗是如何让读者联想到人类自身的“生”“死”过程的呢?不可否认,概念隐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隐喻认知的支配下,读者在进行诗歌赏析时,必然会将“LIFEIS ADAISY.(生命是雏菊。)”当作贯穿于诗歌始终的核心概念隐喻。在此核心概念隐喻下,读者会很自然地将雏菊的各种特质和人类生命的各种特质相关联。
诗歌伊始,读者在“LIFE IS A DAISY.(生命是雏菊。)”这一核心概念隐喻的认知引导下,已感受到了雏菊和人类生命之间的关联性:雏菊的消失,实质上也相当于人类生命的殆尽。因此,诗歌的前两行诗“一朵雏菊今天/已经从田野里消失——”成为了核心概念隐喻的引申隐喻:“雏菊的消失即人类生命的消逝”。那么雏菊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在第二诗节里有这样的描写“开花——轻跳——漂流——”。这里,核心概念隐喻“LIFE IS A DAISY.(生命是雏菊。)”又引申出一个隐喻表达“雏菊的一生即人的一生”。雏菊的一生会经历花开、花败,人的一生也正是如此,有生就有死,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然经历。
由此可见,以“LIFE IS A DAISY.(生命是雏菊。)”这一概念隐喻为核心,诗歌引申出了两个相关概念隐喻“雏菊的消失即人类生命的消逝”和“雏菊的一生即人的一生”,它们构成了一个概念隐喻系统,在此隐喻系统下,也让读者对“死亡”有了新的理解:人的生命如同一朵雏菊,有如花般绽放的美丽,也有如花般凋零的没落,美丽也好,没落也罢,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你可跟上帝在一起?”
二.“死亡”:一只停摆的钟
狄金森笔下,“死亡”可比作一朵凋零的雏菊,“死亡”也可喻成一只停摆的钟。
一只钟停了——/不是壁炉上的——/日内瓦最远的技艺/无法使那木偶点头——/它现在正静悬在那里——║敬畏向小摆设袭来!/数字隆起背,好痛苦——/然后颤抖着脱离了小数——/进入零度的正午——║它不肯为医生动一下——/这个白雪的钟摆——/这个店员对它纠缠——/它却冷冷的——不予理睬——║镀金的指针频点头——/细长的秒针把头点——/几十年的傲慢横在/钟面生活——/与他之间——[1]
“一只钟停了——”,如此的开场白,读者会毫不犹豫地联想到时钟与时间的关系:时钟停止不动了,那么钟表上的时间也必然不再前行,时间与时钟间建立了显而易见的隐喻关系,但诗人并未止步于此,第二诗行:“不是壁炉上的——”,很明显,诗人在此表达了此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彼钟,也暗示了这里的时钟并不仅仅只是与时间有关联。那么,诗中这只停摆的时钟到底是和什么建立了隐喻关系?在隐喻认知理论的指导下,读者将逐步找到答案。
在第二诗节里,“敬畏”“袭来”“好痛苦”“颤抖”“脱离”“零度的正午”这几个关键词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痛苦与寒意,而這样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死亡”的场景,只有在面临“死亡”时,人们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此一来,隐喻认知理论下,以“钟”为关键词,诗的核心概念隐喻得以成形:“DEATHISACLOCK.(死亡是时钟。)”根据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对结构性隐喻的定义:结构性隐喻是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式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如“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里,“DEATH IS A CLOCK.(死亡是时钟。)”和“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一样,也属于结构性隐喻,它也引申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隐喻,如:“一只钟停了——”“它现在正静悬在那里——”“数字隆起背,好痛苦——”“这个白雪的钟摆——”。可见,在构建了“DEATH IS A CLOCK.(死亡是时钟。)”此结构性隐喻的思维框架后,诗人运用了一系列与时钟有关的词汇表达“死亡”,如:“钟停了”“静悬”“数字隆起背”“白雪的钟摆”等。这些词汇与结构性隐喻紧密关联,是结构性隐喻的引申表达,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涵,让读者不自觉地将“死亡”和“时钟”两种意象关联起来,并对“死亡”有了新的领悟:“死亡”的脚步无法阻挡,正如一只无法修复的停了摆的时钟。这也暗示了“死亡”降临之时,即便再恐惧、再痛苦,当事人都无法逃脱“死亡”。但诗的最后一节也表露了:虽然人类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却可以选择以辉煌的形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即使“死亡”降临,也会是“几十年的傲慢横在/钟面生活——/与他之间——”。
三.“死亡”:一次战役
狄金森还把“死亡”比作一次战役。在如此新奇的比喻下,读者对“死亡”有了耳目一新的认知理解。
我的战争搁置在书里——/我还有一次战役——/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仇敌/却常常把我端详仔细——/并在我和我的战友之间/踌躇彷徨,/但终于选中了精英——忽略了我——/直到其余的,全部死亡——/如果我没有被故去的弟兄们/遗忘,那是何等的美妙——/因为到了古稀之年/游伴是那样稀少——[1]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解释“概念隐喻”时,曾以“ARGUMENT IS WAR.(争论是战争。)”为例,探讨了“概念隐喻”的特征:“人们在进行争论的时候,往往会把‘争论’当作一场战争,将与战争有关的一些规则放入‘争论’之中,如攻击他人观点、捍卫自己观点、失去和赢得阵地、运用策略等。由此可见,人们在争论时的所说所为是由战争概念所构成,‘争论是战争’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构建了人们在争论中的行为方式”[3]。在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的例子里,当“争论”被喻作“战争”,人们在谈论“争论”时会使用一系列有关“战争”的术语去描述“争论”、理解“争论”。诗歌《我的战争搁置在书里——》,诗人使用了有关“战役”的隐喻:“我还有一次战役——/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仇敌/却常常把我端详仔细——/并在我和我的战友之间/踌躇彷徨,/但终于选中了精英——忽略了我——/直到其余的,全部死亡——”。这里,隐喻的本体不再是“争论”而是“死亡”,根据隐喻认知理论,诗人笔下的“死亡”必定会与一系列“战役”术语密切相关,而读者也会在此概念隐喻的指引下,开启对“死亡”的全新解读。
在隐喻认知理论下,“DEATH IS A BATTLE.(死亡是战役。)”和“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一样,是结构性隐喻,此隐喻贯穿全诗。然而,作为诗歌开篇之句“我的战争搁置在书里——”,此诗句里的“战争”和“死亡”之间并无隐喻关系。“‘战争’或‘战斗’是狄金森终身的核心隐喻——‘她孜孜以求地创作不是为了得到认可,而是为了表达一场无法逃避的,艰苦的、关乎生存的战斗。’斯人已逝,那一场场战斗都已成为历史,埋进文字和书册,吸引着一代代读者前来挖掘:编辑、阅读、翻译、书写……”[4]由此可见,开篇之句里的“战争”也是隐喻,只不过这里是把“诗人的创作”比作“战争”。狄金森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其作品的创作过程并非易事,每一次创作都是诗人与内心、与思维的“战争”。在创作的“战争”里,诗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首首佳作最终得以问世。虽然诗首句里的“战争”没有和“死亡”构成隐喻认知关系,却是结构性隐喻“DEATH IS A BATTLE.(死亡是战役。)”的重要引出:诗人穷其毕生精力进行诗歌创作,每次创作都是艰苦卓绝的“战争”,当生命走向尽头,“死亡”成为诗人在世间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诗歌第二句开始,诗人开始构建“死亡”和“战役”之间的隐喻认知关系,“DEATH IS A BATTLE.(死亡是战役。)”成为贯穿诗歌的结构性隐喻,一系列相关隐喻也随之引申而出,如:“从未谋面的仇敌”“我和我的战友”“选中了精英”“故去的弟兄们”等,将“死亡”和“战役”从认知层面进行了关联:当“死亡”成为“一场战役”,“我”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毕竟“死亡”是“战役”里“从未谋面的仇敌”,时刻在挑选对手,“并在我和我的战友之间/踌躇彷徨,/但终于选中了精英——忽略了我——/直到其余的,全部死亡——”,随着“战友”们接连在“战役”中失去生命,作为幸存者的“我”越来越感到孤独,“如果我没有被故去的弟兄们/遗忘,那是何等的美妙——/因为到了古稀之年/游伴是那样稀少——”。
四.“死亡”:灵活的求婚者
此外,狄金森笔下的“死亡”也是一位灵活的求婚者。那么,“死亡”和求婚者之间又有怎样的隐喻认知关联呢?
死亡是灵活的求婚者/最终赢得了芳心——/那是一場偷偷摸摸的追求/最初的发动/用苍白的影射/和朦胧的接近/但最后吹响号角/驾着一辆散架的车辇奋进/它胜利地驰往/未知的姻缘/和亲属关系,回应积极/跟瓷器一般。[1]
《死亡是灵活的求婚者》以“死亡是灵活的求婚者”开场,此诗句本身就构成了结构性隐喻“DEATH IS THE SUITOR.(死亡是求婚者。)”。在此结构性隐喻框架下,诗人以概念“求婚者”的结构来构式“死亡”这一概念,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死亡”。这里,“死亡”化身为一位灵活的“求婚者”,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新娘”的芳心,让她心甘情愿地奔赴“死亡”。
一开始,“死亡”这位求婚者也和大多求婚者一样,对求婚是否成功并未有十足把握,也只能“偷偷摸摸的追求”,使用“苍白的影射”和“朦胧的接近”试探地接近新娘,但不管怎样,“死亡”毕竟是一位“灵活”的求婚者,头脑灵光的它,“最终赢得了芳心——”。可见,诗歌将“死亡”这位求婚者的求婚经历描写得细致到位,“DEATH IS THE SUITOR.(死亡是求婚者。)”这一贯穿全诗始终的结构性隐喻也引申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隐喻,如:“最终赢得了芳心”“那是一场偷偷摸摸的追求”等,让读者从认知层面将“死亡”和“求婚者”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奔赴“死亡”就是奔赴一场蓄谋已久的婚约;“死亡”会如同求婚者一样耐心等待,直到婚约达成。但这场婚约(“死亡”)的结局到底是幸福还是悲伤?答案也是无从知晓,“它胜利地驰往/未知的姻缘/和亲属关系,回应积极/跟瓷器一般。”
狄金森的“死亡”诗歌想象力丰富,里面充斥了大量的新奇隐喻,这些隐喻在丰富了诗歌的内涵的同时,也常让读者感到含混难解,从概念隐喻视角对狄金森“死亡”诗歌进行解读,不仅能从认知层面合理解释诗歌里的新奇隐喻,还能对狄金森作品所隐含的深邃之美有深层次了解。
参考文献
[1](美)艾米莉·狄金森著,蒲隆译. 狄金森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259,273,315-316,314.
[2]刘晓晖.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5.
[3]Lakoff,George&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4.
[4](美)阿尔弗雷德·哈贝格著,王柏华,曾轶峰,胡秋冉译.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艾米丽·狄金森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认知诗学视角下的狄金森诗歌艺术风格研究”(20B5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