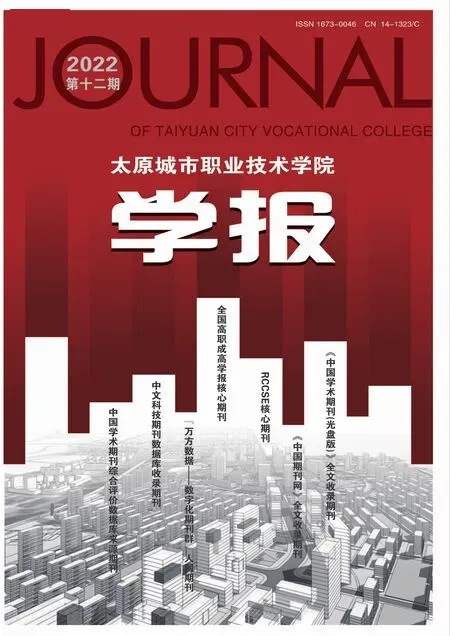共同主体性、交往理性、合作治理:考察习近平互联网思想的三个维度
2022-02-27彭文利
■彭文利
(中共梅州市梅江区委党校,广东 梅州 514000)
习近平互联网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代表和展现着新时代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价值哲学和方法路径。基于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哲学分析的必要,可以从文化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对习近平的网络思想进行一个“结构化”的审视,主要的动机在于加深对于习近平互联网思想的认识。因此,笔者尝试运用文化主义分析最为时尚的框架,从“集群性假设”“行为实践层次”“物质器物层面”三个方面开展考察。
一、集群性假设层面:共同主体性价值的主要面向
时下学术界流行的组织文化结构分析理论在分析文化的时候往往从“集群性假设、文化实践和外显事物三个部分”[1]展开,其中集群性假设是一种最为神秘、最为核心的价值范畴,对于文化结构和功能具有根本性的价值制约作用;“文化实践”主要是呈现为具体的实践行为;“外显事物”则指向最为表层的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元素、符号等。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本身既具有一定的理论边界,呈现出自身理论建构的规范性;他的互联网思想又是与其治国理政思想、“中国梦”思想、文化宣传思想、教育思想、国防安全思想等互相渗透和互相交织的,存在边界的重叠。因此,从“集群性假设”的角度来考察习近平网络思想的“价值内核”既是对其“价值论”的进一步求索,又是厘清其理论品质的必要前提之一。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在集群性假设方面代表的是一种关于古老的“共和主义价值”的复苏,这种价值借助于实践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传播,在政治哲学、社会管理等领域繁育出了从“交互主体性”(或者说主体间性)走向“共同主体性”的果实。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论述多次提到了“合作”“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等,在主体性哲学方面实际上就是要在尼采所讲的“上帝已死”基础上通过跨主体的、跨层次的、跨部门的、跨国别的、跨文化的合作精神来实现对于某种基于共识的“共同主体性”价值的追求;也是一种从西方近代以来确立起来的理论哲学导向的“主客体二元论”出发重新建构起一个基于交互主体性建构起来的“天人合一”的共同体。由于互联网这种客观的技术形态在技术延展和现实联结方面赋予了这种共同体价值实现的更大可能性。习近平网络思想体现出来的这种共同体价值集群性假设代表着以下几种价值源流。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倡导的“和谐”“中庸”“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价值道统。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性以来确立起来的诸如“民主”“自由”等价值都是基于分化的、分裂的个人主义建构起来的,紧张的人际关系、分化的利益、科层制的诞生、人与自然的冲突、国际秩序的冲突和对立等大多都与这种现代性的弊端有关。当互联网通过技术和实践将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结起来了之后,我们发现在深层次的价值理念角度、意识形态角度等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裂痕。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的网络思想巧妙地借助抑或某种程度上复苏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儒家道统”和“禅宗思想”“道家伦理”等,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现代化改造,使之更加具有了共同体的色彩。所以习近平的网络思想之“共同体价值关怀”并不是纯粹的那种“国家主义导向的”[2],而是基于全球一体化、从全球角度出发阐释的“共同体主义导向的”集群性假设。
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人学价值”。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和人学价值区别于自由主义人权思想、旧式人学思想的主要面向在于其“类的关怀”,即从人类共同体的视角对如何实现“人的解放”进行思考。习近平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价值之后,既用“共同体主义”的人学价值超越了西方那种“原子式的自由主义价值”,也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削弱国家认同趋势进行了一种控制和改造,重新借助于共同体实现了社会伦理的聚合。总体来看,这种带有共同体主义的人学价值构成了习近平互联网思想集群性假设的重要部分,它“强调生活的社会性质和身份关系而不是选择自由”[3],并且它“从类型上看,共同体包含了大共同体(国家、民族和阶级)、小共同体(社团、邻里)乃至全球共同体”[4]。
二、交往理性实践层面:交往中的实践与实践中的交往
网络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因此作为“人的延伸”,网络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其价值,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促成“网络共同体”——无论这种共同体是一种“主观的想象”,还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政治哲学的向度上,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具有典型的“交往理性实践”的光辉含义,当然这种意义是作为“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再到共同主体性”之本质规定性的附属物来体现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海德格尔、胡塞尔、哈贝马斯等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系列论述中都能找到相关的实践依据。
比如说,海德格尔在针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现代性哲学的批判时就致力于从“人的本质”这个角度对现代性哲学的“理论哲学”属性进行解构。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建构起来的“人的理性化”这一界定进一步巩固了“主体—理性”的现代性哲学思维,在这种理性化思维的框架中,“人的实际存在始终被理解为对特定的‘理性’的懵懂无知,对特定‘真理性’的不足与缺乏,而人的历史也就相应地被理解为按照某种神圣目的的引导而向着已经预定好的、现成存在的、亘古不变的某种完满状态的不断接近”[5]。因此,对于这种“历史是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人是理性化的产物”,海德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从历史性、实践性、物质性、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构和重构“主体性哲学”,致力于通过“交往理性”来克服主体性哲学的“狭隘化理性”。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超越理论哲学、从交往理性的角度来克服狭隘的功利性理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实践)是整合主客体分裂的‘手段’和‘跳板’”,同时证明“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一向已经逗留着寓于世内上手的东西,而绝非首先寓于‘感知’,仿佛这团纷乱的感知先须整顿成形,以便提供一块跳板,主体就从这块跳板起跳,才好最终到达了一个‘世界’”[6]。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的设想中,人的本质不在于“原子态的理性化”,而在于“交往性的理性化”。
对此,马克思也从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出发,较为系统地创立和阐释了其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在实践中创造的,以劳动为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应……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同时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7]。用马克思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无论网络作为一种“技术”,还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或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平台”,抑或是“人的延伸”,本质上都是符合实践哲学所讲的“交往理性”的。
又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也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交往哲学”理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的构建当中,他基于现代公共领域的结构化转型的背景,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公共权力部门“的三元化社会结构当中围绕着“公共性”的展开和实现,引入了“对话民主”(也称协商民主)理念作为在公共领域中开展民主合作治理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存在的本质性结构功能在于“让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从而对公权力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即“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8]。在关于人的“主体间性”之阐释方面哈贝马斯超越了马克思所讲的“交往理性”,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内涵穿插其中建构出了“交往理性实践”,或者说“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9]。今天学术界广泛探讨的“协商民主”“慎辩民主”等概念正是源于哈贝马斯对于人的交往理性实践的建构、对主体间性进行深度思索、朝着共同主体性建构的必然学术趋势。
在工业化时代,学术大师们建构出来的“交往理性”大多都是基于对单向度的社会大众传媒工具的批判开展的。然而当前在我们进入信息社会、后工业化社会形态之后,“交互式的互联网新媒体”为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提供了实践交往理性的技术可能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的网络思想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点就在于其交往中的实践性和实践中的交往性。
三、公共事务治理的层面: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透视习近平互联网思想最为直观、最为表层的一个视角就是公共事务的治理视角。实际上在当前关于“公共性哲学”的探索过程中,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最为显著的一个知识生长领域。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无论是从“网络共同体的公共性建构”角度来说,还是从“共同体建构中如何实现网络公共性价值”角度来说,借助于特定的公共事务治理话题来探索这一主题是学术界自觉的共识,“通过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和探讨,社会成员由围观到行动、由分歧到共识,网络公共性不断地凝聚和建构”[10]。借助于特定的公共事务治理,我们可以很好地洞察习近平互联网哲学、互联网思想的“合作治理”基因。
第一,习近平网络思想本身带有“形而下”的特点,在其整体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属于“实践理性”的部分。自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着当前我国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阐释了自己对于治国理政的系统化想法。当前,在其整个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当中,有学者将其思想框架归结为“一条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目标”(即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一个中心”(即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个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四个保障”(即政治保障即密切党群关系和惩治腐败;法治保障即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思想保障即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国际环境保障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1]。在这个整体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体系当中,网络思想是作为一种“术”存在的,区别于宏观上的“道”;网络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理政之术”,代表的是“采用的思路、方略、方式方法,解决的是怎么治国理政的问题”[12]。用公共事务的治理视角来看,习近平互联网思想的“术学”精髓即在于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对话、合作来实现风险社会中的各类公共问题。
第二,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合作”——政治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事务的治理属于形而下角度的问题向度,在宏观上受制于政治哲学、政治伦理等上层建筑的约束和制约。习近平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时代性的产物,依托“公共领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关于网络的民主监督功能方面,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13]在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结合网络具有的“合作治理”功能,习近平强调要重视和利用网络具有的“凝聚共识”作用,“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为此“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14]。从中可见,习近平的互联网思想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自然延伸,而因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不断完善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对话、民主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机制正是习近平网络思想的发展主轴。
当前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消费等诸环节的渗透在不断深化,在知识学意义上亟需一种成熟的互联网哲学指导我们的实践。近十年以来,习近平互联网思想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已经在我国互联网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着从“集群性假设”“群体性交往”“形而下的实践”三个维度透视了习近平互联网思想的结构,对全面、准确、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联网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